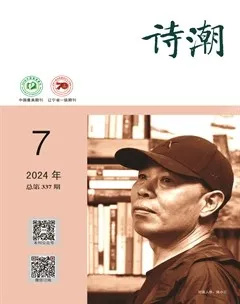牛越界及其他 [組詩]

蟒蛇的故事
王工愛抓蛇
無論有毒無毒的蛇
見到他都老實
他抓到蛇
就讓食堂的
媳婦做了吃
有一天聽說他媳婦
跟礦上來的
一個貨車司機跑了
他在宿舍
躺了三天
誰叫也不起來
我們就研究
編個瞎話:
說后山溝
有一條
能吃人的大蟒蛇
聽說把村里一戶人家的
孩子都吃了
他“嗖”地跳起來
帶上刀具
就去了后山
半晌
看他從遠處回來
肩上扛著重物
有人說
還真的是條蟒蛇
待走近一看
是他媳婦
已餓得奄奄一息
原來是自己
上山采蘑菇時
走轉向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去外地辦事
沒注意到提醒
手機因欠費停機了
我借用別人電話
給妻子打電話
想讓她用手機
給我續存話費
可不管我怎么打
她就是不接
錯 位
有一個婦女
報警說
她牽著
女兒的手
進入車站后
女兒不見了
警員調監控
沒看見她
曾牽著一個
小女孩兒
只看見她
牽著一個
粉色的
氣球
在過安檢時
松開了手
牛越界
牛被宰殺時
扯斷韁繩
一溜煙兒
涉過界河
到對岸
干農活兒去了
四目相對
小時候
有一次東溝子漲水
把木橋沖壞了
父親他們在搶修木橋
我和表弟在附近
偷著玩水
表弟不小心被水沖走了
我大喊救命
看見父親他們往這邊跑
就爬上岸逃走了
聽說表弟被救起
想看看他到底咋樣了
又怕被父親打
貓著腰走到舅舅家
開著窗戶的窗外聽
沒聽見有父親的說話聲
就大著膽子站起來
正好看見父親
瞪著我的眼睛
罵飛機
戰爭年代
老蘭太太的丈夫
被日本軍機
扔下的炸彈
炸飛后
她見到天上
有飛機過
就指著飛機
跳著腳詛咒它
如何從天上
摔下來
他兒子告訴她
現在是和平年代
那是祖國的飛機
也阻擋不住
她的罵聲
直到她孫子參軍
給她發來照片
說自己成了
空軍中的
一名飛行員
她才住口
可笑的夢境
我向天空
扔一塊石頭
石頭停在空中
不往下落
我用另一塊石頭
往下打
另一塊石頭
也停在了空中
我報警求救
他們上報說
發現了離地球
最近的兩顆
最小的星星
還要以我的名字
命名
停擺的鐘
有人看老房子
看了一圈后
不說買不買
卻說墻上的鐘停了
房主說因為沒人住
就沒有上弦
他說墻上的鐘停了
預示著會有人
死在這所房子里
房主說不買算了
別詛咒人
他說他就是
想為自己買一所
終老的房子的
現在可以談價了
守墓人
他承包的
那片山
原來想種
紅松樹
十五到二十年
就可以
采松塔賣錢
沒種成的原因是
聽說種人
來錢快
結果不到十年
一座座墳丘
就長滿了
整片山
他就住在
山下的草屋
平日里望著
山上的墳丘發呆
到了清明
就會看到
墳丘邊
站著活人
好像里面的人
出來曬太陽了
視頻效果
我妹在看了
法國鵝肝的
生產過程
農場主養鵝時把一根
20—30厘米的鐵管
捅進鵝的喉嚨深處
往里塞飼料的
視頻后
含著淚對她家養的
兩只大鵝說
我為你們兩個
能夠生活在中國
感到特別的幸福
為了增加你們的
幸福指數
我決定讓你們兩個
一直下蛋
即使有一天
下不出蛋了
也不殺
讓你們
壽終正寢
打一段車走一段路
有一次打車
沒帶手機
翻翻衣兜
只有六元錢
就和司機說
一直往前開
花夠六元
把我放下
剩下的路
我自己走
抓 賊
那是雪后
他尋著腳印
來到一住戶
他走進去
屋里沒人
出來時發現
院里站著
一個雪人
頭上戴著
他丟失的
那頂帽子
一只專門在夢里蜇人的蝎子
一個拿著
手電筒
專門上山
抓蝎子的人
翻遍了山上
所有的石頭
也沒有找到
那只深紅色的蝎子
他說那只蝎子
不管他怎么
用手電光照射
怎么用嘴吹氣
它就是不老實待著
一直往他跟前跑
他說那只蝎子
在夢里把他
蜇死過好幾次了
可在現實中
連它的影子
也沒有找到
上小學時走小路
在玉米、高粱或者
葵花地里穿行
總感覺自己是地鼠
而不是昆蟲
一旦穿出它們的重圍
看見陽光
把地頭草曬暖
又總是就地躺下
喘口氣
曬一會兒太陽
那時又覺得自己
是一只懶貓
愜意得
像把剛才的自己
吃了
野鴿子
在礦上時
我每天都有
跑步的習慣
有一天發現
有一只鳥兒
在我的頭上
跟著我飛
我感覺異樣
便停下來察看
它獨自飛了一段
又飛回來落在了
我前面的
一棵樹下
我走過去
原來是一只鴿子
它的一只腿上
有一只用鐵線做的
捕鳥夾子
銷上還有一粒高粱
這分明是
有人故意害它
被它逃脫了
我奇怪的是
它怎么還會相信
另一個人
怎么知道
我一定會救它
這是一個謎
技 藝
我大姑
九十多歲了
還能用筷子夾起
掉到桌上的
一粒米
我也想過舍身飼虎
那是在夢中
被老虎追
眼看追上時
突然福至心靈
知道是在做夢
心想不跑了
就讓老虎吃吧
也算做了善事
醒后還不是一樣
不缺胳膊
不少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