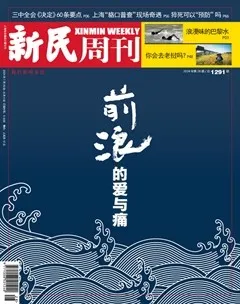在上海宜家“相親角”,看見老年人的“異托邦”
宜家在中國有37個賣場,位于上海徐匯的一家店大概是最特別的一個,不是因為它誕生最早,而是因為過去十多年里,它成了滬上知名老年相親圣地。
每到周二、周四,老人們不約而同聚集于此,多的時候有好幾百人。前往宜家餐廳的單身老人,大多是想找個伴。他們一面沖著心儀對象大膽示愛,一面又出于自我保護本能地猜疑與提防,唯恐吃了虧。日子久了,大家變成了保有邊界感的熟人,聚一塊只是圖個熱鬧。
6月11日,新一檔紀錄片《前浪》播出,將鏡頭對準老年人,通過長時間的跟蹤拍攝,記錄他們所遭遇的愛與痛。阿寶,年過古稀,在宜家的成名事跡是三次婚戀被分走了三套房產,目前在遠郊租了一小間房子居住;75歲的金阿姨,與前男友不歡而散后,認識了體貼的顧先生,兩人執手相伴,游山玩水,她被寵成了小公主的模樣。78歲的張爺爺和談了九年的女朋友分手了,他說老了就是要靠自己頑強地活下去。
十幾年來,他們用情感交織起了這一座“異托邦”,成為一種都市現象。愛情,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它是一個永恒的命題。
大多數老人說宜家根本找不到愛情,原因種種:年齡、長相、金錢、房子、健康、性格等。他們習慣地歸結為一個原因——沒有眼緣。雖然配對成功率并不高,但他們依然勇于表達和追求愛情,面對身體機能和容貌逐漸衰老的無奈和痛楚,他們緘默隱忍,戴上假發,認真打扮,努力熱愛生活,守住老去生命的尊嚴和體面。

在宜家相親角,熱鬧的聚集只是一群人的龐大孤獨。老人試圖抓住逝去的時間,完成對自己的一種和解。而在孤獨之下,我們還看見了人間百態,以及無法言說的隱秘情愫。
他走后,我不再笑了
可能你無法想象,相親的儀式感從漕溪路地鐵站就開始了。
周四是相親角約定俗成的日子,除了周二,大批老年人從上海各區甚至江浙滬周邊,前往這座“異托邦”。早上太陽熱烈地照射著,出了漕溪路地鐵站,陳阿姨疾步走向宜家家居的方向,手里的黃色環保袋跟隨腳步前后擺動。紅燈亮起,陳阿姨捋了捋額前的白頭發絲,理了理衣領,高分貝的車流噪聲中,聽到陳阿姨扯著嗓子喊:“我在宜家餐廳等你哦。”
五年前,陳阿姨的丈夫因病去世,宜家相親角成為了她排遣寂寞的“自留地”。電話里的爺叔正是陳阿姨看中的人。相遇那天,陳阿姨哭得“梨花帶雨”,封閉的內心被爺叔一點點打開,但讓陳阿姨放下戒備,重新開始的理由,是更為現實的物質條件。爺叔71歲,年齡、外表,退休養老金和房子,全都符合陳阿姨的要求。
上午十點鐘,宜家餐廳有些冷清,餐廳700多個位置空了大多數。陳阿姨找到一個靠窗位置坐下,戴上老花鏡安靜等著。“儂不來啦。”陳阿姨掛了電話,有些失落,爺叔失約了,這是第三次。爺叔上周出去旅游,陳阿姨沒有跟去,中間撥過去,視頻被掛斷,陳阿姨猜測爺叔八成有伴兒了,要繼續走下去不太可能。
這是一次失敗的相親。常來宜家餐廳的人都知道,在這里找對象是頂難的事。老年人的相親是迅速果斷的,在門當戶對之上,陪伴遠大過愛情。午餐時間一過,人們從上海四面八方匯聚過來。阿姨們流行穿肉色絲襪、黑色小皮鞋,戴著禮帽,時不時對著手機自拍一張;爺叔們則是襯衫,最上面那顆紐扣都系得規規矩矩。
也有些人不是來找老伴的,植物角邊上凳子坐著一位92歲的老太太,每周四老太太從浦東坐公交,花費1小時來到餐廳,只是默默坐在角落看人頭攢動;旁邊自稱姐妹的開朗說笑的阿姨,從塑料袋里掏出一些瓜子給老太太吃,兩人自打餐廳認識,至今有四五年之久了。“為什么要找老伴呢,這里涼快舒服,聊聊天開心就好。”
格格不入的還有65歲的曲美枝,每次來都是各式花色襯衫,搭配皺皺的黑色褲子,她從不特意打扮。曲美枝手里拎著一個皺巴巴的手提包,除了放著一些必需品,還隨身攜帶丈夫的照片。“他是大學教授,很帥氣,又有才。跟著他,我幸福了大半輩子。”曲美枝是貴州人,只有高中文化,但上海高知的丈夫唯獨偏愛她,不顧家人反對,非她不娶。
傍晚,炊煙升騰,丈夫緩緩拉著小提琴,曲美枝開心地伴舞,孩子們在旁嬉鬧玩耍。曲美枝時常想起這個畫面。2021年,曲美枝的丈夫罹患肺癌,化療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三年了,曲美枝再也沒有笑過。下午三點,一位端著保溫杯前來搭訕的爺叔問:“老妹,聊一聊嗎?我退休金很高的。”曲美枝眼都不抬一下,擺手拒絕了。
“像談合同一樣的,大家想的南轅北轍,怎么可能走在一起呢?”曲美枝活得通透,她明白老年人的愛情并不純粹,相親角里年紀大的男人,就想找一個免費保姆,女的還像十八歲時想的一樣,需要男人提供情緒價值。問題是就算找到伴兒,或者再契合的靈魂伴侶也不會結婚的,畢竟婚姻的法律效力背后涉及復雜的財產問題:“結婚了以后,如果要分開,房子算誰的,錢又怎么分?”
張口就要50萬元彩禮
在宜家相親角待上一會,你就會發現,這里已經形成了固定的人脈圈,甚至固定的座位。哪幾個爺叔坐在一起喝喝茶,哪幾個阿姨們的下午茶聊天聚會吃什么,都如上班打卡一般按部就班。表面上看,來這里常駐的都是頂有錢的老年人。亮閃閃的配飾,諸如金項鏈、腰間玉佩、锃亮的墨鏡,都可以最快立住有錢人設。
午餐時間到了,李培義推著餐車招呼著一旁打扮靚麗的阿姨,“咖喱飯儂吃?”74歲的李培義在相親角上了五年“班”,他指了指手腕上的大金表,又扶了扶墨鏡,得意地說:“酷不酷?”李培義超級自信,自稱“韓系帥哥”,退休金8000元,還有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這種條件在相親角相當拿得出手,相親過的阿姨沒有看不上他的。
宜家的老年相親人群跟人民廣場相仿,年齡從四五十歲到七八十歲,最大的共同點是多數人經濟條件一般。
但李培義不想定下來,矛盾點卡在他只想戀愛不想領證。之前他交往過幾個女友,吃過飯、送過禮物,一提到同居,對方就說必須領證,他不高興領,只好逃掉。對于領證,阿姨們也有自己的考量,有人介紹過一位條件很好的爺叔,說現在可以住在一起,以后生病了,各人找各人小孩。“意思是我現在給你當免費保姆,生病了把我一腳踢開,我腦子沒病吧?”
在相親角,相親的人群也是分等級的。有房子且退休金高的上海男人最受歡迎。再講究一點的,對上海各個區的人也能分出個三六九等。至于女人們,年輕漂亮的上海人就是香餑餑,有些退休金最好不過。外來人處在鄙視鏈底端,會被懷疑別有用心。李培義講了一個故事,幾個月前,相親角來了一位35歲的外地年輕女子,特別搶手。
有爺叔提出交往看看,對方張口就來:“我可以跟你走,但要給200萬彩禮。”大家立馬悻悻散去。“天吶,這是過日子還是敲竹杠啊?”,很顯然,誰也不愿意財產在暮年時被人分割,但也有人明知是陷阱還自愿“上鉤”的。
65歲的獨居老人許二海,也遇到過幾次“敲詐”。一位50出頭的阿姨曾問他要50萬元彩禮,他不想給,氣急敗壞地把這套問題拋給對方:“你有退休金嗎?沒有,有房子嗎?沒有,你就是不要彩禮,也沒人要你。”許二海指了指不遠處的卷發阿姨,“就是她”。卷發阿姨不以為然:“這里的男的,只想住在女方家里,不出一分錢,只想索取不想付出,可能嗎?要彩禮就是讓他們別做白日夢。”
上回他好不容易看對眼一個44歲的年輕女子,打定付出真心,結果女子又想在房產證上加名字。許二海氣得直跺腳:“我又不欠你的,憑什么加你名字?”
許二海說,自己年輕時和妻子賭氣離婚,到老了女兒也對他不管不問,僅有的這些家底是給他兜底的安全感。相親,也無非是想把這種安全感不斷放大。周三、周五去人民廣場,周二、周四到宜家。周一和周末三天休息,工作節奏“做四休三”,基本全勤。
在相親圈里,許二海這類樣貌平平,退休金5000元不到,房子42平方米也不大,代表著宜家相親角的絕大多數。李培義這種條件較好的相親對象反倒不多。相親角有名的紅娘阿軍說,宜家的老年相親人群跟人民廣場相仿,年齡從四五十歲到七八十歲,最大的共同點是多數人經濟條件一般。有爺叔說,“但凡收一塊錢門票,人都要少95%”。
社會學博士李沁曾聚焦“老年搭子”這一現象,做了8個月田野調查,她說,只有中國有老年相親角,或許因為老年人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網絡。各地相親角成功率都很低,她之前調研的15對老年人,真正走入婚姻的只有一對,兩人年輕時便相識,同居兩年后領了證。
“他們比年輕人更謹慎。”李沁說。訪談了許多老人后,她也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每個老人都在感慨,為什么這里充滿著利益計算,但他們每個人自己又都在談利益”。
難以啟齒的性需求
在相親角多待上幾次,你大概會被里面的坦率甚至赤裸所驚訝,頻繁出現的話題除了退休金、房子、戶口,如果幾個爺叔聚在一塊,多半還會有關于性的討論。
82歲的蘇老伯今天第一次來相親角,是李培義的提議。他穿著一件格子襯衫,黑西褲熨得展平,腳上一雙黑色尖頭皮鞋,和幾個好友坐著,看起來很精神。
七年前,蘇老伯的老伴兒離世,他成了孤寡老人,被迫搬去和兒子一家同住,同時也結束了他安穩有保障的日子。妻子性格溫順,在世時,蘇老伯一向對她呼來喝去。怕魚刺卡住喉嚨,妻子每次都將魚刺一點點挑出來,萬一哪個沒挑出來,立馬會遭到蘇老伯的破口大罵。蘇老伯內心愧對妻子,但往事已不可追。
蘇老伯沒有三高、心肺功能也很好,他自認為身體機能蠻好的。用完午餐,他從褲兜里掏出一小瓶白酒,咕嚕咕嚕喝了兩口。“我找的另一半必須得會喝白酒,主要是談得攏。”單就喝酒這一個條件,就把很多阿姨都排除在外面了。更為難以啟齒的還有性。蘇老伯說,性是一段關系里的必需品,他希望能找一個固定的老伴兒,不結婚領證,也不住在一起,有需求的時候才見面。


蘇老伯期待著在一段關系里,如果兩個人情投意合,性就是yn02tqKpEYvJOE0LEjVJRS+iY2tYkl3dgauCHSnERIA=其中自然而又重要的一件事。但總的來說,性仍然是“污穢之欲”的態度。這把年紀了,擺在桌面上談性通常被認定為不正經的表現。相親角的阿姨們則認為,直白提出這種需求的男人,多半很自私不負責任。“談戀愛尊重女性是最基本的,保持這種關系怎么可能嘛?”
刻板印象里,老年男性對性的需求更強烈,女性則少得多,但根據2015年四川性社會學與性教育研究中心對四川省3000名老年人的抽樣調查,60至80歲老年人中,有83%的男性和70%女性表示需要性生活。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性欲有著很強的羞恥感,再加上沒有合適的出口,有人轉而選擇商業性行為,而他們當中,老年男性占據大多數。
這也指向另外一個有關性的困境——艾滋病。2019年,中國新診斷報告艾滋病感染者中,25%都是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受經濟能力限制,只能選擇便宜的性服務,這無疑也增加了感染風險。有人說,當前這一代老人,是最缺乏正規性教育的一代人。當年輕時的正常需求,變成了一種社會性“罪名”,很少有老人能夠坦然面對。
如果放在相親角的語境之下,也多少顯得不合時宜。人本能的欲望并不會隨著機體的衰老就退去,他們在逐漸老去,但他們也同樣需要愛、陪伴和性。有些時候,我們在談論老年人的性需求,也在談論老年人的孤獨和寂寞,談論那些無人傾訴、無人理解、不懂表達的時刻。可能,對老年人來說,年齡可能不是影響性與愛的關鍵因素,忽視和偏見才是。
宜家相親角也在見證很多人的衰老。隔三差五,這里會消失一張老面孔。相互問一問,就聽見壞消息:有的不再來宜家餐廳的老人,已經離開人世了。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無法對抗的事實。
獨居時間長了,許二海時常覺得自己被遺忘了。在這座超大人口的城市,喧囂與璀璨都是年輕人的。時間將他推向暮年,伴著強烈的孤獨,沒有一點辦法。面對日復一日的老面孔,許二海不再苛求心靈契合的另一半,成不了對象,索性就當朋友聊天好了。
曲美枝在傍晚就離開了,她去附近的菜場采購,準備給孫子做他最愛吃的酸菜魚。家庭的溫暖會讓她短暫忘卻心底的悲傷。相親角只是相親角,無聊了來坐坐。只是她做好了準備,以后再也找不到與丈夫如此琴瑟和鳴的人了。
落日時分,夕陽的微光透過窗戶照進來,宜家餐廳的人群逐漸散去。李培義和蘇老伯起身邁著蹣跚的步子準備離開,下樓,出了宜家大門,剛走沒幾步,蘇老伯就累了。坐在花壇邊沿,他抿了幾口酒。兩人互相攙扶著到對面的198路公交站,背影穿過內環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漸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曲美枝、許二海、李培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