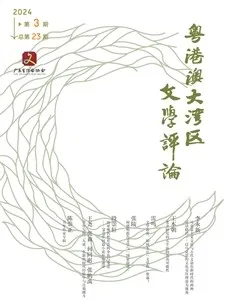文學教育陷入危機了嗎?
摘要:文學教育在工具性層面的滯留和人文性層面的匱乏,是“理想之域”與“現實之區”的脫節所致,是“教”之外部規律與“非常教”之內部規律相互作用、彼此制約的結果。所謂“危機”,其實是文學教育在外在的規定性制約力量發生全方位變革的情況下,所作出的適者生存的必然選擇。面對人文屬性的日益萎縮,重要的不是惶恐和焦慮,而是厘清思路、尋找為塑造形式與內容相匹配的新形態的文學教育提供更具實踐性的學理支撐。
關鍵詞:文學教育;危機;工具性;“理想之域”;“現實之區”
中國現代大學的文學教育始自20世紀初。歷經百年探索,大學的文學教育逐漸從稚嫩走向成熟,成績顯著。然而,在社會價值取向和文學觀念急劇變革的世紀之交,學術界關于文學教育之“扭曲”“異化”“式微”“萎縮”“困境”的憂慮卻愈加急切。關注點很多,表現在“對文學教育的功能和意義認識不足”“學科建設與教育教學的關系明顯失衡”“文學教育的目標認知與手段配合之間尚未達到真正統一”等方面1。身份有異,立場有別,但對文學“合法性”的缺席和“工具情結”根深蒂固之影響的判斷卻異曲同工。換言之,人文屬性的被遮蔽尤其是“知識傳授和生存訓練”2式的工具化傾向,被視為當前文學教育的首要危機。
一、從“來”如“此”
其實,關于文學教育偏“審美”還是重“實用”的分歧,在現代教育的醞釀和發生階段便已存在。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文學功能的一種表現方式,文學教育就已經肩負起經世救國的責任與使命。近代以來,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歷史境遇促使有識之士上下求索,救亡圖存是唯一目標;當國門被迫洞開后,取法西方、走向世界又幾乎成為不二選擇。在“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3和“無文學者國必敗”4等思想的影響下,知識分子們認識到文學對于革除舊弊、啟迪民智的推動作用。他們倡導面向現實,反對厚古薄今;他們要求文學通過教育民眾推動社會變革,挽救國家于危亡。于是,一場包括“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在內的文學運動應時而行。
龔自珍強調一代之學,能夠“通乎當世之務”,要“以有用為主”1;魏源主張“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無道,文之外無治……文之外無學,文之外無教”2。龔、魏二人對于文學(教育)經世致用功能的認知,是中國傳統社會視文學為“經國之大業”價值取向的自覺傳承。不同的是,中國古代的文學教育旨在培養健康的倫理型人才,其倫理指向性的特點比較鮮明。而近代以來的文學教育,在西方教育理念和文學思想的影響下,已經逐漸溢出教化意義的范疇,與時代緊密相連,因此,改良社會、變易世俗的現實功用目的尤為突出。梁啟超就明確提出小說在“開啟民智”“造就新民”方面具有“不可思議之力”,而時日中國,新民乃“第一急需”3。在梁啟超的倡導下,文學尤其是小說成為挽狂瀾于既倒的法寶,他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也成為“經世致用文學轉化為‘文學救國論’的一篇宣言”4。此后,無論是“五四”時期,新青年們倡導文學是“改良人生”“改造國民性”的手段;還是戰爭時期,文學教育對對敵斗爭、教育民眾的革命化傾向;抑或1958年提出的“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5;甚至近年來對于文學教育偏重知識傳授、注重技能等趨向,都是文學教育功利化傾向的延伸與發展。
與此同時,即便是秉持工具論的梁啟超,也注意到文學的本質特征是“情感的表現”,文學教育是“情感教育”6“趣味教育”7。這就意味著,即便在救亡圖存的危急關頭,文學教育的超功利性、審美屬性也依然在場。和工具論者一樣,超功利派也認可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只有文學藝術才能救民于水火,教育可以借文學來塑造國民精神、給民眾以心靈的撫慰。不同的是,他們更強調文學“無與于當世之用”8的審美屬性,王國維的超功利說就倡導以智育、德育、美育,建設身體與精神“發達且調和”的“完全之人物”9。在王國維看來,“修明政治、大興教育”,可以“鼓國民之希望”,但只有文學發達,才能“供國民之慰籍”;且“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因此“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10。文學教育是“無用之用”,無法帶來實際的物質效益,但在充實精神、療救情感方面,卻又具有“萬世之功績”。觀點看似極端,卻也顯示出對于文學超時空之恒久性的重視,這也同時意味著“文以載道”的傳統教育理念與聚焦文學本質的現代教育思想的根本區別。
如果說,王國維對于美育的倡導還停留在學理層面;那么蔡元培以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的身份,提出陶養性靈的美育為“健全之人格”1的“五育”之一,甚至美育可以替代宗教、升華人生境界的主張,則首次將美育提高到教育方針的層面,這對于在國家層面注重并推動文學教育的審美功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除特殊時期外,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學理層面,對于美育以及文學教育審美屬性的重視都被不斷提及。1951年3月,新中國首次提出智、德、體、美全面發展;1980年代,學者們在批判工具論的同時,倡導由他律轉為自律、回歸文學本體;直至近年,再次重申“五育并舉”。
縱觀一個多世紀的文學教育,倡“經世之用”者有之,主“無用之用”者亦有之。文學教育在建構人文精神、培養審美趣味等精神層面的作用毋庸置疑;在承擔歷史重任的實踐層面,自文學救國至文學興國,再到文學強國,文學教育也始終不曾缺席。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但就總體而言,盡管情感說、趣味說、超功利說更逼近文學教育的本質,歷史卻更偏愛“經世致用”的一維,這是近現代國勢“惘惘的威脅”導致的災難意識所致,更是企求中國的現代化的現實目標使然。從龔自珍、魏源到梁啟超、黃遵憲,從力主“致用”到呼喚“新民”,“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經世致用思潮,它可以說是19世紀文學思潮的標志,其他思潮的興盛往往都要仰仗于它,與它合流”2。
二、何以如今為“非”
文學教育的工具屬性從“來”便“有”。既然歷來如此,又何以如今為非,甚至連文學教育都屢被唱衰呢?其實,所謂文學教育的“危機”并非指向工具性本身,而是因工具屬性對人文屬性碾壓式的遮蔽和教條化的肢解所導致的種種弊端,如知識論3主張、制度化和專業化4傾向、職業化與技能化5趨勢,以及快餐化、媚俗化、模式化6表現等等。表面看來是由于文學教育在工具性層面的滯留和人文性層面的匱乏,但究其根本,是文學教育在理念層面與實踐層面的錯位乃至脫節所致。
文學教育不是“文學”和“教育”的簡單疊加,它是二者相交叉形成的次生概念,“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經由文學文本的閱讀、講解與接受,豐富情感體驗,獲得審美愉悅,培養語文能力,進而傳授人文知識、提高文化素養、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種教育行為。”7這個界定,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文學教育不是個體性、封閉性的文學閱讀、審美品鑒,它是一種社會性的教育行為。作為與人類社會共始終的現象和活動,文學教育是影響人的詩性存在與國家的全面發展的重要因素。作為整個教育系統的組成部分,文學教育理應具備教育的一般特點,或者說共性,即“更為專門化,具有鮮明的系統性、目的性與組織性”8。
這種復雜的特質決定了文學教育的多重屬性:它不只是審美教育,工具屬性也僅僅是它的目的之一種,而絕非全部。但目前的問題在于,工具性幾乎是力壓群雄、壓制性的存在,與此同時,人文性又始終千呼萬喚、蝸行牛步。無論是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對審美趣味的消解與搶占,還是庸俗化、物欲化潮流對人文精神的威脅與褻瀆,抑或生存危機、現代科技對文學教育傳統的挑戰與顛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文學教育的確被“工具情結”所牽制。但如果就此認定文學教育走進了死胡同,也不符合事實。因為,與其說文學教育陷入了危機,不如說這是在經濟關系、制度設計、技術手段等發生全方位變革的情況下所作出的適者生存的必然選擇。
其次,文學教育不是文學的教育,而是借助文學去實現教育目的。在高校學科建設體系內,文學教育“不可能不受到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教育發展的歷史現狀這樣一個基本現實的制約”1。文學教育功能的發生和實現首先不是來自文學本身,而是源自外在的社會現實與歷史的制約。20世紀的中國,風云變幻,幾多波折,文學教育背負著沉重的社會使命;改革開放之后,伴隨經濟結構轉型,社會分工越加精細,高校的專業化程度隨之提升。然而尷尬的是,文學教育的超專業特性使它很難擁有其他專業那樣的排他性技能表征。加之倫理化、技能化教育的傳統根深蒂固,人文性教育的制度化缺席以及教學效果、評價方式的難以計算等因素的掣肘,文學教育逐漸被簡化為知識性、規范性、模式化、教條化的專業學習和學科教育。長此以往,對文本的真切感受逐漸被知識海洋淹沒,無限的閱讀可能被可量化的標準答案所制約,性靈之光漸趨暗淡。
再次,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它在推動社會發展、帶來生活便利的同時,深刻改變了知識的生產方式和信息的傳播途徑,在以更高、更強、更完美為標準的競賽式發展路途中,以熏染、浸潤為主導方式的審美教育呈現出孤芳自賞式的“歲月靜好”,與時代的快節奏格格不入。這必然帶來勞動力的被擠壓,甚至被局部替代(如AI和文心一言的文本生成功能);文學教育也會因被詬病為“無用”而愈加邊緣化。尤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與普及,幾乎要引發文學創作、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領域的顛覆性變革。在“快捷”“有用”“高效”等原則的審視下,精神自我建構的指向顯得無限飄渺,文學教育本就稀薄的“本源之思”脆弱得不堪一擊,文學教育逐漸異化為“異于文學教育本身的獨立存在物”2也就在所難免。
此外,還有制度層面針對性關注的缺乏、學理層面多學科交叉共融的難以實現等因素。在強大的外界力量面前,文學教育要以啟蒙主義的方式影響人的感受、抵抗人的異化,絕非易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這5pdSmM5RGxshoPznCOPHZQ==一現狀也讓我們注意到,令文學教育如此難堪的主要是實踐過程中外在于文學的他在的規定性力量,而無論怎樣游移,它始終沒有脫離“人”。文學教育在引導人求真、近善、向美的過程中出現曲折,但目標從未更改。
三、所謂“療救”
重要的不是惶恐和焦慮,而是厘清人文屬性與工具屬性之間的關系,尋找打破屬性壁壘和信息繭房的路徑,向能夠適應時代要求的層面躍升,為塑造形式與內容相匹配的新形態的文學教育提供更具實踐性的學理支撐。
現代教育本身是思想知識教育和審美情感教育相統一的產物,它指向人。文學教育的人文性與工具性都以人的成長為旨歸,它們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而是共存、共融、共生。因此,厘清并正視這種關系,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架構一座橋梁,才是療救的有效方式。
1.“理想之域”與“現實之區”
審美與致用是“理想之域”與“現實之區”的相遇。人“時或活動于現實之區,時或神馳于理想之域”1。在“8wqpk3Kj96guTRvPqojunw==理想之域”,期待精神層面的滿足,“以能涵養吾人之神思”,訴諸情感的熏陶和趣味的培養,體現文學教育的審美本質,屬形而上層面。在“現實之區”,則首要在生存,“致力于善生”,其“致用”的趨向則將文學教育外化為有目的的活動和行為,以知識傳授、能力培養、人生觀與世界觀的塑造為目標。現實社會中,生存第一,發展第二。因為“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此外,無論是“國魂之現象”,還是“精神遞變”,雖為“一時及一族之思惟”,卻均可憑借文學教育(魯迅語為“美術”)“長留人世……為之保存,俾在方來,有所考見”2。如此,文學教育方能“無用”,卻又有“大用”。
理想之光照進現實并平衡文學教育的人文與工具屬性,是價值(實質)合理性與工具(形式)合理性相統一的必然要求。“合理性”是馬克斯·韋伯在改造黑格爾的“理性”概念基礎上提出的一個社會學概念。“工具合理性行動,是指以能夠計算和預測后果為條件來實現目的的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則指主觀相信行動具有無條件的、排他的價值,而不顧后果如何、條件怎樣都要完成的行動。”3工具合理性指涉事實,屬于客觀的合理性;而價值合理性指涉價值,屬于主觀的合理性。文學教育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工程,它不是坐而論道,它具有開放性和有效性,在“現實之區”,受到教育環境的制約,在手段選擇和路徑探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常規化、傳統化甚至知識化、技能化等指向工具合理性的教育行為。文學教育是人文教育,它借由文學的力量賦予人自由的意志、啟發主體的自覺、構建人性的豐滿,屬“理想之域”,價值的合理性要求它以表現價值訴求的人文或審美屬性作為終極意向。這是自文藝復興時期便已明確的現代教育理念,是學者們孜孜以求、急切呼喚的人文價值,也是文學教育實踐過程中從屬于價值、理想、信念等無法用理智去計算、控制和評價的價值合理性行為。人文性與工具性看似對立,實則是“理想之域”與“現實之區”的相遇,二者殊途同歸,統一于合理性行動,或者也可以說,文學教育的理想境界應是人文性與工具性的和諧共處。
2.“教”與“非常教”
審美與致用是“教”與“非常教”的糾纏。所謂“教”,即是說與其他教育一樣,文學教育也旨在“救國”,因“其力足以淵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輔道德以為治”4,可以“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5。這是文學教育的外部規律使然。人是作為勞動力和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存在的,文學教育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著必然性的聯系,它“必須受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所制約,并為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服務”1。“受制約”與“為之服務”是文學教育必然要遵循的外部規律,主要體現在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時日中國乃“沙聚之邦”,救亡即是對文學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非常教”則體現了文學教育的內部規律:“發揚真美,以娛人情”“自覺勇猛發揚精進”。文學教育以“培養和提高教育對象的審美素養和審美能力,進而營造整個民族的審美精神”2為首要目標;并通過自我感悟、經典閱讀、人生體驗等多方面的途徑去啟發和培養人的自覺。“歌者即生存”,文學教育的審美理想是由教育謀求人的全面發展的內部規律決定的。因此,審美與致用也體現了文學教育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的互相影響。
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彼此制約、相互作用。一方面,內部規律的運行受到外部規律的制約。“文學教育是附麗于……國家政治實踐的需要發展起來的”3,因此,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社會多方力量的聚合,文學教育要考慮社會的發展需要,而不能僅停留在個體性的審美視野,更不能僅以個人的自我發展作為終點和衡量標準,否則容易步入精致的利己主義的歧途。另一方面,外部規律最終要通過內部規律來實現。教育的本質是人類對自身和世界的認識和反思,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實踐,是人類對自由和責任的把握與擔當。如果無視這一本質要求,而任由生產力、社會制度等外力鉗制,那么文學教育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知識灌輸、技術濫用等工具性膨脹的傾向。因此,文學教育要把審美屬性和工具屬性調和而非對立起來,這也是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相統一、社會需要和人的自身發展相融合的必然要求。
問題應該是比較清楚了。文學教育的審美構想是美好的,但理想遭遇現實常常變形;同時,內部規律在外部條件的作用下不得不改弦更張,談不上是非對錯,只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不可同日而語。掃清理念上的障礙后,如何在教育實踐中增強審美教育和人文價值——即文學教育的重構,就因此顯得必要且迫切。在這方面,魯迅主張“增人感”“啟人思”,其由“立人”而“救國”的文學教育思想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路徑依循;梁啟超所看重的小說之熏、浸、刺、提的四種力量,雖以為社會改造服務為終極目標,卻也注意到文學不可思議的審美功效,給我們提供了可操作的實踐方式。“人立而后凡事舉”。所謂危機,更似機遇,在文學教育教學過程中,更為深入、客觀地洞察文學教育的現實處境,以“完全之人物”的培養為目標,在人文性與工具性的遭遇與糾纏之間尋找平衡,并借助信息技術的力量努力拓展文學教育的空間,才是勢所必然。
總體來說,本文認為應對文學教育的前景滿懷期待,不必為當下所謂的“危機”憂心忡忡,它只是一種全新教育生態的社會癥候,是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狀態下,文學教育應對危機的變通方式。因此,“我們用不著夸張地看待今天的文學危機,也不要把文學教育功利地看作是力挽狂瀾的一貼良方。”4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