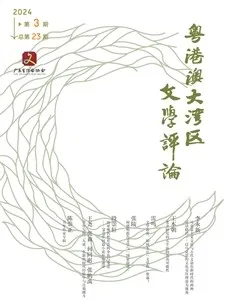走筆如行世:從風塵仆仆到月白風清
摘要:《月白如紙》是一部具有鮮明特點的散文集。無論作者所寫的對象是什么,她伸出的所有觸角,都返歸、回向心靈原點的圓覺,近似于心靈自傳。讀者閱讀其中的風物景象的同時,也是跟隨著作者,進行著一趟心靈旅行,領悟人生百味。
關鍵詞:普通人的神圣;自傳性;心靈渡引
通常,我們說“形散神不散”,是對散文這個文體的指認,這一特點在張鴻的散文集《月白如紙》中得到了高度確認。不只是在某一篇或某一類題材,而是整體的體現。無論她所寫的對象是什么,她伸出的所有觸角,都返歸、回向心靈原點的圓覺。讀者閱讀其中的風物景象的同時,也是跟隨著作者,進行著一趟心靈旅行,領悟人生百味。
這部散文集展現了張鴻走讀四方,深入邊地、村落、高原、河海的行跡,氤氳著各地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文化特點以及藝術特色。這部集子并沒有分輯,仿佛是以形式上的整一性來契合她主題原點上的統一性。她筆下的人物有中國第一位傳教士、中國報業之父梁發,理學家朱熹,有蟄居深山的獨龍族喃奶奶,“瘋子”卓瑪,比丘尼,退伍兵司機、收買佬等各式成名或無名者,也有身邊的朋友和家人。張鴻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颯爽英姿的行動派,早年常有和她一起組織詩歌活動的共處時光。那時,對于張鴻一個人去香巴拉行走,我是既驚嘆又羨慕。她有時會給我看她存在電腦上的攝影作品,無一不是遼闊幽深的靜美之境,賞之給人帶來塵囂盡息的松弛和舒暢感。而對于出現在我們周邊的人,她也會基于了解而給予善意的提醒,可見其對朋友的古道熱腸。她率真的為人處世,也同樣顯現于行文走筆中。
一、小處著墨,大喻于中
張鴻的書寫不拘一格,有的帶著田野調查的細節追尋,流動著市井間馨香的生機,像《牙香街的女兒香》《文面的喃奶奶》;有的開篇,像《江湖·故事·偶遇》系列中的散章,用一幀相片、兩枚戒指的來路作為肇始;有的以日記式的天氣注釋開啟或接續文意,如《聽,陽光穿窗而來》《行走于聲色元陽》《那一年,香格里拉》;還有親近貼心的書信體《給淏兒的信》。那一絲絲記掛,一縷縷情愫,絲絲縷縷的細節交織,是一種家常式的娓娓道來。其中《寬巷子 窄巷子》的抒寫則輕盈靈動如散文詩,“我喜歡這兒,我肯定來過這兒,一定和誰一起買過那個小伙兒的白蘭花、茉莉花,一定和誰在這兒飲過漂著花瓣的清茶。小巷依舊,沒有人理會我。不知名的花默默地落,落著不知名的憂郁”1。而她人生的第一首詩,寫給父親——“你的最后一滴淚,/我的第一首詩。//我是一個喪失了文字的寫作者,/無法記錄下與你的不再相見……一片樹葉/我參與了,飄落。”2(《夢境里的父親》)——這也是我迄今為止讀到的,張鴻的唯一的一首詩。生命如眼前的一片樹葉般凋落,樹葉有多輕,父親在她心里的分量就有多沉重。最極致的情感,在靈魂的幽深處,是詩。它是對逝者的紀念,對自我的慰藉,也是面對生命的消逝無能為力的隱痛。它宛如一朵黑暗中的火花,真切而動人。《給淏兒的信》中,她那舐犢情深的諄諄之告,恨不得把自己的平生所得傾囊相授,讓人看到一個母親對兒子深摯的愛,而其中也有超越特定個人對話的普適性,包含著生命的體悟,生活的智慧和思想的沉淀。
張鴻的行文多為寫實,時而又宕開一筆,逸出超然的雋語。就像在淡淡地聊著天的人,突然就起興哼起了曲兒。或如織物中的墊高繡,從平面中凸起,又自如地回落。“順著彎道向上望去,曲折的路基宛若游龍,盤桓在如蓋的穹廬之中,飛舞在寂寞的群山里”3(《新疆老張》)。家國情懷也時常顯于她的筆端,但她不像有些刻意書寫大散文的作者那般虛高凌空,而是小處著墨,大喻于中,踏實樸素地用一些不動聲色的細節,串起情感的聯結,一次紀念碑前的憑吊,立起一個人的形象;一個軍禮,勾連起身份的認同。最初不怎么惹人喜歡的新疆老張,因為在烈士陵園的祭奠而在作者心目中改變了形象,“雪域高原的早晨靜悄悄,風卻很大,寒氣襲人。我們在靜默中走在陵園里,向105位先烈們致敬……他脫下帽子,大風吹亂了他一頭本來就亂的長發,右手抬起,敬了一個軍禮。我站在他的身后,也抬起了右手,敬禮!……從這一刻起,新疆老張在我的心中立了起來”4。她緬懷先烈,心懷大愛,她的家國情懷,基于她對生命的疼惜,對河山的深情。“從昆明到騰沖,我在國殤墓園祭奠了烈士們的英魂,在寂靜中完成了內心的一次洗滌”5(《昆明到騰沖:三個地方》)。“每位老人都是一部書,有厚有薄。有的可為歷史經典傳承于世,有的可為家族記憶,成為小歷史,都有其在的價值和意義”6(《郁孤臺下一萍飄》)。曾經從軍的經歷使她帶著濃濃的戰友情結,對關于軍人、退伍兵等相關的人與事具有天然的親緣感。讀著她與女戰友之間的點點滴滴,她那有點皮,有點拽的樣子便浮現在眼前,想起有段時間她掛在嘴邊的一句玩笑話“砸他家玻璃”,不禁莞爾。
從這類篇幅中,可見其細膩溫柔之韻致,又可見其自由灑脫,豪氣干云之情志。
二、普通人的神圣
張鴻常常被樸素的情感所打動,那看似沒心沒肺的急性子表象下,卻跳動著一顆柔軟溫煦的心。仿佛粗線條下隱匿著易感的細弦,冷不丁就被某事、某物、某句話輕輕撥動,進入混沌中的出神境界。她筆下描寫的,多為普通人,與神圣相遇的普通人。她寫《山高誰為峰》里駐守在艱苦環境中的邊防官兵們,“他們每個人的夢想都那么具體和現實,‘將來要陪著家人周游世界’,‘要有平凡的生活有自己的小屋’……”;“入伍近6年的龍熙想當一名‘像鄭淵潔那樣的作家,為孩子們的童年帶去更多樂趣’,按常理來說,這并不是一個有啥特別的理想,可常年工作、生活在海拔4360米以上雪域高原的邊防派出所,在缺氧、寒冷、生活條件差、工作環境惡劣的情況下,他的這種簡單而純凈的理想卻顯得嚴肅了起來”1。而被貓狗抓傷咬傷,要打個狂犬疫苗都得歷盡艱難險阻,但他們無怨無悔,每個人都如山峰般,鎮守在高原,“山,就在那里,因人的仰視而成峰!”。她寫洞頭的畫家《海霞》們,“她們的成長也是付出了種種代價的,更有價值的代價是她們面對神圣時的謙卑和敬畏;是對個人內心生活無比關注,是讓自己的作品與營造的氣場相通。而這一切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最終的與神圣相遇”。“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她們完全融于生活,這種真實也許眼睛不一定能看見,但能叩動靈魂”2。在這里,張鴻的精神和她們是相通的,她知道內心生活的樸實呈現,因豐富充沛而形成了作品的氣場,而海霞們于庸常生活中對藝術的堅定追求,也是一種超然出塵的神圣。
長年行走的張鴻,兼具著散文家和攝影家的視角,常能給人帶來獨特的感受。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充斥著張鴻散文的大量篇幅,《獨龍江,那一刻我無語……》《那一年,香格里拉》《去新篁》等,把自然之美,造物之奇描繪得生動飛逸,宛若神祇在前,翻云覆雨。“那輕煙一般散開的薄霧,那星斗一般寥落的村莊,那棋子一般點綴的牛羊的存在……各種線條、地勢、色彩、光以及聲音,無時無刻不在產生新的變化……大自然就美而言,尚未形成自己的語匯。這樣的地方無疑是有神靈的……靈魂使生命得以鮮活,得以被光照而映現出五光十色”3,“我的想象就如一只鳥兒飛翔,無限散發開來。當原本恐懼的事情發展到一個極致時,便不再可怕,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種無以言表的美麗”4。大自然的神跡,給她帶來宿命般的頗具宗教感的體驗,“那時,車窗外、天空一道光穿過云層的縫隙,形成了電筒光束狀照在草原上,我仿佛被照亮,這是一道獨屬于我的光,那道光穿過我的胸口。我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寧靜的、滿足的、委屈的、存在的喜悅……”5。
普通人久久為功的樸素所呈現的超凡脫俗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洗禮,讓張鴻更清醒地堅定了心志——我所能做好的就是“自己”,不論是塵世還是“天堂”。她認為:天堂在自由的心中,在人心所及之處!
三、心靈渡引
張鴻自稱為“行者”,既可視為行走,也可視為行世,她在行走中思考、感悟生命存于世間的意義。“與自然的無窮貼近就是一種宗教意味的審美,而這種審美是經典的傳承”6(《在吉祥的陽光照耀下》)。“風把耳朵都要吹走了,面部強烈地皺著的褶皺里,風把細沙打進去,又抽走,生疼,皮膚上起了一層層的雞皮疙瘩”1(《也拉曼的艾斯肯》)。如其所言“每一次旅行中都隱藏著另一次無形的旅行,它需要被喚醒,需要被塑造,需要以心誠實地面對”2。在《奔子欄的此里卓瑪》《去新篁》中,她把一種被照亮的宿命感真切地呈現出來,讓讀者進入身臨其境的氛圍之中。去奔子欄找朋友扎西的張鴻,偶遇到熱情的卓瑪,或許是因為卓瑪毫無顧忌,對她敞開一切的信賴與自由的感染力,使她“聽命于一種原初之力的調遣”,跟隨卓瑪一起在山野間奔跑玩耍,沉浸于恣肆的快樂,抑或是心中的郁結或激情,直覺地借此得以釋放。當她從扎西口中得知卓瑪是一個瘋子時,她無法厘清自己的激情共振,但這種困惑繼而在與扎西的通話中得以解開,她說:“我們同時進入了一種語境,就如當時我和卓瑪的情境。”3這,就是頓悟吧,出于慈悲之心的動念與起意,每一個人都是在世佛,渡己也渡人。
《月白如紙》擷入的各色人物,有的來自有意的探訪,有的是無意的邂逅。人生不也如是,在可控與不可控中不斷前行。故張鴻且行且記,動靜隨心。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不斷的行走,我更加平和地對待事物,能更自然地為他人設身處地地著想,這就是一種成長”4,也明白“客觀條件有時起的作用遠遠大于自己的努力”5,所以,“我和他們是一樣的人,只不過我的生存空間與他們不同”6。她在《3路車,通向松贊林寺》中體味陌生人的善意,在菜市場流連于物產的喜悅。對于出家的朋友,她體會到“歷史,常常在伸手覆手之間將一個人的命運玩弄于指間”7(《寂靜的房子》),“什么樣的生活都是生活,每個人的選擇都自有道理”8(《塔什庫爾干的夕陽》)。“生活給你的苦,不能指望佛替你消化。還不如心懷快樂地信自己身上善的力量,快樂地安放好一顆潔凈的心”9(《梵鐘之聲,自雁蕩而來》)。
在《達洛維太太的時光》《怒放的弗里達》中,張鴻展現了她審美上的深刻一面,把電影、生平與事件共置透視,以同情的理解去貼近其中的女性,體會不同的角色。她寫弗吉尼亞·伍爾夫,“我從未見過如此細膩和非同尋常的描寫,似乎每一陣風都訴說著心情,每一次衣襟的擺動就是一次思緒波動。在她的世界里有一種讓人很痛卻宣泄不出來的悲傷,那是一種憋悶、壓抑的絞痛,那樣的悲傷只能被困在風中,撞擊、搖曳、呻吟著”10,“自由的品性和思想的能力,讓她更好地保持了藝術家生命中的超然和孤獨”11。她說,“弗里達充盈機智,有點男孩氣,又極具女人味”12,“生活太痛,同時也很美。痛和美,同樣要用身體和能量來承受。身體瓦解了,只能讓靈魂飄飖”1,“她的一生都在用心靈在熾熱的巖漿上舞蹈著,直至再也不能承受,不能承受……而墜落、墜落……”2。張鴻在這些杰出女性之中得到最極致的情感觸動,把自己的心靈放在其間共同淬火,獲得如“羽毛上自由的光輝被陽光喚醒”的精神飛升。
當一個人反求諸己,不再企借外力,便已走向自我渡引的澄澈之境。
結語
人生在世,難的是持真守樸,看似輕描淡寫的走筆行世,正是有難度的創作。從這部散文集里,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切的張鴻。“真善美”“修辭立其誠”是我們的文化所推崇的審美因子,張鴻在其中自我剖析、自我修為的坦誠,使得文以人彰,人以文立,兩者互為注解,形成近似于心靈自傳的鮮明特點。而綜觀整體,這些文本不僅僅是有“我”的在場,還進而在作者的一次次抒寫以及重構現場中,構筑起心靈的圓融與覺慧之境。“大地包容萬事萬物,每一個生命的存在都有合理性。人們理應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地時光流逝中,感受每個平淡生命的喜悅和沉重”3(《如光影常在》)。她用一次次的行旅,丈量大地的遼闊,以良善之心,記錄下點點滴滴的溫情。這些真誠的文字,是她與萬事萬物的應合與唱和,也是她從風塵仆仆的行旅,進入月白風清的人生之境的見證。走筆如行世,這是現實的人間,也是現實之上的人間。
作者系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