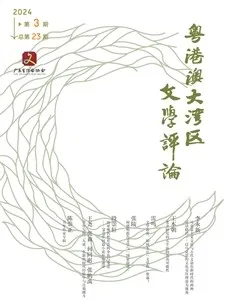地方·海岸·群島
摘要:在“新南方文學”的討論熱潮中,著有《關關雎鳩》《暖若春風》等多部作品的海南作家林森,在2024年推出的中篇小說集《心海圖》中用飽蘸海風的蠻荒筆法,完成了“小鎮書寫”向人海關系的探索轉向。以“心”“海”修飾海南民俗風情的圖繪,既指向海南漁民生活、民俗風情的社會史與情感結構展演,又在海與岸的動態離合中拋出文明寓言的隱喻。從海洋口岸向域外拓展,板塊的游徙奔涌著南方流動的審美特質,摹畫著新南方文學以“群島”為思維基質的全球化景觀。
關鍵詞:林森;新南方文學;海洋
隨著2024年1月中篇小說集《唯水年輕》的發行,林森筆下的海南氣息聚攏成川,從南渡江畔的瑞溪鎮走出,隨滔滔江水匯入南海。《唯水年輕》收錄了自2018年來林森對人海關系的集中思索,《海里岸上》(《人民文學》2018年第9期)、《唯水年輕》(《人民文學》2021年第10期)、《心海圖》(《人民文學》2023年第9期)三部中篇小說一經發表即登上《收獲》文學排行榜、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等各類文學榜單。《唯水年輕》水下攝影師與海底村莊的邂逅,《海里岸上》老蘇與子輩兩代漁民的價值變遷,《心海圖》美籍華裔船員方延返瓊揭開父親死亡之謎的艱難歷程,浪濤與群島,廢墟與村落,魂靈與生者,在潮汐奔涌中漸生漸長。
向中國文學傳統中回看,將海洋對象化、背景化的處理形式,從古典語匯中的以海寄情,以海詠物,以海言志,到十七年文學飽含戰斗化與意識形態色彩之海,延至新時期喋喋私語與啟蒙意識的海域,“海洋書寫基本止于‘人地關系’變種的‘海岸書寫’,難以深入海洋的腹地。”1海南島地處偏南,孤懸海外,瓊州海峽將之與熱鬧喧囂的內地文化舞臺相隔,有如“一顆似乎將要脫離引力墮入太空的流星,隱在遠遠的暗處。”2彼時一海之隔的潮汕,在近現代中國的文學版圖中,同樣遭遇著地理方位、經濟力量與文化心態上之“省尾國角”的位置。二者因海而興,以海為業,身份的邊緣在“脫嵌”于文學史范式的同時,涵納著文明的野生、冗雜與可能,激發出一套自我反思、更新、創生的活力裝置,賦予兩地族群在復寫歷史中獨具一格的海洋氣韻。在國家發展相繼舉起粵港澳大灣區與海南自貿港建設的旗幟后,“海洋”被提舉為新南方寫作的一大關鍵詞獲得學界廣泛討論。1新南方文學對海洋傳統的召回,為新時代文學景觀帶來松散、碎片、流動的美學特質,將“南方”的地理指向由陸地向海拓伸,如浪濤翻轉破除著南北二元邏輯的認識局限,疊印華夷夾雜、斜溢旁出的文化面貌。
詹姆遜從胡塞爾出發,將“文類”(genre)稱作“一種形式沉淀的模式”,“形式”(form)即一種內在的、固有的意識形態,在社會和文化語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變后,縱使信息持續存在,但在功能方面必須被算作新的形式。2在完成“海洋”為新南方地域質素的指認后,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新南方文學中的海洋書寫如何區別既有以海洋為對象的小說范式,在文類意義上獲得美學風格與想象空間的展演?倘若“新東北文學”在失落階級懷舊中構成了一場“在民族與人類意義上的世界性文藝潮流”3,那么與之意涵對舉、遙相呼應的新南方文學,是否同樣涌流著與全球化接軌的時代動能?在林森《唯水年輕》《島》、厚圃《拖神》、林棹《潮汐圖》等多部小說中,伴隨著跨越地域區塊的行旅與出返,“流動”的文化自覺有效超越了一種民族的自戀式價值生產(narcissisistic value-production),拓展著“群島”的思維格局。
一、非歷史的地方:
一本“開放的百科全書”
小說集《唯水年輕》的地理坐標,沿著海岸的曲線降落于海南臨海的漁村、漁港。地理景觀多與現實有所對接,如《唯水年輕》中“我”在水下拍攝的“海底龍宮”指向海口市東寨港至文昌市鋪前鎮一帶的海灣村落,明朝萬歷年間因地震造成100多平方公里陸地沉落入海,72個村莊隨沉陷體塊垂直下降,村莊庭落、貞節牌坊、戲臺遺跡依稀可辨。而多數村落無名,近乎虛指:《唯水年輕》中“我”對漁村的體認源于沙灘之“白”,是經高溫和常年暴曬后從海水析出的鹽粒;《海里岸上》里與十字街齊整布局的小鎮相對,村落周生木麻黃,有著灌滿腥臭海風的蠻荒;《心海圖》歸瓊船員方延喚回童年記憶的旋鈕在于村莊咸腥海風與浪濤起伏的節奏。林森并未著筆于對漁村歷史與地理方位頗為宏闊的全景敞視,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僅僅在背景性的浮游中獲得聲色氣味的辨識。
出生于海南省澄邁縣的林森,長于四面環海之處,他的寫作姿態是其海洋書寫的天然優勢,外在性的眼光向內偏移,跳脫出浪漫主義的抒情氣質與象征隱喻,海洋被還原成一方“討生活”的日常空間:“鎮子和漁村挨著,是海南島上最著名的一個漁港,多少年來,一代代‘做海’的人,從這里揚帆向廣袤的南中國海。”4海洋是漁村休養生息的經濟命脈,《乾隆陵水縣志》可見記載:“桐棲港,在城南三十里。外通大洋,港內有漁船二十余,朝出暮歸。”5“做海”取自海南方言,讀作“duo hai”,涵納從捕撈、養殖等多種海洋相關的作業方式,近海為“做小海”,遠海則“做大海”。每逢東北信風之際,漁村男子組成船隊,揚帆而起,乘風而去,站峙行盤、圍網捕撈是海南漁民的主要生產方式。
“做海”是一項并不穩定的生計,在浪濤波涌中能夠攫取的確證之物,是漁村寄寓于食色的情感結構。《海里岸上》有一處寫得生動:“老蘇有時候也會想,出海這么危險,一代代人把命丟在水里,卻還要去,其實和這水中之物的味道關系極大,當舌尖觸到一塊煎得略微焦黃的馬鮫魚,所有海上的歷險,都那么值得。”1從早期小鎮書寫中噴香的粉湯與糯米酒,到海邊漁村的一塊馬鮫魚,林森敏銳地將海南地域特點包藏于飲食,經由島民口齒間的咀嚼、吞咽,內化為身份記憶。女人不能上船是漁村多年的風俗,以欲望延宕和懸置的“等待”為系紐,性是老蘇等漁民出海歸來的情感傳承方式:“每次船回漁村,老蘇和其他男人一樣,在船頭看到岸上的女人后,內心的焦灼和渴盼達到了頂點。”2梅洛·龐蒂從肉身主體“身體性的存在”入手展開對空間性的理解,認為“身體本身的空間性”與外部事物的空間性所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再僅僅是一種“位置的空間性”,而是一種“處境的空間性”。3身體是漁民與妻子相互觀看的介質,既是情感距離由遠及近的相互關系,也是出漁經驗的分享、擴散或浸漬,幫助身份位置在漁村共同體中獲得補充調節。林森在詩集《海島的憂郁》中坦言:“生命,是靜默無聲的海水/那些暗流,終究會長高成浪”4,浪濤的起伏是身體節奏的循環,亦是生命節律的刻度,依憑食色所生成的文化認同機制,較之概念化的鄉土情結與故鄉依戀,回到了情感記憶結構的原初——通過身體對地域的品嘗與撫摸,傳遞著最為本真的直感。
卡爾維諾以《極度雜亂的美魯拉納大街》為例,認為傳統小說始終實踐著“百科全書”(encyclopedia)的寫作方式,沉耽于將知識的各部門匯總并織造出立體多層的世界景觀。他繼而提出“開放的百科全書”(open encyclopedia)設想,本質上與“百科全書”的詞源學意涵構成矛盾,后者指向一種“竭盡世界的知識,將其用一個圈子圍起來的嘗試。”5當知識的總體難以用穩定嚴謹的次序和形式獲得測量,這一設想投射出卡爾維諾對知識宇宙在不同時代表現差異的反思。因循“開放式”的文學作品不再試圖將知識包容于一個和諧的形體,而是以該形體為核心生成向外輻射的離心力,衍生豐富多層、相互映射的文化藏品。《心海圖》中的“地方”雖然橫亙著從民國至新世紀的漫長坐標,標記了海南歷史中幾處極為關鍵的發展刻度——1939年海南島抗日戰爭、1950年海南解放、1988年海南建省、2018年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但僅僅提供了一種情景化的敘事背景和潛在語氛。這種對歷史在文化而非知識層面的處理,是“地方”在某種程度上賦予的“非歷史性”:“地方是一個具有意義的有序的世界。它基本上是一個靜態概念。如果我們將世界視為經常變化的,那么我們可能無法發展出任何地方感。”6林森小說中真正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往往是奔逸于歷史褶皺處“非歷史”的晦暗未明,歸向宗教儀式支撐起的民間信仰系統。《島》中村民在拒斥拆遷隊到臨時,伯父于伏波將軍神像前懇請給予提示,擲木圣杯得到了海涯村拆遷的認定,自此漁村成為歷史。在厚圃的《拖神》中有著相似的儀式互文,世代居于山林的畬族因發展需要試圖轉變生計,向三山國王誠心跪拜并投擲筊杯,最終得以下山。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史重構中,小說既保留著再現社會歷史與生活經驗風格的維度,又向著神靈復魅的舊文類中追溯,歷史和真相被置放回一個僅供遙望的位置,朦朧著宿命的引力,構成了林森海洋題材書寫獨特的敘事肌理。
二、海與岸:“對稱”離合與文明寓言
林森對海與人關系的思考,由《唯水年輕》中的“我”在策劃拍攝方案時提出的一組對稱關系發端:“以沙灘為中軸線,水下龍宮和岸上村子,是相互對稱的。”1以海岸線為對稱軸,岸邊漁村映于海面,人化成魚蝦,和千年前沉落的海底漁村疊印。與傳統海陸書寫的固定視點不同,林森的海洋題材小說生成了“海里”與“岸上”的動態離合,漁村的傳統生活與現代建筑的迭代構成小說最具戲劇張力的時刻。《島》開篇伊始即是海涯村的強制拆遷,取而代之的是一張“寶島上最氣派的大型小區”的規劃藍圖,行至小說尾端,博濟村和火牌島的摧毀和“海星現代城”的修建象喻著海洋時代的沒落。《海里岸上》則處理了前后兩代漁民在經濟運營模式上的變更,從老蘇以海為生的海洋捕撈到子代遠離海域的硨磲貝加工販售,從肆意生長的漁村遷移到秩序井然的小鎮,海洋氣質的蠻荒波動被商業模式的規整單一逐步瓦解和清除。
海南島20世紀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城市發展的鐵騎橫掃千軍,漁村之“變”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加速發展中不足為奇,但漁民“做海”應對潮汐與臺風的熟稔卻難以應付小鎮生活的穩定,外部震蕩所激起的內心裂隙驟然顯現。基于生活慣性被時代甩出的“脫嵌”,化成最為直樸的身體抗爭。《島》中身為漁民的二堂哥無法接受淪為廢墟的殘破,兀自在深夜中泛舟,葬身于海。吳志山在據守幾十年的火牌島被夷為平地之際,選擇在臺風的風雨交織中再度游泳歸返,消失在巨浪中。海洋提供了生命“臨界”的場域,伴隨潮汐退下與涌起的節奏,代際在此輪轉與更新。二堂哥的離世促使“我”變成了游歷海南島、難覓精神皈依的“浪蕩子”,而吳志山對火牌島的堅守為我提供了彌合創痛的桃花源地,在其消失后自覺接續起守島者的使命。
在海與岸的兩處地域空間中騰挪,海洋如鏡像折射出歷史與當下、家族與自我、存在與死亡的交錯熔鑄,似西西弗斯“命中注定的命運,令人輕蔑的命運”2,釋出難以抗拒的指引將離岸者召回,相似的生命片段在家族傳承中不斷復演。《唯水年輕》里“我”的曾祖父與祖父相繼葬身于海,出海成了家族的苦難時刻,“我”卻沉迷于海底龍宮的水下攝影,抗拒海洋的父親最終克服水性不佳的隱疾,循著父輩的道路潛下海洋。《海里岸上》與海搏斗半生的老蘇,見證曾椰子等船員命喪海里,卻在休漁多年間持之以恒地雕刻著船的模型,將海洋視為生命終結的歸處:“自大潭往正東,直行一更半,我的墳墓。”3閱盡悲歡離合、死生沉浮,“做海者”的生命歷程與情感認同始終圍繞海潮鋪展,人物在海中靜謐平緩,死亡所負載的滯重感遭到解構,遵循一種自我迸發、自我毀滅的本能(instinct),在重復中返回無機與初始狀態,抵達生命狀態的輪轉。
大海詢喚起源與進化的故事脈絡悠長,而近年來“海洋”在新南方文學中獲得重提的答案,掩藏在陳思和2000年的一篇名為《試論90年代臺灣文學中的海洋題材創作》的文章中。他援引黑格爾對海洋文明在文化性格上的海盜性與商業性之洞察,指出以海洋為題材的西方文學作品中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征服與受制的對立,與其海洋主體的振興,毋寧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制下對海洋的爭奪、控制與重新分配。1莫言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創作的小說《生蹼的祖先們》中已然傳達出相同的顧慮,手足生蹼,退化為蛙形,“我”高呼這是“人種的進步”,并非剝離文明衣缽的“去蔽”,僅因提供了侵占海洋的便利:“親愛的生蹼的兄弟們!我們的同族兄弟已走向大西洋!要知道,當貪婪的人類把陸地上的資源劫掠殆盡后,向海洋發展就是向幸福的進軍!”2海洋書寫往往模仿殖民主義強加的大陸知識形式,衍生為陸地文化的變種,葉瀾濤以吳明益《復眼人》等臺灣文學作品為例,認為新世紀向“生態化海洋”回歸,海洋的自然屬性獲得強調,而大陸海洋文學卻仍然將海洋作為征服和開發的對象,而非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3可以看到的是,無論是《島》中吳志山在野菠蘿叢中自掘墳墓,還是《唯水年輕》飛魚馳騁、蝦蟹成群的海洋風貌,以林森為樣本的新南方文學海洋書寫,呈現出海洋認知方式轉變與行為模式重塑,環境生態意識構成了與掠奪意識相互抗衡的新機制。
新南方文學中的“海洋”在生態層面發揮效能的同時,于島嶼的時間隱喻中共同植入了一場文明寓言的重置。《島》在故事框架上可視作一場海南本土化的“魯濱遜漂流記”,但后者顯然帶有資產階級上升期的強烈侵略性和征服欲。南非作家庫切在1986年的小說《福》中將星期五設置為被割舌的沉默者形象,當他在結尾終于張開緊閉的嘴唇,海浪、風聲匯成小島綿延不絕的浪濤涌流而出:“這股細流流經他的身體,向我直沖出來;它流過船艙,流過沉船的殘骸;沖激著荒島的峭壁和海岸,向南北兩面散開,直至世界的盡頭。”4庫切對魯濱遜殖民神話的解構在星期五意義豐饒的“不可言說”中抵御語言意義的侵占,《島》中的海島則將時間凝為亙古,吳志山以事紀年,活在時間之外。與之發生巧妙互文的,是馬華作家黃錦樹于小說集《雨》中的《后死》一篇搭建的Pulau Belakang Mati(后死島),地處海峽的最南端,大陸的盡頭在此消逝,L在此找到了暗戀許久卻消失三十年的M,他“活在沒有時間的時間□”5,容貌依舊。兩座島嶼也構成了陳春成《夜晚的潛水艇》筆下的一組封閉裝置,是家門閉合后啟動潛水艇的“堅實的果殼”,暗合著博爾赫斯在《阿萊夫》中援引的《哈姆雷特》臺詞:“即便我困在果殼里,我仍以為我是無限空間的國王。”6時間疊壓成片,空間無限擴充,島嶼與潛水艇凝結成果殼般永恒的時空體(chronotope),在一種空而無序的度量中,夢與亡靈溢出,世界無限耗散。
在《唯水年輕》里,“我”坦言潛水有回歸胎腹之感,大海如包孕的母體,統生萬物,借海水之名,郁熱的生命片瞬轉化為流傳的自然恒常。本雅明在1939年的《歷史哲學論綱》中提到“歷史天使”:“這場災難不斷把新的廢墟堆到舊的廢墟上,然后把這一切拋在他的腳下。”1千年前的地震災難將古漁村推下海底,作為鏡像對照,“水下龍宮”成為漁村物質精神消殞之際“靈氛”(aura)的碎片化癥候。“我”不斷潛入廢墟觀測,正如飛魚翱翔于現有文明上空敞視,在歷史褶皺的幽微處重掘文明碎片,將漁民烙印于心的情感記憶拉攏、聚合于當下:“除了海底村莊的照片,還有一些岸上的,彼此夾擊,共抗時光。”2在歷史生成與消失、完成與未明之間的張力結構中,《海里岸上》的老蘇沉入水底,映入眼簾的是如同“水下龍宮”的蜃景,曾椰子、父親、一百零八弟公等海中逝者與神靈齊聚。這一跨時空并置將老蘇放逐于時間之外,通往過去的方式不再是記憶縱深的回溯,而是向著橫向的地理平面跋涉,傾頹的海底漁村如同圖層疊加生成的立體派肖像,折射出多時空交疊的歷史,向著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回歸。這正是新南方寫作的“超越性”:“它不能僅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風俗與語言,而應該是在一種多元文化形態環境中所形成的觀察世界的視角與表達方式,代表著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無窮探索。”3在廢墟與文明伴生的語法中,南方得以復魅與再生,保留著歷史與碎片的光影,在海與岸的持守中抵達生命歷程的求索。
三、板塊:新南方文學的世界圖景
王德威在《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一文中以人類學及地理學研究熱點——東南亞高地佐米亞(Zomia)為例,指出其跨越國家、族群或文明的界限,將南方之南的觀點延伸到東南亞的半島高地和山嶺,新南方人文經驗的可貴“在于夾出于潮汐起落和板塊碰撞之間。”4在探討新南方文學中的海洋氣象時,倘若僅停留于海洋原始思維對現代化浪潮的抵御與烏托邦建構,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喚醒生態保護意識,顯然難以區別于既有的海洋書寫范式,也不具備可供持續討論的動能。海南作家孔見在《海南島傳》中的自白或許可以提供一個思考啟示:“從很早很早的時候起,我就意識到自己降生在一座島上,它已經被腥咸的海水重重包圍,承受著波浪永無休止的沖擊,所有堅固的事物都已遁離,朝任何一個方向走去,最終遭遇的都是深淵與迷津。”5海水消解穩固之物,走向碎片與彌散,這種“孤島情節”幾乎構成了新南方作家的行文底色。板塊的“脫域”6成為了抵御精神困惘的有效途徑,鑄就了新南方文學流動的世界圖景。
林森在一篇創作談中指出:“往更早的時期追溯,下南洋、出海外,不斷往外蕩開,不安分的因子早就在廣東人、廣西人、海南人的體內跳躍——就算茫茫南海,也游蕩著我們勞作的漁民。但是,這些元素遠遠沒有進入我們的文學視野,遠遠沒有被我們寫作者所重視、所表達、所認知。”7中國于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戰敗后,相繼簽訂《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允許契約華工出洋。厚圃的《拖神》在描摹樟樹埠的崛起與沒落之時,追溯了晚清時期潮汕人遠下南洋的社會與精神畫卷,《三桿帆》一節插敘了陳鶴壽在暹羅(泰國)打拼的經歷,其中便述及被騙去馬來群島種植園作苦力的契約華工。20世紀初,來自東南亞各殖民宗主國的工商資本紛紛涌入東南亞,傳統的采礦、種植、原料加工、商貿等行業有著較大發展,加之東南亞華商企業大多雇傭華人,引發對廉價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吸引東南、華南沿海民眾遷移至東南亞謀生。《唯水年輕》的主線是“我”與父輩兩代的故事,但曾祖母在孤寂中操持家庭、含憾老去的大篇幅書寫牽絆起小說另一條隱秘的敘事線索:村里的曾祖父隨船下南洋后從此消失。“我”在整理曾祖母遺物時偶然抖落了兩張發黃的信箋,詳細記錄著曾祖父由海口至新加坡的下南洋自述:“余隨村人往橡膠園內之工寮,膠工皆為華人,瓊島之人亦不少,通鄉音,時有人來探故鄉事、言故鄉物,無不眼紅灑淚。”1《心海圖》中方延的大哥早年跟隨村民去馬來西亞,同樣從事的是割膠產業。據唐若玲考察,1922年至1925年間,海南人出洋人數呈現增加狀況,一方面是海南社會秩序遭到廣東軍閥鄧本殷的嚴重破壞,民眾生活困苦,被迫出洋謀生;另一方面則與南洋橡膠業復蘇相聯系,1922年史蒂文生橡膠限產條例奏效,1925年橡膠價格回升, 也是海南人出洋人數增加的原因之一。2在黃錦樹的小說集《雨》中,馬來半島的橡膠林更是構成了普泛性的寫作背景,《南方小鎮》唐山表哥的故鄉來信中,述及祖母是年輕時下南洋的割膠工人,“返鄉”成為了其在世時難以根除的心結。正如《唯水年輕》中指認的,曾祖母并非孤例,這層時代隱秘的創痛均等地輻射著漁村的其他村婦,“下南洋”在移民的過程中,不僅是社會經濟史的結構議題,更構成了圍繞故土彌生的羈絆與情感結構。
“下南洋”中橡膠工人的碎片化書寫是帝國殖民的一處側影,而《心海圖》與《拖神》等作品直面民族國家遭遇帝國侵略的解殖民(decolonization)議題,窺見南方在板塊互動中遭遇的歷史震蕩。與大規模的都市殖民不同,作品大多立足鄉村殖民的間接性、滯后性與片段性,講述民間群眾直面殖民勢力旁敲側擊的抵抗歷程。《拖神》中村民與殖民勢力的對沖源于英國海軍派出專家視察開埠情況,因沖突爭執遭到英軍的大面積進攻,陳鶴壽登上紅頭船與之決戰,最終逼退英軍戰船。《心海圖》的殖民紛爭同樣開始于日軍殖民瓊島前夕對其礦藏資源的一次考察,方延父在1939年日軍全面入侵海南島并再度要求尋礦時,帶領日本考察專家以爆炸的形式一同赴死,為國捐軀。一組有趣的細節是,方延父親年輕時帶領日本人田祝瀾勘考成冊的《海南島行記》,原件來自1936年一名湖南籍中學教師田曙嵐所著《海南島旅行記》,對海南島之土產、地理、風俗詳加考察記載。田曙嵐在“小引”中表達了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侵略下海南作為大陸邊陲的重要地位,用以“分寄沿途后方各界”,“報告各界友人”3。這一民族主義關切被林森創造性地轉化為日本殖民話語,展現出文學文本與歷史現實的微妙互動。《海里岸上》中的南海爭端并非政策性的說道與搬演,而是圍繞著老蘇的一本傳家寶《更路簿》(南海航道更路經)展開。二十世紀初美西戰爭后,美國作為主要帝國大國的崛起,將西方對“殖民地南海”的想象重新配置,轉向以美國為中心的“太平洋島嶼”愿景,把控東亞諸國經濟命脈的南海為“繪制全球完整球體的最后階段。”1作為海南島漁民最早在南海諸島從事生產的物質證據,《更路簿》成為證明中國南海主權的關鍵性歷史材料,老蘇祖輩對《更路簿》的持守,在殖民與解殖民的張力中詮釋著保衛民族國家的海洋之“心”。
林棹的《潮汐圖》透過巨蛙之眼觀看19世紀上半葉的清代中國,板塊遷移剝脫了人類中心主義視點,獲得更為松動的釋放。巨蛙擅水,故大陸與海洋所框定的邊界趨于松散,從廣州珠江出海口肇始,中經蠔鏡(澳門),抵達游增(歐陸帝國)帝國動物園,復歸虛構的“灣鎮”,向內為珠江口岸的南方風物賦形,向外鉤織著與域外的連接、交流與互通。費正清指出,中國之民族主義即“文化中心主義”的視點,面對軍事上弱于“化外之民”的情境,仍然以龐大的“天朝上國”而非亞文化集團作出回應。2直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海國圖志》(1842年)、《海國四說》(1846年)、《瀛寰志略》(1848年)等域OAqTxAOkczprI6mjdcvZo4s349pgYTmlp8sRtiVJZeE=外史地的介紹,正史四裔傳體例得到打破,“世界”這一概念獲得松動。在《潮汐圖》里,來自蘇格蘭的博物學家H描述世界“形似巨卵”,廣州如浮落之微塵。“世界”并非虛設,但能指懸浮,所指滑動,小至“澡盆生物”的水面浮城,大則伸展至蘇格蘭與亞墨利加(美洲)。按照馮喜的說法:“兩個生埗人初相逢——不是在路口,就是在港口——他們立定,交換世界。世界在路口港口相逢,似乞兒王縫起百衲衣。”3“世界”預示著“天朝上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借由馮喜、H與巨蛙的行旅圖繪著晚清中國與西方際遇的歷史瞬間。伴隨板塊遷移的,是語言的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指向《潮汐圖》中官話、廣府話(粵語)、番話、皮欽英文間雜使用的跨語際實踐,象征著“一種新的、原始的維度,允許每個人都在那里和其他地方扎根和開放。”4語言在不同民族與區域間旅行、流通、繁殖、爆炸,雕刻著新南方地域文化多元包容、磅礴冗雜的復雜肌理。
新南方文學對世界圖景的描繪一定程度上呼應著80年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核心關切,文化內尋的自覺更廣泛地與全球一體化背景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想象性建構、民族主體的確證緊密關聯。韓少功指出尋根文學“體現了一種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構成了全球性與本土性之間的充分緊張,通常以焦灼、沉重、錯雜、夸張、文化敏感、永恒關切等為精神氣質特征。”5面對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東方/西方、民族/世界、本土/他者、傳統/現代的矛盾對抗體,尋根文學試圖通過批判和繼承兩種方式,從本土文化中尋找到能夠和西方文化霸權進行抗衡的精神氣質——一種東方化的思維優勢以重建一種東方新人格、新心態、新精神、新審美的文化體系。而新南方文學對世界版圖的重組,顯然卸載了尋根文學中過于急迫的文化使命和焦灼的追趕心態,以歷史感和生活性更為豐厚松弛的積淀碎裂著自我陶醉的民族神話,在海洋的縱深與流動性中,文化呈現出非線性、反軸心、跨國境的開放律動。
讓我們將目光回溯至1955年的非洲-亞洲萬隆會議,解放之初的印度尼西亞與菲律賓等國宣布自己為群島(archipelagic)國家,陸地和海洋,流體和固體,作為非殖民化進程“混合遺產”(殖民主義歷史經驗中的克里奧化與殖民空間不同類型的跨越)的一部分,蘊含著全球范圍內對20世紀國家的重新想象:“不是堡壘和陸地,而是一個可接受變化和交換的流動和開放的‘國家’,一個連接不同島嶼的實體。”1連接民族國家的異質網絡(“一體性”)被置放在流動的海域而非區塊化的大陸中獲得認知,‘群島’指認了國家政治和文化地理在堅實輪廓中建構平等交流網絡的可能。新南方文學“以‘南方’為坐標,觀看與包孕世界,形塑一種新的虹吸效應。”2南方的流動特質在解殖民與遷徙書寫中獲得賦形,因循潮汐起伏與循環的節奏,刻寫著于群島間豐沛、互利共生的一種全球化方式。
四、結語
在近年“新東北文學”“新南方文學”的討論熱潮中,自然物候、地域話語、民族史詩的集中浮現不僅是一種區域文學的姿態,其背后更有重塑中國形象的歷史淵由與話語動力。在歷史綿延的縱軸上,大陸地域的諸多概念指稱從來未能形成永恒統一和跨歷史連續的整體范疇,而海洋則始終提供著一種脫出政治囿制而融匯、更新、連續的文化脈搏。在國家戰略大力推動“海上絲綢之路”、海南自由貿易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今天,海洋性作為新南方文學的美學特質之一,既與液態現代社會的流動與可變不謀而合,也是全球化格局中急需的一種“群島”性思維格局,在不均衡的個性差異中克服島嶼孤化與種族邊界化之困境,重新聯想區域關系的相互構成,抵達一種經驗片瞬的延續。
中國與世界在互動中滲融,林森、厚圃、林棹等新南方作家的文學書寫提供了富有海洋氣質的時代樣本,但海洋與陸地關系的真正平衡與持續維護,依舊道阻且長。《島》中違建停工的“海星現代城”雖然解除了生態危機,卻難以填補吳志山的精神空缺,他不得不踏上重復性的尋島過程。《海里岸上》里的《珊瑚礁和硨磲保護規定》縱使從法律上禁止了漁民子代販賣硨磲的經濟模式,卻未能提供將海洋火種向后代賡續的可持續生存路徑。“保衛海洋”始終以一種自我隔絕、自我取消的方式完成,漁村傳統向現代變遷的戲劇沖突、漁民淳樸深厚的人海情誼,作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飛速發展的群體性經驗結構,無疑正走向封閉與動能的持續耗竭。如何在新時代語境和“海二代”迥異的情感結構中開拓海洋書寫的新空間,仍是在新南方文學需要進一步探索和關注的話題。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