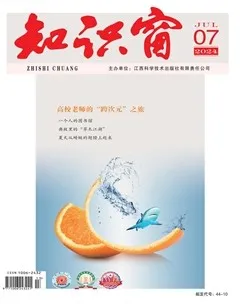歸程,滿載青山和燕語呢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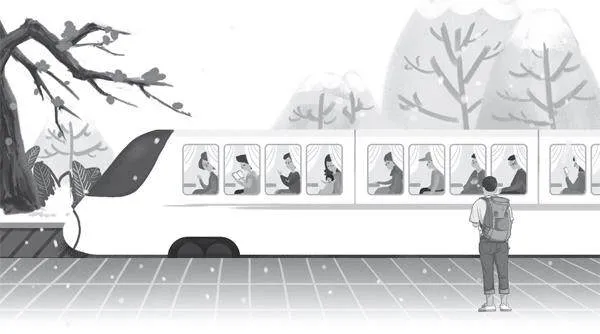
總在失意時買上一張歸鄉的票,薄薄的,我攥著它,就像在茫茫的海霧中望見了燈塔。這世界很大,很喧囂,但我總有我的退路。
每次踏上綠皮火車,就好像一封信終于寄出,你知道,即使千山萬水,總能到的。路途跌宕,可我的心卻安于一隅。
一扇小小的窗。
窗外,可以是山水綿綿,也可以是燈光依依;手上,可以是一本法國的浪漫小說,也可以是一本頗有年代感的日記本……火車下方好像不是軌道,而是流淌的歲月。我好像一個時間的旅人,心里揣著一片茫茫的海,尋春天來做海浪,邀孤峰來做燈塔。
車廂里的竊竊私語聽起來像20世紀情人耳鬢廝磨的愛語,流淌在時間里,被風攜來,盈滿耳朵,聽不甚清,但別有韻味。不時而過的乘務員幾聲吆喝,又驚醒哪個人的淺憩。他們的夢里會有春光深處姥姥帶著皺紋、輕笑的臉嗎?陽光在姥姥的肩頭跳躍,仿佛時間被打上休止符,青天白日的憶想也有了歸處。
每個站點都能等到它的游子,就像每個窠臼都有春天的歸燕。鄰座哪位又到了站,攜著多年的風霜,等家鄉的暖陽烘干沉默與孤寂,即使眼下青色,也掩不住明亮得似住進了月亮般的眸子。我知道不多久,你的眼中會佇立真正的、你心中的月。而我是一個記錄溫情的旅人,在無情流淌的時間里,尋覓每一個有情人。
還在幾十千米之外的終點站,是我幼時渴望遠離的“窮鄉僻壤”,是年長后夢寐以求的“烏托邦”。為了離開,我只用了一步。一輛擠滿人的大巴,嘈雜,暗沉,但掩不住少年對未來的憧憬。而為了回來,我卻用盡全力。如今,當望見寂寥的火車站口,那盞被飛蛾駐留的路燈時,我終于理解了被世人嘲笑的白色撲棱蛾子。世間哪個年少有志的青年不是如此,對未來、對成熟的追求,是不撞南墻絕不回頭的。
我記憶里的那座獨棟小土屋,夏天時墻側攀著葡萄藤,秋天時積著黃葉……經過歲月洗禮,墻皮坍落,鐵門斑斑,我下意識地摸向以往姥姥給我留鑰匙的地方,出乎意料地,鑰匙竟然還在原處。我摸著光滑的鑰匙,熱淚一滾,姥姥曾多少次撫摸這把鑰匙,又把它塞回積灰的門檻縫里,等著唯一一個能找對路的人,打開無人問津的心房,來陪她,來愛她。這么多年來,千山風雪外焦頭爛額的我,卻將愛嗤之以鼻。
我拿著鑰匙,卻叩了叩門。“誰啊?”昏黃的燈光在濃墨般的夜里暈染開,熟悉的嗓音伴著窸窸窣窣的拾掇聲裹挾著記憶的浪潮向我襲來,使我的心里翻起巨浪,從眼尾落下兩行玉箸般的清淚。我帶著哭腔叫了聲“姥”,便打開門,沖進屋抱住了她。我能感覺到她瘦弱的身軀輕輕顫抖,就像蝴蝶剛破蛹時輕顫著翅膀。望著她背后早已泛黃的全家福,我的心好似被月色沸煮。
回來后,我才明白,我的退路早已成為我的前路。我撫摸著姥姥那雙癟瘦的、粗糙的手,心卻似蚌肉般柔軟。歲月如泉涌,淌淌而過所謂人生,雕琢著一輩輩的青春。在院中,柿樹碗口粗細,嫩葉綴掛幾枝頭,不知名的風一吹,葉子就想掙開束縛,征程遠方。
離鄉的車票厚厚的,裝載著半腔愛和半腔月光。我站在燈塔下,看清了無數個彷徨失意的我和這如茗般的人生。滾滾逝水,哪一路不是歸程,滿載青山和燕語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