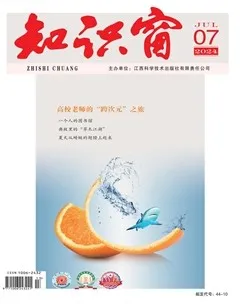金色的麥秸垛

在河套平原高遠的天空下,我的目光穿過收割過的麥田,落在幾戶人家的門前,高高聳起的麥秸垛像一個個金色的大蘑菇,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身在異地他鄉,又見到熟悉的、親切的麥秸垛,我的心中涌起感動和溫暖。以田地為生的北方農人,誰家門前沒有一兩個麥秸垛呢?
堆垛是麥粒入倉后的一件大事。二叔善于踩垛,村子里一個個麥秸垛大都是從二叔腳板底下誕生的。堆垛需要三五個人合力完成,其他人用鐵叉傳送秸稈,二叔則不停地把麥秸分散攤到自己腳下,并踩實壓勻。麥秸稈十分光滑,沒有一定技術和經驗很難做成麥秸垛。麥秸越堆越高,堆成一個傘狀蘑菇頭,最后還需用麥糠和成的稀泥糊好抹勻,以免因漏雨而造成發霉。
那時,麥秸在農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資源,它可以燒火、鋪炕,也可以喂牛、喂羊,還可以堆一個溫暖的雞窩。麥秸垛佇立在那里,任憑日曬雨淋,干了又濕,濕了又干,卻始終挺拔。人們只有在需要時才會想起它,它融入人們的生活中,卻又游離于生活之外。經歷了豐收的歡騰,也能忍耐被冷落的寂寞,它靜默無語,像在等待著什么,也似正孕育著什么。在農事稼穡的季候輪轉中,它是參與者和守望者,也是最懂農人心思的知己。
麥秸垛間是孩子的樂園,孩子可以繞著它奔跑嬉戲,也可以捉迷藏,累了的時候便聚一堆麥秸稈,或坐或臥,它真是天然的軟床。剛收獲的麥秸稈散發著柴草的清香氣息,在溫熱的晚風中繚繞、擴散,使人昏昏欲睡。這誘人的氣息附在孩子的身上、發間,一直縈繞進夢里。
麥秸垛間也是大人時常逗留的地方。大人喜歡捧著飯碗聚在麥秸垛旁,邊吃邊聊些閑話,有私密的談心,也有家長里短的八卦。當然,他們聊得最多的還是農事收成,說說耕作的體會,聊聊來年的愿景。在短暫的休憩后,他們養足精神,又開始新一輪的勞作。
新打的麥子很快被農人磨成面粉,巧婦會做一頓手搟面犒勞家人。新面粉麥香濃郁,在搟面杖底下抖動絲滑如綢緞,吃起來也是筋道柔韌,咬勁十足。這時,麥秸稈決不旁觀,而是擁圍在爐灶里,等著自己的熱情被點燃。麥秸稈焰熾火急,適合做快飯,是既顧農事又顧家的巧婦的最愛。只要兩三把麥秸稈,一碗新鮮面條便可出鍋了。
奶奶的茶飯手藝是村里數一數二的,最拿手的便是攤煎餅。麥收一過,新面粉入了甕,奶奶總要用麥秸稈為一家人攤回煎餅解解饞。土鍋大灶,手拉風箱,柴草氣、煙火氣像奶奶的愛心四處彌漫。隨著風箱“卟嗒卟嗒”的歌吟,麥秸稈也在爐膛里跳起歡快的舞蹈。麥秸稈的火焰熱情但不猛烈,不會將鍋內的食物燒焦,是攤煎餅最適合的柴火。一勺面糊沿著鍋邊撒下去,迅速在鍋內凝成圓圓的面餅,奶奶再鏟起翻兩次身,一張煎餅便做成了。咬一口,煎餅筋薄軟彈,令人唇齒留香。在麥秸稈的助力下,奶奶身邊很快就疊起厚厚的一摞煎餅,再爆炒一碟土豆絲,涼拌兩根黃瓜,用煎餅卷起來吃,真個是人間美味。
麥秸垛在人們的一日三餐中逐漸縮小身形,不過來年,又會有一個新的麥秸垛佇立在人們眼前,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土地從不辜負熱愛它的人們,糧食滿倉、秸垛成山便是大地對農人辛勤勞作的最好回報。
如今,我的家鄉已經很少能看到麥秸垛了。那親切又熟悉的麥秸垛只能遠遠地佇立在我的記憶深處,我透過歲月的煙塵回望,麥秸垛一會兒模糊,一會兒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