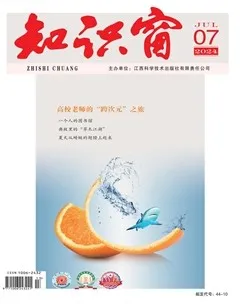不是所有的月亮都為我而來

我偏愛夜晚的月亮。在無事的夜晚,我常常獨自在校園里漫無目的地走啊走。褪去了白日的喧囂,夜晚是謙和的。正好今夜月亮皎潔,視線所及皆如鋪滿了霜雪般明澈。
思緒拉回到十多歲的年紀(jì),我時常在夜晚戴著耳機(jī),聽著歌在陽臺讀書,身上落滿了月光和星光。當(dāng)看得累了時,我關(guān)上讀書燈,一身都是月光。伴著蟲鳴,我望向天空,任由自己的思緒漫無目的地飄遠(yuǎn),想象著月亮陰晴圓缺背后無數(shù)的人間悲歡離合。
大概文藝的人都多夢,我常常在深夜醒來,看月亮如玉壺光轉(zhuǎn),心里醞釀了無數(shù)的詩情畫意。
那些靈感纏繞在腦海里,催促著我快點將它們安置下來。我沒了睡意,趕快鉆到被窩里偷偷打開手電筒寫文章。等到文章終于完成了,我從被窩里爬出來,心滿意足地大口吸氣,再舒展疲憊的肩膀望向窗外。月亮似乎更大、更圓了,室內(nèi)被照得宛如白晝。
上初中時,我在博客上與名喚阿硯的姑娘相識,我們惺惺相惜,成為彼此忠實的讀者。阿硯喜歡寫“海是倒過來的天”“好想用玻璃罐貯藏一縷夏風(fēng),到冬天給你我滿腔的熾熱”諸如此類的文藝句子。我們沉迷于簡單文字排列組合而成的無限可能性,同樣的文字在不同作家的筆下,創(chuàng)造出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阿硯在博客上連載了一些小說,她說自己的夢想就是出一本書,創(chuàng)造出自己心里獨一無二的世界,讓她筆下創(chuàng)造的人“活”過來。我和阿硯互相打氣,約定好等到未來完成了出書的夢想,一定要見上一面。
我嘗試參加了一些征文比賽,拿了不少獎項,雜志樣刊很快堆積了厚厚一疊,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順利。我甚至收到了一個名家的親筆信,夸贊我很有寫作天賦,一定要堅持寫下去。
那時候,我喜歡在夜晚一個人到院子里散步,張開雙臂,踮起腳尖,任由晚風(fēng)把我的裙擺高高吹起。無論我何時抬頭,月亮都會悄悄跟著我。
可文字的世界就像是變幻莫測的宇宙,當(dāng)我更近一步,以為能和星辰大海撞個滿懷,殊不知目光所及,也許是更遼闊的黑暗。
我第一次獨自背上行囊,信心十足地去遙遠(yuǎn)而陌生的城市參加一場全國性比賽,可僅僅在第一輪初審,我便被淘汰了。不服輸?shù)奈矣謪⒓恿撕芏鄨稣魑谋荣悾谷粚覒?zhàn)屢敗。禍不單行,在那段時間里,投出去的稿件也大多石沉大海。
我沮喪地認(rèn)識到,自己的實力離我的文學(xué)夢想相差甚遠(yuǎn)。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寫不出任何打動人的文字,也深深懷疑自己到底是否適合寫作。一個熱愛文字的人寫不出文字,無異于蝴蝶被折斷了翅膀。
在某個深夜醒來,我發(fā)現(xiàn)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時間似乎也在這絕對的黑暗里停滯不前,我就像無邊黑暗海洋里唯一的鯨,孤單又無措。
上高中后,學(xué)業(yè)繁忙,我在文字上花的時間更少了。我喪失了文字上的一些靈性,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都變得困難。某天,我無意翻開日記本,看到我曾經(jīng)寫下的夢想——完成一本小說作為自己的成年禮。
可我期待的都沒有來,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忙碌的、瑣碎的大學(xué)生活,那些過往都恍若隔世。我才恍然發(fā)覺,自己并不是“天生的寫作者”,不是天賦異稟的“仲永”,在時光洪流里泯然眾人。
我開始和許久未聯(lián)系的阿硯聊天,渴望從對方身上找回曾經(jīng)那個忠于文字的自己。一切都好像發(fā)生在昨天,我和阿硯相約“攻”下一家心儀已久的雜志,互相打氣。許久之后,我們竟然真的在這家雜志的同一期上了稿,那種驕傲和滿足簡直無可替代。我們美滋滋地認(rèn)為,成為一個大作家指日可待。
我問阿硯是不是放棄了文字,她回復(fù)我:“沒有,我依然熱愛文字,只是我不再執(zhí)著于成為優(yōu)秀的作家。”郵件的末尾,阿硯給我發(fā)了一個很俏皮的表情。
很久以后,我看到阿硯更新了博客,是博爾赫斯的詩:“一朵玫瑰正馬不停蹄地成為另一朵玫瑰。你是云,是海,是忘卻,你也是自己曾經(jīng)失去的每一個自己。”
我想起自己曾經(jīng)趴在被窩里寫文章的日子,寫完后我會溜到院子里,走到哪里,月光便跟到哪。
長大后,在無數(shù)個被平庸刺痛的夜晚里,我終于明白不是所有的月亮都為我而來,我來或者不來,月亮都停留在原地,不遠(yuǎn)不近。可是,月亮曾那樣長久地照亮過我,在我不曾注意到的時候。
后來的我依舊熱愛文字,認(rèn)真生活,時有作品發(fā)表,但我不再執(zhí)意成為一個厲害的作家。
沒想到,也會有人對我說:“我被你的文字深深打動過。”當(dāng)收到消息時,我正百無聊賴地坐在院子的秋千上,正好清夜如塵,月色如銀,院子里的植物蹭著月光變得毛茸茸的。這樣寧靜的夜晚,不適合多愁善感。
我伸出手來,不知何時落下的眼淚在月光的照射下如霜雪般凝在我的指尖。我這才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許久不曾抬頭看過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