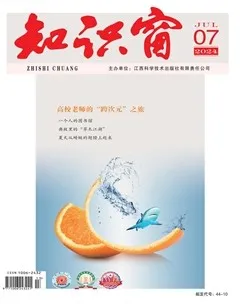用耳朵閱讀
“從小我就是個用耳朵閱讀的人,是一個聽故事的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校區演講時說道。
按照常理來說,如果提及閱讀,孩子主要通過眼睛來看紙質的報刊和圖書,或是啟蒙學習,或是找尋趣味。但莫言小時候是用耳朵來閱讀的,顯得與眾不同。
莫言的故鄉在山東省高密市東北鄉,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還是一個相對閉塞的農村。村里沒有通電,每到夜晚,伸手不見五指,孩子們沒有其他娛樂活動,聽故事便成了他們最感興趣的、最期待的事情了。
村里的老人多半不識字,但腦子里裝了很多光怪陸離的故事,并且老人都是特別會講故事的人。莫言說,他的爺爺、奶奶、父親都是講故事的高手。
在神秘的夜色下,村里的老樹邊,老人煞有介事,拿腔捏調,講得繪聲繪色,講到情節跌宕處,還會手舞足蹈。莫言和小伙伴圍攏在一起,豎起耳朵,聽得真切而入迷,時而興奮,時而恐懼,時而嚇得尖叫。
鎮上的小集市是莫言用耳朵閱讀的另一個好去處。在兒時的莫言眼里,集市上的說書人儼然是高密鄉間的故事大王。他們會把鄉間搜羅到的和書上讀到的故事,進行隨機地添油加醋和各種雜糅,再次生動演繹,深深地吸引、感染著莫言。據莫言回憶,他最癡迷的時候,甚至夢想成為一個集市上的說書人。
值得慶幸的是,莫言這一夢想實現了,只是方式由“說”變為“寫”罷了。在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莫言演講的題目即為《講故事的人》。
兒時用耳朵閱讀的這些故事,主角全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但蘊含的都是人間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有美善,也有丑惡。這些豐富而鮮活的文化元素已經深深根植于莫言的心底,以巨大的養分供給,孕育出這樣一個成功的、會講故事的作家。
莫言很多小說作品的靈感和素材都來自小時候這些用耳朵閱讀來的鄉間民野里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奇思妙想,更是讓他腦洞大開,受益終身。他還專門寫過一本書,名叫《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分三個部分,即“奇奇怪怪的動物”“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事”。 他在序言里寫道:“小時聽人說鬼狐,夜晚走路心發虛,長大執筆寫精怪,揚善抑惡學蒲書。”這不僅是對童年耳朵閱讀經歷的懷念,更是對鄉村父老的致敬致謝。
用耳朵閱讀并非莫言專屬,在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作家,還是莫言的山東老鄉,被莫言稱為“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在村口,這個作家每天用桌子支起一個簡陋的茶攤,外加幾張破舊的凳子,供南來北往的行人歇腳、喝茶、聊天。就在這種輕松而自由的閑聊中,他用耳朵傾聽,搜集了許許多多的奇聞逸事。他把聽來的這些故事一個一個梳理,慢慢寫了出來,經年累月,成就了一部經典的包羅萬象的《聊齋志異》。這個擺茶水攤的人就是蒲松齡。
用耳朵閱讀,也許更能調動感官,腦海里的形象思維更加活躍,內容的畫面感更強,但這只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閱讀方式。其實,無論是用眼睛、嘴巴,還是用耳朵來閱讀,要讀得好、讀得深,終究還是要用心。我想無論是蒲松齡,還是莫言,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