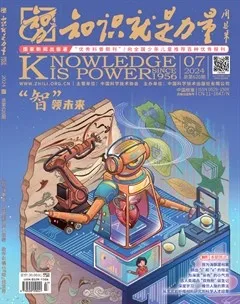自然的啟迪、生命的共振與超越之美
初看之下,這是一篇帶有唯美主義色彩的短篇小說,凄美、靜謐、幽遠、孤峭。暗夜里倔強地閃爍著光芒的螢火,與藍天碧湖映襯下的白帆,分別與兩位不幸的青年人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自幼失聰的唐鵬不僅又聾又啞,而且缺失母愛,像極了蘇州灣湖邊那些“沉默、倔強、自生自滅的蘆葦”。進帆船學校是他向父親主動提出的要求。身患絕癥的姑娘章虹,先是跟隨父母從吳江到深圳,后來成了一名生態攝影師,像候鳥一樣在全國各地跑來跑去、飛來飛去。有一次偶然間,章虹被草叢間的螢火蟲徹底迷住,從此她便成了一個“追光人”,從西雙版納到怒江,從四川天臺山到南京紫金山。……那些閃閃發光的小昆蟲,那些“漫漶的光帶”成為她手中鏡頭唯一的主角。
小說篇幅很短,語言極為節制,雖唯美但絕不堆疊意象,亦不見隨意的抒情和哀惋,完全以人物內心世界的點滴感受與微妙體驗來推動敘述流程。細讀之下,讀者會看到,在流動的唯美表象背后隱含著一個謹嚴細密而符合邏輯的敘事結構。故事流程可歸結為從大自然的啟迪到生命的共振,再到精神的超越,而這一結構的實現完全是通過作家對于人物內心世界體貼入微的觸摸來抵達的。
雖然缺失母愛,但少年鵬的父親還是給予了力所能及的父愛與理解,幾乎可與史鐵生《我與地壇》里的母愛相提并論。然而,對于這種愛和理解,唐鵬表現得又聾又啞,幾乎是毫無感覺。18歲的少年,心境一度超過40歲,對一切都沒有興趣。少年鵬的這種“冷冰冰”的態度并不意味著他喪失了感知愛的能力,而是因為來自人間的愛的缺失或者愛的豐盈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個人的生命問題,甚至有時候越是試圖理解和包容一個不幸者,反而越是強化對方對于不幸的感受;當這種愛的表達方式不恰當的時候,這種反作用力更是不容小覷。在這里,小說作者直擊生命感知的肌理。在某種程度上,相對于人類,唐鵬認為自己與湖面上那些無名的水鳥更為相似。“孤僻、敏銳、隨時能夠感知危險,或許,還有某些……善意”。直到這時,少年鵬才從對象身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某種必然性,從而開啟了重新自我認知的里程。與唐鵬同樣孤僻且更加冷靜和神秘的章虹,也是在偶遇螢火蟲之后,深刻體驗到自然之神的啟迪。章虹原本就對人間的同情不抱有過高的幻想,看到更多的戲劇性人格的表演后,她以生態攝影的方式來匹配自身的孤獨。
從自然的啟迪到生命的共振,標志著作家對于人類生命體驗的極度敏感和深度介入。唐鵬從自己的脖子、耳朵邊流動的風來感知風力與方向,并將之巧妙地傳導給白帆,使船在水面上優美地滑翔。這就如同全身潔白的鷺鳥在水面上飛舞,超凡脫俗,自由自在。雖然沒有聲音,但人、白帆與風的和諧足以使少年鵬尋找到生命的共振和存在的價值。螢火蟲對于章虹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螢火蟲的生命周期大約有一年時間,但閃閃發光的成蟲只有三到七天的壽命。但就是在這幾天之內,它們散發出絢麗燦爛的極致之美。于是,身處化療第三階段的她甘愿與寥落、夢幻、孤獨相伴,生命共振之下,她深刻地體悟到,螢火蟲之美不是浪漫,也不是神秘,“那就是命運”。作為攝影師的她真正要做的是追蹤并留下“所有美麗而轉瞬即逝的事物”。
一男一女兩個主人公本不相識,且一個追求陽光下的揚帆逐浪,而另一個追蹤的是黑夜中的螢火星光。是整體性的生命共振將他們聯系在了一起,也是美將他們聯系在了一起。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曾深刻地指出,有這樣一種不合格的讀者:“他對藝術的興趣絕對地不是在道德方面,就是在自然方面,只是恰恰不在應該在的方面,即不在審美方面。”真正的審美就是人類靈魂的表現形式,它讓我們超越了自然與善惡的對立,超越了物質世界的局限,達到的是一種擺脫了一切強制的最高程度上自由的狀態。唐鵬與章虹二人彼此之間的吸引便起因于不期然的美的力量。小說寫章虹在拍鷺鳥時,鷺鳥很美,湖面很美,鷺鳥和湖面的組合也很美。但是一切都“好似太完美了”,“因此有什么東西仿佛不對”。顯然,僅僅有自然之美還不是完整的藝術,人化的自然與自然的人化相結合,才是最高的審美狀態,“就在這時,少年鵬和他的帆船出現了”,而鵬也注意到了拍攝風景的章虹。兩個彼此都深感對方“很特別”的人互為風景,互相陶醉于美的構想之中。
小說作者以獨到的敘述和架構演繹了真善美之間,唯有美才是小說的真正目的,這也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的,這是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這也是小說告訴我們的有關存在的“一種人類可能性”。就像螢火蟲發光本就有引誘異性的作用,兩位主人公以滿足對方需求的同時,也實現了自由之美,進而通達精神的超越性。這一轉折發生于唐鵬向開旗袍店的父親追問:“穿上旗袍能讓人變得更美嗎?”“如果一個人沒有了頭發,她穿上旗袍也能變得更美嗎?”于是,穿著藏青色改良旗袍的章虹出現在國際服裝節開幕式上,在滿屏螢火蟲的襯托下,章虹的平頭、消瘦和堅毅的臉部線條將故事推向高潮。
唐鵬和他的白色帆船也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俊少年和絕佳構圖,甚至有人在遠處似乎聽到這位少年大叫了一聲“我能聽到風聲了!”“我聽到了風聲!”小說至此,這叫聲是真是假已經不再重要,因為美的超越性業已降臨。
作者簡介:張光芒,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江蘇文學院副院長、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