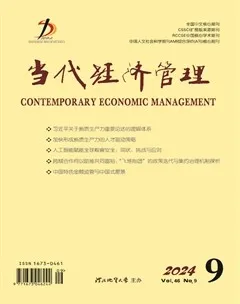勞動力外流背景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農戶收入效應研究






[摘要]推動農民增收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任務,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農業經營體系變革的重要內容,其能否及如何促進農戶增收,在學術界尚未形成一致定論。文章基于中國13個省份的132個村莊1385份農戶問卷調查數據,通過構建一個包含農業社會化服務識別工具的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以及勞動力非農轉移在其中發揮的中介效應。研究表明,農戶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會顯著促進勞動力非農轉移,由此造成兩方面的農戶收入效應:一方面,勞動力非農轉移會直接促進非農業收入的增長;另一方面,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在生產效率方面彌補農業勞動力減少對農業收入造成的不利影響,實現農業收入增長。同時,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農戶收入效應存在異質性。現階段我國距離農業規模經濟還存在較大差距,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成為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促進農戶增收的重要路徑。由此,應重視農業社會化服務薄弱環節的發展,為勞動力非農轉移創造空間并提供配套支持,從而更好地促進農民增收。
[關鍵詞]農業社會化服務;非農收入;農業收入;勞動力非農轉移;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3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9-0038-10
一、問題的提出
農民收入是“三農”問題的重點和難點,提升農民群眾的收入水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最艱巨任務[1]。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強化農民增收舉措。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整體上還維持在245∶1(2022年)的較高水平,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城市化轉移不利于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配置,不利于實現鄉村振興,只有兼顧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增長,才能解決以上矛盾。因此,在農村勞動力不斷外流背景下,如何進一步強化農民的增收措施已然成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農業社會化服務大量興起,得到各界廣泛關注,被認為是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關鍵,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促進農戶增產增收[2]。當前,政府已經出臺諸多政策引導和支持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例如2013年農業部印發《關于大力推進農機社會化服務的意見》指出,要積極推動農機社會化服務機制創新,構建新型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最大限度滿足農民實際需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以上重要政策文件為農業、農村和農民現代化發展確立了主體方向。
目前,僅有少量文獻專門討論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認為農業社會化服務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增收作用[3-4],而土地規模化經營是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農戶稻作收入的重要作用路徑[5]。其他大部分研究聚焦于農業機械化和生產環節外包等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一些研究表明,農業機械化可以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提升勞動生產效率[6-7],從而有效增加糧食產出,促進農業收入增長[8],農業機械化還會促進勞動力非農轉移,提高農戶的非農收入[9],但勞動力老齡化會抑制農機服務的收入增長效應[10]。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對生產效率和技術效率存在積極影響,但在不同要素密集型環節呈現顯著差異[11-13]。生產環節外包對生產成本也具有顯著影響,能夠降低水稻生產成本[14],但是在病蟲害防治環節的外包卻得出相反結論[15]。而且,服務外包的福利效應呈現環節差異性,且田間管理環節高于其他環節,但是沒有找到相應的證據表明播種環節外包具有福利效應[2]。總體上,生產服務外包能夠顯著提高農業生產凈收入[16-17]。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現有文獻主要聚焦于農業機械化采用和生產環節外包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但是整體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是否具有同樣的作用還有待研究,相應的影響機理和作用機制尚未清晰詮釋,特別是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大規模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而勞動力非農轉移在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戶收入構成關系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現有研究缺乏從勞動力非農轉移角度討論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其二,大部分研究都是探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整體收入的影響,忽略了農戶收入結構的變化,在勞動力結構向非農轉移背景下,農戶收入結構中非農收入占比日益上升,勞動力結構和農戶收入結構都在發生重要變化,當前缺乏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結構的細分研究;其三,農業社會化服務與勞動力非農轉移的關系可能是雙向的,將農業社會化服務、勞動力非農轉移與農民增收三者的關系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如何有效識別相互之間的因果關系是急需解決的難題。現有研究對以上問題都缺乏系統性討論。
鑒于此,本研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否能夠通過勞動力非農轉移促進農戶增收,并得出各自中介效應的比例,既可以量化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又能夠進一步探索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勞動力非農轉移作用于農戶收入的具體路徑。此外,為克服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構建了Probit模型,估計出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的概率預測值,將其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識別工具,引入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分析。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根據“經濟人”假設,無論在任何生產環節,農戶自愿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均能提高農戶效用水平。理性農戶選擇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原因在于,通過農業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有助于獲得更高收益。他們并非簡單追求農業產出或個人效用最大化,而是合理配置家庭資源,從而最大化家庭收入[18]。農戶家庭收入主要包括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這與勞動力結構密切相關。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農村勞動力在城鄉二元地區的流動能力不斷增強,農戶可以在城鄉之間兼顧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兩個方面,而農業社會化服務恰好可以提高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效率,通過要素替代效應作用于農戶收入。
(一)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的影響
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顯著降低單位投入的生產成本[7,14],提高農業生產的收入。同時,農業社會化服務還可以通過資源配置[19]、專業化分工[20-21]和技術引入[22-23]等三種效應影響農業產出,進而作用于農戶收入。通過土地托管或生產環節部分(或全部)外包給專業化服務組織,農業生產的效率會得到顯著提升,最終提高農戶農業收入[24]。譬如,黃季焜等(2008)發現,相比農戶自種,采用統防統治服務在施藥時間和頻率上更為精確,有助于提高防治效率[20]。而且,雖然農業機械不可分,但是可以利用農機服務可分的優勢克服單個農戶耕地規模過小的問題。農業領域的技術進步促使部分生產環節和農藝能夠由專業化組織供給,農業機械化服務克服了資產專用性的劣勢[23],小農戶采用機械服務亦可獲得先進機械技術形成的優勢,進而增加農業產出。因此,總體而言,農業社會化服務有助于農戶增收。
(二)勞動力外流背景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結構的影響
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要素替代效應會推動勞動力非農轉移,作用于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農業社會化服務會加速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造成負面影響。根據劉易斯的“零值農業勞動假說”,當農業剩余勞動力邊際產出為零或者為負值時,勞動力非農轉移并不會對農業產出產生影響。但根據舒爾茨的觀點,這一假說似乎并不完全成立,尤其在農忙時節,農業勞動力供給不足將對農業產出造成顯著負面影響。在中國,農業機械化的蓬勃發展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替代效應,勞動力外流似乎并沒有制約糧食生產。但實際上,東北三省、廣西等地由于勞動力大規模外流,導致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村莊空心化、拋荒等現象惡化,顯著減少了農業勞動時間,對生產和技術效率產生負面影響,減少了農戶的農業收入[25]。因此,在勞動力外流背景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采用對農戶的農業收入會產生不利影響。
在非農收入方面,正是由于農業社會化服務具有勞動力替代效應,農業勞動力有更多的時間從事非農就業,促進非農收入增加[7,24]。對于理性的農戶,考慮的是家庭收入最大化,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夠將他們從繁重的農業勞作中解放出來,轉移到工資率更高的非農部門就業,獲得更高收入。由此可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非農收入的增長效應主要由勞動力非農轉移實現。
綜上所述,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存在總體和結構的影響。理論上,在不考慮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情況下,農業社會化服務總體上是有助于農戶增收的,現有研究也得到了相應結論[3-4]。但是在勞動力非農轉移背景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不同收入結構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其中不利于農戶的農業收入增長,但有助于非農收入的增加。因此,在考慮勞動力非農轉移因素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總體影響需要取決于對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影響程度,相應結論需要進一步進行實證檢驗,具體的影響機理如圖1。
圖1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機理
三、數據來源、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新型經營主體調研”問卷調查。該調研問卷涵蓋受訪農戶個人和家庭信息、土地利用、分地塊信息、糧食作物的生產成本與收益等信息。根據研究需要,采用玉米種植戶的樣本數據,并剔除極端異常值和信息不完善的樣本,剩余1385個觀察值,覆蓋13個省份(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甘肅)112個縣的132個村莊。其中,693戶農戶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約占總樣本的一半。
(二)模型設定
1中介效應模型
為檢驗勞動力非農轉移在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農戶收入過程中的中介效應,即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勞動力非農轉移對收入的影響,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Yi=φ0+φ1Xi+φ2Zi+ε1(1)
MEDi=ω0+ω1Xi+ω2Zi+ε2(2)
Yi=ρ0+ρ1MEDi+ρ2Xi+ρ3Zi+ε3(3)
式中,Yi為第i農戶的收入,Xi為自變量,MEDi為中介變量;ε1,ε2,ε3為隨機擾動項;φ1,φ2,ω1,ω2,ρ1,ρ2,ρ3為待估參數;Zi為影響勞動力非農轉移和農戶收入的其他控制變量。φ1是自變量對收入的直接效應;ω1為自變量對中介變量的影響,ρ1,ρ2分別為自變量、中介變量對收入的影響。本研究采用Sobel檢驗的顯著性評估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考察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否能夠通過推動勞動力非農轉移,進而促進家庭農業收入、非農收入和總收入提升。
2Probit模型
由于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二元變量的內生性本質,特別是勞動力非農轉移可能影響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為有效解決以上問題,本研究采用兩階段處理方式,第一階段運用Probit模型預測出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概率,第二階段將概率預測值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識別工具[26]。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模型設置為:
Servicei=α0+αm1Xmi+i(4)
式中,Servicei為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二元變量,采用即賦值為“1”,否則為“0”;Xmi為一組影響農戶采用服務的變量,包括農地規模、細碎化程度、耕地特征、固定資產投資、農戶和個人特征等;i為隨機誤差項。
(三)變量與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核心變量為農業社會化服務,在Probit模型作為因變量,在中介效應模型中將Probit模型估計出的概率值作為核心解釋變量。中介變量為勞動力非農轉移,采用外出務工人數占家庭人口數的比重進行衡量。借鑒既有文獻的研究成果[27-29],控制了經營規模、耕地細碎化、土地特征、生產經營決策人特征、農戶家庭特征、政策因素、區域因素等影響。特別地,根據李江一等(2021)[30]的研究成果,控制了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見表1)。
從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來看,戶均玉米種植面積為1328公頃(1992畝),平均地塊數量為5264塊,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大農場的經營規模,如2017年美國農場的平均土地規模為441英畝(26708畝)②、澳大利亞的小麥種植農場平均規模達到1500公頃(22500畝),中國農業經營主體以小規模農戶為主,土地碎片化嚴重,符合農業生產實際情形。同時,這也表明,現階段我國農業發展距離規模經濟還存在較大差距。從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采用情況看,1385個農戶樣本中,近一半的農戶采用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從勞動力非農轉移情況看,平均每戶家庭勞動力向非農轉移的比例為039,說明我國農村地區勞動力非農轉移已成為時代所趨。
四、實證結果及解釋
為實證檢驗農業社會化服務、勞動力非農轉移和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本研究構建一個中介效應模型,該模型包含Probit模型估計出的概率預測值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識別工具,以克服二元決策變量的內生性問題。首先,運用Probit模型估計出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的概率預測值,其次,將它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工具變量引入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檢驗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農戶收入的中介效應。
(一)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的影響因素
表2報告了Probit模型估計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總體上農業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存在顯著正向效應,這與現有研究發現類似[23]。REARDON等(2000)[31]發現農業機械化能夠有效替代勞動,緩解農戶從事農事活動中所需的繁重體力勞動,開展非農就業活動。可見,農戶向非農部門轉移,將助推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采用。農地規模和地塊數量的估計系數分別顯著為正值和負值,說明農地經營規模越大、耕地細碎化程度越低,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概率越高。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影響并不顯著,與YI等(2019)[32]的研究結論略有不同。根據QIU和LUO(2021)[29]的發現,經營規模與機械化服務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戶采用農機服務的概率增加,當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農機服務采用概率開始下降。本研究在模型中引入經營規模的平方項,Probit和OLS估計結果均表明,經營規模與農業社會化服務可能存在“倒U型”關系。這進一步印證了QIU和LUO(2021)[29]的觀點,經營規模越小,購買農機服務的成本較高,因而農戶更傾向于采用傳統耕作方式,而隨著規模增加,會逐漸傾向于采用農機服務,但是當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農戶更傾向于購買機械進行生產,農機服務采用概率下降(見表2)。
從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的影響因素來看,農地經營規模和耕地細碎化程度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產生了顯著影響,勞動力非農轉移促進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與勞動力非農轉移的雙向關系得到了證實。農業生產性資產投資與農機服務采用決策呈反向關系,換言之,不同規模的農戶采取不同的耕作方式和種植決策,小規模農戶可能傾向于采取傳統耕作方式,大規模農戶傾向于選擇自購機械進行農業生產。
(二)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直接影響
本研究將上一步各環節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的概率估計值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識別工具,基于式(1),在不考慮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情況下,檢驗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總收入的直接影響。同時,還考察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結構影響,結果如表3所示。
表3模型(1)回歸結果報告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影響,顯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值。意味著在不考慮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情況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采用能夠顯著提高農戶家庭收入,這與現有的研究結論一致[10]。模型(2)回歸結果報告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的影響,顯示農業社會化服務并未對農業收入造成顯著影響。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采用雖然有助于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縮減勞動時間,提高作物產量[33],進而促進農業收入增加,但是農業社會化服務也促進了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會產生不利影響。綜合兩種效應,在忽略了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情況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的影響還有待考察。模型(3)回歸結果報告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非農收入的影響,顯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值,說明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概率越大,農戶非農收入越高。由上文分析可知,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有助于非農收入的提高,因此,在模型中即使不考慮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情況,也可以得到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非農收入的顯著正向影響。
(三)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影響的勞動力非農轉移中介效應
1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影響
基于式(2),本文考察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影響,實證結果如表4模型(1)所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值,說明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有助于促進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這與宦梅麗和侯云先(2021)[23]得出類似的研究結論,進一步證實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勞動替代效應。
2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戶收入的影響
基于式(3),本文分別考察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總收入、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影響,并進行Sobel檢驗,結果證實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農戶增收效應中存在勞動力非農轉移的中介效應。實證結果如表4模型(2)和模型(4)所示。
對農戶總收入的影響。表4模型(2)回歸結果報告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總收入影響的回歸結果,以及勞動力非農轉移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考慮勞動力非農轉移后,農業社會化服務依然有助于提高農戶家庭總收入。Sobel檢驗結果表明,勞動力非農轉移發揮了顯著的中介效應,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總收入的正向效應中有5479%是通過勞動力非農轉移產生的。
對農業收入的影響。表4模型(3)回歸結果報告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存在顯著負向效應,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存在顯著正向效應。Sobel檢驗結果表明,勞動力非農轉移在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農業收入過程中產生了顯著中介效應,且中介效應為-15242%,即勞動力向非農部分轉移抑制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的增長效應。以上回歸結果與表3模型(2)回歸結果相吻合,在剔除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的不利影響后,農業社會化服務會在技術服務領域提升農業生產效率,顯著提升農業收入水平。
對非農收入的影響。表4模型(4)回歸結果報告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非農收入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勞動力非農轉移對非農收入產生了顯著正向影響,而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非農收入的影響由顯著為正向(見表3模型(3))變為不顯著(見表4模型(4)),表明勞動力非農轉移在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非農收入的影響中存在完全的中介效應,Sobel檢驗結果證實了這一論斷,勞動力非農轉移的中介效應為9015%。
(四)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影響的區域差異性
中國內陸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不過土地資源豐富,例如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等都是我國的糧食生產大省,農民土地經營規模相對較大,農業收入成為農戶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進一步探討了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關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影響的區域差異性③,回歸結果如表5。其中,非邊疆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戶總體收入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雖然勞動力非農轉移減少了農業收入,但顯著促進了非農收入增長,以上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相同。但是,邊疆地區的樣本回歸結果有一定差異性,其中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戶總體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而且,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可以顯著促進非農收入的增長。邊疆地區回歸結果的差異性可能是因為邊疆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水平顯著低于其他地區,勞動力非農轉移水平也具有同樣的特點④。因為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家庭的土地經營規模相對較大⑤,農戶大多會采取購買機械化設備的策略進行規模種植,而非采用農業社會化服務,而且,邊疆地區的農業技術服務的可得性也有待進一步提高。此外,以上地區的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工業就業機會較少,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很大,較少農民會選擇到對應城市務工,大多勞動力會選擇直接向大城市進行轉移。因此,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等地區,并未發現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戶總體收入產生顯著影響。
綜上所述,無論是否考慮勞動力非農轉移存在的中介效應,農業社會化服務都有助于顯著提高農戶總收入和非農收入,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確實推動了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業收入存在顯著負向效應,不過農戶整體的農業收入水平并未因這種不利影響有所減少,因為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在生產效率方面彌補農業勞動力減少對農業收入水平的不利影響。換言之,盡管勞動力非農轉移抑制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收入的增長效應,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總收入仍然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這種增收效應主要由非農收入的直接增加和農業收入的凈增加所實現。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研究采用農戶層面的數據,以玉米種植為例,考察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以及勞動力非農轉移在其中發揮的中介效應。在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外流的現實情境下,試圖從農業社會化服務角度為農戶增收路徑提供一個解釋。具體而言,基于2019年中國13個省份132個村莊的1385份農戶問卷調查數據,構建一個包含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的Probit概率估計值的中介效應模型,考察農業社會化服務、勞動力非農轉移和農戶收入的互動關系。
本研究發現:一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決策由農地經營規模、耕地細碎化程度、勞動力非農轉移、農業生產性資產投資、個人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共同決定;二是農業社會化服務推動了勞動力非農轉移,直接促進了非農收入的增長,而且農業社會化服務可以在生產效率方面彌補農業勞動力減少對農業收入的不利影響,實現農業收入的增長;三是農業社會化服務能顯著促進農戶家庭總收入增長,這種增收效應主要由非農收入增長和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形成的農業收入增長共同構成;四是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等邊疆地區,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和勞動力非農轉移對農戶總體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
本研究認為,現階段我國距離規模經濟還存在較大差距,農業生產依然以小農戶為主體,但是只有當從事農業經營的人地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才能保證農業機械化可以有效促進農民增收。因此,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非農轉移背景下,需要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配套支持,避免農業和農村的“空心化”問題。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重要手段,能夠有效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和工資率剛性上升的不利局面,對農戶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產生雙重促進效應。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層面繼續推進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農戶增收機制構建:一是通過鼓勵培育家庭農場、農機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創新跨區服務、土地托管、服務外包等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二是增強農業機械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補齊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薄弱環節的短板,降低服務價格,增加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可得性;三是消除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資源要素流動壁壘,推進農村地區的基礎服務建設,特別是推進城鄉交通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民在農作時節和城市務工期間,城鄉往返的通勤條件和通勤成本;四是加快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在農村地區加大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宣傳,引進更多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經營主體,發揮農業社會化對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雙向促進作用,實現城鄉融合互動發展。
[注釋]
①
本研究根據農戶所在省份的地理區位劃分三個地區:東部地區包括河北、遼寧、江蘇和山東;中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四川和甘肅。
②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USDA)2017年農業普查(CensusofAgriculture)。
③受制于樣本數據,本研究將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等省份作為邊疆地區,其余樣本為非邊疆地區。
④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的平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為036,其他地區為0565;勞動力非農轉移水平為022,其他地區為047。
⑤邊疆地區農戶的玉米種植經營規模平均達到3063公頃,其余地區為0515公頃。[BFQ][ZK)]
[參考文獻]
[1]陳錫文.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J].農業經濟問題,2022(5):4-9.
[2]楊志海.生產環節外包改善了農戶福利嗎?——來自長江流域水稻種植農戶的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9(4):73-91.
[3]曲朦,趙凱.糧食主產區農戶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增收效應及要素貢獻分解[J].農村經濟,2021(5):118-126.
[4]張哲晰,潘彪,高鳴,等.農業社會化服務:銜接賦能抑或歧視擠出[J].農業技術經濟,2023(5):129-144.
[5]周宏,高燦.基于環節差異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業種植收入:來自江蘇省水稻種植戶的實證研究[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23,22(2):193-202.
[6]LIUY,HUW.TheinfluenceoflaborpricechangeonagriculturalmachineryusageinChineseagriculture[J].Canadi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2014,62(2):219-243.
[7]WANGX,YUMACHIF,HUANGJ.Risingwages,mechanization,andthesubstitutionbetweencapitalandlabor:evidencefromsmall scalefarmsysteminChina[J].Agriculturaleconomics,2016,47:309-317.
[8]周振,張琛,彭超,等.農業機械化與農民收入:來自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的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6(2):68-81.
[9]李谷成,李燁陽,周曉時.農業機械化、勞動力轉移與農民收入增長——孰因孰果?[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112-127.
[10]唐林,羅小鋒,張俊飚.購買農業機械服務增加了農戶收入嗎——基于老齡化視角的檢驗[J].農業技術經濟,2021(1):46-60.
[11]陳超,李寅秋,廖西元.水稻生產環節外包的生產率效應分析——基于江蘇省三縣的面板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2(2):86-96.
[12]張忠軍,易中懿.農業生產性服務外包對水稻生產率的影響研究——基于358個農戶的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5,36(10):69-76.
[13]宦梅麗,戴瑤.農機服務、技術引入與中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J].商業研究,2023(2):145-152.
[14]TANGL,LIUQ,YANGW,etal.Doagriculturalservicescontributetocostsaving?EvidencefromChinesericefarmers[J].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2018,10(2):323-337.
[15]SUND,RICKAILLEM,XUZ.Determinantsandimpactsofoutsourcingpestanddiseasemanagement[J].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2018,10(3):443-461.
[16]MACHILAM,LYNEM,NUTHALLP.AssessmentofanoutsourcedagriculturalextensionserviceintheMutasadistrictofZimbabwe[J].Journalofagriculturalextensionandruraldevelopment,2015,7(5):142-149.
[17]LYNEMC,JONASN,ORTMANNGF.AquantitativeassessmentofanoutsourcedagriculturalextensionserviceintheUmzimkhuludistrictofKwaZuluNatal,SouthAfrica[J].Journalofagriculturaleducationandextension,2018,24(1):51-64.
[18]孫頂強,盧宇桐,田旭.生產性服務對中國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基于吉、浙、湘、川4省微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6(8):70-81.
[19]王志剛,申紅芳,廖西元.農業規模經營:從生產環節外包開始——以水稻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1(9):4-12.
[20]黃季焜,齊亮,陳瑞劍.技術信息知識、風險偏好與農民施用農藥[J].管理世界,2008(5):71-76.
[21]張露,羅必良.小農生產如何融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來自中國小麥主產區的經驗[J].經濟研究,2018,53(12):144-160.
[22]胡祎,張正河.農機服務對小麥生產技術效率有影響嗎?[J].中國農村經濟,2018(5):68-83.
[23]宦梅麗,侯云先.農機服務、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與中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69-80.
[24]李忠旭,莊健.土地托管對農戶家庭經濟福利的影響——基于非農就業與農業產出的中介效應[J].農業技術經濟,2021(1):20-31.
[25]秦立建,張妮妮,蔣中一.土地細碎化、勞動力轉移與中國農戶糧食生產——基于安徽省的調查[J].農業技術經濟,2011(11):16-23.
[26]WOOLDRIDGEJM.Econometricanalysisofcrosssectionandpaneldata[M].London:TheMITPress,2010.
[27]陸岐楠,張崇尚,仇煥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非農勞動力兼業化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影響[J].農業經濟問題,2017,38(10):27-34.
[28]MAW,RENWICKA,GRAFTONQ.Farmmachineryuse,offfarmemploymentandfarmperformanceinChina[J].Australianjournalofagriculturalandresourceeconomics,2018,62(2):279-298.
[29]QIUT,LUOB.Dosmallfarmsprefer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services?EvidencefromwheatproductioninChina[J].Appliedeconomics,2021,53:26,2962-2973.
[30]李江一,仇童偉,李涵.農地確權影響農戶收入的內在機制檢驗——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面板證據[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4):103-116.
[31]REARDONT,TAYLORJE,STAMOULISK,etal.Effectsofnonfarmemploymentonruralincomeinequalityindevelopingcountries:aninvestmentperspective[J].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2000,51(2),266-288.
[32]YIQ,CHENM,SHENGY,etal.Mechanizationservices,farmproductivityandinstitutionalinnovationinChina[J].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2019,11(3),536-554.
[33]鄭旭媛,徐志剛.資源稟賦約束、要素替代與誘致性技術變遷——以中國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為例[J].經濟學(季刊),2017,16(1):45-66.
StudyonFarmerIncomeEffectsofAgriculturalSocialized
ServicesundertheBackgroundofLaborOutflow
ZhanShaoguo1,HuanMeili2
(1.InstituteofChineseBorderlandStudie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2.ChinaInstituteforRuralStudies,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Promotingthefarmer’sincomeisanimportanttasktocomprehensivelypromotethestrategyofruralrevitalizationandacceleratethemodernizationofagricultureandruralareas.Asanimportantpartofthereformofthefarmingsystem,theacademiahasnotreachedaconsensusonwhetherandhowitpromotesthefarmers’income.Basedonasurveydatasetwith1385farmerhouseholdsinChina,thisstudyconstructsamediatingeffectmodeltoconductananalysisoftheimpactsof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onfarmerhouseholds’income,aswellasthemediatingeffectsoflabormigr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adoptionof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byfarmerswillsignificantlypromotethenonagriculturallabortransfer,resultingintwoaspectsoffarmer’sincomeeffects.Ontheonehand,labortransferwilldirectlyincreasenonagriculturalincome;ontheotherhand,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canmakeupforthenegativeimpactsofthereductionofagriculturallaborforceonagriculturalincomeintermsofproductionefficiency,andachievethegrowthofagriculturalnetincome.
Meanwhile,thefarmerhouseholdincomeeffectsof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areheterogeneousbetweenfarmerhouseholdsinborderareassuchasHeilongjiang,Jilin,Liaoning,InnerMongolia,andthoseinnonborderareas.Atpresent,thereisstillasignificantgapinChina’sagriculturaleconomiesofscale.Developingsocializedagriculturalserviceshasbecomeanimportantwaytopromotetheorganicconnectionbetweensmallfarmersandmodernagriculture,andtoincreasefarmers’income.Therefor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weaklinksi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creatingspaceforlabortransfer,providingsupportingfacilities,andbetterpromotingtheincreaseoffarmers’income.Atpresent,thereisstillasignificantgapbetweenChinaandthescaleeconomyofagriculture.Developingsocializedagriculturalserviceshasbecomeanimportantpathtopromotetheorganicconnectionbetweensmallfarmersandmodernagriculture,andtoincreasefarmers’income.Therefor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developmentofweaklinksin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creatingspaceforlabortransferandprovidingsupportingfacilities,inordertobetterpromotetheincreaseoffarmers’income.
Keywords: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nonagriculturalincome;agriculturalincome;labormigration;mediatingeffects
(責任編輯:張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