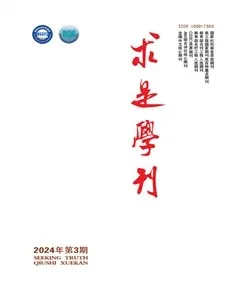以自主的道德實踐重塑現(xiàn)代理性文明
摘 要:蘇東劇變后,作為20世紀思想家群體重要成員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現(xiàn)代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們將共同體的道德精神與每個人的道德個性生成視為人類與人自身的激進需要和整體社會變革的內在組成部分,倡導以自主的道德實踐重塑現(xiàn)代理性文明。通過分析現(xiàn)代性的悖論及其道德后果,揭示現(xiàn)代性的理性化邏輯及其道德危機的社會生產,他們提出以良知和責任構建道德自我,不斷培育和生成道德個體和倫理共同體,從實踐上使現(xiàn)代性合法化。他們的理論還是一種現(xiàn)代性理論,以真正實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本質和價值為旨歸,其中貫穿的精神內核是馬克思式的道德愿景和人道主義,因而可以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一種具體化。不過,我們顯然不應該期待他們的現(xiàn)代性倫理批判能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提供完整而切近的解釋。如何從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思想遺產出發(fā),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考世界歷史和革命實踐,依然是我們尚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現(xiàn)代性;倫理批判;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齊格蒙特·鮑曼;阿格妮絲·赫勒
作者簡介:張笑夷,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哈爾濱 15000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及其現(xiàn)實啟示研究”(21BZX109)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3.002
如果我們同意當代波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說法,那么人們即便對自己的文化不可避免地無知,以及滿足于對現(xiàn)代性的表面觀察,但要想從心中抹去對于我們生活的精神基礎和現(xiàn)代性的追問恐怕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很顯然,對于我們的文化為何如此的追問,過去任何時代從來沒有像20世紀那樣熱烈。似乎成為現(xiàn)代性的拷問者就是20世紀思想家的命運。無論是對人類文明總體性的和歷史性的省察,還是對特定時代的文化作構成性的分析和反思,20世紀的思想家總是通過識別和揭示我們自己生活時代文化的基本預設和現(xiàn)代性的基礎,來試圖認識我們自己,并給出他們認為必要的關于文明樣態(tài)和生活方式的出路。
作為20世紀思想家群體重要成員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同樣對現(xiàn)代性問題進行了持續(xù)的思考。蘇東劇變前后,盡管從馬克思主義演進來看,作為一種獨特的新馬克思主義類型和一個思想共同體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逐漸走向解體,但是,出走海外的部分理論家仍保持著旺盛的理論創(chuàng)造力。他們的哲學和理論不僅具有深刻的連續(xù)性,始終聚焦于20世紀人類經歷的深重歷史災難和現(xiàn)代性危機,而且在移居西方世界后,深厚的思想文化積淀、深刻的歷史創(chuàng)痛和嶄新的“他鄉(xiāng)”的現(xiàn)代性經驗進一步激發(fā)了思想活力,他們能相對自由又拉開距離地審視資本主義制度,在整個世界的變化中更為真切和徹底地思考現(xiàn)代性問題,從而使得一種有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屬性的現(xiàn)代性思想得到了系統(tǒng)的闡發(fā)和深刻的表達。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在英國完成了《經受無窮拷問的現(xiàn)代性》(1995)。先后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生活的匈牙利哲學家的阿格妮絲·赫勒出版了“歷史理論三部曲”,即《歷史理論》(1982)、《碎片化的歷史哲學》(1993)和《現(xiàn)代性理論》(1999)以及“ 道德理論三部曲”,即《一般倫理學》(1988)、《道德哲學》(1990)和《個性倫理學》(1996),這些著述共同構成了她對現(xiàn)代性的系統(tǒng)性思考。長期定居英國的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完成了現(xiàn)代性三部曲,即《立法者與闡釋者》(1987)、《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1989)和《現(xiàn)代性與矛盾性》(1993),又相繼出版了《后現(xiàn)代倫理學》(1993)、《生活在碎片中——后現(xiàn)代道德》(1995)、《后現(xiàn)代性及其缺憾》(1997)等一系列著作,更在新世紀以“流動的現(xiàn)代性”概念來探討現(xiàn)代生活的當代變遷。不難發(fā)現(xiàn),貫穿于這些從東歐走向世界的理論家著作核心的,便是對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后果的批判性思考。
一、現(xiàn)代性的悖論及其道德后果
當“人類20世紀的大屠殺經歷究竟意味著什么”“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究竟意味著什么”這些揮之不去的歷史謎題與對當代社會運動的持續(xù)的激進理論探索碰撞在一起時,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得出結論:“我相信,我們的文明的發(fā)展包含著證實其錯誤的論據(jù)。”①而“錯誤的論據(jù)”從根本上來說是抽象的理性邏輯不斷蠶食人的生活世界。盡管現(xiàn)代性邏輯的實踐樣式是多重的,但他們更傾向于在根本上將其理解為理性化的邏輯。人類無法忍受無序,在文化創(chuàng)造中尋求一種秩序或意義,以便使人類獲得安身之所和前行之力。現(xiàn)代性便是一種“建立秩序”的努力,而且將“建立秩序的任務”視為“其他一切任務的原型”②。然而,一旦工具理性成為唯一的標準,那么人也不得不面對成為工具的命運。現(xiàn)代性的悖論將產生出一個異化更為深重的世界。
(一)通過大屠殺的棱鏡思考現(xiàn)代性的理性化邏輯及其道德危機的社會生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較早地對大屠殺、集中營等歷史體驗和歷史災難進行自覺反思并揭示其現(xiàn)代性根源的理論家是漢娜·阿倫特。她關于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大屠殺所反映的現(xiàn)代道德困境和文化肌理的分析,對東歐理論家尤其是鮑曼和赫勒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鮑曼在2015年一次接受采訪中提到,“就我通過大屠殺的棱鏡得到的有關現(xiàn)代性的批判性靈感而言,我會說我受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的影響更多。她真正通過寫作分析了現(xiàn)代人的條件、極權主義的起源、大屠殺的根源等,并且將它們置于日常生活的層面加以闡述”③。鮑曼始終在理論和生活的相互滋養(yǎng)中不斷追問現(xiàn)代性的本質是什么,現(xiàn)代社會何以如此以及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等問題。相比于阿倫特對大屠殺和極權主義的反思提出的“平庸的惡”的思想,鮑曼則進一步思考了“平庸的惡”的根源,將之歸結為“理性的惡”。在鮑曼看來,盡管現(xiàn)代理性文明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然而卻是它的必要條件:“進一步說,我認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殺主張得以構思,緩慢而持續(xù)地發(fā)展,并最終得以實現(xiàn)的特定環(huán)境;它促使我們將社會視為管理的一個對象,視為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的一個集合,視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進’或者‘重塑’的一種‘性質’,視為‘社會工程’的一個合法目標,總的來說就是視為一個需要設計和用武力保持其設計形狀的花園(一種園藝形態(tài),將植物劃分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應當被刈除的雜草)。我還認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將它制度化的現(xiàn)代官僚體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殺之類的解決方案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發(fā)生的可能性。”①科拉科夫斯基稱這種現(xiàn)代性是“病態(tài)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所確立起來的“極權主義制度把人民視為國家機器上可以更換的部件,可以按照國家的需要被使用、拋棄或銷毀,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合理性的一個成果”②。
指出大屠殺是理性化邏輯和工具理性精神的后果并不是鮑曼等人的獨創(chuàng),在揭示現(xiàn)代官僚制度的組織形式基礎上,認清這種組織形式與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技術合謀如何成功地將道德變?yōu)椤八摺保瑢崿F(xiàn)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是鮑曼研究大屠殺的新意所在。如何使普通的德國人變成實施暴行的劊子手?為什么如我們一樣有愛妻、子女、朋友,有正常的喜怒哀樂的人一旦穿上制服就變成令人膽寒的殺人魔?在鮑曼看來,這是現(xiàn)代官僚制度的組織成就和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技術成就合謀的后果。現(xiàn)代社會被作為一種“園藝社會”(gardening society),一種被管理的社會,國家機器要想對其“控制”“掌握”并加以“改進”或“重塑”,管理設計的首要野心和目標便是“制定秩序”(order-making)。因此,這種官僚體系的第一原則便是組織紀律原則,上級命令高于一切,盡心盡責地執(zhí)行上級權威的命令成了組織中執(zhí)行者的信念,由此,現(xiàn)代管理體系得以運行并極力推行的紀律原則取代了道德責任。“惟有組織內的規(guī)則被作為正當性的源泉和保證,現(xiàn)在這已經變成最高的美德,從而否定個人良知的權威性。”③比如,在紐倫堡審判中,奧倫多夫解釋道:“我認為,我處的位置不是去判斷他的措施……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個軍人的事實,因此我只是龐大國家機器中一個相對微不足道的齒輪”④。現(xiàn)代性嚴厲的紀律約束使暴力通過享有合法性的命令而被賦予了權威,罪惡的行動成了例行公事,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個人的道德良知都受到抑制。
使道德保持緘默只是理性化趨勢導致的道德后果的一個方面。因為道德冷漠尚未完全泯滅個人的道德良知,個人還會面對自己所持的道德正當標準與行為的社會后果的不道德性之間的沖突。但是鮑曼進一步指出,為了實現(xiàn)有效的管理,消除執(zhí)行命令的行為過程中產生的道德選擇機會,現(xiàn)代官僚社會體系和現(xiàn)代技術還會通過“分隔”和“中介”原則來有意識地掩蓋行為的道德特征,使道德困境消失在視野之中。這種社會機制所造成的道德盲視則是理性化趨勢的另一個更為嚴重的道德后果。“行為與其后果之間的身體和(或)精神距離的增加超過了道德自抑發(fā)揮作用的程度;它抹殺了行為的道德意義,因而預先避免了個人所持的道德正當標準與行為的社會后果不道德性之間的一切沖突。”⑤現(xiàn)代社會使意圖和實際完成之間充滿了大量的復雜中介,不僅讓施暴者看不到他行為的結果,也讓受害者變得心理盲視,從而導致人類的道德災難。無論是道德冷漠還是道德盲視都是“一個有意設計、徹底控制、沒有沖突、秩序井然和和睦協(xié)調的社會的現(xiàn)代理想”⑥才會達到的趨勢。只要現(xiàn)代性的工具理性化和工程化趨勢不受控制或不被減緩,現(xiàn)代性的矛盾性被銷蝕,那么大屠殺就不會只是一次異常現(xiàn)象或功能失調,而是與這種現(xiàn)代性的趨勢如影隨形,是其合法性的內在組成部分。
(二)建立在個人生活經驗基礎上對現(xiàn)代性本質及其道德困境的“理智直覺”
當現(xiàn)代理性文明和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到科拉科夫斯基和鮑曼所說的披著合理性外衣的極權主義文化精神階段,“現(xiàn)代性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必然會成為反思現(xiàn)代性的一個核心問題。人們勢必要追問:現(xiàn)代社會運行機制背后的根本原則和基礎是什么?這種工具理性精神最初的推動力來自哪里?
赫勒從個體生命經驗出發(fā),將從阿倫特那里受到啟發(fā)的“人的境況”作為一個有待解釋的概念和現(xiàn)實,在此基礎上思考現(xiàn)代性的本質及其危機。在赫勒看來,人的生命是自我馴化的結果,自我馴化就是以社會規(guī)范替代了本能的規(guī)范,“當這一替代完成之后,‘人的境況’開始了,或用另一種方式說,在其抽象的不定性中,社會規(guī)范就是人的境況,因為它既規(guī)定了‘人的境況’的潛能,也規(guī)定了‘人的境況’的限度——也即人自身的潛能及其有限性”①。歷史地看,人的在世生活、人的不斷生成的過程就是具體地歷史地彌合內在方式和社會規(guī)范之間裂縫的過程。赫勒說:“無論人干了什么,他們必須彌合這一裂縫,并必須學會如何縫合這一裂縫,如此才能成為一個人。”
那么,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境況與傳統(tǒng)社會相比,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本質的變化?赫勒發(fā)現(xiàn),盡管現(xiàn)代人和傳統(tǒng)社會中的人一樣,有可能出生在任何社會、任何歷史時期與任何地域、種族和家庭,也就是說,都具有出生上的偶然性,但與傳統(tǒng)社會中人從一出生就有貫穿生命始終的預定目的相比,“現(xiàn)代人生來就是沒有終極目標的可能性集合”③。“被拋入自由中”,從出生到在世生存的雙重偶然性是現(xiàn)代男男女女們的基本生命體驗。因此,在赫勒看來,自由是現(xiàn)代人生存境況的本質特征,現(xiàn)代人的生活建立在自由這個普遍價值或觀念基礎之上。雖然現(xiàn)代人自由了,但自由這個終極基礎摧毀了一切普遍性的價值和觀念。自由也意味著虛無。相對于傳統(tǒng)社會而言,現(xiàn)代社會的道德結構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并仍處于變化之中。對現(xiàn)代這些尚未成為自為的道德主體的個人來說,不再有任何普遍價值或規(guī)范、觀念可以確立現(xiàn)代社會的秩序和現(xiàn)代人的確定性,道德的社會規(guī)則體系始終表現(xiàn)為外在于人的“義務”之網,加之其常常包括彼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規(guī)則,所以現(xiàn)代人在相互沖突的倫理中,總是陷入“我該如何生活”“如何做才是對的”這種道德困境之中。
波蘭的亞當·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也都揭示過作為自由一體兩面的道德空虛和道德困境。在前現(xiàn)代,人們相信神圣世界的存在,神圣世界賦予文化以意義,加固了文化的特性。神圣世界的存在恰恰肯定了人是自主的存在,肯定了他的可塑性和可完善性。現(xiàn)代世界張舉理性,否定神圣世界的存在。而如果沒有神圣世界的牽引和限制,人可能會迷失在意義世界的恣意汪洋中。此時,人相信自己是絕對自由的存在,是意義的完全創(chuàng)造者。他可以選擇創(chuàng)造任何一種意義,也可以選擇不去創(chuàng)造任何東西。無論在何種狀況下,人都深深地陷入虛無狀態(tài)之中。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講:“意義上的完全自由,完全避免來自傳統(tǒng)的壓力,意味著我置自己于空虛中,因為,非常簡單,意味著瓦解。”④“瓦解”也意味著善惡之界限的消失,因為,沒有神圣,惡將無法被識別并受到評判。一切將被允許。沙夫不僅認識到現(xiàn)代性進程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和規(guī)范體系的崩潰、社會的失范以及個體的“生存空虛”,還特別提出了與之相伴而生的政治異化乃至文化異化:“從一個特殊的觀點來看,政治異化是指個人與社會相異化;他拒絕行為規(guī)范中的某些價值觀隱喻,那些有關機構和社會政治行為的規(guī)范的行為規(guī)范……個人的異化可以進一步發(fā)展,超過界限,拒絕整個現(xiàn)有的規(guī)范價值體系,即用默頓的話來說,拒絕社會現(xiàn)有的整個文化結構。”①無論是通過放縱自我還是逃避現(xiàn)實的方式來完成拒絕,它們本質上都意味著將自己置于道德虛空之中。
在將自由理解為現(xiàn)代人的基本境況基礎上,赫勒進一步得出對現(xiàn)代性本質的一種判斷:自由是現(xiàn)代性的“始因”。“歐洲的自傳始于對自由的愛”②,并且自由最終取得了勝利,“自由成為了現(xiàn)代世界的基礎。它是沒有什么東西以它為基礎的基礎”③。自由不僅是現(xiàn)代世界的始基,還成了現(xiàn)代社會的最高價值。然而,自由作為一切的基礎也就意味著一切都失去了確定性和牢固的基礎。因為一切都可以以自由為由重新開始,重新確立自己的根據(jù),重新自我奠基。為了保障自由的實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宏大”敘事總是愿意追求諸如“必然性”“規(guī)律”“天意”之類的終極根據(jù)。在赫勒看來,這種或多或少是目的論的敘事在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世界方面是有益的,但它也問題重重。其中一個重要問題便是,自由如果是通過其自有規(guī)律或必然性實現(xiàn)的,那么我們每個人需要如何行動?如果一切都無法逃離必然性的藩籬,那么我們所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自由地行動,也就是說,為了實現(xiàn)自由我們需要放棄自由。這樣一來,現(xiàn)代性的“宏大”敘事以必然性的方式許諾了自由,同時也驅逐了自由。它始終無法解決“最高價值(自由)和相同價值(與其他相關價值的)本體論化之間的矛盾”④。赫勒認為,通過必然性達到自由之實現(xiàn)的理性必然傾向于追問、反思、制定最高的、普遍的道德律令,以此一勞永逸地指導和規(guī)范世俗生活。于是,理性的僭越必然導致道德危機。在這里,赫勒與科拉科夫斯基、鮑曼等東歐思想家殊途同歸,她通過對現(xiàn)代性的自由本質的分析,通過自由的悖論揭示了現(xiàn)代性走向其反面以及由此導致的道德后果。
二、邁向道德自主的后現(xiàn)代:從實踐上對現(xiàn)代性負責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現(xiàn)代性的激進拷問揭示了:道德與實用理性相分離是現(xiàn)代性文明取得的最蔚為壯觀的成就和最令人膽寒的罪行的基礎。于是,消除現(xiàn)代性困境的根本方法是如何使二者統(tǒng)一。換言之,“有沒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門檻,能讓邪惡的技術在跨越時戛然而止?”⑤他們身處現(xiàn)代性悖論之中,并在對此的自覺意識之上積極尋求可以對現(xiàn)代性負責的倫理學和道德生活策略。他們認為,我們每一個人仍然可以代表現(xiàn)代性并對它負責。赫勒提出,負責的辦法就是承認現(xiàn)代性的偶然性及其自由的悖論是我們的命運,是我們現(xiàn)時代的命運,而作為這樣一種現(xiàn)代性命運和個體命運的承擔者,我們“只能從實踐上對現(xiàn)代性(現(xiàn)在)進行合法化”⑥。
從實踐上使現(xiàn)代性合法化也就是從實踐上對現(xiàn)代性負責、對作為一切之根基和最高價值規(guī)范的自由負責。對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來說,這意味著道德和理性在人的內部結合為人有意識、有目的的對象化活動構成要素,從而使人的實踐活動走向積極的自由而不是其反面。赫勒認為,尋求一種對現(xiàn)代性及其自由本質負責的倫理學可以回到馬克思的思想遺產。在馬克思那里,自由不僅是總體的人的生命表現(xiàn)和自我實現(xiàn),而且是“作為內在的必然性、作為需要而存在”⑦。自由總是意味著人本身的內在生命需要。赫勒認為,“內在的需要”這種觀念使馬克思的自由概念預先設定了類與個人的統(tǒng)一。“內在的需要”意味著不存在任何外在權威,絕對沒有任何外在的權威決定人的行為和行動并凌駕于人之上。也就是說,人的絕對自主與作為一個整體的個人的絕對自主是一致的。因此,赫勒認為,雖然馬克思拒斥道德規(guī)范和原則,但馬克思對自由的這種解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道德公設”。自由在馬克思那里實際上成了內在于人自身的絕對道德律令,是人的全面發(fā)展和自我實現(xiàn)的目標本身。由此,赫勒進一步提出,作為最根本的價值原則和最高道德公設的積極的自由乃是“內在牽引”的結果,是人內在地決定朝向類個體的自我實現(xiàn)和全面發(fā)展。具體到現(xiàn)代性的人的境況之中,赫勒認為,盡管現(xiàn)代性的自由本質意味著現(xiàn)代人的偶然性命運和缺乏確定性,但同樣意味著現(xiàn)代人必須自我選擇和自我決定,“將偶然性轉換為決定性(determination)和自我決定性(self-determination),這恰好就是‘在一個獨特的世界中成長’的全部內涵”①。將偶然性的命運轉換為自我決定的積極自由和個體的自我實現(xiàn),這就意味著,作為“內在的需要”,在不受任何外在權威和義務壓迫的意義上,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是一種“良知的道德”“實踐理性的道德”。超越了任何外在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超越了任何外在的目的,這“并不意味著一個沒有道德的社會,而是意味著道德權威完全被置于‘內部’”②。這種觀點并不孤立。鮑曼也認為,在這個一切都處于流動狀態(tài)的獨特世界中,道德只有成為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倫理規(guī)范只有建基于人性之上,才不會使道德處于“漂浮”狀態(tài),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道德不在場的困境。他所提出的“無倫理的道德”意味著“將道德從人為創(chuàng)設的倫理規(guī)范的堅硬盔甲中釋放出來”③,使道德重新個人化,喚醒個人的道德沖動,使個人向道德自我回歸。因為在他看來,既然現(xiàn)代社會以外在的理性化的倫理規(guī)范取代了內在的非理性的道德沖動、以倫理法典取代了道德自我、以他治取代了自治,其道德后果是個體的道德沖動和道德責任處于休眠狀態(tài),那么將道德重新引入現(xiàn)代生活的關鍵就在于道德自我的出生。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道德是教化的還是自然的?在現(xiàn)代生活中這似乎不能成為一個問題。因為現(xiàn)代觀念早已把現(xiàn)代社會作為一種明確的道德化力量,把現(xiàn)代社會制度作為文明化的力量,把現(xiàn)代社會的理性統(tǒng)治作為人抵擋動物性的一道堤壩。然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并不認為社會是道德的,因為他們注意到現(xiàn)代社會早已成為一種使善惡中性化的機制和裝置,恰恰是這種社會使個體的道德良知和道德責任處于休眠之中,甚至使道德自我有被摧毀的風險。與一般認為的社會自我先于道德自我的觀念相反,他們傾向于把道德視為一種本真的生命沖動和良知,認為道德自我先于社會自我。因為以人與人的關系作為基礎的倫理性作為一種條件總是先在的,在邏輯上和認識論上都先于社會的干預和操縱。只要人們存在于世,無論愿意與否,都不得不與他人共享這個世界,并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相互關系。與他人共存這一人類基本的存在境遇首先意味著責任。鮑曼提出,自主的道德選擇從一開始就是人的基本存在樣式。“道德責任——在能與他者相處之前首先為他者考慮——是本我第一位的實在,是社會之起點而非社會產品。……它沒有‘根基’——沒有原因,沒有決定要素。”④同樣,赫勒在思考道德是如何產生的、人們依據(jù)什么進行選擇和判斷時也發(fā)現(xiàn),個人道德首先是受良心引導的,其次才是每個人必須與之打交道的倫理世界。她提出,當一個人在他所生存的特定世界中成長時,不僅他人(以各種倫理規(guī)則、要求、規(guī)范等名義)注視著他,他自己也在注視著自己。他會觀察自己做什么,他人做什么以及如何受良心引導走向這個倫理世界。或許,科拉科夫斯基在《沒有道德準則的倫理》一文中的講法更能清晰地說明問題。他說:“我們憑直覺就知道,我們對世界的接受是清楚明白的……我們接受這個世界所包含的一切……我們接受這個世界,接受它的苦難、殘酷、羞恥、痛苦和一切。除非我們徹底拋棄它,否則我們別無選擇。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就會把自己托付給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同時,“我們也就接受了這個世界的義務,將其視為我們自己的”①。
在鮑曼那里,道德自我有兩個構成性原則或規(guī)范,即“對他者的責任”和“自我限制”。它們不是社會外在地強加于人的倫理規(guī)范,而是人之為人的非理性的道德沖動的基本內涵。它們所規(guī)定的道德自我是人的基本存在樣式,是使人成為獨一無二的我的自我。“對他者的責任”是在不要求互惠的條件下關心他人,鮑曼將之視為個人道德沖動的覺醒。也就是說,一個人僅僅是出于自由個體的自我意志而負有對他者的責任。不要求互惠的條件下關心他人意味著道德責任是單項的、非對稱的。不過,“對他者的責任”本身具有一種二元矛盾,即“關心”和“強制”的辯證法。承擔責任既可以是自我犧牲地“關心”他人,也可能會按照其自身邏輯轉變?yōu)榻y(tǒng)治他人的“強制”。因此,鮑曼提出了“自我限制”來進一步規(guī)定這種非理性的道德責任,“不論追尋中的道德將會是其他什么樣子,首要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必須是一種自我限制的倫理學”②。“道德人的誕生,是這樣的自制:他/她是我的責任,而且只是我的責任。這就表明,我,只有我,應該為他/她的完整和幸福負責。”③鮑曼一再重申道德責任的本體論地位,把道德責任視為人權,規(guī)定為與個人最密不可分的私人性特征,并一再強調道德責任的存在不需任何保證也沒有任何理由,存在于任何保證之前、任何借口或赦免之后。
但個人道德沖動的覺醒和自我限制是如何可能的?畢竟通過大屠殺等歷史經歷,我們看到,“在一個理性與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tǒng)之內,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敗者”④。大多數(shù)人在陷入道德困境時往往做出選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選擇而置道德良知和道德責任于不顧。那么,是什么和如何使得人們在抗爭中堅守住人性?是什么使得鮑曼確信道德良知不會泯滅、道德責任乃是人性之根本?赫勒回答說,是“好人”。她正是從她父親的選擇和行為中看到了好人的力量和光芒。我們也可以在歷史上無數(shù)次的慘痛經歷中看到好人的存在。正是他們的抗爭,正是我們可以經驗到他們的存在才使良心和道德力量得以煥發(fā)出來。因此,赫勒把“好人存在——他們可以可能”作為對現(xiàn)代性負責的倫理學的核心問題。“如果沒有這一設定:起碼存在著一些‘好人’,那么無論怎樣,道德哲學的研究將無任何意義。無論人們是否相信規(guī)范是神圣的,或規(guī)范是由神圣的司法所授予的,或是否相信它們代表的是純粹的便利或習俗,規(guī)范和價值都不能視為是有效的,除非有人確證這些規(guī)范和價值。”⑤赫勒認為,對于想要問做什么是對的,想要有道德的生活的現(xiàn)代人,我們c4e0b08c34f7a0c25647990a7fad2280總會受良心引導沿著好人散發(fā)出的光亮走向倫理世界。從理論上講,這是人根據(jù)良知作出的關于存在的選擇。與其說她根據(jù)克爾凱郭爾的“存在的選擇”理念,將“好人”設定為人來自內部的、自己選擇的命運,不如說,她受“好人”引導,將之作為人自我決定和自我創(chuàng)造的“目的”。
可以看到,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設想的倫理世界是將人類的意義和價值重新安置于人自身和人的創(chuàng)造活動之中。這種“自我決定”和“自我限制”的倫理學強調人的自由本質和“自我決定”的命運,將個體的道德良知以及由此而來的為他人承擔絕對責任作為惟一倫理基礎,肯定承擔“為他者而在”的絕對責任就是“做真實的自己”。不過,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種道德實踐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的、充滿不確定性的、艱難的過程。誠如鮑曼所指出,“一旦人們開始努力使需求可以聽得到,以及一旦開始承擔責任,道德人的磨難便從此刻開始了。從此,人們只能在介入道德自我的危險航程的暗礁間航行”①。內在的道德責任不同于外在的契約義務,而且道德責任越大,越是將道德生活系于人自身,我們就會越覺得我們自己還不夠好。道德自我永遠不會達到它所指向的確定性,因為道德自我的困境無法通過其內在的矛盾性來克服。這是流動的現(xiàn)代性時代個體面對的唯一真實的生活,也是一種冒險的生活。但鮑曼認為,恰恰是這種矛盾性才能成為道德自我生成的土壤,只有在這種矛盾性中不斷尋求確定性,道德自我才能進入并保持道德狀態(tài)。因此,鮑曼多次提到,在一個恐懼、不安全感以及乏味的消費文化充斥的“液態(tài)”世界里,愛和友誼等這些人類紐帶顯得更為重要,且需要人們每時每刻將它們復活、重申、照料和呵護。因為生成道德自我和建構人類共同體的愛和友誼等這些人類紐帶是我們僅有的(社會的)“穿越湍急水流的護航者”。道德“它不是幸福的良方。它是艱難生活的法門。道德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它永無止境”②。同樣,赫勒之所以不是以“好”這個有待解釋的概念或任何相應的美德為標準,就是因為她清楚地知道,任何一種抽象概念或具有歷史局限性的倫理規(guī)則都不足以成為倫理生活的起點,而我們每個人的道德良心才會讓我們總與自身,與我們生活的世界(各種倫理規(guī)則、要求、規(guī)范等)保持距離,去作出何為道德的判斷。也正因為這種良知,“好人”才會被看見并成為內在牽引的普遍性規(guī)范。“好人”作為普遍性規(guī)范,不是一個完成的和完滿的結果或固定的德性和品質,選擇成為“好人”是選擇“做”“一個”好人,不斷地如此行動。“每個好人不只是一般詞義上的一個好人,而且是正在具體化的這樣或那樣的好人,這種具體化過程僅在死亡時刻才結束。”③
現(xiàn)在,讓我們再回到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有沒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門檻,能讓邪惡的技術在跨越時戛然而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東歐理論家的思考和回答:以良知和責任構建道德自我,不斷培育和生成道德個性,不斷邁向我們所是的道德主體。
三、對相關學術爭議的理論分析和回應
關于上述理論,學界近年來主要有兩點爭論:一是他們離開東歐并經歷蘇東劇變之后的作品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二是他們對現(xiàn)代性的倫理批判是一種現(xiàn)代性理論還是后現(xiàn)代性理論?對此,本文試圖作出分析和回應。
(一)對現(xiàn)代性的倫理批判可以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一種具體化
從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發(fā)展過程來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理論現(xiàn)象,即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經歷了走近馬克思主義、走進馬克思主義和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一開始,他們被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開始接受并信仰馬克思主義,致力于回到馬克思的思想并復興馬克思主義。但是,隨著他們經歷的東歐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的具體推進以及現(xiàn)代性的新發(fā)展,他們開始懷疑馬克思主義解釋框架的有效性,進而在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找或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理論框架來把握社會歷史現(xiàn)實。比如,赫勒在她理論生涯的早期是在盧卡奇的引導下走進馬克思的思想,逐步形成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即人通過對象化的創(chuàng)造活動來生產和再生產自身,并最終建立一個個體和共同體在其中得到自由和全面發(fā)展的美好世界。但這種觀念隨著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消失了。在東歐社會主義改革的希望破滅之后,按照她自己的說法,她很快便擺脫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嘗試在馬克思的解釋框架之外建立自己的激進理論。不過,問題在于,這是否意味著赫勒后來的現(xiàn)代性理論和倫理思想從根本上來說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答案是否定的。這種不連續(xù)性只是表象,掩蓋了馬克思主義在其整個思想行程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赫勒的理論工作存在著驚人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赫勒受馬克思啟發(fā)形成的人的觀念和人道主義價值理想始終是她的理論“前見”,構成她理解和把握現(xiàn)代性及其文化的結構基礎。“如果把赫勒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僅僅看作是她最終能夠從中解脫出來的某種形式障礙,那將是個錯誤……它為她的道德意圖提供了形式,也提供了方法……她是從馬克思的實踐介入的角度來理解哲學的。”
同樣的結論也適用于鮑曼。人們一般認為,鮑曼的學術生涯經歷五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階段、1970年初到1980年初的反思的社會主義烏托邦階段、1980年至1990年初的反思的現(xiàn)代性階段、1990年初到中期的后現(xiàn)代階段以及1998年以后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階段。就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而言,這里看似有兩次轉變:一是在第一階段走進馬克思,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闡發(fā);二是在第三階段告別馬克思主義。問題在于,這是否意味著他真的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不得不承認,鮑曼個人在東歐的親身經驗不可能不對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構成挑戰(zhàn)和沖擊。同時,其他一些思想家也影響了鮑曼。按照鮑曼自己的說法,這要歸功于葛蘭西。但是,鮑曼也明確肯定,他不是反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拋棄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他始終堅持著馬克思的原則和立場。在與凱茨·泰斯特的對話中,他明確指出,“我對多年來對馬克思思想的癡迷并不后悔。我從馬克思那里得到了學識,或者說受到他的激勵去發(fā)展我自己的認知和價值框架,我希望它們今天依然屬于我”②。在鮑曼看來,馬克思在改變世界的理論探索中,將認識論轉變?yōu)榱松鐣W。③因此,鮑曼將歷史唯物主義視為一種“元社會學”(meta-sociology),并認為社會學就是要探求和給予世界一個方向。鮑曼的倫理道德理論不僅分析現(xiàn)代社會的道德狀況和道德狀況的現(xiàn)代性社會機制的根源,還一直將道德的社會學理論作為人的自我發(fā)展和自我實現(xiàn)的一項“內部”工作,作為與重建人類生活意義和文化精神相統(tǒng)一的工作。
同樣是享譽世界又根植于馬克思思想傳統(tǒng)并具有鮮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印記的理論家,科拉科夫斯基曾明確宣稱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以至于人們認為他之后的理論是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但仔細辨析一下,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所放棄的馬克思主義是他所判斷的已經從“普羅米修斯式的人道主義”轉變?yōu)榻┗慕虠l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從未否認過根植于馬克思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價值立場和批判精神。正如弗蘭尼茨基所說,“這些知識分子把波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到本國疆界之外,并成為國際馬克思主義就當今世界十分關鍵和困難的問題進行對話的真正伙伴”④。在對現(xiàn)代性的分析中,科拉科夫斯基認為,現(xiàn)代性危機表現(xiàn)為“禁忌的消失”,更深層來看是人類失去了道德紐帶。盡管科拉科夫斯基清醒地知道通過恢復道德力量來推動現(xiàn)代文明的自我防衛(wèi)、自我調整和自我治愈是艱難的,但他仍然認為只有通過道德個體擔負起責任的行為才能使人類連接在一起。
因此可以看出,蘇東劇變后,以科拉科夫斯基、鮑曼和赫勒為代表的東歐理論家沒有完全否認馬克思的學說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價值。相反,他們仍然堅守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價值遺產,并試圖在新的理論形態(tài)中將其具體化。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并非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需要在新的人類實踐活動中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具體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在這個意義上,這些來自東歐的理論家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就其思想特質而言,與馬克思的理論傳統(tǒng)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其中貫穿的精神內核是具有深刻連續(xù)性的馬克思式的道德愿景和人道主義的價值取向。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理論追求和核心思想,即將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具體化為批判的社會理論,以便使異化的、物化的世界轉變?yōu)槿说氖澜纭LK東劇變后,盡管這些理論家所涉及的內容和主題有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性,但從根本上來說,他們繼續(xù)致力于探尋的對現(xiàn)代性負責的倫理學,以個體的自由發(fā)展為理論旨歸,以個體不斷的自我超越為實踐基礎,符合馬克思思想的徹底批判精神和人道主義價值立場。這種立足于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義實質,從實踐理性(良知)出發(fā)建構的倫理學,其核心要義是給“規(guī)范”一個“世界”,即將馬克思的思想視為一種最徹底的人道主義,把馬克思關于人是自由的存在、自由是個體的生成和全面發(fā)展的倫理規(guī)范“內化”為人的對象化活動的可能性,由此,以馬克思的“徹底的人道主義”為價值規(guī)范建構起來的倫理學呈現(xiàn)的便是一條不斷探索建構于道德個體生成基礎之上的人類自由的生存之路。通過把馬克思在哲學層面建立的“規(guī)范”內化為人的“激進需要”,使哲學達到改變世界的目的,使世界成為合乎人性的家園。他們的倫理批判不是主要從倫理層面來思考個人的行為方式和思考如何成就好的生活的倫理學,而是從對人的生命意義和自由價值的捍衛(wèi),從對世界和他人負責的高度來理論地呈現(xiàn)個體的人和人的歷史的真正生成。
(二)對現(xiàn)代性的倫理批判本質上還是一種現(xiàn)代性理論
不少學者認為,蘇東劇變后,這些來自東歐的理論家的作品是一種后現(xiàn)代理論。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鮑曼和赫勒在不同的場合都使用了“后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主義”這樣的詞匯。比如,赫勒在與丈夫費赫爾合著的《后現(xiàn)代政治狀況》的書名便用的是“后現(xiàn)代”。鮑曼所著的《后現(xiàn)代倫理學》《生活在碎片中——后現(xiàn)代道德》《后現(xiàn)代性及其缺憾》用的也都是“后現(xiàn)代”。二是鮑曼和赫勒確實引入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資源,從后現(xiàn)代的視角對人的道德救贖作了闡釋。也就是說,他們的理論視角與利奧塔、波德里亞等典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有著一致之處。
使用“后現(xiàn)代”這樣的詞匯并不表明他們的思想是“后現(xiàn)代”的。鮑曼和赫勒深知這一概念的混亂與模糊,因此他們在使用時予以了明確的界定。鮑曼提出,“‘后’不是在‘按時代順序排列’意義上的‘后’”①,而是“現(xiàn)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毀譽、自我拆除的階段”②。同樣,在赫勒看來,“后現(xiàn)代性并不是在現(xiàn)代性之后到來的一個階段,它不是對現(xiàn)代性的補救——它是現(xiàn)代的。更確切地說,后現(xiàn)代視角也許最好被描述為現(xiàn)代性意識本身的自我反思”③。可以說,把“現(xiàn)在”理解為現(xiàn)代性歷史中的一個新階段是鮑曼和赫勒反思現(xiàn)代性的認識論前提。他們都認為,我們所經歷的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和多元化的社會仍是現(xiàn)代的,現(xiàn)代性遠未結束,“使得21世紀的社會和20世紀的社會同樣現(xiàn)代的,是那些將現(xiàn)代性和所有其他的人類共存的歷史形態(tài)分開的東西:是強迫性的、使人著迷的、連續(xù)不斷的、永不停息的、永遠沒完沒了的現(xiàn)代化(modernization);是對創(chuàng)造性的毀滅和破壞……的壓倒一切的、根深蒂固的和無法遏制的渴望”④。當然,我們的時代有自己的現(xiàn)代性,它由一種穩(wěn)定的、有序的結構已經發(fā)展為一種流動的、不穩(wěn)定的形式,而這種流動的現(xiàn)代性從20世紀60年末就開始了,至今一直存在著。鮑曼使用“后現(xiàn)代性”“流動的現(xiàn)代性”等概念只不過是在描述處于轉型中的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赫勒用“在車站上生活”的隱喻闡釋我們生存狀態(tài)的這種流動性。通過對現(xiàn)代性的自我反思,鮑曼和赫勒的理論工作是試圖移走阻礙啟蒙價值(自由、平等、正義)實現(xiàn)的障礙,使現(xiàn)代性還沒有實現(xiàn)的本質和價值真正實現(xiàn)出來。
鮑曼與赫勒的后現(xiàn)代視角與典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有著本質的區(qū)別,不能貼標簽似地將他們的思想標定為“后現(xiàn)代”的。對于赫勒來說,典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是對現(xiàn)代性的激進反叛,是“天真的后現(xiàn)代主義”。它將傳統(tǒng)甚至合理的價值和規(guī)范徹底拋在了垃圾堆里,弘揚一種“越壞越好”的哲學范式。它要么自行其是,要么轉向犬儒主義。雖然赫勒的后現(xiàn)代視角與“天真的后現(xiàn)代主義”都基于自由,都拒斥基礎主義的宏大敘事,但她既要堅持普遍價值,給規(guī)范一個世界,又要努力堅持對文化多元化的認識,使人們認清自身的境況,自我決定以自己的方式成為創(chuàng)造最好道德世界的一分子。同樣,對于鮑曼來說,身處“后現(xiàn)代棲息地”是我們在轉型中的現(xiàn)代社會無法忽視的境況。他進入這塊棲息地,調用后結構主義的理論資源,但他卻不能歸屬其中。因為某些典型的后現(xiàn)代作者倡導的“怎么都行”最終導致了一種無政府主義。他贊同自由和平等這樣的價值和規(guī)范是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但也認為這些價值和規(guī)范的實現(xiàn)動力來自于個體的道德沖動。與赫勒一樣,他的理論工作是要對這兩個方面加以綜合,讓后現(xiàn)代棲息地的居民們自由地創(chuàng)造出有意義的生活。
因此,在對現(xiàn)代性進行反思的過程中,鮑曼和赫勒對傳統(tǒng)歷史宏大敘事展開了激進批判。他意識到也希望同時代的現(xiàn)代人意識到,建立在理性同一性邏輯之上的強制性倫理規(guī)范無法成為現(xiàn)7fa47d8575ac3d4f12e4d63bfc10c6b0821f5bd2a71238a0be37a4038834d0ec代人道德生活的真理。我們要懷疑任何確定性或許諾。因為每個個人的道德生活不再有任何保證、任何終極的且是不容置疑的價值。真理只能是具體的,與每個偶然的個人相連。雖然歷史不再是絕對精神或超級主體的歷史,而是生活于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之中的個體的歷史。真理不再是普遍的、永恒的大寫的目的,而是與人的偶然性生存和選擇相連的個體的、具體的真理。然而,一切固定的東西的缺乏恰恰是個體自由和社會自治的條件。自由成了一切基礎的基礎意味著個體進行道德選擇和承擔道德責任的絕對性。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時代,個體的良知與責任便成了走出現(xiàn)代性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因此,從理論的文化精神來看,鮑曼和赫勒的倫理批判是一種對現(xiàn)代性文化的自我反思。他們所要建立的新的倫理學是要穿越抽象的道德哲學,達到具體的道德理論,將現(xiàn)代性從實踐上合法化實際上就是追問個體如何在碎片化時代保持完整,如何尋求全球化時代全人類范圍內文化精神的統(tǒng)一。
結語:一點延伸的思考
其實,赫勒從寫作《日常生活》(1970)以來就始終認為,生產力的發(fā)展能帶來社會結構的變革,但不一定能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激進需要同樣也是變革社會的物質力量。從《日常生活》開始,直到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理論和倫理思想的完成,赫勒一直把作為激進需要的集體的道德精神和每個人的道德個性生成視為整體社會變革的內在組成部分,強調生活方式革命將是新的社會革命和實踐。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赫勒和鮑曼一樣,自覺肩負著獻身于實現(xiàn)人類利益?zhèn)ゴ笫聵I(yè)的“道德使命”,鮑曼更是提出,“社會思想就是有關人道的”①,他們的目標是讓人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潛能和道德良知,讓人們對自己的選擇標準、選擇行為及其后果有更多的認識。而他們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創(chuàng)造秩序和意義,為人們自主地作出選擇提供可能性及其合法性的論證。
但是,如果我們跳出對他們理論內容的具體闡釋和理論性質的分析,對這樣的現(xiàn)代性理論進行自我反思,那么不可避免地會提出下列問題:“道德”究竟是現(xiàn)代性危機的“癥候”之一,還是把握現(xiàn)代社會辯證運動的“總體”?“道德”“倫理”“自我決定”這類字眼和主題會不會掩蓋了更重要也更危急的問題?重建道德世界和道德個體固然是人內在地超越現(xiàn)代性矛盾的實踐方案,但對剝削和導致不平等不自由的確切機制和本質缺乏認識,是不是說明他們已經離開了馬克思思想的堅實土地?如果他們建構的旨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進而改變世界的倫理學使文化革命與政治的和經濟的革命脫離開來,如果這種倫理學使人及其歷史的生成變成了充滿不確定性和脆弱性的漫長的事業(yè),那么,革命和進化的界限將消失,這樣設想出來的整體實踐方案是否還有意義?
我們必須認識到,就思想范式而言,以鮑曼和赫勒為代表,這些來自東歐的理論家構建的倫理學是對總體性原則的一種實踐。他們將人類的道德生活作為從整體上包含和表現(xiàn)全部社會生活的一個具體層次,在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中對人類的倫理規(guī)范和道德生活做歷史的、辯證的理解,更在道德問題與現(xiàn)代社會運行機制和現(xiàn)代性文明危機的深刻關聯(lián)中研究作為整體的道德問題,同時通過對現(xiàn)代倫理道德的重建推動現(xiàn)代性理性文明的重塑。但是,這種總體性的理論實踐提供的方案只是具體總體性實踐或革命的一個層次或方面,而且,正因為人是理性的存在,革命性變革才不能只寄希望于內在的道德個性的生成和向存在的躍遷。
因此,盡管他們反思現(xiàn)代性的理論范式依然對我們有很大啟發(fā),他們的思想主張也會對人類歷史命運和每個個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但我們顯然不應該期待他們的現(xiàn)代性倫理批判理論能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提供完整而切近的解釋。如何從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思想遺產出發(fā),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考世界歷史和革命實踐,依然是我們尚待解決的問題。
[責任編輯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