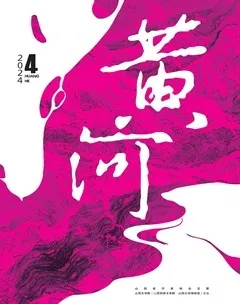鄉村文學和鄉村藝術家絕唱
鄉村作為一個千百年來最為主要的社會生活舞臺,今天已然變得有些陌生,但反映它的文學作品仍然相對平穩地出現在我們的期刊與出版物上。我們今天讀鄉村文學,除了領略正在發生的故事,還有更多對往昔的追憶。
《黃河》雜志本期編發的兩篇優秀作品———也可以說是兩篇帶有較強非虛構色彩的小說《河灣人杰》和《向一支桔色鉛筆懺悔》———就帶有這種強烈的追憶印記。作者韓振遠、舟山,一位已退休,一位邁向退休,他們當然還有很多精力,但相對于那些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作家,這種精力已經不能說是旺盛了。而隨著韓振遠、舟山這樣一批鄉村藝術家退隱和息筆,我們對鄉村之余韻———鄉村文學———這一曾經輝煌的藝術形式可能沒有新的期待了。正因為如此,在看到這樣兩位鄉村藝術家所集中火力寫出的關于已經消失的鄉村的作品時,我心中誕生了博爾赫斯作品《永生》里出現的那種因為訣別而帶來的分外惋惜又夾雜難以置信的幸福的情緒:“他們的每一舉動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張臉龐都會像夢中所見那樣模糊消失。……一切都有無法挽回、覆水難收的意味。”
我們不能認為《黃河》雜志只是出于巧合而刊登這兩篇分別描述晉南、贛北鄉村景觀的小說。《河灣人杰》可能不敢說是關于人類農村的史詩、中國農村的史詩,但放膽去說山西農村、晉南農村的史詩是有余的。因為它以較高的水準清晰交代了河灣村三位五十年代末出生的船工后代上學、救人、訂報、轉學、畢業、參軍、讀大學、留守、說親、結婚、就業、創業的歷程,描繪了他們在時代的變遷中(主要是面對榮耀與財富的沖擊),如何扭曲,如何堅守(或退縮),如何欣慰,如何悲愴。當他們逐漸老去,那個浸入他們血液、給他們帶去福利與災禍的黃河仍在不息前行。“范熱內普在其經典之作《過渡禮儀》中指出,個人和群體在時間、空間、社會地位乃至精神世界上都頻繁經歷著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過渡……不同文化群體為確保上述過渡的順利進行從而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行為方式,是為過渡禮儀;它包括分隔禮儀、邊緣禮儀和聚合禮儀三種類型或階段”(歐陽曉莉研讀《吉爾伽美什》語),我們也可以認為,韓振遠小說《河灣人杰》是對河沿子子弟從一年齡到另一年齡、一職業到另一職業、一地域到另一地域、一境況到另一境況之變遷所經歷的禮儀(包括融入前、融入中、融入后)的集中書寫。這其中不僅包括待客、成人、訂婚、開業所應盡的人情義務,也包括富則分發電視、窘則以死償債等即興之舉。甚至可以說,自河南濟源逃荒至河沿子的侯三(主人公學儀之父)逢人遞笑也可被視為一種融入新環境的禮儀(在這里,一個人處于“個人與群體、少數與多數、分支與主流”的邊緣位置):“他(學儀)說他看不慣侯三那么對人笑,說他爹好像誰都討好,誰都奉承,又賊眉鼠眼,好像對誰都心懷鬼胎,電影里漢奸狗腿子才那么笑。”而《向一支桔色鉛筆懺悔》則緊盯物質匱乏年代某一細節。鉛筆在今天,從經濟層面上說,完全被我們看不上(僅我書房就有70余支,往往寫到手握不太住就扔掉),在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作者舟山那里,卻是童年里一件極其金貴和龐大的事物。在當時的等價交換表里,它抵得八分錢,一個多雞蛋,加上削筆刀,等于家中僅有的兩個雞蛋,等于招待從鄰縣跋涉三四十里山路來做客的舅公的唯一葷腥,等于家長們對孩子存在價值的無情判決。殘忍的是,這樣的事在小說敘事者身上發生了三次———仿佛這事越不允許發生,主人公就越是因馬虎而使之發生,或者不馬虎,而命運的神總是讓他在漏洞面前防不勝防(有一次是真的具象的漏洞:老鼠把用來做書包的雨布袋咬了一個正好讓鉛筆掉落的花生米大的細洞)———分別丟失的是一支火紅色的鉛筆、一支草綠色的鉛筆和一支深藍色的鉛筆,并且是在一個月內發生。小孩即使丟失的只是雞毛蒜皮的事物,也容易被父母和自己夸張若干倍視之,容易篩糠戰栗。何況鉛筆在那時并非什么雞毛蒜皮之物。同時,即使丟失鉛筆這樣一件大事得到大人的原諒,也因為無法及時補充而使得主人公在學校的學業幾乎得不到開展。巨大的惶恐和失落使得敘述者走向撿別人掉的鉛筆、求助、借用、自制的道路。當他發現人們并不擁有多余的這一資源,也沒見誰在他面前遺失這一資源,甚至是匱乏、只好用舊電池內的碳棒充抵(雖然一端削尖,但它寫出的字仍然像“沙子地上曬死的蚯蚓一樣彎彎曲曲”),同時自制的產品也歸于失敗時,終于在一位同學對它疏于防范時將之盜走。“忽然,我眼睛一亮,看見在一戶人家的大門口的石墩上擺開了一本書,書的中間躺了一支金子一樣閃光的鉛筆。……這時我沒有任何辦法控制我不去拿起這支鉛筆……”失竊者險些因此輟學,而另一名同學因為被誤斷為盜竊者而失學。事情可謂嚴重。《黃河》雜志正好從兩個維度———一個宏觀、一個微觀———為我們共同經歷過的鄉村生活提供了兩份看起來就要晚了但實際恰當其時的證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壓軸之作)。并且,我們不能認為二者各有偏廢,一個失之闊大,一個失之狹小。因為我們在有史詩野心的小說里不僅看到它對時代變遷的大寫意,也看到它在具體而微的細節里精心耕耘,我們在朝深處詳挖的小說里不僅看到它對塵埃之事的雕琢,也看到它在嘗試用偉岸的姿態面向自己軟弱而顫栗的心靈。而且,可以說,《黃河》把二者編發在一起,使得它們相得益彰、價值翻倍。
兩篇小說讓人覺得成功之處在于它們用文字復現了人們經歷過的真實。而真實———特別是能傳遞到讀者心里的真實,讓讀者嘆服“就是這回事”“就是它”———是使得事物永恒的保證。法捷耶夫在評價《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提到:“它不是自始至終都有著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所非常需要的‘立體感’,也就是空間的感覺。應當善于在每一個情節中借助于某些筆觸暗示出當時人們所處的環境,周圍的事物———自然景色、物件、光線的明暗、人們和事物之間以及人們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你都描寫得不夠;有時甚至叫人感到:人物似乎是在與外界沒有聯系的空間中行動。當執筆寫作時———根據自己的經驗,我很了解這種情況———常常很少注意到事件是在一間什么樣的房子里(大的、小的)和在什么天氣下(陰天還是晴天)發生的,這時的天空是高、是低,接不接近山頭,事件中的人物誰坐在椅子上,誰又站著,以及其他等等。”而這樣的“立體感”正是本期兩篇小說所不缺乏的。讓我們看看韓振遠對童年的兩截記憶:一、“每天午后,趁大人昏昏欲睡,我與學儀、敬文相約來到河灣,站在河岸崖上,高舉雙臂,猛蹬雙腿,在空中躍出個拋物線跳下,砸在平靜的水面,啪一聲,水花四濺,皮膚生痛。泥漿泛上來,一圈圈往外漾。河灣對面,一只白老等受到驚嚇,再也顧不得優雅,慌忙扇動翅膀,噗塌塌,噗塌塌,將被泥沙淤沒半截的細腿往出拔,好生狼狽,費好大勁也飛不起來,翅膀扇動得更急,河水被扇起波紋,好容易將腿拔出來,呼呼飛上天空,看上去又那么從容優雅。三個家伙拍著水面笑,原來,白老等的高貴是裝出來的,受到驚嚇一樣慌亂。三個家伙下河,從來一絲不掛,光溜溜入水,光溜溜在水中嬉鬧,玩夠了,光溜溜上來,邁開細腿,裸露出豆芽般的小鳥鳥,爬上河邊那道斜坡,走在村前小路上。一天,剛到村口,學儀不走了,將手里的短褲抖開,急急穿上,又搓搓手,抹臉上的泥沙。我看見女同學曉燕甩著小辮在遠處一閃,也不自覺地捂胯間。學儀往手心吐唾沫,抹頭發。我和敬文也知道男女大防,不再光屁股在村里跑。那時候,我們十一歲,上小學三年級。”二、“有幾天,我和學儀每天都被留下背書。學儀背書姿態和我不同,我背不下去時,低下頭,抓耳撓腮,實在想不起,氣也喘不勻,只好停下。學儀背不下去時,頭反倒仰起,瞇上眼,并不停止,不斷重復一句話,像一波接一波流水沖擊渠閘,有時候驟然沖開,滔滔奔涌,有時候怎么也沖不開,只能反反復復接著沖。”像這樣讓人感覺活靈活現、讀起來如癡如醉的片段在小說前半段比比皆是。它使我們想起昂托旺父子對普魯斯特的高尚評價,認為他的偉大價值在于去好好地生活,又好好地用文字把生活復活。后半段的敘述好像弱了些。如果我們只是獨立看后半段,會覺得它精彩異常,但因為前半段的存在過于登峰造極,因而后半段一下變得晦暗起來。我想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童年,三個人———學儀、敬文、敬遠(敘述者)———長期生活在一起,水乳交融、彼我不分,就像是一個人,或者說即使是一個人,也兼容了其他二人,所以對別人的描寫就像是在描寫自己。沒有不熟悉的。而在成人之后,三人從地理、職業、行動上常年隔離,來往多半靠不及時的飲酒敘舊維系,已經失去了從深處感知和理解的自然條件。更何況,在后半段,側重的是敘述者之外的人,可以說是陌生人的學儀。
舟山《向一支桔色鉛筆懺悔》同樣貢獻了精彩紛呈的真實細節。這位作者我見過,在路上他展示了自己能背誦魯迅文章的能力。他的用詞———特別是動詞———頗有魯迅一擊即中的遺風。另外,他也展示出自己利用想象來呈現真實的功力,比如:“晚上我不停地做夢,一時夢見就在皂角樹小學的操場上空,漫天的五顏六色鉛筆不停地往下掉。我一伸手抓,它就像泥鰍一樣滑溜了。又一時夢見外婆到我家來,提著一竹籃子鉛筆,花花綠綠的,一時又變成隱隱約約的發著白光的小火箭,小飛船,小衛星。我迷迷糊糊地說,我不要火箭、不要飛船……我只要鉛筆。”這樣恣意的想象過去我在莫言《四十一炮》里也見過,羅小通幻聽到肉對自己說:“如果你不來吃我們,就不知道什么卑俗的人來吃我們了……這個世界上,像您這樣愛肉、懂肉、喜歡肉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啊。羅小通,親愛的羅小通,您是愛肉的人,也是我們肉的愛人。我們熱愛你,你來吃我們吧……你不知道,天下的肉都在盼望著你啊,天下的肉在心儀著你啊,你是天下肉的愛人啊……”另外,此文勝在自始至終都在克制,沒有讓視覺逾越出一個孩子的范疇,因此我們得到的惶恐是一個孩子貨真價實的惶恐,得到的失落是一個孩子真金白銀的失落,我們仿佛被一個小孩附體,和他一樣臉憋得通紅,和他一樣悔恨、逃避,感到自己造孽。
感謝兩位作者,他們沒有對自己經歷過的生活表達出厭惡和控訴,也不去頌揚。他們對它們做到盡可能的理解和尊重。在此,謹向所有堅持寫作的鄉村藝術家表達最深重的敬意(我自己也是這其中之一啊)。
【作者簡介】阿乙,本名艾國柱,1976年生于江西省瑞昌市,曾任職鄉村民警和報社體育編輯,出版有《鳥,看見我了》《灰故事》等四部小說集及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早上九點叫醒我》《未婚妻》。曾獲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等十余獎項。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意、西等語種在十余國家出版。
責任編輯:曹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