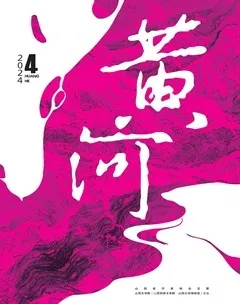鄉情、傳統與遺產:解碼《我們這代人》的三重進路
代際意識作為現代意識的一種,強調作為“當前一代”的“我們”承前啟后,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慷慨激昂,指點江山。在現實的生活中,每一代人的代際意識無一例外都會經歷三個階段:青春時期的意氣風發;中年時期的躊躇滿志;后中年時期的意猶未盡或余味無窮。文波的小說《我們這代人》(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1月版)著力刻畫了1960年代生人的奮斗歷程,講述了父輩們的快意恩仇,并且回望了祖輩們的滄桑往事,由此,“我們”這代人的故事與父輩們、祖輩們的故事重疊起來,營造出厚重的歷史感。本文從鄉情、傳統和遺產三重進路入手,對《我們這代人》的基本符碼予以解讀和闡發。
鄉情
小說之為小說,首先在于其虛構性,其次才是藝術性。虛構緣于想象,任何想象都有一定的現實基礎,現實主義小說是如此,現代主義小說是如此,后現代主義小說也是如此。越是富有虛構性和想象力的小說,越能激發讀者的好奇和聯想:這是可能的嗎?這是哪里的事情,哪些人的事情?或許,正是為了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小說作者的想象力越來越發達;正是為了挑戰讀者的聯想力,小說作品的虛構性越來越離奇。當然,也有一類作者對讀者的好奇心不以為意,有一類小說無意挑戰讀者的聯想力。文波就屬于這一類作者,《我們這代人》就屬于這一類小說。
當代的讀者反應批評理論注重考察作家對其作品的讀者所持的態度和要求,探究不同文學文本所意指的不同讀者類型,發掘現實讀者在確定文學意義上所起的作用,研究閱讀習慣和文本闡述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讀者在“作者—作品—讀者”關系網絡中的地位。作為業余作家,文波寫作《我們這代人》,對“虛構讀者”和“理想讀者”之類的專業批評術語可能不甚了了,但小說一經出版、投放到市場上,他對“意向讀者”應當會予以反思,對“現實讀者”應當會有所判斷,對“內行讀者”不能不有所期待。
基于專業批評和市場營銷的角度,需要考慮《我們這代人》的“虛構讀者”和“理想讀者”。“虛構讀者”概念旨在為現實讀者提供“標準讀者”的楷模,使其依據文本的內在要求而自我調整。“理想讀者”概念是由作者或批評家根據文學作品的預期效果得以實現而設想出來的讀者類型,用堯斯的話來說就是:“理想讀者不僅具備我們今天可及的一切有關文學史的知識,還能夠有意識地記錄全部審美現象,并反過來印證文本的效果和結構。”①閱讀《我們這代人》時,作為外在的讀者的我們不能不猜想文本內在的讀者亦即“虛構讀者”,這個讀者隨著文波寫作的過程而不斷成長,隨著寫作的完成而將自己凝固在作品之中。在“虛構讀者”定型之時,“理想讀者”脫穎而出,并處于不斷的生成和再生之中。
而“意向讀者”概念反映的是作者對讀者的期待,文波寫作《我們這代人》,毫無疑問,“意向讀者”首先指向1960年代生人,文波作為“我們這代人”中的一員講述“我們這代人”的故事,有望推動“我們這代人”的內部對話。這樣的一種內部對話,并不排斥年長的一代或年輕的一代,而是期待乃至渴望他們的傾聽。就此而言,《我們這代人》的“意向讀者”有著跨代際的指向。進而言之,《我們這代人》反映的主要是生活在并西也就是山西,且具有廠礦和機關經驗的人們的故事,“山西”“廠礦”“機關”“社會”也就成為吸引“現實讀者”的四個要素。“現實讀者”概念旨在根據實際閱讀作品并做出反應的讀者,揭示他們各自的社會規范和趣味。就《我們這代人》而言,“山西”“廠礦”“機關”“社會”四個要素中的任意一個,或任意兩個、三個的組合,或四個要素同時具備,生成“現實讀者”的不同類型。至于“內行讀者”,通常指的是有文學鑒賞能力的讀者,他們有能力將文本鞭辟入里、融會貫通。就《我們這代人》的“內行讀者”而言,除了文學專業特別是小說批評行當的人士外,還應當包括對山西的歷史、地理、社會、民俗有所了解乃至無所不曉的人士,對廠礦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對政府機關特別是省級機關的情況輕車熟道的人士。
“意向讀者”“現實讀者”“內行讀者”中,“山西”不可或缺乃至鰲頭獨占,這就提示我們,在考察《我們這代人》的讀者情況時,緣于山西的鄉情是至關重要的要素。作家、批評家劉醒龍為《我們這代人》作序時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這代人》看似情節簡單,繼承‘山藥蛋派’‘講故事’的傳統,其實是有一定閱讀難度和‘陷阱’的。”《我們這代人》在何種意義、何種程度上繼承了“山藥蛋派”“講故事”的傳統,有待深入細致的分析,不過,緣于山西的鄉情的確是它的一大基礎,應當作為我們解讀《我們這代人》的首要符碼。
小說伊始,“胡春來開著奧迪車,離開原太市向北飛駛”,這是黃昏時分。當晚八點,胡春來在老家平原縣找了一個小旅店住下,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半夜三點就退了房,向同州市進發。山西老鄉或者對山西地理有所了解的讀者,很容易在語言中尋到原型,“原太”即太原,“平原”即原平,“同州”即大同。小說中的地名在現實的地圖上有了著落,讀者頭腦中的畫面感自然活靈活現起來,故事也就成為發生在我們自己或周邊人身上的事情,感覺熟悉而親切,期待也就愈發現實起來。
胡春來經常陪妻子薛桂花去河東,“河東在并西省的南部”。運城市古稱“河東”,讀者由此獲得充分的自信,“并西”即山西。胡春來不大喜歡河東人,覺得他們總是自我感覺良好,“喝個酒也喜歡繞來繞去,以顯示自己的學識”,相反,他喜歡同州人“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直來直去”。河東人稱同州人為“北路人”,同州人叫并西省南部的人為“南縣人”,河東人屬于此列。胡春來不大喜歡河東人,但對自己和關公是老鄉津津樂道,他從小就崇拜關公,在外地出差時每每對不了解關公家世的人不厭其煩地解釋:“關公,山西運城解州人,世界上最大、煙火最盛的關帝廟就位運城解州。”初到同州的胡春來從夏縣訂了一尊關公銅像,送給裴七龍以聯絡感情,并且,特意拎了一箱聞喜煮餅。“運城解州”和“聞喜”的出現,使得小說具有了寫實的意味。胡春來初次拜訪裴七龍,帶了關公銅像和聞喜煮餅,就是“想喚起七龍的這份感覺,拉近彼此的距離”,于讀者而言,這喚起了山西老鄉特別是晉南老鄉的濃濃鄉情。
鄉情是具體的,是和具體的人物、地點聯系在一起的。閱讀《我們這代人》,胡春來的江湖義氣,羅躍強的鄉土情結,李春梅的質樸純真,衛蕊花的脫胎換骨,矬三的憨厚老實,七龍的復雜面相,還有諸多人物的性格特點,都具體而實在地呈現出鄉情,并在鄉情的氛圍中得以構型。胡春來是平原人,羅躍強是河東人,兩人在對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或者是自己缺乏且冀求的,或者是自己欣賞卻又疏離的。“羅躍強自1986年從安西市調回原太市,胡春來對他一直特別關照。”用“調回”而非“調入”或“調到”,表達的就是對于并西省的鄉土之情。
鄉情是廣泛的。《我們這代人》大體上可以分為上、下兩部分。一到十八章為上半部,胡春來是顯而易見的主角;十九到四十二為下半部,羅躍強是當之無愧的主角。上半部的故事發生在并西省,下半部的故事從安西市開始,中經烏魯木齊,其后以原太市為主要場景。“安西”即西安。太原、西安、烏魯木齊、蘇州,都屬于《我們這代人》的“鄉情”之列,如果說有什么區別,就是太原、西安、烏魯木齊、蘇州構成不斷擴大的同心圓。烏魯木齊的場景非常有限,但卻相當重要,羅躍強和馬英蓮的情感故事是在安西到烏魯木齊的出差途中開始的,并且,在烏魯木齊一揮而就。如果沒有這趟出差,羅躍強不會邂逅馬英蓮,和李春梅的戀愛應當會直接走向婚姻,不會出現情感上的一波三折。就此而言,烏魯木齊之旅意味著遠鄉之旅。此外,蘇州對馬英蓮的母親奚夢雅至關重要,她回到蘇州“就像一個復活的少女”。《我們這代人》中,有對家鄉的長年累月的堅守,更有“遠鄉”與“還鄉”的相輔相成,這些共同造就了“鄉情”的質地與核果。
傳統
《我們這代人》第一章就寫道,胡春來老家平原縣是有名的“中國摔跤之鄉”。當地俗稱摔跤為“撓羊”或“跌對”,“撓”即“扛”,“撓羊”即“扛起羊”,意味著“勝利與強大”,是一種“宣告、展示與炫耀”。小說對“撓羊”的介紹,實則是對胡春來性格的揭示。小說把平原人的摔跤史追溯到宋朝,特別是在南宋的時候,身為岳飛部下的一名平原老兵返回故里,把軍中所學的“角”(近似于摔跤)傳授給鄉鄰,使得這項運動得以“廣泛開展,世代相傳,終成習俗”。
胡春來是名門之后,他的祖先呼延贊是并州太原人,北宋名將,后周淄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呼延琮之子。元朝時,蒙古人將他們這支改姓為胡。“胡春來父親從小就經常給他講這段家族史。”胡春來的父親胡一德是平原有名的摔跤教練,胡春來三四歲時就跟著父親學習摔跤,后來又跟著父親請來的保定師傅學會了保定摔跤的二十四式。十四歲時,胡春來參加并西省少年摔跤比賽,勇奪桂冠。《我們這代人》第一章對胡春來所從屬的地方傳統、家世傳統的介紹,使得胡春來的個人形象意味深長。事實上,胡春來、羅躍強及其他諸多人物都背負著各自的歷史。由此,“我們這代人”也就不僅僅是一代人,而是承載著悠久的歷史,作為歷史的傳人而演繹當下的故事。
第二章中,胡春來所住的小旅館旁有一家刀削面館。“并西省是面食的故鄉”,海內外早有“世界面食在中國,中國面食在并西”的說法,并西的刀削面又屬同州市“最有名氣”。“鐵皮切面”的典故由來已久,并且,大酒店里的刀削面不如刀削面小館的筋道。第三章顯示,胡春來對飲食比較挑剔,衛蕊花最初打動胡春來的,除了樸實自然的美麗,就是她做的飯菜———涼粉、羊肉、土豆粉羊雜割、胡麻油炒雞蛋還有主食黃糕———都具有同州地方特色。第十六章中,薛桂花做了幾道正宗的河東菜,“蜜汁葫蘆”“糖醋茄盒”“肚絲湯”“麻椒菜”,每道菜都顯現出“南縣人”的“細曲”。
同州民間有句諺語:“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十里的蕎面餓斷腰。”諺語蘊含著歷史故事,也蘊含著人生哲理。同州還有一句諺語:“砍柴要刀,吃飯要糕。”從古至今,黃糕在同州人的餐桌上始終扮演著主角。“衛蕊花做的飯菜,咸淡相宜,剩菜剩飯也能添加混搭,不浪費還有新鮮感,胡春來很喜歡吃。”“食色性也”,果不其然。告子是一位年輕的哲學家,他對孟子的“人性善”觀點很不滿意,就找上門與孟子辯論,說了句“食色,性也”。按照通常的理解,意思是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還有一種理解,“食”是動名詞,表喜愛之意,“色”為態度、美好之意,“食色性也”即喜愛美好東西是人的本性。
作為地方傳統的摔跤,作為生活習俗的刀削面,富有文化底蘊的諺語,所有這些構成了傳統敘事。所謂傳統,離不開社會關系的傳承,兩性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中基本的關系,由此,兩性關系的模式傳承構成了傳統的重要內容。《我們這代人》中,胡春來一出生,母親就送了性命;十四歲時,父親又遇車禍去世。少年當自強的胡春來,在岳父面前毫不示弱,薛桂花主動追求的胡春來,但并不能約束胡春來,事實上,正是胡春來的男子漢氣魄強烈地吸引著她。胡春來的形象比羅躍強的形象有力得多,胡春來周圍人的形象則比羅躍強周圍人的形象要弱不少。羅躍強一直有父母的關愛。這種關愛的根本意義,在于傳統的有效傳承,這離不開家庭的作用。羅躍強很早就認識到,“父親能從人性的角度理解別人”,思考問題總是從多方面考慮,懂得“位置越重要,承擔的責任越大”,他希望兒子“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就好”。“妻賢夫禍少,好妻勝良藥。”羅躍強能在權力面前始終保持清醒,面對巨大的誘惑也能平淡處之,“全靠背后的賢妻李春梅”。并且,“李春梅總能給羅躍強一種力量,他知道,即使他在事業上碰得頭破血流,梅子都是他堅強的后盾”。
《我們這代人》中的愛情婚姻宛如越羅蜀錦,各有所長。胡春來在并西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就讀于專科班的薛桂花為胡春來賽場上的颯爽英姿所吸引,主動發起攻勢。由是之故,在胡春來和薛桂花的婚姻關系中,薛桂花事實上處于弱勢的一方。而在羅躍強的第一段婚姻中,馬英蓮主動追求羅躍強,并始終處于強勢地位。顯然,主動追求并不意味著將自己置于下方。裴七龍和梁美娟相濡以沫、忠貞不渝的愛情婚姻,令人潸然淚下;衛蕊花和裴三龍的婚姻不乏戲劇性,令人啼笑皆非。當然,占篇幅最大的,是羅躍強的愛情與婚姻故事。小說中,胡春來的故事以事業為主,羅躍強的故事則把情感作為貫穿始終的軸線。胡春來的故事是社會與市場的故事,羅躍強的故事則是家庭與婚姻的故事。在講述羅躍強的故事時,連帶引出了其他的愛情婚姻故事,包括:李春梅父母的故事,馬英蓮父母的故事,馬英蓮的姨媽姨父的故事,馬英蓮的表姐王青亞和李奎義的故事,等等。“一段婚姻的締結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在特定的大時代和大環境面前,個體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更是微不足道的”,羅躍強的這種認識,大體上適用于《我們這代人》中的所有婚姻。
《我們這代人》的下半部,是從羅躍強離開家鄉到安西上班開始的,之后他回了四次老家。第一次是帶馬英蓮回老家,馬英蓮大衣肩膀上有煙頭燒過的痕跡,羅躍強以為是自己的煙灰所致,一直心神不寧。其實是馬英蓮先前出差時,不知什么時候讓人給燙的。她跟羅躍強回家,擔心路上比較臟,特意穿了這件大衣。她在羅躍強的村子里不大自在,覺得自己像動物園的猴子一樣被人打量。羅躍強第二次回老家,是一個人回去的。第三次回老家時,他跟馬英蓮已經離婚,是李奎義和馬青亞陪他回去的。馬青亞說:“選擇什么樣的伴侶,往往就會擁有什么樣的婚姻,而長久的婚姻,從來不單單是兩個人的相濡以沫,更多的是兩個家庭的戮力同心。馬英蓮和羅躍強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他們開始的吸引只是沖動,而真的走到一起才發現彼此格格不入。這次來河東這種感覺更加強烈。”馬青亞的觀點屬于老生常談,重要的在于,她在河東更為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羅躍強第四次回老家,是帶著李春梅一起回來的。“羅躍強母親準備烙餅,李春梅熟練地把火點著拉起了風箱,羅躍強拿個小板凳坐在李春梅的旁邊,心中劃過從未有過的踏實”,因為他看出了“母親對李春梅非常滿意,眼睛里流露出的那份慈祥好舒坦”。當晚,羅躍強到南房睡了,“他好久沒有睡得這么香”,第二天睜開眼時,天已經大亮,“聽見母親和李春梅在院子里開心地聊著”,他驀然感覺“這個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可以說,返鄉之旅構成了《我們這代人》下半部的一條主線。離家遠行是為了回歸,回歸又是為了更好的遠行。泛泛而談,返鄉之旅就是傳統的“溫故而知新”。《我們這代人》中,傳統具有地域性,也具有多元性。“同州市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匯處,曾是民族混居之地,漢、鮮卑、匈奴、契丹、女真、蒙古都曾在這里廝殺、混居在一起。或許,正是這樣一段歷史才造就了同州市文化的多元,才造就了同州人的包容,才造就了同州人的美麗、豪爽、大氣。”同州文化具有多元性,南縣人也并非鐵板一塊。“同州市人叫并西省南部的人為南縣人。同州市大街小巷很多南縣人打餅子,其實這些人也不是一個地方的,他們口音各異,但在同州人聽起來是一個樣。”對傳統的守護并不意味著排他,薛桂花和女兒莎莎到同州看望胡春來時,參觀了云岡石窟、應縣木塔、渾源懸空寺,親眼目睹這些世界級的建筑文物,不得不“對雁北人多了幾分敬重”。
《我們這代人》中的傳統敘事,既有歷史文化傳統、地方文化傳統,也有革命歷史傳統和新中國建設的成就經驗。小說中出現的“陳家莊”是具有光榮傳統的革命老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黨在陳家莊建立了太岳三分區的地委、政府及稷麓縣委、縣政府各個機關,有河東“西柏坡”之譽。2009年12月,陳家莊被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命名為“山西省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13年6月,被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命名為“山西省黨史教育基地”;2015年,被山西省定為省級美麗宜居試點村;2016年,“太岳三地委舊址”被列為山西省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歷史的傳說中,西漢末年劉秀逃難途中為農婦陳氏所救,登基做皇帝后感念救命之恩,敕封陳氏為一品誥命夫人,所居鄉民免除五年賦役,鄉人為此將村名改為“陳家莊”。陳家莊將歷史文化傳統、地方文化傳統和革命歷史傳統有機地貫穿、連接在一起,206廠和303廠的故事則屬于新中國及改革開放事業的樣板。此外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這代人》中,城市基于農村的背景而存在,機關基于廠礦的背景而顯現,這或許表明了農村和廠礦更能稱得上傳統的根基。
遺產
鄉土的意義在于傳統,傳統的價值取決于我們對傳統的利用,這就導出了“遺產”概念。遺產是一個非常寬泛的術語,從建筑、古跡、紀念碑等實體,到歌曲、節日、語言等非物質性事物,皆可冠以遺產之名。根本而言,遺產關乎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和未來。英國學者羅德尼·哈里森指出:“遺產不是消極的過程,不單是保存古物這么簡單,相反,它主動地將一系列物品、場所與實踐集合起來,我們的選擇猶如一面鏡子,映照著我們當代所持并希冀能帶向未來的某種價值體系。”②
前面講過,《我們這代人》可以分為兩篇,第一到十八章構成“上篇”,第十九到四十二章構成“下篇”,前者以“現在進行時”為主,后者以“過去完成時”為主。敘述結構上的這種安排,使得下篇已然具有追溯、增補和反思的意味,上篇徐徐展開的情節為下篇確立了基本的立場和站位。現代意識包含三重追問———我們從哪里來、我們現在置身何處、我們將要往哪里去,上篇主要講述的是胡春來的當下和前行,下篇著重講述的是羅躍強的過往。就此而言,《我們這代人》隱含了一個重要的思想旨趣:應當怎樣面對遺產?遺產的意義究竟何在?
胡春來初到同州,為了跟當地的裴七龍結交,特地從夏縣訂制關公銅像。不料,起初送來的是一尊古代女性的銅像,整體上是唐式之風,他猜測是文成公主。“楊貴妃在歷史長河的扮演中并未以正面形象顯現,所以為楊貴妃制作的可能性不大;武則天大權在握時已是中年,即便是制作銅像也是中老年居多。”胡春來大學是學歷史的,典故信手拈來,這合乎他的角色安排。這樣的角色安排值得深究。司馬遷《史記》有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羅新認為:“歷史學家歸根結底不是傳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種古代的東西保存下來。他的使命本質上是質疑現有的歷史論述,去反抗、去抵制種種主流的歷史理解。”③當代英國歷史學家表示:“事實上,歷史賦予我們兩種形式的權力:一方面,通過將人們牢固‘捆綁’在對過去的同一性敘述之中,歷史可以被用來加強群體認同感(對國家或是對社群);另一方面,通過充實那些有作為的公眾的思想資源,歷史賦予他們權力。”④《我們這代人》中,胡春來為歷史學專業的畢業生,意味著小說同時在發揮這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關于歷史的,人們都是在歷史的邏輯上翩翩起舞;另一方面,翩翩起舞的人們羽扇綸巾,將歷史的邏輯予以延展和偏移。
關公銅像于《我們這代人》而言,具有輻射性的意義。關羽在世時,魏、季漢、吳三國上流社會從道德信條、人格特征、勇烈風范等方面給予高度贊譽。歷代朝廷對關公多有褒封,清朝雍正時期尊其為“武圣”,與“文圣”孔子地位等同。經過1800年傳承和發展,關公形象已經從歷史人物逐漸升華為人們心中的道德楷模,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道德榜樣”,關公文化應運而生,其所蘊涵的忠、勇、仁、義,智、信、禮、廉,無一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胡春來將關公銅像贈與裴七龍,有和七龍結義之意,也有推崇七龍急公好義之意。七龍的正屋東墻上有“貽謀燕翼,勿忘祖恩”八個大字,這是他的祖父所賜,是裴氏祖訓第一章節的最后一句。七龍也是讀過大學的人,由于俠義之舉而被退學。俠義之舉值得肯定,遺憾的是,他終究是違背了祖訓,也沒能全面地貫徹關公“忠勇仁義智信禮廉”的精神。胡春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按照關公文化研究專家胡小偉的觀點,在有關關羽的“造神”過程中,文學諸樣式,包括傳說、筆記、神話、戲曲、小說等,與民俗、宗教、倫理、哲學、制度一起相互作用,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關羽是與中國古代小說、戲劇這些文學樣式共相始終的一個形象”。⑤《我們這代人》講述了諸多的友誼故事,堪稱關公文化的當代延續。概括起來,小說中的友誼分為四類:一是戰爭年代的生死之交,如馬英蓮的父親馬占武和秦劍波,抗美援朝時,秦劍波救過馬占武的命。二是特殊年代的患難之交,如羅躍強的父親羅寶學和當過國民黨軍醫的鐘云寧,羅寶學時常帶些吃的給鐘醫生,鐘醫生則使得羅躍強安全地出生。三是同窗歲月的金石之交,如羅躍強和李奎義,二人是大學系友,原本一個分配在303廠,一個分配在206廠,由于馬英蓮的緣故,羅躍強調到206廠工作,跟李奎義成為同事。羅躍強把李奎義介紹給馬英蓮的表姐王青亞,二人也就成為姻親。四是忘年之交,如馬進和羅躍強,馬進由最初對羅躍強的欣賞到信任,“現在又多了點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感覺,他的眼睛發濕,緊緊地握住了羅躍強的手”。此外,胡春來和衛蕊花一夜貪歡之后,轉瞬“用最無邪的心”欣賞她來自“天然的純凈”,從而轉換為友誼和親情。胡春來和羅躍強更是莫逆之交,也是君子之交,赤誠相見,肝膽相照。
《我們這代人》的人物中,女性不可或缺,并且,個性鮮明通過女性之間的比較得以彰顯。比如,羅躍強兩任妻子的比較,羅躍強妻子和胡春來妻子的比較,羅躍強的岳母與其姐姐的比較。還有,衛蕊花和陳美馨的比較,這兩個人因為胡春來而有了關聯,因為相互的倚重而成為姐妹。胡春來是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陳美馨是公司副總,主要負責公司房地產專業流程及規劃,衛蕊花是辦公室主任兼營銷部主任。由于胡春來,衛蕊花“要向過去告別,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由于陳美馨,衛蕊花變得現代和時尚起來。衛蕊花家里有很多老物件,“一個老物件代表一段回憶,能夠打撈出年深日久的陳年往事”,老物件匯集而成的“就是一個時代的記憶”。“裴張村”這個村名,或可理解為裴氏家族從河東向北方的延展,裴張村的拆遷則表征著老村落的革故鼎新。在參與薛張村拆遷的過程中,衛蕊花依據北方農村的實際情況提出建議,后來,自己也開公司當了老板。
衛蕊花意味著年輕女性的成長,奚夢雅則標志著年長女性的變化。馬占武身上有老革命的無私和大局觀,對待妻子奚夢雅則比較霸道。馬占武突發心臟病去世后,奚夢雅跟著蘇市來的哥哥弟弟回了蘇市。回到蘇市的奚夢雅“就像一個復活的少女,變得開朗陽光”,和“反右”時落難的戀人邱炳光重逢后結為夫妻。這使得作為女兒的馬英蓮大為光火,羅躍強最初也是大吃一驚,“但轉而一想,這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在別人眼里是那樣的不可思議,而在當事人身上卻是合情合理的必然”。和衛蕊花、奚夢雅不同,李春梅和王青亞代表了始終如一的堅守。李春梅做事得體,積極上進,雖然父親是一廠之長,她身上卻沒有半點的“驕奢之氣”,“李春梅的家人,相互間的關心是由衷的,互相之間說話是溫和的”,讓羅躍強感覺“很溫暖很踏實”。羅躍強有負于李春梅,她卻怎么也恨不起來,最終和他重續前緣,結成恩愛夫妻,甘心夫唱婦隨。王青亞和表妹馬英蓮長得有幾分像,但比馬英蓮溫順得多,心如明鏡、善解人意,在羅躍強和馬英蓮離婚后,跟李奎義一起陪羅躍強回老家,對其父母解釋事情原委。通觀《我們這代人》的敘述,胡春來和羅躍強的視角最為主要,王青亞、李春梅乃至衛蕊花的視角不分軒輊,這無疑表明了對中國傳統女性品德的褒獎。
《我們這代人》中,多次出現夢境的描寫。去往烏魯木齊的列車上,羅躍強和馬英蓮同處一個臥鋪車廂,一見鐘情、動心不已,當晚“居然夢到了馬英蓮”,早晨醒來,擔心自己說什么夢話讓她聽見,心中忐忑不安。和馬英蓮互訴衷腸后,羅躍強又夢到李春梅的父親“橫眉冷目”,李春梅站在一旁“哭個不停”,脾氣和善的李春梅母親也“指著羅躍強的鼻子”。羅躍強和馬英蓮結婚后,并沒有真正放下李春梅,幾次說夢話都提到她的名字,這是馬英蓮最不能容忍的,也是導致二人離異的根本原因。此外,胡春來對自己父親的夢,對自己未曾謀面的母親的夢,都具有象征性的意義。依據弗洛伊德的觀點,“夢的工作對思想進行加工,是夢唯一的本質特征。也許在實踐中我們可以忽視它,但理論探討絕對繞不過這一點”。⑥夢是一種重要的心理現象,對《我們這代人》中的“夢”進行分析,無疑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認識和把握人物心理。
《我們這代人》中,裴七龍對胡春來講述自己的家世,衛蕊花對胡春來講述自己的家事,馬英蓮對羅躍強講述自己的家事,王青亞對羅躍強講述自己的家世,等等,所有這些敘述都具有創造性的意義。自我是我們講述的產物,我們講述故事不僅是為了和他人交流,也是為了和自己交流,就此而言,敘事具有返璞歸真的效用。生命故事基于客觀事實,反映的是個體所處生活的價值觀念和規范,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兩代人的生命故事也是各有千秋。生命故事的功能是“為自我提供自我認同”,同時也有助于“改善情緒”及心理健康的“整體維護”。⑦《我們這代人》作為文學敘事,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包含了諸多的敘事形式和內容,所有這些敘事都在自覺地介入過去,積極而富有創造性地創造未來的自我和社會,從而在客觀上發揮了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價值。根本而言,遺產是一種“參與過程”,一種“交流行為”,一種“為當前與未來制造意義的行為”。⑧
余論
2011年,我主編的《六十年代生人:選擇抑或為哲學選擇》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具有三個方面的旨趣:為六十年代生人提供“自我反思、總結及整體展現的平臺”;向五十年代生人以及更年長的前輩們,匯報“六十年代生人的努力和風格”;對“七零后”予以必要的示范,使得他們更為明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已經達到的層面,由此更為順暢地做進一步的發揮。⑨文波2022年出版的《我們這代人》,則是以小說的形式,對六十年代生人予以描述和刻畫。于我而言,這部小說具有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我屬于小說所言的“我們這代人”。其次,故事所發生的場景主要是在西安、太原,及運城和大同。運城是我的老家所在地,大同是我大學畢業后工作過三年的地方。再次,主人公所在的工廠屬于軍工企業,我大學畢業后曾在大同的一家軍工企業子弟中學任教。對于個體的意義無疑是有限的,對于“我們這代人”的意義總歸也是有限的,《我們這代人》的真正意義在于傳遞鄉情、激發傳統,并提示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現時代應當如何繼承遺產?應當繼承怎樣的遺產?
文波速遞《我們這代人》一書的同時,把稿本一并遞了過來。稿本和成書的區別,首先在于章節上,稿本有49章之多,成書則只有42章,字數壓縮了五六萬,情節自然有所刪減,比如,鐘云寧的孫子回鄉探訪,陳美馨的情感糾葛,等等。經由這些刪減,小說顯得更加凝練,然而,鄉情的戲碼受到不少的折扣,特別是鐘云寧的孫子從臺灣返鄉將鄉情發揮到極致,成書對這一情節的刪除無疑令人遺憾。陳美馨的情感糾葛,陳美馨和衛蕊花的傾心交談,具有女性成長與互助的重要意義,成書中刪除了這些,也就使得意義向度受到很大的削減。稿本和成書更大的區別在于胡春來和羅躍強的出場順序,稿本中,前半部分以羅躍強為主,后半部分以胡春來為主,成書則顛倒了這種順序。這就使得“正邪”結構變為“邪正”結構,恰好預示了“邪不壓正”。劉醒龍為《我們這代人》作序,題為“向正直平常的人生致敬”,應當是注意到了這種結構。就故事的力度而言,“邪惡”終究比“正直”要有力的多,小說的后半部分之所以能壓住前半部分,從表面上看,是因為后半部分在章節和字數上壓倒了前半部分,實質上是后半部分所呈現的傳統意涵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促成了“扶正祛邪”的文本效果。
《我們這代人》正在由小說向電視連續劇轉化。從文波提供的編劇創意來看,小說著重于刻畫大時代中的兩個從社會基層崛起的人物,劇本則通過對代表性人物的刻畫,展現時代的風云變遷,這樣就具有了宏闊澎湃的史詩性,超出了劉醒龍所說“山藥蛋派”講故事的套路。目前擬定的主演人選(暫且保密)符合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應當能夠很好地演繹角色。電視劇敘事和小說敘事,有很大的不同。看電視劇,看的是畫面營造的劇情;看小說,看的是文字(在讀者頭腦中轉換后)呈現的故事,然而,無論是看電視劇還是看小說,都是參與、創造、鞏固自我的過程,是民族文化認同和面向未來的過程。相信《我們這代人》能夠很好地發揮橋梁維護的意義,并且,呈現意義建構的辯證法,由此,《我們這代人》將遠遠超出“我們這代人”,在歷史文化的傳承中擁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①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頁。
②[英]羅德尼·哈里森:《文化和自然遺產:批判性思路》,范佳翎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頁。
③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象力》,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7頁。
④[英]約翰·托什:《歷史學的使命》,劉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⑤胡小偉:《關公崇拜溯源》,北岳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6頁。
⑥[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徐胤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頁。
⑦[加]安格斯、[挪威]麥克勞德:《敘事與心理治療手冊》。吳繼霞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96頁。
⑧[澳]簡·史密斯:《遺產利用》,蘇小燕、張朝枝譯,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i頁。
⑨張立波主編:《六十年代生人:選擇抑或為哲學選擇》,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作者簡介】張立波,山西聞喜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史館副館長。出版有《坐言起行錄》《鄉村的文化意象》《研究生課程記》等隨筆集。
責任編輯:曹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