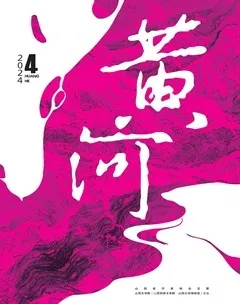新東北對談
編者按:繼第3期“新時代文學晉旅”訪談之后,本期我們將視線轉向“東北”。作為近幾年在文壇崛起的新勢力作家群體,“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得到了肯定,也涌現出一批諸如雙雪濤、班宇、鄭執、楊知寒等杰出的青年作家。他們所形成的創作熱潮至今未退卻,且更多更年輕的寫作者加入其中。周羽、郝瀚、程惠子、史癑琦便是如此,四位青年作家均為90后,既可稱此群體之一員,又在各地求學或工作,這樣的身份特征或可對“新東北作家群”的“新”持有更為敏銳的洞見,特呈奉讀者以饗。
后身份時代的主體漂流
上世紀30年代,以蕭紅、蕭軍等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是站在“九一八事變”前后的一系列劇變的歷史背景上成形的;而“新東北作家群”則與“東北衰落”的現實性指認密切相關。在其中,我們看到兩個作家群體都有一種共性,即“被迫流浪”,有時是身體的,有時是心靈的。那么對于“新東北作家群”,你認為流浪會終止嗎?如果會,應該在什么時候?倘若沒有這種流浪狀態,是不是就不會有如今的“新東北作家群”?
周羽(作家,游戲劇情設計師):1934年6月,蕭軍和蕭紅離開哈爾濱,在大連乘坐郵船“大連丸”號前往青島,開始了在文學史上具有象征意味的離鄉之旅。如今的新東北作家群們業已離鄉,再一次將異質化的生活經驗帶往京滬,毅然決然。
離鄉帶來的是對身份的反復拷問和自我的重新建立。初抵上海,蕭軍在給魯迅的信中寫到:“一直生活在北方———特別是東北———的人,一旦到了上海,就猶如到了‘異國’。一切都是生疏,一切都是不習慣,言語不通,風俗兩異,無親無朋……猶如孤懸在茫茫的夜海上,心情是沉重而寂寞!”而身份重建的標簽則是左翼、抗聯和東北鄉村。新時代的東北寫作者不用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國族敘事退而其次,要么作《邪不壓正》式的歷史風情畫(《武術家》,雙雪濤),要么作《小姨多鶴》式的家族口述史(《藏著》,史癑琦),成為新東北文學復雜敘事陣列中厚重的一隅。
國族安穩如山,新東北作家們卻不得不走入心靈漂流的旅程。在轟轟烈烈的文化解構浪潮面前,緬懷過去成為一種奢侈。東北人到底是什么?從赫魯曉夫樓中眺望孤獨佇立煙囪的下崗工人?漂泊在異國街頭掙取外匯的勞務輸出人員?從白山黑水走出的最后的獵人、薩滿法師?還是對“新東北作家群”這個概念具有自反意味的,一種新東北藝術的建構者?東北人精神譜系的復雜,似乎不能用數個標簽精準地概括,進而凝聚成網絡上“請選擇你的東北人陣營”的中式“meme”,并含混不清地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式的精神危機中游走。新的社會范式尚未建構,舊的話語卻已轟然倒塌,隱匿在敘事中的大廈崩塌的塵煙,飄在每一個孫旭庭(《盤錦豹子》,班宇)、王戰團(《仙癥》,鄭執)和莊德增(《平原上的摩西》,雙雪濤)的頭頂,盤旋繚繞,久未散去。
作為工人階級的父輩,在工廠倒塌后的無所適從是新東北文學敘事種類的一極;與之對照的是,新的一代在隱秘遭受歷史間接性的創傷后,遭遇的后現代的存在性的危機。這是一種更普遍意義上的精神流浪。懸疑故事因而成為一種極佳的載體,主人公們要穿越的是如《白日焰火》中從時間另一端靠近的隧道盡頭和雪。與其說懸疑、推理是新東北寫作公眾接受的焦點,不如說找尋身份、解開謎題的黑色電影情節才是有效敘事的最大公約數。《平原上的摩西》固然撐起了東北文藝復興的大旗,但在探討現代人精神危機的命題上,反倒是《大路》(雙雪濤)《夜鶯湖》(班宇)這些篇目走向了更遠的去處。一種新的零余者的文學形象在慢慢出現:年齡三十好幾,貧,說話沒譜,沒有固定伴侶,往往有一個嘴更貧或者特立獨行的女伴,有些神奇的朋友,像耿軍《東北虎》中公園里販賣詩集這樣的朋友。文學性在綿密幽默的東北話和詩學的碰撞中激蕩出來;精神危機具象為供暖差的小屋、手術、離婚、車禍、葬禮、沒有勝利的賭局。這些意象蘊含著復雜的對抗性:有供暖但是不多;有過婚姻但是離了;有意外但又瑣碎細小,在語言沉默的地方質問生活本義。
新東北作家們因具備更加豐富的文學視野和文化資源,自由流浪在文體與媒介中。有時放飛想象,深掘寓言,進而有《刺殺小說家》《長眠》;有時擁抱電視媒介,進而有《漫長的季節》《膽小鬼》。新東北作家們也有意識地運用更加豐富的文體樣式,如跳大神的唱詞(《工人村》),來豐富閱讀上的體驗。展開來講,薩滿教傳統的再發掘成為當下時髦且犀利的文學富礦。韓國電影借用跳大神招喚國人喪失良久的國族意識(《哭聲》《破墓》);而在《仙癥》《工人村》中出現的“看事兒的”,往往在超驗的有效性和故弄玄虛的滑稽性間游弋,體現出現代人既試圖尋求超驗體驗,又自暴自棄,知曉預言又能如何的復雜心情。這是一種前現代與后現代間的流浪。
所以,流浪何時中止呢?這是個社會經濟學的問題,還是存在主義的問題呢?我想默爾索在海灘開槍時,也沒想過太多。新東北文學或許是指向歷史的一支槍,彈殼滿地,不見彈孔。流浪或許也并非一種處境,而是一種選擇,而精神上的返鄉,正是文學一遍又一遍書寫的母題。雙雪濤的《長眠》或許是有關東北文學流浪命題的絕佳寓言:去往北方,去一個叫玻璃城子的地方,去埋葬行李箱中的詩人朋友,去打一場土匪般的槍戰,在蘋果河中游泳,看人變成六只鰭的魚,去念朋友最后留下的詩,那詩是這么寫的:
握手吧,
或者扇我一個耳光,
和在下沒有關系。
你要變成石頭,
我卻變成冰,
在下已經準備好了,
回去。
作為話語與現象的雙面“東北”:“地域”抑或“空間”?
我們知道,一旦涉及“群”,就有被“群”吞噬的危險,你在創作中,或你認為,寫作者如何才能從“群”里突圍?
郝瀚(青年作者,電影研究者,編劇從業者):當我們談論“新東北作家群”這個話題時,實際上我們在談論地域與空間的關系。我兼有創作者(小說/電影)與研究者(當代中國電影中的東北問題)的雙重身份,因此我想從話語與現象兩個側面切入東北。這不僅是我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也是對我當下寫作的一種自反。無論作為話語抑或現象的東北,去主體性并非地域性給予的,而是空間給予的。
東北不應該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空間概念。
首先我想強調的是,當下早已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無論文學藝術還是經濟政治,其指向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東北?是黑龍江(東北)人的東北,還是“中國東北”,甚至是“世界的東北”?作為學術話語抑或創作現象的“新東北作家群”,都試圖制造一個狹隘地域性范疇的概念。這顯然是一個悖論,因為一旦此概念成熟,也是其喪失生命力之時。所以,任何以地域命名的藝術“群體”,都應該是一個僅供指認的話語。也即是說,命名比意義自身更重要,一旦賦予群體具體意義,便會造成兩種令人遺憾的結果,一種是按圖索驥般的研究與創作,即創作者與研究者在這套模式中各取所需。每個舊作者可以自我循環,而新作者可以憑借籍貫、地域與經驗進入到“群體”之中,反之研究者更可以按照一套既定的學術話語泛泛解讀任意新作品與新作者。另一種則是在賦予意義的過程中,盲目涂抹所謂的文化色彩,實則建構了一堵堅實的文化壁壘。就像趙本山的春晚小品在廣東甚至整個長江以南都遭到冷遇一樣,何以去期待一個澳洲人或巴西人去理解其中的笑點?
所以,任何“文化圈地運動”式的“群”,都已在或即將陷入到盲目中。甚至可以說,在中國范圍內,群與群之間的刻板印象都無法破除。這并不新鮮,提到北京要寫舊北京的人情味與新北京的都市感;提到西北要寫民族之苦難與精神之豐饒;提到曾經的東北我們要寫反殖民經驗、工人階級與烏托邦。如今要寫東北什么,新東北作家群似乎已昭示一切。
所以,作為地域概念的東北也只是一種命名的方式,作為概念的能指而已。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中國的東北,更是世界的東北。新東北作家群的所指,是對狹隘地域文化的超越,即所謂的“空間”。空間(space)是東西方哲學中一個極難解釋的概念,當下談論的空間概念大多是指20世紀60年代以降西方當代空間理論的成果。作為奠基者的列斐伏爾與福柯,以及將空間理論帶到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的卡斯特、霍米巴巴、大衛哈維等人將空間打造成充滿意義的工具。他們都在緊緊圍繞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空間并非無生命的容器,而是充滿了社會關系與文化表征,即空間并非簡單物質,而是種種復雜的關系。
關于東北共享的空間性,北美社會學家李靜君的勞工研究已經在側面給出過答案,她將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東北國企工人的經歷稱之為中國“銹帶區(Rust Belt)”的抗爭。銹帶區原本指以美國五大湖區工業城市衰落所造成的大規模失業、貧困與社會動蕩。當然,德國的魯爾區、英國的伯明翰都曾經歷過銹帶階段。在空間層面上,無論中國東北,還是西方世界,彼此都獲得了空間意義上的感知與共振。新東北寫作與世界所共享的,并非是那些在寫作中喜聞樂見的地域文化,那些停留在簡單的物質性層面的噱頭與符號,譬如工人們喝的“老雪”吃的“雞架”;也并非那些被改造的“咸淡適口”的所謂“東北話”;更不是那些日常性的“嘎啦哈”抑或“倒騎驢”……在世界范圍內,東北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諸如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的變化都在空間層面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空間變遷具體落實到的情節與元素,諸如犯罪、懸疑、下崗、流動等并非為東北所獨有的地域性。
東北是一個名字,而非意義。
從底特律到魯爾,從魯爾到伯明翰,從伯明翰到沈陽,或許也可以從沈陽再到我筆下一次又一次出現的“島城”。關于新東北寫作突圍的秘密似乎非常明確,即空間經驗的共享,絕非狹隘地域文化的共享。如果按照既定的評價方式,那么我的寫作似乎也要歸結到新東北作家群之中,但我書寫的卻與東北毫無關系。這也充分說明空間自身對地域的超越性,社會改革所波及的空間變遷不僅局限于東北,更是蔓延全國,甚至是整個世界。當然,同時作為一個電影研究者與編劇從業者,在大眾文化的維度上看待這個問題,勢必會關注與新東北寫作的種種嘗試,特別是與電影的聯動。這個話語試圖獲得一個更宏大的話語結構———“東北文藝復興”。在這個由說唱歌手(寶石GEM)有意無意戲謔說出的概念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命名的狂熱與渴望,于是電影、音樂、脫口秀、綜藝節目、網絡大電影、電視小品甚至“二創視頻”都加入其中。而電影正是與新東北寫作之間跨媒介運作的典范,無論是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的售賣影視版權還是越加技術化的視覺性寫作(小說服務于電影劇本改編),這個趨勢都相當明確。但正如剛才所說的,這些文化產品販賣的大多是已成刻板印象的“東北文化”,而逐漸隱藏了空間經驗。或許這就是新東北寫作的尷尬,站在以東北命名的熙攘的十字路口無論向前、向后,抑或向左向右,茫然四顧的,也只能是散落在地上的“嘎啦哈”罷了。
風景、抒情、與“赤裸生命”:關于東北的讀法
———間談“新東北文學”的轉型可能
現在看來,新東北作家群的敘事策略,似乎開始形成了某種模式,比如下崗,比如懸疑,比如過往和現實雙重線索的交匯,你覺得這樣正常嗎?而當這些經驗被反復書寫、反復確認后,這個作家群體又將該向何處去?
程惠子(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風景的書寫作為一種媒介的存在,所傳達的是創作者想要傳達的情感體驗和情感經驗,在“新東北文學”中,關于廢墟、廣場、密道等一系列后工業社會文化景觀很是常見,其中代表作如《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逍遙游》等均出現過類似的描繪。風景作為介質銘刻了記憶,繼而傳遞作家的切身感受。“新東北”小說中的風景多帶有白色、黑色及昏黃的色調,對廢棄風景的移情隨處可見,如此明顯后工業時代風格的懷舊色彩創造了一種連續的不安全感。傳遞碎片化的記憶對接不可靠的歷史,對于過去的流連與對于現實的懷疑并存,這確立了“新東北文學”的情感基調。
過往與現實的重合十分多見,唯有碰撞到曾經的記憶,抒情才得以展開。小說反復提及記憶中的過往,歷史發展的至高點與恣肆的抒情相碰撞,締造了想象中的“黃金時代”。然而在欣欣向榮的環境中,歷史的危機亦在衍生,經歷過動蕩與休克,再到今日渴求的“復興”,父輩身上所承載的歷史債務以記憶的方式重歸現實。盡管執筆的“新東北作家”并非“被下崗”的對象(相反,他們幾乎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有著光輝的學歷),但被回避的歷史債務在他們筆下逐漸演變成現實中的危機,故事背后潛藏的是對“故鬼重來”的不安與焦慮。關于未來的幻想在成長的某一刻宣告破碎,友誼失落,家人離散,即便事業與家庭上相對順遂,也都被賦予了虛妄的含義。
在歷史終結與意識形態懷舊之間的含混時刻,抒情成為“新東北”敘事的隱匿語法,他們無法分辨過去和未來,只能以抒情的形態“搖擺”。新東北作家的“東北”書寫,在文學史上的“革命—東北”“鄉土—東北”之外,提供了“抒情—東北”的審美編碼。這種抒情性產生于作家代際經驗中兩種歷史感覺之間的拉扯,作品對廢棄風景的移情,語辭中感傷風格的反諷,以及記憶里那些秩序之外孤獨的“人”,透露出意識形態祛魅與懷舊之間的情感擺蕩。而同代影視創作者對“東北”書寫的創作(如《鋼的琴》《心迷宮》《漫長的季節》等),同樣分享了個體抒情的隱匿語法,有效參與了“抒情—東北”的敘述過程。
“懷舊”也是評論新東北文學時常被提及的語匯,也反映了新東北文學的某種共通性。“懷舊”(nostalgia)一詞最早為瑞士醫生用來描述遠離家鄉的士兵的心理癥候(思鄉病),后成為現代性文化癥候,往往用來修復個體“同一性”的茫然,而集體性懷舊多發生在社會轉型期,在新東北文學作品中,主人公總是流連過去,在遠行中拒絕遠行,私人化的情感試圖抗衡宏大歷史的敘述,在不斷的回想中陷入時間旋渦,把“情感”還給了語言和故事本身。
此外,不難發現新東北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有著明顯的“局外人”色彩:《大師》中落魄潦倒卻癡迷下棋的父親;《逍遙游》中在透析中艱難生存的許玲玲;《仙癥》中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戰團等等。關于此類人物的特征,吉奧喬·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一書中有相關闡述:在當代語境中,當我們再去理解人的存在方式時,是不能被祭祀但是可以被殺死的生命,他們存在于共同體中,但遭遇棄置。以被共同體排除在外的方式納入秩序。他們被標注為“非法”,但他們的非法恰恰確立了共同體內人群的“合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東北文學中被現代世俗秩序放逐的主人公們正是后工業時代以懷舊形式存在的“赤裸生命”。
在“新東北文學”不斷被標簽化的同時,關于東北,或者說“類東北”的書寫,也形成了某種相對固定的模式,即寫作套路。然而,套路意味著易模仿,也意味著被打破。班宇和雙雪濤近兩年分別推出了新作,都有著非常明顯的“去東北化”傾向,不再強調故事發生的地點,轉而將“東北”擬轉為一種寓言式的象征,流水般滲透在故事當中。關于新書,班宇曾在一次談話中提及:“‘東北’這個詞可能不再是一個被觀看、被凝視的對象,絕不止于此,而是在不斷地重新滲入我們的生活和地表之間,像是一顆顆很小的分子,穿過細微的縫隙,貫穿在南與北、歷史和現實交織的部分,企圖達成一種平衡感。這個詞不再只是一個遙遠的象征,或者為命運的某種循環所代言,可能是會引向一個動蕩的、莫測的結果,一種事關未來的映像。”雙雪濤的新書《不間斷的人》,在他前幾年的小說集《獵人》之上,更進一步走出了曾經筆下的S市(沈陽),轉而討論人工智能、幻想、虛擬等與地理上的東北有著相對距離的主題,他在新書出版時表示:“S市一直沒有從我的小說里離開,是我經常會想到的一個地方。其實應該警惕一點,小說不是紀實,是虛構,是藝術,在藝術里你不能確鑿地認定它就是東北,它是我意念中、頭腦想象中的世界,并不是一個狹窄的地域寫作。”
將地域作為方法,并最終模糊地域的概念,去解決關于文學的核心問題,即“人”的問題,“走出東北,走向未來世界”,這或許可以被理解為“新東北文學”代表性作者對寫作轉型的一種嘗試,也讓“新東北”展現出突破地域文學的可能。外話一句,在生育率下跌,人口流動加速分化,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當下,社會學意義上的“東北化”不止發生在東北。“新東北文學”之所以如此熱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關“東北”的故事及其背后的隱喻與當下生活產生了共鳴,當人人都處于“東北化”的精神困境中時,地域自然變得不再重要,與此相對應的,文學層面上的“去東北化”也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從東北出發:我的經驗和美學
有人以“東北文藝復興”來標定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但我們知道,崛起并不意味著完美,你認為這個群體的寫作還有哪些不足之處?能否提一些建議?
史癑琦(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方向博士研究生):任何在賽博式社會中的前現代地域指認,都形成了某種有力的區分或遮蔽,當作家們從家鄉出發,書寫人事和流變,都會向自己提問,我變了嗎?我拿這個問題問過班宇先生,他在電話那頭說,我是個在沈陽生活了三十六年的人,我只能說我寫的是我自己。當我把這個問題指向自己,十九歲離開東北,去南方求學,去國外交流,地方性知識涌向我,讓我在各自的區域主體間來回跳脫,我也很早地意識到,要通過多媒介體會和觀察我身處的景觀,當居伊·德波的“情境”概念穿過五十多年的迷霧來到一個東北青年的眼前,我知道,我們所處的世界正在發生改變。
圈地運動自有代價,地的外延會反噬地的存在,這就給我們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生產了非地域的精神和知識,一方面我們用地域的方式命名它。王德威談到東北學的可能,正在剝離能指和所指,這個縫隙被作家們輕盈地跳過,沒人想被指認是東北的,或非東北的,他們更愿將自己歸類為文學。這個堅實的符號給“東北”增加意義含量,多義性就此展開,“新東北”所局限的鐵西區以及工廠子弟代際書寫等命題,常常蓋過了賽博社會、信仰問題及“現代”遮蔽掉的區域民俗等美學指向,這些切近的槍靶可以抬到話題的靶場中央來了,它們爭先恐后,成為某種后現代知識,扯著東北的旗幟,本不該為東北獨有。
東北的內在一致性也是我長期關注的一個話題,當沈陽形成了獨有的工廠色調,大連親近了海洋,哈爾濱成為某種煙火漫卷的歷史自留地,長春常常被遮蔽掉它獨有的顏色,這座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建城史短促而幾經易手,歷史在這里成為日常的陰影,與當下的人同頻共振。我在《花園特工》中寫到了一位曾臥底長春偽滿皇宮的被授勛章的英雄老關,但隨著敘述展開,我們發現,在歷史邏輯中,無人能成為正義或惡的代言者,生存取代了意義,情感虛擬了真實,小說結尾中,我這樣寫:“在偽滿皇宮博物院門口,老關朝來往的車輛招手,像隔空撥弄池里的游魚。有一輛格格不入的馬車會停下來,載著老關回到過去。那時老關渾身健碩,沒有傷口,檔案上一片空白。老關一下子從輪椅跳上來,張望來往的行人,企圖分辨出什么。而我停住,只在他身后悄悄注視。我知道,我將消失,又在每一次清晨的懺悔中,走向每個人罪孽的終點。”我想,這種痕跡的存在正是新東北文學的某種不言自明的遠景和底色,遠看是原始的荒涼,其實是一輪輪人煙留下的聲影。
就此看來,與其談黃平式的美學崛起,不如說這是一場漫長的歷史還原,這種回顧是現代發生后的反芻營養,是平緩過渡陣痛期后的“賽季總結”,是隱喻現代中國的角力場,是一種因明確的坍塌而領先的新尋根運動,我在一片德國的草地上完成了《夜游神》,我那時望向天空,發現這里和東北并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