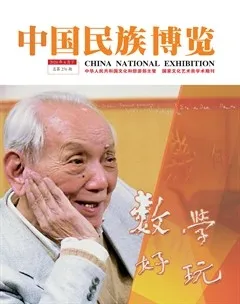現代文明下民族文化的困境隱喻
【摘 要】電影《氣球》中將目光聚焦于新時代浪潮下的少數民族生活的變革,通過描繪藏民在面對生活時的掙扎與沖突,構建了一個豐富的影像世界。影片運用一系列符號化敘事,一方面展現了導演對藏地人民自我身份的找尋,另一方面也呈現了藏族民族文化在時代變革下的傳承與發展。因此從影視符號學的角度出發,能夠更好得解碼影片呈現背后的底蘊,從而實現導演對少數民族形象解構與反思。
【關鍵詞】電影符號學;《氣球》;隱喻探析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08—068—03
電影《氣球》是藏族導演精心打造的一部作品,該片以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象為隱喻,細膩地描繪了藏區人民在現代與傳統的掙扎與抉擇,這種掙扎與抉擇使得影片充滿了張力與深度。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大量符號來構建影片的視聽語言,使得影片在真實呈現藏區生活狀態的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因此本文采用電影第一符號學的分析方法,通過將《氣球》中影視符號分類為鏡語符號與意象符號。一方面利用電影視覺語言,聚焦影像文本,通過對拍攝手法、構圖、景別進行解析,從而挖掘人物行為背后的動機并由此深入人物的內心,解碼導演背后的意蘊表達。另一方面結合電影的意象符號,對影片中出現的服裝、人物與道具進行分析,探討藏地在面對傳統與現代、生育與生存等問題時的抉擇,并由此透視少數民族文化在時代背景下的矛盾與焦慮。
一、鏡語符號:現代語境下的人物焦慮
電影是以視覺和聽覺內容來呈現文本內容的,電影符號學的研究擴散了電影研究的跨學科融合視角,電影的鏡頭語言中也包含著豐富的符號屬性。除卻《氣球》的敘事層面,視聽手法的使用也為影片本身增添了不少隱喻深度和戲劇張力。瑰麗旖旎的藏地風光在真實生動的鏡頭語言下徐徐展開,體現出濃郁的符號美學色彩。
(一)晃動的畫面
影片采用了偽紀錄片式的拍攝手法,導演和攝影別出心裁的使用了手持的晃動鏡頭。“我覺得它是表現人焦灼不安的狀態的,所以我和攝影師商量,主體用手持攝影拍攝。手持的感覺能凸顯人物那種內心不安的狀態,能把人物在現實里的焦灼感很強烈地凸顯出來。”[1]晃動的畫面讓影片增添了不少真實性,同時,這種拍攝手法也讓觀眾從單純的“觀看者”身份中剝離出來,不得不去觀察和凝視一種與自身文化相近或相反的生活方式。搖晃擺動的攝影方式,也使片中的人物關系變得焦灼起來,人與人之間像隔了一層無法溝通的幕布,在無法言表之間,焦慮和緊張在人群中蔓延。
這種焦慮的主題表達,是導演一直以來堅持在自己的影片中表現的,作為“藏地新浪潮”的掀起者,他在自己的影片中投射、放置了許多關于藏地文化找尋的探索,同時也凝結著一種面對新的生活方式的積極反思。
(二)割裂的構圖
洛特曼在《電影符號學與電影美學思想問題》一書中指出:“符號的相互轉換過程是人類借助符號文化掌握世界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這在藝術中體現得尤為明顯。”[2]導演有意向觀眾傳達一種“割裂”“對立”的人物關系和影片主題,展示某種對位的構圖俯拾皆是。
如在醫院的場景里,卓嘎被醫生周措告知自己又懷了孩子,畫面被門框和人物割裂重組,卓嘎被擠壓在大夫周措和醫院的門框之間,面對周措大夫的追問,卓嘎內心更加茫然和無措。在家庭的場景中,回到家的卓嘎渾渾噩噩的將這個消息告知給丈夫達杰。在人物和場面調度上,畫面被窗戶分成四個部分,達杰首先出現在畫面中,占據了畫面的二分之一,他將羊骨綁在有缺口的窗戶上的繩子上,此時卓嘎騎著摩托車漸漸入畫,但觀眾看不清卓嘎的臉,達杰回頭看了卓嘎一眼,繼續沉默的進行手中的工作。卓嘎沉默無力的往前走,終于在畫面的左下角,破碎的三角形玻璃窗中露出了卓嘎的正臉,但她只占據了畫面很小一部分。在這個分裂的畫面中,導演向我們傳遞了太多信息:夫妻關系的異化,丈夫的冷漠與妻子的回避;家庭關系的主導權,達杰的主導與卓嘎的被動;家庭經濟的困難,場景設置的破碎與灰暗;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卓嘎騎的摩托車和家庭賴以生存的畜牧業。
(三)連貫的長鏡頭
在視聽語言上,《氣球》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就是使用了多個長鏡頭來加影片的臨場感、真實感與沉浸感。導演通過精密的設計,借由手持、變焦、遮擋、反射等各種手段,讓長鏡頭在不知不覺中實現復雜的表意功能。[3]連貫的長鏡頭中不斷變化著的人物位置與景別,生成了影片空間上與時間上的紀實與完整。
跟隨著影片角色的腳步,長鏡頭凝視著的這片名為“安多”的土地,呈現出一種樸實自然的生活狀態。家庭中人物之間都有著親密的血緣或親緣關系,卻不能讀懂彼此內心的真實想法。在具體的長鏡頭中表現為人與人之間有著頻繁變化的物理距離,同時照應著卓嘎一家人忽近忽遠的心理距離。片中的長鏡頭往往不是固定的,它游離、擺動于人物之間,形成一種不安和憂懼的環境氛圍。空間隨著鏡頭中人物的運動徐徐展開,環境與影片角色之間形成潛在的對話場域,完成基于文本之上的角色與基于影響之上的地域環境的交融與和合。
二、意象符號:民族文化的追問與反思
1916年,符號學奠基人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了有關語言學中符號學的理論,其將符號看作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在電影符號學中,“能指”是電影中畫面中的意象符號,“所指”則是符號所反映的事物概念。電影《氣球》中,導演構建了多個意象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如影片中多次出現的羊、摩托車、痣等。這些意象符號并非直白現實的存在,而是承載著不同的具象含義。
(一)紅白氣球背后的制度隱喻
一個民族喜歡的色彩如同另一種形式的民族語言,凝結著某種獨特的象征意義,這種色彩經過千百年來的迭代和傳承,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屬性,滲透在民族的飲食、服飾、建筑等領域。但色彩的表現形式只是一種外象,為何運用這種色彩,才是本質。
在藏族人的心目中,白色是最美、最崇高的顏色。藏語中的‘白’——‘尕魯’,多代表合理的、正確的、忠誠純潔的以及大吉大利的意思。[4]《氣球》的開頭,導演就著意設計讓“白氣球”出現,遮擋住觀眾的視線。畫面透過白氣球,幾乎以偷窺的視角觀察著故事發生的這片土地,仿佛帶著觀眾的眼睛進入一種現代式的審判中。90年代全國實行計劃生育,藏地也不例外,“白氣球”作為一種計生用品,是現代制度下的產物。換言之,“白氣球”也代表著一種基于現代制度之下的理性象征。
紅色象征著火,往往與藏袍等高度關聯,因此,紅色也一般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象征。影片結尾,達杰在縣城的雕像下躊躇徘徊,面對現實猶豫不決。在逛市場時,看到了兩個兒子心心念念的氣球,于是買了兩只從縣城帶回家。然而兩個兒子拿到氣球后,一個立馬被扎破,另一個也脫手飛向天空,導演用了一個超現實鏡頭將片中所有主要人物連接起來,“讓他們一起看這個氣球,從不同空間看,好像所有人都看到這個氣球逐漸飄走,越來越高,幾乎消失了,似乎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期待。” 這種期待既是一種對于未來生活的向往,也是基于優秀傳統文化之下對于現代文明的期待。
此外,影片中卓嘎作為藏族的傳統女性,一直身著一身鮮紅色的藏袍,而周措大夫作為現代女性的一種象征,從出場到結尾一直穿著純凈的白大褂。在這里,紅色和白色的符號象征意義聚焦在作為“紅”的傳統性和作為“白”的現代性上。這種紅色和白色的對比,不僅展示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也反映了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影片中的碰撞與融合。
(二)“夢中取痣”背后的生死觀隱喻
在藏族影像中常能看到別具一格的、呈現地域物象特征的敘事元素,在電影《紅河谷》中,哈達作為傳遞友好,結成情感關系的樞紐,在戰爭的背景下,被賦予了和平的意義。電影《老狗》中,藏獒作為藏族的特有品種,象征著藏族人被遺忘的優秀傳統文化。《農奴》中,直觀的展現了藏族建筑的藝術魅力,同時構建了電影的敘事空間。這些物象符號為電影文本貼上了藏族文化的標簽,描繪了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景象。
如果說“紅氣球”和“白氣球”象征著傳統與現代的飄搖,那么“痣”的存在和摘取就象征著生存與死亡的思考。影片中大兒子江洋身上的痣被認為是親人再次回到家里的印證,這顆痣雖然寄托著家人的思念和期待,但同時寓意著舊時代藏族人的生死觀,鐫刻著藏族以往的文化。在夢中,江洋身上的痣被取下來,既有跳出對于逝去親人“逝者已矣”的祝福,又有著對于生者“生者如斯”的期許。新的精神力量在此刻筑成,現代性的文化和藏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迭代和升華。
(三)交通工具對比背后的現代焦慮
藏族是在馬背上長大的民族,馬匹在藏族人的生產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養馬也是藏族民族文化的一種象征。但隨著藏區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更多的現代交通工具進入藏區,取代了馬匹的位置。“摩托車對于藏民族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最為顯著的一個影響是馬的使用頻率大大降低,如今在草原上人們出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車。”[5]
在導演的電影里,“馬”和“摩托車”不僅僅是簡單的交通工具,更是生活方式的延伸。他頻繁地使用“摩托車”作為影片重要的意象符號,在《塔洛》里,主角塔洛騎著摩托車從群山走入縣城,最后憤怒的坐在摩托車上引燃了鞭炮。《氣球》里,父親和爺爺一開頭便與父親達杰就摩托車的問題進行了討論。爺爺明顯還在留戀人人騎馬的時代。而父親達杰卻說:“現在哪有馬呀?時代變了。”爺爺的表情中透露出一股失落。在爺爺這輩人看來,馬和羊是可以養來換錢的資源,而摩托車作為異化的外來物,只是消耗金錢的一般機械,它作為現代性的一種符號,打開了草原之門。父親和爺爺的對話隱喻了藏地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群在使用生活工具的不同,也顯然是一種對于歷史性與現代性的追問。爺爺去世后,藏地老一輩人對于傳統生活方式的懷戀、對新的社會工具或者新的文明的怯魅再一次得到了印證,在江洋的夢里,爺爺佝僂著身子行走在風光旖旎的湖邊,一只馬兒默然的低下頭。在導演的多部作品中,都能看到這種物象二元對立,而主題同一的表達——藏地人民的現代性焦慮。
(四)人與羊背后的生育觀念反思
藏族先民與羊有著特殊的關系,他們曾經視羊為重要的精神文化載體,寄托藏族先祖的希冀與渴望,刻錄著藏族在歷史發展中的辛酸與愁苦。[6]在傳統的藏文化中,羊既是藏族人民衣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被視為上天賜予藏地的禮物。
《氣球》中的“羊”以多種符號形象出現,它被分解為母羊、種羊、熟羊肉等一組影像單位,組建成影片的敘事內涵。這組符號形象不同于藏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羊,而是對于現實的寫意,它被放置于一個工具化的位置,成為經濟價值的附庸。影片的中心問題聚焦在藏地9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上,人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動物,必須為共同的規則所制約。而羊不同,養羊是卓嘎一家的職業,是他們的經濟來源。因此,羊要多生,而人要少生。已經有三個孩子的家庭承擔不起沉重的經濟負擔,無法再供養卓嘎懷的第四個孩子,兩年沒產出羊羔的母羊因為無法帶來經濟利益而被達杰賣掉,體魄強健的種羊則需要通過人情關系來得到,這種對于經濟價值的追求反映了現代社會打壓下的文化放逐與失落。
三、結語
本文利用電影符號學對影片進行剖析,雖然分析的是藏地人民的故事,但背后是社會變遷對個體命運的影響。影片中的家庭面臨著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挑戰,如經濟壓力、價值觀沖突等,這些挑戰不僅影響了家庭成員的生活,也塑造了他們的性格和命運,展現了在大時代浪潮下少數民族地區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抉擇與思考。同時這種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一方面展示了導演對于藏地人民身份的探索與定位,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社會在新思想影響下的變遷與發展。
參考文獻:
[1]導演,索亞斌.《氣球》:意象、故事與困境——導演訪談[J].電影藝術,2020(6).
[2](愛沙)尤里·米哈伊洛維奇·洛特曼.電影符號學與電影美學思想問題[M].凡保軒,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1.
[3]沙丹.《氣球》:視覺敘事的極致典范[J].當代電影,2020(12).
[4]陳笑鷗.藏族的色彩審美和藏族文化[D].蘭州:蘭州大學,2007.
[5]劉生琰.游牧民生計方式變遷與心理適應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5.
[6]林繼富.羊與藏族民俗文化[J].青海社會科學,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