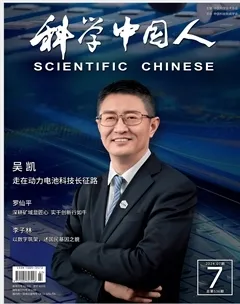以免疫治療曙光融化肝癌“堅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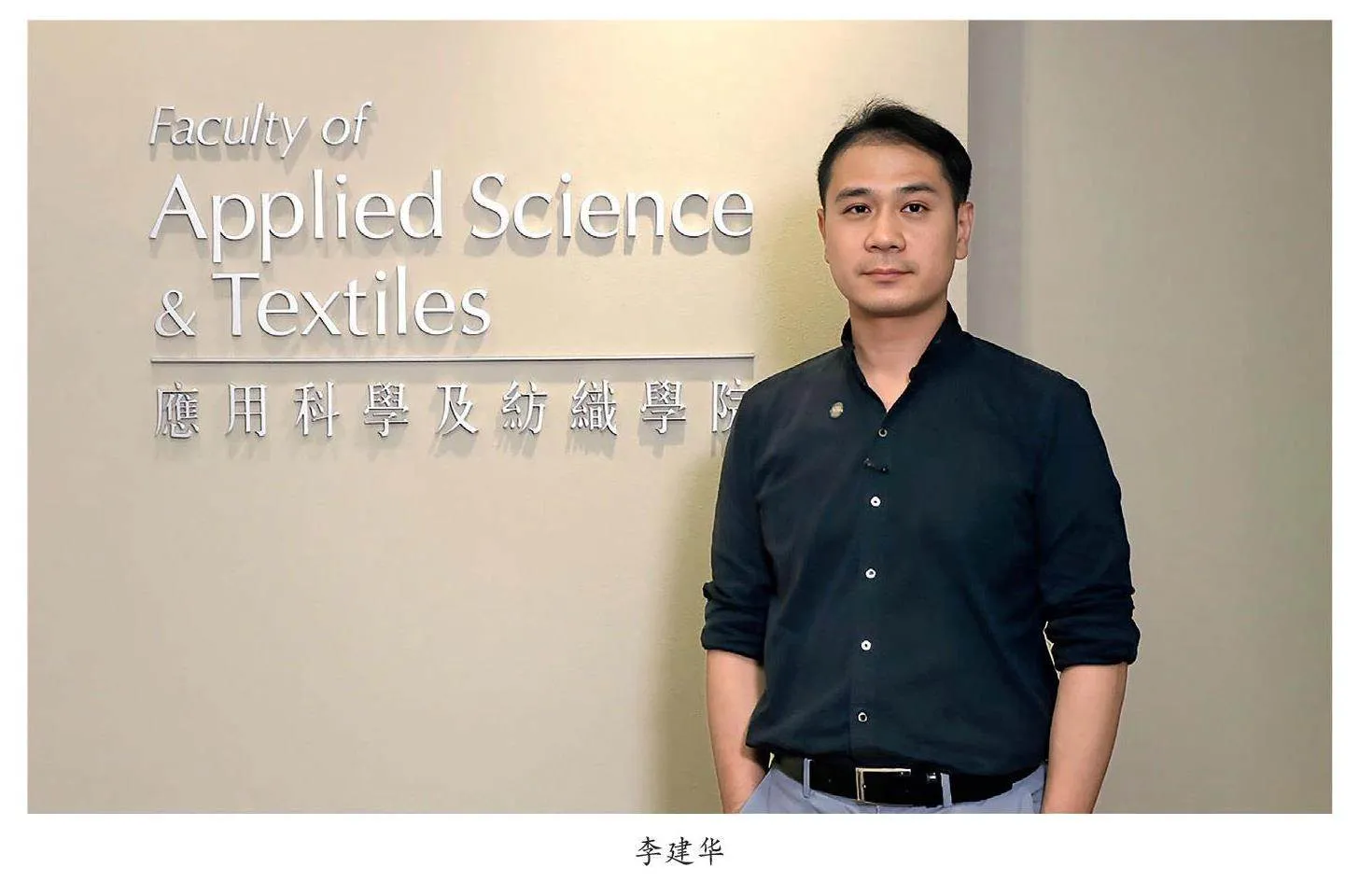

人類同癌癥的戰爭,已經持續了4000余年。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醫生印和闐將求診的病人送出門外時,二人臉上都難掩失望之色。病歷上記載的乳腺癌診斷令人嘆惋,而在“治療”一欄中,“沒有療法”4個字落在這位“醫神”眼中則更是刺眼。這是人類有史記載的第一例乳腺癌患者,也開啟了人類的“談癌色變”。
史海回眸,針對各類癌癥產生的藥物和療法如過江之鯽般不計其數,各種傳聞和偏方也層出不窮,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這場戰役至今仍然勝負未分。不過,如果被奉為神祇的印和闐能看到如今的癌癥生存率和醫療科學發展,相信他會十分欣慰和感嘆,因為至少在治療方法上,人們不再毫無手段。因切除手術、放化療等手段再到各類靶向藥物的出現,人類在抗癌戰爭中贏得了局部戰役的勝利——早期癌癥的治愈率攀升到了一個新的臺階,治療副作用也在不斷降低。但大家都很清楚,要在疾病無情侵襲的領地之上插滿紅旗,還需要新的“武器”。于是,一個嶄新的抗癌療法——免疫療法,一步步走上了歷史舞臺。
作為當今此領域的中流砥柱、骨干力量,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與化學科技系教授李建華已在探索抗肝細胞癌的偉大事業中沉浸多年。正在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與化學科技學系副系主任及生命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一直堅持以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作為模型系統,將目光鎖定在癌癥干細胞、治療抗藥性、腸道微生物群和癌癥免疫學的研究之上。迄今,李建華已發表超過135篇學術文章,論文被引用超過10 300次,H指數達57,并且其載體不乏眾多高影響因子期刊,包括《自然·評論-胃腸與肝病綜述》(Nature Review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細胞·干細胞》(Cell Stem Cell)、《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肝病學雜志》(Journal of Hepatology)及《癌癥研究》(Cancer Research)等。
“之所以會選擇肝細胞癌作為研究對象,根本原因還是患病率太高了。”正所謂醫者仁心,疾病無情,但醫療卻是有溫度的。以臨床轉化為目的的研究者總是迫切地想為大眾健康實質性地做些什么,李建華也毫不例外。執此初心,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用心傾聽、用行動關懷、用專業去治療,致力于煥發醫學研究的溫度,在醫患和諧的美妙盛景中創造更好的明天。
用“藥”探索耐藥之“鑰”
在少年李建華的個人規劃中,長大后自己應當“白衣執甲,丹心為矛”,站在無影燈下為人民健康事業保駕護航。但命運的車輪往往不遂人愿,追尋夢想的旅途也通常不會是一條筆直大道,好在李建華始終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做基礎醫學研究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做醫生是直面病人,為其排除病患,做科研則可以連接技術與疾病,推動醫生的治療手段不斷向前,一樣是為生命而奮斗。”基于此種認知,李建華極為珍視自己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學士與在香港大學攻讀博士的日子,即便轉向生命科學研究的過程是苦澀與甜蜜兼具,他也能將道路的曲折崎嶇都視作命運的贈予,視作“天將降大任”前的“苦其心志”。
李建華研究生涯的轉折點發生在1997年。那一年,他在導師的引領下開啟了肝細胞癌分子機制的相關研究。起病隱匿、發展迅速、病勢兇險的肝細胞癌已上升至東南亞和香港地區致死率第三高的癌癥,因此探尋應對之策迫在眉睫。但由于腫瘤早期通常都是“不聲不響”的,所以很難引起民眾的警惕,而肝癌又更為特殊,即便是在中晚期,腫瘤大小也不會那么明顯。曾有業內專家稱:“在我們國家,只有1/4的患者會在早期發現,通過手術得以根治,而3/4的患者,有癥狀來到醫院治療時,病程已經發展到不適合做手術的階段了。即便創造條件治療了,效果差、復發率高的噩夢也始終伴隨著他們,這才是可怕的。”
2007年,索拉非尼藥物的出現讓人類看到了曙光。此藥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成為第一款肝細胞癌全身性治療藥物,有效改善了晚期患者的生存率。然而,好景不長,癌細胞對索拉非尼的耐藥性在病人長期服藥的過程中逐漸被激發出來,進而演變為阻礙生命延續的巨大關卡。這時,深入了解肝癌細胞對索拉非尼耐藥機制便成為了迫在眉睫的重要問題,吸引了無數研究者投身入局。而在2013年已被評為臨床醫學領域前1%“高被引”學者,在肝癌研究獨當一面的李建華也責無旁貸,果斷帶隊向其亮劍。經過數年研究,他證明了對索拉非尼耐藥后,癌干細胞(CSC)的干細胞特性會增強,靶向介導肝癌干細胞特性的信號通路可能是逆轉抗藥性的一種重要策略。
2016年,李建華帶著此疑問和猜想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學。“剛加入香港理工大學的時候,我只有一兩個學生,不過學校非常支持我的研究,為我提供了很多平臺和項目上的幫助。”從“一兩個人、三四條槍”的狀態壯大到十幾個人的隊伍,李建華用了多年,而關于對抗肝細胞癌獲得耐藥性的策略,在其團隊的成長過程中,也逐漸成型。
2021年,李建華團隊通過建立索拉非尼耐藥的肝細胞癌患者的源性腫瘤異種移植模型(PDTXs),發現EPHB2激酶在獲得性耐藥機制的形成中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據此,他們確定了一個EPHB2/β-catenin/TCF1的正反饋環,以調節肝癌的腫瘤干性和對索拉非尼的耐藥性。
“最初,經過測序及定量分析,我們發現肝臟腫瘤干細胞標志物在源性腫瘤異種移植模型中顯著上調,且肝癌組織中EPHB2的表達明顯高于正常及肝纖維化組織,這提示了EPHB2的致癌性。”為進一步研究EPHB2在肝癌中的促腫瘤作用,李建華團隊在免疫活性小鼠中進行了內源EPHB2的敲除,并發現此后腫瘤結節的大小和數量顯著減少,且小鼠的存活時間更長。接著,他們又通過探尋上下游效應因子及一系列體內外實驗,最終確定了一個可以調節腫瘤干性與耐藥性的EPHB2/β-catenin/TCF1正反饋環。
那么,EPHB2的下游效應因子究竟是什么?其發揮作用的機制又是如何?一系列疑問開始在李建華心頭不斷盤桓,為進一步揭示其中機制,他們很快開啟了下一步的探討工作。從探究EPHB2突變對β-catenin反式激活活性的影響切入,李建華發現當EPHB2被抑制時,β-catenin的反式激活活性被抑制且蛋白表達量降低,而EPHB2過表達的細胞情況則截然相反。此外,免疫沉淀實驗證明了EPHB2能磷酸化SRC激酶,進而導致AKT/GSK3β/β-catenin信號通路的變化。這共同證實了Wnt/β-catenin確系EPHB2的主要信號因子無疑。“但要聯合索拉非尼探究EPHB2體內治療的靶向性,還需要活體生物實驗來佐證。”李建華說。
而肝癌小鼠模型無疑是最優解。通過靜脈注射rAAV8-shEPHB2抑制EPHB2的表達,并在一周后給予小鼠30mg/kg的索拉非尼治療21天,李建華團隊成功獲取了實驗組與對照組小鼠的肝重/體重比,并分析發現rAAV8-shEPHB2聯合索拉非尼對腫瘤生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成功證明EPHB2通過TCF1/EPHB2/β-catenin正反饋環來調節腫瘤的干性和耐藥性,從而使靶向EPHB2與其他靶點聯合治療,成為肝癌靶向治療的全新可能。
“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以非常之策應對非常之難”,這是每位科研者每天都在做的事,但可喜的是,非常之難或可為人類健康事業帶來非常之功,而這始終是李建華心中的非常之追求。“腫瘤細胞上的特異性結構好比鑰匙孔,靶向藥好比一對一匹配的鑰匙,兩者一旦配對成功,即可開啟腫瘤細胞的凋亡之旅。而未來,我想讓這個過程開始得更早一些。”李建華說。
用“新”守護“心”希望
2023年,李建華入選斯坦福大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最近也獲頒香港理工大學理學院杰出研究員。這些榮譽既是對他多年科研生涯的肯定,也被其視作對下一步工作的鞭策。“現役的肝細胞癌治療方法主要有3種,即介入治療、免疫治療和靶向治療及放療,各有各的優勢,卻也都尚存痛點亟待解決。而無疑的是,科學決策和創造性應對永遠是化危為機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說,這條路還有很長,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
于是,李建華最近又以《一種基于肽嵌合抗原受體巨噬細胞靶向癌干細胞的全新療法》一文探討了抑制腫瘤干細胞(CSCs)特性療法的可能性。“腫瘤干細胞產生新腫瘤的增強能力表明,這些細胞可能在逃避免疫檢測方面具有優勢。所以我們團隊鑒定了幾個假定的肝臟腫瘤干細胞標記物,包括CD24和CD47。通過觀察,我們發現它們確實具有誘導巨噬細胞從而逃避吞噬作用的獨特屬性。”
基于這一觀察,李建華團隊進一步提出了“使用巨噬細胞靶向治療方法可能實現對肝臟腫瘤干細胞的弱點靶向”的相關假設。“盡管CAR-T細胞療法在治療血液惡性腫瘤方面取得過喜人成績,但其在實體瘤中的應用卻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T細胞不具備強穿透性且無法在腫瘤微環境中存活。”腫瘤微環境(TME)為癌癥的發生和發展提供著重要的生態位,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是腫瘤微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它是許多實體瘤的腫瘤微環境中最豐富的先天免疫細胞,可調節腫瘤細胞增殖、抗原呈遞及免疫逃逸和治療抵抗等各種腫瘤行為,在腫瘤進展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并且,這些功能特性使CAR-巨噬細胞(CAR-Ms)正在成為一種針對實體癌的全新免疫療法,以克服CAR-T療法的不足。而此結論的出現無疑點燃了李建華的熱情。
“傳統上,CAR-M療法指的是通過病毒感染將編輯過的特定CAR基因轉移到巨噬細胞中,但這種方法成本高昂、涉及程序繁瑣,并且在長期的安全性上保障不足。為了克服這些缺點,我們采用了一種替代方法獲取CAR-巨噬細胞,以減少其不確定性,縮短生產時間,且性能可逆。如果后續實驗一切順利的話,我們或許會實現通過質譜分析鑒定選擇性結合肝臟腫瘤干細胞受體表面的肽,來建立起肝臟腫瘤干細胞特異性的pCARMs庫;同時基于細胞模型的功能表征優化pCAR-Ms,并在相應的動物模型中評估其療效。總的來說,我們已經設計好了一種系統方法,致力于將pCAR-Ms策略推向肝細胞癌治療。”李建華說。
產學研用,理當貫通,從一開始,李建華的研究導向就十分明確:“我希望把研究成果應用至臨床,只有切實為患者帶來福音,我的工作才真正有價值。”而針對上述成果的落地推廣,李建華也早有布局,“我不會將碩果獨享,一定會在申報專利之后,將授權下放給醫藥公司來產業化我們的科研成果。由于肝細胞癌已經為香港地區乃至世界人民帶來太多的威脅和挑戰了,攜手共克疾病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在李建華的眼中心中,醫藥學的發展就是為生命延續而鑄造的基石,并且他堅信,隨著基因編輯手段的不斷突破及對業界腫瘤生成發展現象的深入研究,癌癥的治療手段只會愈加豐富多樣。在不遠的前方,針對高效低毒的新型腫瘤靶點的藥物研發、細胞療法的安全性和經濟性改造、克服耐藥性的聯合用藥方案及以預防和早期發現為主的精準醫療將是癌癥治療領域最引人注目的光亮。“即便我們現在仍處破曉之前,但曙光何其溫暖熾烈,只要熬過黑暗,終將融化堅冰。”李建華說。21世紀,人類和癌癥或將真正決出勝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