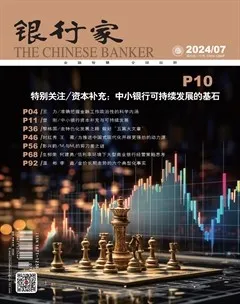M1與M2的剪刀差之謎
2024年6月14日,央行公布了5月末中國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后,引起廣泛的關注。不僅因為同比7%的廣義貨幣(M2)余額增長率創下了20年來的最低水平,還因為狹義貨幣(M1)余額出現了同比下降4.2%的鮮見現象。鑒于貨幣對國民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筆者就中國貨幣供應總量與結構做一些分析。
中國貨幣總量充裕:低貨幣增長率并不意味著貨幣緊縮
在討論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變化時,有必要先看看中國的貨幣總量。從國內外比較來看,中國現在的貨幣總量非常充裕,流動性總量寬松,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2024年5月末,中國M2總量已達301.85萬億元,按同期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5月末收盤價)計,相當于41.67萬億美元。2024年4月末美國M2余額為20.97萬億美元,中國M2的余額接近于美國的一倍。而在2023年末,按當時的匯率折算,中國M2的余額為41.21萬億美元,而美國、歐元區和英國M2的總和為41.43萬億美元(見圖1),中國M2已相當于美國、歐元區和英國的總和,是2023年末日本M2余額(8.80億美元)的4.68倍。回顧過去,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中國M2余額僅相當于美國、歐元區和英國總和的16%左右,也僅相當于日本的29%左右。僅僅20余年的時間,世界貨幣總量的格局已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就當下而言,以M2的余額來衡量,說中國是全球貨幣供應量最充裕的國家,是不為過的。
隨著貨幣余額的增長,中國的金融相關比率(M2與GDP之比)也不斷上升且已處于全球最高水平。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金融相關比率一直高于其他幾個國家。從圖2中可以看到,2023年末,中國M2與GDP之比為231.85%,日本為209.67%,英國為112.38%,德國和美國均不足100%,分別為91.57%和76.35%。尤其是,當人們都在說美聯儲“放水”的時候,美國的M2與GDP之比不足中國的三分之一,多少有些讓人覺得意外。
盡管2008年危機后,美國采取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急劇擴張,但美國的M2與GDP之比并沒有相應地急劇上升。在危機前的2005年與危機后的2010年,美國的這一比率分別為51.45%和58.56%,同期,中國的這一比率分別為159.49%和176.13%,到2023年末,美國和中國的M2與GDP之比分別上升至了76.35%和231.85%。這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M2增長率其實明顯高于美國的增長率。進一步與其他主要經濟體進行比較后,也不難發現,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也是最高的。
毫無疑問,中國較高的貨幣供應增長率和高貨幣化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盡管中國也曾出現過較高的通脹率和資產價格泡沫,但貨幣供應總體上與名義GDP增長率是相稱的,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見圖3),更高的名義經濟增長率往往伴隨著更高的貨幣供應增長率。這反映了收入、價格與通脹預期對中國貨幣需求的影響。如今,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潛在增長率和收入增長率下降,貨幣需求的增長率也相應地下降了,質言之,未來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下降,順應了貨幣需求增長率的下降,是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后,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結果。這正如央行行長潘功勝在2024年陸家嘴論壇上所說的“金融總量增速有所下降也是自然的,這與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在中國貨幣總量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后,即便面臨著經濟下行的挑戰,如果想依靠進一步采取大規模刺激性的寬松貨幣政策解決問題,可能會為以后的穩定與發展帶來更加棘手的問題。過去中國M2總量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既有高儲蓄率的因素,也有信用擴張的因素。因為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下,M2是通過銀行貸款來創造的,過去中國的高貨幣增長率就是信貸較高增長的結果。如今巨量的M2也對應巨額的債務總量,所以我們看到,中國貨幣總量擴張的背后伴隨著杠桿率不斷攀升。通過計算發現,到2023年,中國的全部債務與GDP之比已達350%左右,如此高的宏觀杠桿率,恰恰是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的一個重大隱患。
早在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的講話中就指出:“去杠桿,千招萬招,管不住貨幣都是無用之招。過去我們常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加物價上漲率、再加一定其他因素來界定貨幣供應增長的合理區間。按照這個標尺,當前貨幣信貸總體是比較充裕的。我們要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堅決管住貨幣信貸、防止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這是總閘門。貨幣政策實施要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系,既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促進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也防止貨幣供應過于寬松而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毫無疑問,當我們在討論穩健的貨幣政策時,對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番講話,應當加以深刻地領會。
貨幣總量背后的結構變動:揭開M1與M2剪刀差之謎
在貨幣總量達到高位水平的同時,貨幣結構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使得各個層次的貨幣統計的經濟意義可能發生了重要變化。
貨幣結構的變化,首先表現為,隨著銀行卡與移動支付的興起,經濟交易中的現金需求大幅下降,因此,經濟交易與貨幣需求的非現金化趨勢在不斷深化。在20世紀80年代,流通中的現金(M0)與M2之間的比率總體保持在20%以上,但自1990年以來,這一比率呈現不斷下降之勢,2015年以來,一直低于5%(見圖4)。

貨幣結構與支付方式的這一變化,直接降低了流通中現金與宏觀經濟表現之間的相關性。質言之,在非現金支付的時代,流通中的現金與通脹(預期)、收入都沒有直接而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了。進而,M0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大幅下降了。盡管如此,受習俗(紅包、壓歲錢等)的影響,人們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現金需求,尤其是在年末和年初,央行投放的現金往往會明顯增長,這也使得流通中的現金余額呈現較強的季節性。具體地說,就是在春節所在的月份里,流通中現金會大幅度增長;春節過后,現金增長率就會迅速地回落到正常的趨勢性水平上。例如,2019年元月,現金增長率達17.2%,但2月份就出現了-2.4%的增長率,接下來的3—12月則保持在4%—5%的增長水平。
移動支付的廣泛應用導致流通中的現金比率出現了下行趨勢,也導致流通中的現金增長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低于M1和M2的增長率。然而,在移動支付已然得到廣泛運用的現實條件下,2024年5月,流通中的現金增長率達到了11.7%,遠高于7%的M2的增長率,更不用說同比為-4.2%的M1的增長率。這種現象簡直匪夷所思。因為這種較高的流通中現金增長率并非春節等季節性因素導致的臨時性上升。實際上,自2022年以來,流通中的現金增長率就大幅度高于過去的趨勢性水平,2022年,除5月份現金增長率只有5.8%外,其他月份總體保持在13%以上,2023年至2024年的現金增長率雖然較2022年有所下降,但仍明顯高于過去的趨勢性水平(見圖5)。根據《地下經濟學》,現金交易越活躍的地方,越有可能存在活躍的地下交易。2022年出人意料的現金增長率,或因此前警方通過二維碼支付發現違法線索并成功抓捕嫌疑人,一些從事地下交易的人發現掃碼支付增加了自己違法會被警方追蹤、曝光并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性,于是轉而回歸使用現金這種“匿名、不可追蹤”的傳統支付方式,從而導致現金發行量的大幅增長。
同M0與M2之比持續下降一樣,M1與M2之比也一直在持續下降。20世紀80年代之初,M1與M2之比高達近90%,之后,這一比率便持續下降。1995—2010年,這一比率大體保持在近40%,相對穩定。然而,2011年以來,M1與M2之比便出現新一輪的下行趨勢(見圖6),到2023年降至22%左右。在中國的貨幣結構中,M0的占比持續下降是支付技術變革的結果,但這種技術變革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企事業單位活期存款在貨幣總量構成中的占比變化。貨幣統計上,M1由流通中的現金和企事業單位的活期存款構成,由于企業事業單位的支付往往是通過賬戶活期存款轉賬進行的,從理論上說,M1與經濟交易的活躍度的相關性最強。
在M1/M2持續下降的同時,近年來,M1增長率也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尤其是,在后疫情時代,當經濟與社會生活恢復至正常狀態后,M1的增長率卻一直在下降。2024年5月,在流通中現金保持明顯較高增長率的情況下,M1卻出現了負增長,這讓許多分析者感到驚訝。央行行長潘功勝在2024年陸家嘴論壇上表示:“個人活期存款以及一些流動性很高甚至直接有支付功能的金融產品,從貨幣功能的角度看,需要研究納入M1統計范圍,更好反映貨幣供應的真實情況。”然而,實際上,把個人活期存款加入M1后,依然可以看到,這并沒有改變M1增長率持續下行的狀況。例如,我們將個人活期存款加入原有M1后得到新口徑的M1,其在2024年5月份的增長率仍然為-0.8%,沒有改變負增長的狀況(見圖7)。
因此,要探究M1與M2增長率之間的剪刀差,需要從M2的各個構成中去考察。

M2由M1加上“準貨幣”構成,是故,M1與M2之比下降,對應著M2構成中“準貨幣”的上升;M2增長率與M1增長率之間剪刀差的擴大,是因為準貨幣的增長率遠高于由流通中現金和單位活期存款構成的M1的增長率。
分析M2中“準貨幣”占比的上升,需要進一步考察其各個構成部分的變動。在現行的貨幣統計中,“準貨幣”又包括居民(個人)儲蓄存款、企事業單位定期存款和其他存款。
先看居民儲蓄存款。20世紀90年代,居民儲蓄存款在“準貨幣”中的占比總體高達80%左右(見圖8),企事業單位定期存款占比則不足20%。但進入新千年之后的前十五年里,居民儲蓄存款占比持續下降,2015年下降至大約56%的水平。之后開始出現了緩慢的回升,到2023年末升至61.48%,較之前的低點大約上升了5.5個百分點。由于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分為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在當今主要依賴第三方支付的時代,居民的購物也基本是通過其活期賬戶轉賬來實現的,如果說居民儲蓄存款沒有參與經濟交易過程是不恰當的。正因為如此,筆者也一直主張,應當將居民活期存款納入M1的統計中。但是,居民儲蓄存款中的定期存款部分,主要是發揮著價值儲藏的職能而不是發揮著支付的功能。


盡管近年來居民儲蓄存款在“準貨幣”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但居民儲蓄存款的構成中,活期存款占比卻在持續地下降,定期存款占比則在持續地上升。2019年初,居民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比重接近39%(見圖9),然而到了2024年5月,這一占比已降至27%左右。這可能反映了兩個事實:一是由于近年來收入增速放緩,人們對貨幣的交易性需求也隨之放緩;二是由于股票市場持續低迷,人們對投機性貨幣的需求減弱,流動性偏好的下降,使得許多人重新將金融資產配置到了定期存款中。
關于M2與M1增長率之間的剪刀差,更大的秘密隱藏在非金融企業的存款構成中。在統計上,構成M1的活期存款中,包括非金融企業的活期存款和事業單位的活期存款。先看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與構成M1主體部分的“單位活期存款”之間的相對變化。從圖10中可以看到,2019年初,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占“單位活期存款”的比重達到52%左右,隨后便開始震蕩下行。到了2024年5月,這一占比就降至了42%左右,在不到五年半的時間里,下降了10個百分點。
因此,M2保持了7%的增長而M1出現-4.2%的增長(M2與M1之間剪刀差擴大),一定對應著“準貨幣”中企事業單位的定期存款在不斷增加、企業事業單位的定期存款增長率明顯高于活期存款增長率。事實也是如此。圖11顯示了中國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增長率的變化。可以看到,自2017年以來,非金融企業的定期存款增長率就一直高于活期存款增長率。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23年5月以來,除了2024年1月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略有增長外,其余月份非金融企業的活期存款增長率就一直為負,特別是2024年4月和5月分別為-11.52%和-14.42%。當然,2023年5月以來,非金融企業的定期存款增長率也在下降,不過仍然保持著正增長。2024年4月和5月非金融企業定期存款增長率分別為3.98%和4.29%,在過去兩年左右的時間里,非金融企業定期存款增長率一直高出活期存款增長率10個百分點以上。
因此,非金融企業的存款定期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圖12顯示,中國非金融企業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之間的“喇叭口”在近年不斷擴大。2011年,企業定期存款相當于其活期存款的1.15倍(見圖13),但到了2023年末,則上升到2.1倍,2024年5月末上升到2.54倍。
如果說居民活期存款是基于交易動機和投機動機而持有的流動性偏好,非金融企業的活期存款則是基于營業動機而持有的流動性偏好。因此,無論是居民活期存款與居民定期存款之比的下降趨勢,還是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與其定期存款之比的下行趨勢,都表明經濟交易的活力有所下行。對非金融企業而言,面對各類不確定性的上升,要想通過經營保持良好的盈利,難度在不斷上升(對應的是工業企業資產利潤率的下降),企業家和經營者們對未來的弱預期,使其基于營業動機的貨幣需求降低。
與之對應的另一面,是居民和非金融企業的存款定期化。在我國M2中,當前有近80%是由儲蓄存款、企事業單位的定期存款等“準貨幣”構成,這一部分屬于沉淀或“沉睡”的貨幣,“準貨幣”占比越高,貨幣的流動性越低,未進入經濟循環流轉過程的貨幣就越多。企業定期存款相對于活期存款增多,可能從一個側面說明,一些企業借助于銀行間的競爭和協議存款的利率優勢而進行套利和資金空轉。對單家銀行而言,這種套利行為可以增加流動性較低的負債的來源,但對整個銀行體系而言,由于非金融企業的經營活力和價值創造意愿減弱,這種套利行為反而會對銀行體系的長期穩定造成潛在的隱患。
總結起來講,在中國貨幣總量非常充裕的背景下,我們更應當關注貨幣結構變動背后的因素。就短期而言,單純調整統計口徑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M2與M1之間的剪刀差,持續下降的活期存款占比,實際上反映了居民和企業家(經營者)對未來的弱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講,改善貨幣環境,根本措施應當是通過改革切實穩定人們的預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