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里的少年精神與盛世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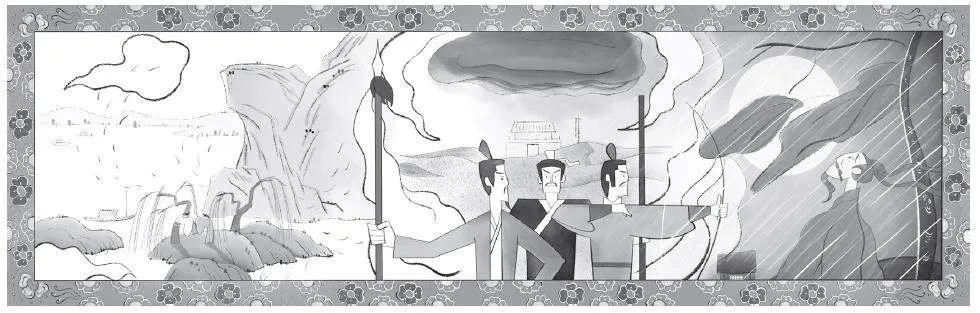
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曾說過:“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就總體特色而言,唐詩重情趣,宋詩重理趣。特別是盛唐詩歌,充盈著一種青春活力和激情想象,即便是享樂、頹喪、憂郁、悲傷,也仍然彌漫和律動著一種青春的氣息。著名詩人林庚先生將這種氣息稱為“少年精神,盛唐氣象”。
唐代詩人大都喜歡用熱烈的情感來感受生活,把熱烈的情感寫到詩中。諸如:“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王維),“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李白),“一生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岑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中充滿激動人心的激情和感發人心的力量,讀了讓人振奮、心神蕩漾。下面從三個方面談談唐詩中所體現的人文精神。
溫馨的平等友善精神
我們知道,從生命的意義上講,人都是平等的。唐代詩人在人際交往中能夠樹立平等理念,不分地位高低,出身貴賤,一律真誠相待,平等相交,洋溢著友善溫馨的氣息。
如詩仙李白晚年在安徽馬鞍山時,皖南有涇川豪士汪倫特別喜歡李白,遂致信詭稱:“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李白一見有美景美酒便欣然前往。到了一看,山村很小,遂不解發問。汪倫乃笑告曰:“‘桃花’者,潭水名也,并無桃花;‘萬家’者,店主人姓‘萬’也,并無萬家酒店。”李白聞之開懷大笑,款留數日,離別時汪倫親自送行。李白感其美意,寫了著名七絕《贈汪倫》。
又如詩人兼畫家王維,多才多藝,在盛唐詩人中享有盛譽。但他與普普通通的詩人也都能友好交往。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中的元二,就是一個不知名的詩人。只知他姓元,排行老二,連什么名字都湮沒無聞,但這首詩卻是唐人送別詩中最有名的一首。
王維還有一首《送沈子福歸江東》詩,所送沈子福也是一位籍籍無名的詩人: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蕩槳向臨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詩人將自己對朋友的相思之情明喻為春色:春色無邊,則對你的相思之情無邊;春色無處不在,則相思之情無處不在;你走到江南也好江北也好,都置身于濃濃的春色之中,那包圍著你的濃濃的春色,就是我的相思之情在時時刻刻地陪伴著你。何等溫馨,何等熱烈!
唐代詩人相互之間能心心相印,命運與共。人之相知,莫過于知心;知心莫過于命運相通,惺惺相惜,比如,李白與杜甫。公元744 年,44歲的李白失意地離開長安來到洛陽,遇見了33 歲的杜甫,兩個人一見如故,攜手漫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杜甫描寫與李白一起游玩的美好時光是:“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分別后,李白寫過兩首詩懷念杜甫,其中有句曰:“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杜甫更是感情深厚,寫了十五六首詩歌懷念李白。特別是李白因“從璘”案入獄后,杜甫寫下《不見》詩: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
詩人向世人表明,對于“皆欲殺”的朋友,自己卻獨獨憐惜其才華和人品,坦蕩地表達對朋友蒙冤的深切同情。
高昂的進取精神
當時的社會氛圍鼓勵人們有所作為,通過立邊功求取封侯,出將入相,時代激發了讀書人投筆從戎的熱情和尚武精神。正如李賀的《南園》詩寫道: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
此詩抒發的就是唐代詩人的這種不愿久事筆硯之中,渴望到邊疆去施展才干的豪情和心態。
唐人邊塞詩十分發達,著力抒發詩人們一往無前的豪邁氣概和高昂樂觀的進取精神,具有為強大國力所激發起來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如楊炯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高適的“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王維的“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誰不知道到邊疆打仗的艱苦呢,但好男兒為了國家,縱然是戰死沙場,化成白骨,那白骨也是香的。為國捐軀,縱死不辭,何等豪情!
在其他題材的盛唐詩歌中,也同樣充滿了激情。如李白的《行路難》中曰:“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杜甫的《畫鷹》中曰:“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李頎的《送陳章甫》中曰:“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這些詩句都展示了詩人的自信和力量,讓人激情涌動,昂揚奮發。
崇高的利他主義精神
古代志士仁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修齊治平,奉獻自我,造福社會。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讀書人歷來具有“達則兼善天下”的報國濟世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了從古到今一代代知識分子精神里的優秀基因。
唐代詩人中,杜甫被尊為“詩圣”,圣在哪里?圣就圣在他總是從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民的不幸;越是想到他人的不幸,越是忘記了自己的不幸。杜甫晚年在成都草堂寫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開頭寫道: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他提筆就寫茅屋被秋風刮破的情景,很有沖擊力,給人一種極度緊張的身臨其境的感覺。接下來寫狂風之后又下起了大雨,詩人的屋子到處漏雨,一家人通宵難眠,寫自家人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最后一段寫詩人在痛苦不眠之夜所產生的宏偉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如果能有廣廈千萬間,庇護著天下窮苦的人,生活都能夠非常的歡樂溫暖,那該多么好啊!詩人從自己眼前的不幸遭遇,聯想到天下人民的不幸,從而產生了一種甘愿為天下人民的不幸,而犧牲自己的偉大情懷。“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什么時候眼前能高聳起廣廈千萬間,讓天下的人都住進去,我一個人受凍,哪怕是凍死了也心甘情愿。全詩在此高潮中戛然而止,給人一種強烈的心靈震撼。這是一種多么偉大的利他主義精神,一種為了他人而甘愿犧牲自己的崇高胸懷!
這里我們將杜甫的詩和白居易的《新制布裘》詩作一個比較。白居易前期繼承了杜甫憂國憂民、關心民生疾苦的優良傳統,創作了《新樂府》《秦中吟》等共六十首詩,表達“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愿望。
有一年,白居易夫人給他新做了一件布裘,詩人穿在身上很暖和,于是寫了《新制布裘》,前面說這件布裘怎么好、怎么暖和,最后說:“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這是化用《孟子》中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接下來說:“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如果能找一個萬里大的裘衣,把四面八方都蓋裹起來,人們都像我一樣暖暖和和,普天下就沒有饑寒交迫的人了。白居易也很了不起,但宋人黃徹在《?溪詩話》中說:白居易是“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寧苦身以利人”。白居易說我暖和了,推己及人,希望天下人跟我一樣暖和;杜甫說只要天下人全暖和了,只有我一個人凍死了我也心甘情愿。我們稱杜甫為詩圣,圣就圣在“寧苦身以利人”。
(摘自《博覽群書》2024 年第2 期,本刊有刪節,佟毅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