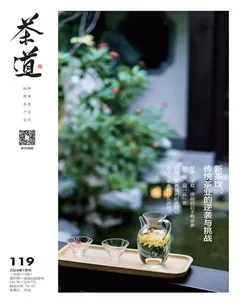莫愁夏日長 小院喝茶去



夏日漸長,若能有個小院度夏,再泡上一壺茶,喧鬧的世界就被隔離在外了。
壹
偶然在森林公園漫步,路過—個院子,看見別人家的院墻里,探出一串玉蘭花,再仰頭看,蔥翠高大的芭蕉樹,結滿一串串飽滿誘人的果實。這樣的景致勾起心中的向往:何時我也能有一個小院子?
小院只有一個簡單而樸實的名字——森林驛棧。既是驛棧,便隨緣進去歇腳泡茶。柴門半開,一大小兩只貓作為門童迎客。主人話語不多,只將庭院里的園林造景噴霧打開,取來收集的山泉水,便又忙活去了。
細膩的小水霧像云煙一樣隨風而動,清風徐來,涼意流動,水霧還驅散了蚊蟲。院中有主人親手布置的盆景、菖蒲、蘭花、奇石。尤其菖蒲養得極好,以石易土,菖蒲附于石上,頓生江湖氣。可見主人的“文人氣節”。四周郁郁蔥蔥,一派“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的景象。
問起為何打造小院?主人答曰:“生意失敗,干脆退休。”院外是紅塵滾滾不由我,院內是自己的精神天地。錢是賺不完的,人卻沒有不老的時候。在城市中忙碌又浮躁不安的我們,何嘗不想遇到屬于自己的小院,安身立命,從容生活,在這小院里收獲心靈的安寧和沉淀,享受生命最本真的恬靜樂趣。
貳
在中國,約九成的人心中都懷揣著對院子的深情厚意,特別是那些揮毫潑墨的文人墨客。
作家馮唐在其作品中提及,人生中有四大難得之事:“后海有樹的院子,夏代有工的玉,此時此刻的云,二十來歲的你。”院子的存在,無疑是他們心中向往的生活象征。
林語堂先生亦曾暢談人生之樂趣,其中就包括了“宅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樹,樹上見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他渴望擁有這樣的院子,用以承載他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對閑逸生活的向往。
巴金在《寂靜的園子》中描述:“現在園子里非常靜,陽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樹上,給那些綠葉涂上金黃色。兩只松鼠正從瓦上溜下來,這兩只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取樂。”巴金的院子,是靜聽松風、賞花聞香的所在。
書畫家張伯駒的院子,薔薇滿架,牡丹芍藥如云似錦。而作家張恨水的院子,則是槐花潔白,清香四溢。每當有客來訪,他總會輕聲提醒:“往旁邊走,別踩著花。”
院子,是人間的—份寧靜與歡愉。無需廣闊,無需奢華,只需有花相伴,便能陪你走過四季。春有芍藥牡丹,夏有荷花石榴,秋有山菊傲霜,冬有雪梅初放。每個季節都有它獨特的風景,如同夢境般年年重現。
古語有云:“格物致知。”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們與自然、四季的聯系似乎越來越淡。而院子,正是我們與自然重新建立聯系的橋梁。踩在泥土上,感受大地的脈動。愿我們都能擁有—個屬于自己的小院子,即使外面的世界喧囂不止,我們亦可在其中細嗅薔薇,擁有每一刻春秋冬夏。
叁
“現在園子里非常靜,那里是我的家,我生在那里,長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磚都是我的生活標記。”老舍先生筆下的院子,是他成長的搖籃,那里有著平坦的土地供他打太極拳,還有他心愛的花貓、金魚、蟈蟈相伴。炊煙裊裊,家人圍坐,盡享天倫之樂。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繪的稻花村,宛如一幅歸隱田園的畫卷。那里瓜果飄香,繁花似錦,雞鴨嬉戲,黃狗悠閑。田園生活自給自足,寧靜而美好。
梁實秋先生的院子,則是他與朋友相聚的雅致之所。月光如水,梨樹下品茗,忘卻外界紛擾,只留茶香與友情相伴。
建筑學家梁思成說:“對于中國人來說,有了一個自己的院落,精神才算真正有了著落。”院子,無疑在中國文化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幾乎成為一種集體的憧憬和追求。這既是中國人骨子里的天性,也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使命。
想象一下,若能擁有一座四季皆宜的小院,生活將會多么豐富多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欣賞花木蔥蘢,竹影搖曳;細雨綿綿時,則可以聆聽雨打芭蕉的旋律,感受苔蘚翠綠的臺階。獨自一人時,可品茶、讀書、聽歌、種花,盡享寧靜與悠閑;周末時光,則可邀請三五知己燒烤暢飲,讓煩惱隨風飄散。在這里,可以聆聽鳥鳴鶯歌,觀賞貓狗嬉戲,無需過多言語,只需沉浸在這如畫般的風景中,便能感受到內心的平靜與安寧。
愿我們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這樣一座屬于自己的小院,擁有—個屬于自己的小天地,讓余生充滿安寧與愜意,隱于庭院,不爭世事,心亦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