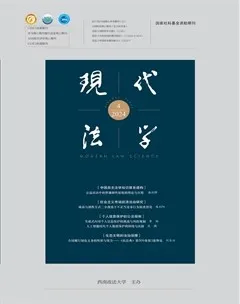關系法理的建構與運用:以夫妻忠誠協議再認識為例

摘 要: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之爭背后是三點預設:家庭關系與合同模式存在錯位;協議財產屬性的弱倫理性與人身屬性的強倫理性相互對立;法律強制與情感關系不相匹配。三點預設使得效力之爭徘徊于個人本位—家庭本位兩造之間而久無定論。“關系法理”以關系契約理論實現了婚姻與合同關系的溝通,為忠誠協議參照適用合同編提供依據。對關系結構的強調,使得人身與財產關系背后共同的倫理屬性得以揭示。“關系性解紛”關注關系事實本身,而非僅僅協議文本;以維護良性關系、阻卻惡性關系而非規制個人為目標;以“關系性自主”而非“個人真意表示”為效力前提;以“關系性善”而非“個人利益”為價值基礎。忠誠協議可區分為“規范型協議”和“累積型協議”,并根據解紛需求適用審判程序和調解程序。最終,法律對情感關系的態度既非以力有不逮為由的回避,也非家長主義式干預,而是一種有效回應和反饋式調整。
關鍵詞:夫妻忠誠協議;關系法理;關系契約理論;關系性方法
中圖分類號:DF03 文獻標志碼:A
引 言
現代制度在許諾一個更為自主多元的生活方式的同時,又必須對相伴而生的內聚力不足、外控力弱化和價值失范作出回應。人們在主張更少干預的同時,亦對公權力的回應和治理能力提出更多期待。法律由此常常面對自由與團結、自主與干預、社會秩序內生與國家秩序建構這類相互矛盾的訴求。家庭關系的泛契約化及其爭議可謂上述張力的生動體現,從未有過一個領域如家庭一般,在有著如此強烈的私密性和自主性需求的同時,又承載著顯著的倫理道德期待。現有法律實踐和理論對此呈現出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之間的搖擺態度,如何突破此種困境值得探討。
本文由是錨定于實踐中已經成為一種現象的夫妻忠誠協議(以下簡稱為忠誠協議)的性質與效力問題,一方面對此作出切實回應,另一方面以該問題為載體,對“關系法理”的分析進路作一呈現。所謂忠誠協議,是指夫妻雙方為維護婚姻關系的排他性,對雙方行為方式作出要求,并通常伴有違反義務相應后果的契約。選取忠誠協議一例,有如下兩點原因:第一,忠誠協議既反映了法律所倡導的忠實義務,又因其契約形式而區別于已有的明確規定,凸顯出“活法”與“國法”的張力。第二,相較于代際關系,現代社會對于婚姻關系的價值基礎和互動模式,有著更為多元復雜的觀點。作為兩個本無血緣關系的人相互的凝聚與結合,婚姻關系在社會秩序建構、人口再生產等方面的作用固然舉足輕重,然而公權力對此種關系的介入往往需要更為充分的理由。因此,忠誠協議可以作為鮮活一例,以說明在面對棘手的張力問題時,關系法理何以具有顯著優勢,以厘清法律的價值理念、功能定位和規制方案。
本文第一部分詳細呈現忠誠協議效力認定所面臨的爭論。第二部分分析指出,爭論背后實則普遍依賴三點預設和二元框架。正是這些預設與框架構筑了效力認定難題,其本身值得反思。第三部分引入“關系法理”,并在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具體說明如何利用關系法理理論對忠誠協議的性質與法律效力認定展開分析。這一方法能夠為現行法律規定提供新的解讀和說理邏輯,使法典化時代的法律運行更符合制度安排的初衷,司法論證更為融貫有力,現實需求得到充分關懷。盡管本文以忠誠協議為例,將家庭作為論述的場域,但是關系法理具有突破家庭問題的生命力。余論部分通過數據權、冷凍胚胎權等例,進一步說明關系法理何以廣泛運用于各種法律經典與新興議題,并提出展望。
一、忠誠協議效力問題的法律異見與理論之爭
(一)法律制度下的協議定位之困
首先,實踐中的忠誠協議拓展了忠誠義務的具體內容和違反后果,并且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所明確規定的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從而溢出于婚姻家庭編的規制范圍。《民法典》第1043條第2款僅對夫妻忠誠義務作出原則性、基礎性規定,并未闡明忠誠義務的具體含義,也未設定違反義務的后果。《民法典》第1043條第2款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雖然第1042條第2款規定禁止重婚,并且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第1091條也規定了因為配偶重婚、與他人同居等重大過錯而導致離婚時,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但上述條款僅適用于嚴重情形,不涉及偶發婚外性行為等情況,抑或僅在離婚階段發揮作用。相較而言,實踐中的忠誠協議不僅涉及社會所普遍承認的家庭倫理和對嚴重情形的制約,還可能包含夫妻個性化的互動。例如,在陳某1訴王某等物權確權糾紛案中,除卻婚外性行為,協議雙方還將與異性超出正常交際的親密行為、長期頻繁且無法合理解釋的信息往來等推定為對忠誠義務的違反。參見陳某1訴王某等物權確權糾紛案,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21)粵0605民初19542號民事判決書。此外,忠誠協議的違反未必導致離婚,訴訟可能發生于婚姻延續過程中。部分學者僅承認離婚訴訟中忠誠協議的可訴性,參見冉克平:《“身份關系協議”準用〈民法典〉合同編的體系化釋論》,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1年第4期,第84頁。但這種觀點不符合現實需求和司法實踐,已有研究對其進行反駁,參見王雷:《論身份關系協議對民法典合同編的參照適用》,載《法學家》2020年第1期,第40頁。《民法典》目前所明確規定的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身份關系確立、變更與消滅。例如意定監護協議、收養關系的確立或解除協議。第二,基于身份關系調整而進一步所做的財產及債務安排。如離婚夫妻財產處理和補償給付協議、遺贈扶養協議。第三,身份關系改變后,延續型權利義務的分配安排,如父母之間有關未成年子女撫養問題的協議等。然而忠誠協議既非對關系類型的重設,也非對財產的安排,而是對關系存續過程中身份行為履行方式的約定,情形不同于既有法律規定的協議類型,其特殊性愈發彰顯。
其次,忠誠協議因其協議模式而涉及合同編的適用,法律在該問題上存在模糊地帶。最高人民法院有關《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司法解釋的第4條規定,對于僅以《民法典》第1043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案件,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4條規定:“當事人僅以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可見,司法對于夫妻忠實義務的干預秉持克制謹慎的態度。然而,忠誠協議以其協議形式讓這一問題重回司法視野之中。《民法典》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2條第2款僅規定“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并未言明能否參照適用《合同法》。相較于此,《民法典》合同編第464條第2款規定:“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有關該身份關系的法律規定;沒有規定的,可以根據其性質參照適用本編規定。”這一規定雖仍顯模糊,但打開了婚姻家庭編與合同編的溝通通道,推動法官在溝通兩者之間作出積極的嘗試,而不輕易回避身份關系協議的效力問題。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62-66頁。其中指出,對忠誠協議的糾紛處理,應結合審判經驗,進行類型化分析。對于忠誠協議能否適用《民法典》合同編關于違約責任的規定,需要認真對待。
(二)司法裁判之間觀點矛盾
忠誠協議的司法實踐自2004年“空床費案”開始進入大眾視野。本案中,夫妻雙方約定如果丈夫0時至7時不回家,則每小時支付空床費100元。人民法院最終以約定為真實意思表示為由,承認約定效力,
而圍繞此案的討論爭議至今未絕。參加劉加良:《夫妻忠誠協議的效力之爭與理性應對》,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4期,第107頁。
司法對此存在觀點搖擺。以2021年至2022年審結的司法判決為例,裁判呈現兩極態度:肯定式判決以尊重真實意思表示為由承認其效力參見
田某與蘇某1離婚后財產糾紛案,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區人民法院(2020)湘0304民初4204號民事判決書。;否定式判決則認為忠誠協議的內容夾雜了人身、情感因素,不能適用合同編法律規范加以調整。參見湯某訴付某離婚后損害責任糾紛案,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人民法院(2021)魯0811民初11734號民事判決書;文某訴黃某離婚后財產糾紛案,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區人民法院(2021)湘1002民初3617號民事判決書。此外,忠誠協議僅僅作為道德約束發揮作用,而無法律強制力,亦不可作為財產分配或確定子女撫養問題的依據。參見湯某訴吳某1等共有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1)滬0115民初90376號民事判決書。在胡某訴張某某等第三人撤銷之訴案中,法院在一審中根據《承諾書》判決男方向女方支付賠償金,此后又以“忠誠協議應由當事人本著誠信原則自覺自愿履行,法院不應予以受理”為由,裁定撤銷原判。參見胡某訴張某某等第三人撤銷之訴案,湖南省長沙縣人民法院(2022)湘0121民撤2號民事判決書。在否定式判決的基礎上,法院可能進一步根據《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91條規定,酌定支持對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參見湯某訴付某離婚后損害責任糾紛案,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人民法院(2021)魯0811民初11734號民事判決書;湯某訴吳某1等共有糾紛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1)滬0115民初90376號民事判決書。
然而前述裁判說理并不充分,且存在矛盾。第一,無論是忠誠協議效力的認同者
抑或反對者,都可將“維護家庭倫理”作為捍衛自身觀點的理由,司法未能對此提供融貫的說理邏輯。第二,如果僅因為協議涉及情感道德范疇而否認協議的法律效力,無法解釋為何法律對于同屬這一范疇的針對子女撫養問題的協議效力予以承認。況且,涉及婚姻家庭的訴訟糾紛往往無法避開人身、情感因素,僅以此為由隔絕對《民法典》合同編的適用,那么《民法典》合同編第464條第2款將形同虛設。第三,無論是強調意思自治的肯定式判決,還是主張協議應由夫妻自主自愿履行的否定式判決,都展現出法院謹慎克制的態度,避免對夫妻雙方關系作出實質評價。但當法院繞開忠誠協議爭議,適用第1091條對無過錯方賠償予以支持時,仍需結合事實對雙方過錯程度進行衡量,且需排除當事人約定的協議內容而酌定賠償金額,其司法裁量的空間不減反增,與法院所說“法律對于情感道德領域不得過多干涉”的理由并不吻合。概而論之,裁判說理仍有增強融貫性和精細度的空間。
(三)理論探討中對話基礎缺失
理論界通說認為,倫理屬性強弱是身份關系協議能否適用合同編規則的重要標準參見劉征峰:《民法典中身份關系法律適用的原則與例外》,載《中國法律評論》2022年第4期,第74-75頁。,而“倫理屬性問題”又進一步轉化為“協議中人身屬性與財產屬性的協調”問題。“財產協議說”“附條件財產約定說”認為忠誠協議以身份關系為條件,以財產為結果參見王雷:《論身份關系協議對民法典合同編的參照適用》,載《法學家》2020年第1期,第40頁;孫良國、趙梓晴:《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律分析》,載《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9期,第272頁。;“身份協議說”強調協議以人身義務的履行為本質,而財產關系僅僅為附隨的第二性義務參見李姍萍:《民法典時代背景下的忠誠協議》,載《交大法學》2022年第5期,第110-113、120頁。;“包含延緩條件的民事身份法律關系說”試圖兼容人身性和財產性,認為協議在一方違反忠實義務之前就已生效,而不是在條件成就時才生效。財產給付和非財產給付是忠誠協議的正反兩面。參見隋彭生:《夫妻忠誠協議分析——以法律關系為重心》,載《法學雜志》2011年第2期,第39頁。亦有研究依據約定的違約后果內容是財產賠償還是人身安排,作出對財產型和人身型的區分討論參見鄒開亮、邰帥:《夫妻忠誠協議的性質及其對內效力——基于社會關系“泛”契約化的一般認識》,載《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第82頁。,甚或作出財產給付型、權利放棄型、傷害虐待型等更為細致的劃分。參見劉加良:《夫妻忠誠協議的效力之爭與理性應對》,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4期,第101-102頁。
與性質界定相對應,主張財產屬性的理論傾向于承認忠誠協議對合同編的適用,但要求賠償金額合乎比例,尤其否定“凈身出戶”條款的效力。主張人身屬性的理論內部存在分歧,有觀點將忠誠協議視為“自然之債”“道德義務”,從而排除適用合同編以承認協議法律效力的可能;亦有觀點基于合同有效性標準作出認定,認為如果協議以婚姻關系終止或子女撫養問題作為違約后果,則此類約定因為違反離婚和撫養問題的法律規定而屬無效。有關此類爭議,參見王歌雅:《夫妻忠誠協議:價值認知與效力判斷》,載《政法論叢》2009年第5期,第41頁;李姍萍:《民法典時代背景下的忠誠協議》,載《交大法學》2022年第5期,第118-119頁。部分理論則徑直否認人身及財產屬性協調的可能性,認為后者將導致婚姻關系異化,有違婚姻所應具有的非計算性、情感性,并據此否認忠誠協議效力。參見郭站紅:《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學思考》,載《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2期,第111-112頁。
各理論就其自身而言皆邏輯自洽,但彼此缺乏對話。忠誠協議往往兼具財產和人身因素,通過將其歸類到任何一側來認定性質,即便得出確然結論,也必定說服力不足。通過類型化兼列舉來分情況討論的分析方式頗具實踐價值,但并未給諸多情形提供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分類依據,分析也往往依賴“違反強制規范”“違背公序良俗”“有損人格權益”等模糊亦碎片化的論證方式,缺乏統一的證成基礎。
概而論之,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爭議是法律解釋彈性較大、司法內部邏輯矛盾和既有理論工具不足交織生成的結果。上述討論集中體現了層層遞進的四大爭議焦點:第一,忠誠協議的性質是效力認定的關鍵,人身和財產屬性的二分是既有分析的基本框架。第二,人身屬性與合同法律規范的適配性存在爭議。第三,對于何種協議內容符合道德倫理這一問題,有待更為明晰的標準指引。第四,忠誠協議是否屬于可予強制履行的協議類型亦無定論。我們需要尋找爭議的共同根源,采用有力的理論工具予以回應。
二、爭論背后的三點預設與二元框架
本部分將指出,上述爭議看似異見叢生,實則普遍以三點預設為論證前提,并受束于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的二元框架,力求在兩造之間作出選擇或進行平衡。通過對預設和框架本身展開反思,可以“一攬子”地回應爭議,并為后續提出更有效的理論工具作鋪墊。
(一)效力分析的三點預設
第一,家庭關系與合同模式存在錯位。“從身份到契約”之線性發展的論斷在婚姻關系內是存疑的。盡管現代社會不再持身份等級制的觀點,但對于角色倫理仍有所期待。廣受推崇的契約自由在家庭關系中所可能引發的自利、疏離與對立始終引人擔憂。法律固然允許通過協議來創設和解除關系,如收養協議、遺贈扶養協議等都是以協議的方式突破原本的角色倫理期待,在本無照料關系的主體之間,構建了更為親密的關系距離。夫妻也被允許在離婚情形下,對子女撫養等人身關系通過協議作出安排。然而在家庭關系存續過程中用協議來安排損益,則被認為可能對關系造成破壞。這進一步驗證了對家庭關系契約化的猶疑。
第二,財產屬性的弱倫理性和人身屬性的強倫理性相互對立。在忠誠協議兼具人身屬性和財產屬性的現實情況下,司法實踐與諸多理論仍然堅持對此作出區分。部分觀點在主張人身義務與財產賠償的相互協調時,固然看到了財產在維護倫理秩序方面的作用,因而試圖在確保協議本身威懾力足以捍衛婚姻的同時,避免情感的物化和關系的扭曲。參見申晨:《〈民法典〉視野下婚內協議的效力認定》,載《法學評論》2021年第6期,第190-191頁。該文認為,過重的義務或責任,都可能產生對于不公平的逆反心理。權利人也可能因為經濟賠償的誘惑,而違背維護關系的初衷,惡意期待對方違反義務,以牟巨利。因此,“輕義務輕責任”是最為理想的協議類型。
其本質是對人身關系能否量化的深刻質疑,又不得不承認財產是規制人類行動的有效工具。然而此處財產發揮作用的方式,恰恰是通過人的理性衡量和利弊博弈。換言之,這并非體現了財產的倫理性,而是進一步驗證了它在現行理論中的弱倫理性設定。既有法律對于夫妻財產協議做了明確規定,允許夫妻雙方約定財產歸屬。相較之下,人身關系協議則處于立法模糊地帶。可見此種預設不僅體現在忠誠協議問題的法律實踐和既有研究中,也是法律中的普遍傾向。
第三,法律強制與情感關系不相匹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43條第2款中明確規定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但否認了僅就此條款提起訴訟的可能性,因此該條款往往被視作缺乏強制力的倡導性條款。而如果忠誠協議的效力得到承認,就可能再次面臨法律對夫妻關系實踐的評判問題。協議效力支持方往往強調強制執行的內容是違約后的賠償后果,而非忠誠等人身、情感關系本身。協議效力反對方則認為此種協議唯有自覺自愿履行才有意義。無論持何觀點,他們都潛在地承認了情感關系的自發性和法律義務的強制性之間圓鑿方枘。
(二)價值取向的二元框架
由此可見,盡管從邏輯外觀上來看,效力分析總是從忠誠協議的性質入手,具有高度的客觀性和描述性,然而這種分析實則是價值前置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分析者在意思自治和家庭倫理之間的價值抉擇,并在價值引導下,以協議中的屬性要素反過來論證結論。部分觀點將忠誠協議視為對法定忠實義務的具體化和有益補充,從而既符合意思自治原則又維護了家庭倫理。參見李姍萍:《民法典時代背景下的忠誠協議》,載《交大法學》2022年第5期,第115-118頁。然而這種觀點并未對上文提及的三點預設作出有力回應,顯然繞開了爭議焦點并簡化了問題。
三點預設背后潛伏著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的二元分立,前者強調個體意思自治,以及個人自由之間相互掣肘而形成的自發秩序。后者則強調共同體倫理,以預先確立的家庭結構和價值規范對成員予以制約。這也是我國目前家庭法理論探討的基本框架。
試圖讓兩者之間協調兼顧的愿望固然美好,但難以實現。前者追求的需求多元和后者的統一規范之間短路相接,無法形成一種穩定的秩序,忠誠協議效力之爭久無定論的癥結也在于此。受束于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的二元價值框架,進而生成了三種二元區分:合同模式與家庭關系、財產屬性和倫理屬性、法律強制與自發情感。既有裁判實踐往往在它們之間自動建立起環環相扣、一一對應的關系,即愈主張對意思自治的保障,就愈側重強調協議的財產屬性,繼而以之論證合同屬性,并予以強制執行力。反之,越關注家庭倫理,則越強調協議的人身屬性和家庭關系的內在約束,否認合同法律效力。
二分圖景之下,選擇任何一側都說服力不足,在既有框架內部獲得平衡的嘗試也遭受挫折。下文由是跳出個人—家庭的二元框架,提出“關系法理”這一進路。它能夠成為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之間的溝通媒介,回應兩造平衡的困境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說明∶上述的三種二元區分預設及其一一對應關系并不成立,“關系法理”可以為忠誠協議的效力認定提供更為融貫、清晰和具有說服力的標準。
三、關系法理的理論溯源與基本內容
關系法理是指基于對“關系”的考察所展開的法律基本概念分析、法律價值證成以及法律制度反思與建構。其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并發展至今,主要包括
關系契約論及關系性方法兩脈。具體而言,關系法理將“關系”作為法律分析的基本單位,將“關系性善”作為法律基本價值原則,以“關系性視角”實現法律體系各部分勾連與綜合,并將“關系調節”作為法律的功能定位。下文對其兩脈理論線索進行梳理,并對其基本內容作一展開論述。
(一)關系法理的理論溯源
關系契約論將社會學納入對法律規范的探討中,重新審視“契約(法)”的含義,對古典和新古典主義契約法學理論發起挑戰。契約不是個人意思表示的聚合,而是在社會中發生的,有關規劃將來交換過程的當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參見Ian R. Macneil,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and Presentiation, 60 Virginia Law Review 589-610 (1974);\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該定義一改契約具有獨立性和明晰性的特征描述,反之強調契約的關系性、動態性和內容的開放性。在麥克尼爾的論述下,“契約”概念的運用不局限于合同法領域,還將原本被排擠出契約領域之外的婚姻家庭、侵權、物權、勞動關系等重新包納進來,予以統一說明和規范。不獨所有契約在實然意義上都嵌于關系之中,對契約的分析與把握也有賴于對關系中關鍵要素的理解。See Ian R. Macneil,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Challenges and Queries, 94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81 (2000) .面向此種契約的司法實踐不僅應關注契約文本,更要關注雙方互動的社會事實,揭示出當事人所身處的復雜關系網絡。See Jay M. Feinman,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in Context, 94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42 (2000) .
關系性方法則更為旗幟鮮明地展現出關系法理的分析進路。20世紀80年代,已有學者從主體間性的視角對既有理論展開批判,例如,Suzanna Sherry, Civic Virtue and the Feminine Voice in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72 Vanderbilt Law School Faculty Publications 543-616 (1986) . 20世紀90年代,內德爾斯基明確提出了“關系性方法”的概念,詳見Jennifer Nedelsky, Property in Potential Life-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Choosing Legal Categories, 6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343-366 (1993) .
關系性方法后來被廣泛運用于家事法的探討中并進一步發展,例如,Jonathan Herring, Relational Autonomy and Family Law, Springer, 2014.其雖然將婦女兒童的權益保障作為主要議題,但探討已然超越這些議題,對整個法律體系的深層邏輯和價值基礎展開釜底抽薪式的追問。關系性方法認為,權利并非反映為不被干預的自由、相互獨立乃至對抗的利益。相反,“相互依賴”才是普遍情形而并非人的瑕疵形態。個人的自主自由應當在關系結構的基礎上加以理解。Martha Albertson Fineman, The Vulnerable Subject and the Responsive State, 60 Emory Law Journal 251-275 (2010) .人們能夠在互動關系中增強自主性,從而有能力面對困難、抵御風險。See Jennifer Nedelsky, Reconceiving Rights as Relationship, 1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Studies 8 (1993) .與關系契約論類似,關系性方法提出了法律實踐的新思路,主張司法應關注每個訴求背后的深層關系結構。相較于思考維護誰的利益、何種利益,司法中更應思考維護何種關系,如何促成和維護具有建設性的關系,阻卻具有破壞性的關系。See Yael Braudo-Bahat, Towards a Relat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Personal Autonomy, 25 American Univerq1YPYVigw8fv5Kxn4tO/eCeBg6/Jp61N8K+iMrM9Zlc=sity Journal of Gender, Social Policy & the Law 111-154 (2017) .
兩脈理論的主攻領域和問題意識雖有差異,但都有志于以“關系”覆蓋整個法律體系的思考。對法律規范之外的社會關系的關注,對人際合作、團結和相互實現的價值偏好,使得兩者存在諸多對話互通的可能。其中方法的互通性已為
學者所察覺,認為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并運Hghtz7NezAEsdqv+nZTcIPys/43F5zG62kDEvMKhx4o=用于婚姻家庭協議等研究中。See Peter Linzer, Uncontracts: Context, Contorts and the Relational Approach, 1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161-162 (1988); Sharon Thompson, Feminist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A New Model for Family Property Agreements,45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617-645 (2018).
(二)關系法理的基本內容
結合上述理論溯源,可以將關系法理的基本內容概述為如下四點:
第一,法律規制的基本單位是“關系”而非“個人”或“集體”。
關系是考察問題的起點,無法被還原成個人的聚合,也不等同于一個固定的結構。雖然傳統意義上的法律關系也展現了當事人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被還原成當事人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借用麥克尼爾的表述來說,如同當事人各自分持一個包裹。正是這種將個人作為基本單位的分析框架,使得“財產的占有與分配”成為思考權利義務的慣常路徑與范式,也促使財產法成為法律體系的基本構造技術和整體基調。參見劉征峰:《民法典中身份關系法律適用的原則與例外》,載《中國法律評論》2022年第4期,第78頁。然而基于關系法理,人們對法律問題的考察,不應以分析當事人各自持有何種資源、享有何種利益為切入口,而應在于法律意欲塑造何種關系,承認何種關系互動的規范。由是,對個人意思表示的把握,應基于對關系事實的考察而展開。此外,個人所持有的資源、能力、權利、義務等不僅是具有特定內容的客觀對象,還能夠表達特定“意義”。重要的不是主體各自所持有的客體內容本身,而是要在關系網絡中實現對“意義”的解讀。澤利澤將“關系包”(Relational Packages)作為經濟活動的分析框架,其中包括:獨特的社會關系、一組經濟交易、交易媒介及參與者協商后對關系、交易和媒介的意義的理解和道德考量。參見姚澤麟:《經濟社會學中的文化解釋路徑》,載《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第18頁。
第二,法學的基本價值原則既非維護個人利益,亦非貫徹某種統一的集體倫理,而在于維護關系性善,保障具有正當性的關系。參見邊燕杰:《論關系與關系網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5頁。不同的關系類型都有其恰當的互動模式。關系性善關注的并非關系所產生的具體后果,而是互動過程本身。具體到忠誠義務語境中,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雙方是否“獲得”了對方的忠誠,即享有某種“配偶權”,以及是否達成了婚姻維系、家庭完整的結果,而是何種互動過程有助于促成對彼此的忠誠,過程本身是否是良善的。此外,不同于社群主義對關系所秉持的頗具浪漫色彩的態度,關系法理并非忽視關系中可能存在的離散性、沖突性,而旨在說明:鑒于關系的普遍性,即便在看似最為個別性、對立性的關系中,也存在相互合作的基本義務和契機,從而指向一種更具責任感、信任感的生活。See Jay M. Feinman,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in Context, 94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48 (2000) .
第三,以“關系性視角”實現法律體系各部分的勾連與綜合。為了更清晰地理解和規范社會,我們固然需要對龐雜的社會現實予以分類化處理,通過子系統的分出以獲取分析框架。正因如此,法律才會作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合同編與婚姻家庭編、財產與人身等區分化安排。然而面對一項具體的社會事實,我們很難說它精準無誤地落入到某個領域之中。《民法典》第464條第2款的設立初衷,正是為不同部分間的共振提供通道。唯有通過關系性視角,我們才能對這一通道加以有效運用。在理解交互主體之間的關系本質、模式和特征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將協議簽訂、財產處分、人身權利義務安排等作為關系要素的組成部分,根據關系特質對此加以理解。這就使得本來出于分析需要而相互割離的要素重新因為關系特質而互動起來。概而論之,既有對法律體系的理解往往是樹狀的,即通過不斷的類型化拆解,來實現法律框架的清晰簡明,然而這往往有賴于對事實的過度裁剪和絕對的、靜態的分類,使得法律無法對復雜的社會現實作出有效回應。關系性視角下的法律體系則是網絡狀的,從而能夠實現法律規范之間的聯動,以此更為有效地回應動態現實。
第四,將“關系調節”作為法律功能定位。一方面,對個體實踐的自由放任往往會加劇沖突,并潛在地延續不公正的結構。另一方面,社會現實并不會僅僅因為法律的倡導、要求乃至強制就形塑成被期待的樣式。相較之下,關系法理下的法律實踐既不因自由主義的濫觴而退居后端,從而被動回應個人需求,也并非以自上而下的強有力規范裁剪多元事實、倒逼社會實踐。它不將社會作為一個被動對象加以規制,而是關注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促使關系各方具有共同反思、塑造、調整和深化關系的能力。其不僅僅關注法律規制的最終結果,更具有程序導向。此外,此種法律實踐不將自身視為外在于社會的約束者,而是同樣嵌入于關系網絡的參與者,因此關系的調節需要在法律與其他參與者的對話、反饋中達成。由此,法律雖無法也不應強制忠誠義務的履行,但以其解紛過程調整互動模式,為關系性善鋪設生成路徑仍屬可能。
概而論之,當我們將關注的落腳點放在“動態的關系互動”而非“個人的利益狀況”抑或“共同體的整合結果”上,制度的解讀方式和法律的實踐模式都將隨之深刻改變。
四、關系法理下的忠誠協議性質再認識
至此,關系法理用以應對忠誠協議效力之爭的線索已暗伏其中。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可協調于關系本位之下:個體本就嵌于特定關系之中,持續的人際互動會進一步涌現出穩態結構,也就是家庭共同體,并能夠產生為社會所廣泛承認的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反過來對關系互動設置條件,但并非決定后續的互動。主體性作用的發揮讓關系存在其他可能性這種“其他可能性”不可能完全脫離于社會結構,但社會結構對其的影響是暗含其中的。所以它相較于其他社會實踐仍具有突破性。參見\喬治·H. 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趙月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3-245頁。,并進而導致結構的進一步更新,由此在循環中演進。下文將對關系法理的運用作詳細展開,在本部分探討忠誠協議的性質問題,借此審視前兩點預設;第五部分探討協議的效力認定和司法應對,以反思第三點預設。
(一)透過關系契約理論考察婚姻關系與合同關系的溝通
將婚姻家庭關系和合同關系區分開來的邏輯,體現了一種“敵對世界觀”,認為情感關系和契約關系一旦發生交叉重疊,就會影響彼此的純潔性,前者會因為交易的存在而受到玷污,后者會因為情感的存在而變得過于復雜,甚至影響效益的實現。See Viviana A. Zelizer,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25 Law & Social Inquiry 823 (2000).然而現代家庭互動和市場交易模式的共同改變,催生雙方必將從“敵對”邁向“互通”。
一方面,現代婚姻關系的起點和終點都不具有確然性。第一,現代家庭模式多樣化和家庭觀念認知開放使其不能被統攝于一種固定的倫理框架內,家庭建構的動機和具體方式的個性化表達是突破舊秩序,邁向新階段的應有之義,因此需要尋找實現家庭共同體凝聚的新進路。第二,現代社會的家庭不僅是溫暖的港灣,也是風險的來源地。由于缺乏熟人社會小社群的內部制約,人際互信往往依賴個體判斷,對風險的預防與規制也更加依賴制度完善。夫妻雙方即便在進入婚姻之初滿懷憧憬,未來結果實則充滿不確定性。
忠誠協議可以回應上述兩個難題。首先,合同為關系模式提供了靈活開放度,又以增強關系紐帶為落腳點,而未必將關系短期化、庸俗化。忠誠協議為雙方在關系中展開合作并持續努力提供了起點和平臺,并對風險作出安排,在結果未知的情況下仍然維護合作行為本身。其次,它將私密不可見的關系可視化,為法律制度發揮作用提供可能。認為有形的契約方式會折損無形流露的夫妻情感的觀點,混淆了“忠誠”的兩種屬性——動機屬性和評估屬性。協議僅僅規定了夫妻行為的外在評估標準,不代表雙方必然僅僅出于遵守協議的動機而保持忠誠,不影響雙方仍然出于情感動機而忠誠于對方。
另一方面,伴隨著“社會市場化”向“市場社會化”的轉型,維系長期合作以實現效益最大化,挪用已有的信任關系來發展交易關系,以及通過有意地促成交易關系外的其他關系來反哺交易的實現,成為當代的顯著特征,在中國本土的交易市場也有深遠的發展歷史。相較于歐美經歷的從個人主義向關系主義的轉向,中國本土對于“關系”有著更為天然的親和性。中國本就強調首先設定關系,根據情境倫理進行交換交涉,由此強調權利義務的相對性。參見季衛東:《互惠的正義——法理學的視角轉換及其實踐意義》,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3期,第4-5頁。以“家”為本的特殊主義倫理內含實質正義和“以義為利”的取向。它啟示我們,商業倫理難以獨立支撐起現代社會的道德。
參見肖瑛:《“家”作為方法:中國社會理論的一種嘗試》,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第189頁。在商業交易中,已然出現“合作型合同”的概念與實踐。這類合同不規定合作必須達成的成果,而是規定合作行為本身,在合同約束下逐步考察彼此的合作能力,形成商業互信,在此過程中增加解除關系的沉沒成本,從而達成穩固合作。這一模型與忠誠協議的運作機理異曲同工,也確被學者借用于探討家庭關系。See Elizabeth S. Scott & Robert E. Scott, From Contract to Status: Collabo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ovel Family Relationships, 115 Columbia Law Review 293-374 (2015).此外,即便是僅僅以自利為目標,除卻交易關系而無其他交易的雙方主體,也必然需要存在最低限度的信任以步入交易關系之中,需要履行最低限度的誠實信用義務,以促使交易的完成。有鑒于此,婚姻關系與契約關系的溝通不僅有立法支撐,也有現實支持。
關系契約論區分了個別性契約和關系性契約,個別性契約的交易短暫、內容精確、雙方主體僅投入部分人格并帶有分離性和自利性。其關注契約成立的一刻,將未來的一切事務都現時性地固定下來,對未來的風險和變動予以否認。關系性契約則持續時間長,契約內容具有開放性。契約雙方即便具有明確利益沖突,也會對統一體予以關注。其關注契約動態性的變化,承認風險的存在。契約內容不可能在形成一刻就得到精準表達并嚴格執行,因此會通過設立規則來應對風險。參見\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9頁。此種二分法是出于理論分析的考慮,現實世界不存在純然的個別性契約,任何契約都必定處在關系之中,所有的區分標準不是涇渭分明,而僅有程度之分。
這種從個別性契約向關系性契約的光譜結構能夠容納多元的婚姻模式。合同模式并不會必然導致婚姻關系的異化,關鍵在于我們如何理解合同,將其對應于怎樣的圖式。關系契約論打通了婚姻家庭編與合同編二元對立的局面,然而這并非消彌關系類型
的區別。相較于交易關系,婚姻關系往往是全部人格的投入,因此更為復雜,投入的情感及所需承擔的誠實信用義務程度也往往比交易關系更深。對于交易關系來說,關系是工具,在關系中流動的資源才是目的,因此其更強調契約的穩定性。但對于婚姻關系來說,關系本身就是目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更強調契約應具有回應關系動態性的能力。
總之,關系契約理論以恰當的中觀視角,在將兩者同時包容于關系性視角的同時,保持對差異的敏感度,避免合同編對婚姻家庭編的反噬。借用哈特對核心領域和邊緣領域的區分,有關婚姻關系的協議不能被視為合同關系的核心情形,但仍然可以在邊緣領域適用合同編的規定。這契合于法律規定中“參照適用”的立法技術,也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空間。
(二)通過關系性所有看財產—人身與倫理性的對應關系
對財產屬性和人身屬性進行二分,將兩種屬性分別標記為弱倫理性和強倫理性,這是既有研究討論忠誠協議性質的基本模型。參見薛寧蘭、崔丹:《身份關系協議的識別、類型與法律適用》,載《法治研究》2022年第4期,第74頁。然而這一邏輯是否成立?
第一,人身和財產屬性的劃分往往是基于協議的文本內容展開的。這種劃分僅僅關注協議所涉客體內容,而忽略了關系本身。正因如此,既有分析總是將通過協議構成的關系視為一種資源流動的管道,情感資源(如伴侶的忠誠與信任)和物質資源(如違約賠償)在管道中流動,協議主體則對自身可獲得的資源進行理性權衡,作出遵循或者違背協議的決定。部分觀點強調人身義務與賠償責任合比例性的原理也在于此。然而,協議并非僅僅作為資源流動管道發揮作用,而是形成一種關系結構。
財產的本質是規制人們之間的關系,體現了我們能夠對他人造成何種影響。換言之,親密和財產并非兩個相互隔離的領域,財產安排直接反映并影響著夫妻關系結構。舉例而言,假設婚姻中的一方長期不忠,而另一方仍然希望維持婚姻。此時,后者已不再期待伴侶能夠盡到忠誠義務,但基于忠誠協議所能夠發揮的效力,至少能夠對伴侶構成制約,實現婚姻的維系。協議主體的意愿不在于獲得某種資源內容,而是關系調整。忠誠協議的目的既非保證伴侶的排他性對待,也非獲得經濟賠償,而是重塑關系結構,是為關系持續所作的策略性安排。這在協議效力的確認之訴中尤為重要。這種關系結構將影響夫妻日常互動的全部方面,而不僅僅是忠誠協議所涉內容本身。由此,對一份協議的倫理性的評價不再取決于它的客體對象具有財產屬性抑或人身屬性,而在于這份協議在夫妻關系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它以既有的關系結構為基礎,并以影響未來的關系為目的。
第二,上文論述側重于將忠誠協議作為雙方當事人基于關系結構所作的策略性安排,尚未打破“理性人”預設,然而這僅僅是忠誠協議的一個側面。夫妻的此種約定也是為了作出情感、態度的表達。它既表明了對這段婚姻的信念,也反過來反映出了協議人此時的價值取向及自我評價。換言之,它關乎我們“如何價值定位”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定價多少”的問題See Gillian K. Hadfield, An Expressive Theory of Contract: From Feminist Dilemmas to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Relational Choice in Contract Law, 14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258 (1998) .,其中的倫理性愈發凸顯。認為金錢一旦進入到親密關系中就會污染關系的結論是武斷的,一項協議的具體內容究竟傳遞出怎樣的態度和情感,仍要結合雙方的具體關系,在意義網絡中加以理解。正如澤利澤提出的,一些金錢給付從行為外觀上看沒有區別,但我們如何對其進行標記、命名,揭示了我們之間不同的關系。例如,部分忠誠協議是在一方出現婚外性行為等過錯行為后簽訂,其中的財產要素并非對忠誠義務的定價,而是表明承認過錯,修復婚姻的態度。而在上述“空床費協議案”中,雖然同樣是財產給付,但是協議的表述在丈夫的陪伴時間和金錢之間構建起明顯的等價關系,從而有扭曲關系之嫌。正因如此,該案判決才會引起巨大爭議,并日益遭受批判。
綜合上文所述,可對《民法典》合同編第464條第2款有全新理解。所謂“根據其性質參照適用”,并非唯有證明協議的財產屬性才能適用合同編,而是指對合同編具體規定的選擇適用和含義解讀,需要結合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倫理來實現。第五部分將詳細闡述關系倫理如何影響對效力條款的適用,例如,如何適用真實意思表示、誠信原則等條款。
(三)從規范型到累積型的協議類型譜系
關系法理協調了家庭關系和合同模式之間的關系,也將財產和人身屬性統攝于關系結構及其意義網絡之下,揭示出背后共同的倫理性。由此,性質劃分的標準不再基于協議內容的人身性抑或財產性,而是協議所反映的關系互動模式。
可根據關系特質將忠誠協議區分為規范型協議和累積型協議。前者是普遍的角色倫理和社會規范,具有公開性和客觀性,有一套界定此類關系的基本標準,因而更容易被制度化為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后者則是關系主體基于具體的關系歷史而形成的互動模式。此種相互的期望在關系伊始并不存在,而是在持續互動中產生的個性化、經驗化表達,體現了夫妻對彼此以及對這段婚姻的態度和知覺,比如對彼此喜愛與否、重視與否、了解與否。
須得說明,對協議的此種區分不能僅憑協議文本內容作出。關系法理要求站在當事人的視角,進而判斷如果身處特定婚姻關系中,作出此種協議約定是否符合普遍規范,抑或具有特殊性。換言之,即便是社會普遍規范也是在內部視角基礎上發揮作用的。因為縱使是為目前社會所廣泛承認的規范也有其生成過程和基礎,是漫長的關系經驗的累積,而非一種自上而下的外在強制標準。唯有置于當事人視角,對特定關系歷史進行考察,才能對協議恰當定性。相較于人身—財產的二分,規范型—累積型的二分框架更有助于法院據其性質采取恰當的解紛策略,對惡性關系作出矯正,并推動形成良善的關系互動,后文將予以詳述。
五、基于關系調節的忠誠協議效力認定
忠誠協議體現并影響著關系結構,法律實踐對其的效力評價和解紛過程相應起到關系調節的作用。基于對協議性質的重新認識,效力認定不再依循家庭—合同、人身—財產的簡明框架,而有賴于對具體關系結構的理解。因此,采用司法而非明確立法的方式規制忠誠協議,是一種智慧的策略,也必然導向更具挑戰意義的司法實踐,有待關系法理的進一步指引。
(一)作為反饋式調整的關系性解紛
關系性解紛參見季衛東主編∶《法社會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44-145頁。將“關系調節”作為司法的功能定位,這要求法院在面對協議效力問題時,不能以人身情感因素為由不予受理,以意思自治為由回避實質評價,亦不能僵化適用公理標準,武斷裁剪多元事實。此種解紛方式有三點特征。第一,法官不能僅僅關注協議文本,而要關注關系事實本身,避免裁判延續乃至加劇惡性關系結構。第二,解紛過程并非外在于關系,而是構成對關系的調整與建構。第三,法官并非高于當事人的一錘定音式的規制者,而是嵌入其中。這有賴于觀點之間的溝通,要求法官站在當事人各方視角來思考,并使其裁判能夠在當事人之間得到證成。See Roxana Banu,
A Relational Feminist Approach to Conflict of Laws, 24 Michigan Journal of Gender & Law 39-40 (2017) . 關系性解紛對關系事實的敏銳把握和基于關系調節的功能定位,契合于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趨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試行)》第2條要求“充分發揮家事審判對婚姻關系的診斷、修復和治療作用”;第3條要求“切實轉變工作方式,強化法官的職權探知、自由裁量和對當事人處分權的適當干預,注意區分婚姻危機和婚姻死亡,正確處理保護婚姻自由與維護家庭穩定的關系”。
此外,司法不僅要考慮效力認定的實質問題,還要考慮司法方式與糾紛類型的匹配問題,以避免法官與當事人的互動模式本身對婚姻關系造成不當影響。通過將審判與調解相結合,可以回應強制性判決不適用于情感關系所引發的困境。針對規范型協議,鑒于其約定符合普遍社會規范的期待,法官對其關系結構也能有較為明晰的把握,宜采用司法審判的方式,強調法官職權。此種方式尤能夠對惡性的關系結構作出糾正。而累積型協議展現了情感關系的特殊性,如若法官對于黏連復雜的關系難以把握,可采用調解的形式。關系契約論者已然意識到,關系性方法或許在調解中有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See Linda Mulcahy, Telling Tales about Relational Contracts: How do Judges Learn about the Lived World of Contracts, in David Campell, Linda Mulcahy & Sally Wheeler eds., Changing Concepts of Contract: Essays in Honour of Ian Macneil, Palgrave Macmillan, 2013.此時調解人并非居中裁判,亦非借助道德倫理標準,不加差別地批評教育,而是通過程序性的安排,促使雙方當事人實現平等對話,輔助梳理事實,厘清爭議焦點,并提供參考性的解決方案。
當然,無論采用何種方式,法官主觀性無法避免。但這恰恰有利于防止濫訟情形的發生,減少基于沖動和戲謔而動用司法途徑的情況。協議雙方應當意識到,一旦其觸發了公權力機制,就意味著允許第三方視角對協議的內容和運行產生影響,這種影響不可能無限貼近雙方真意,而有可能溢出于一方或雙方的期望,因此如果將其作為“情感游戲”,參見隋彭生:《夫妻忠誠協議分析——以法律關系為重心》,載《法學雜志》2011年第2期,第40頁。則需三思而后行。此外,關系性解紛并非主張“司法萬能論”。法院雖然無法憑一己之力化解所有關系危機,但至少可以在關系法理指引下慎重司法,避免司法本身導致關系的惡化。
(二)基于關系性自主的真意表示
意思自治是判斷合同效力的前提性原則,以確保協議的簽訂是雙方自主的安排。忠誠協議支持者往往基于協議雙方成年理性人的預設,以意思自治為由承認協議效力。反對者則認為,此種協議往往是夫妻雙方情感性甚至情緒性的表達,存在理性瑕疵。有關此類觀點的討論,參見劉加良:《夫妻忠誠協議的效力之爭與理性應對》,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4期,第102頁。根據“關系性自主”的理論,上述兩種理論都有所偏頗。所謂“關系性自主”是指人具有確立、調整、發展特定關系的能力,這種自主性并非讓人脫嵌于關系,相反是指人能夠在交互中促成建設性關系,抵御破壞性關系。具體內涵如下:
第一,自主性在關系互動中生成。根據前文對關系法理的論述,人的相互依賴性和自主性并不對立,我們恰恰可以通過他人的輔助而增強自主性,從而有能力和他人建立起良善的關系網絡。傳統對“自主”的定義類同于“自由”,關乎人們如何處理自己的事務,強調抽象的個人選擇,是一項個人主義式的概念。但“關系性自主”關乎我們如何相互對待,因而和“平等”概念更具親和性。這種平等并非分配平等,而是關系性平等。See Elizabeth S.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109 Ethics 287-337 (1999) .
相互依賴的夫妻雙方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持有相同的資源,而往往是相互補充的。這種依賴關系有兩種發展走向,一種是從“依賴”走向“支配”,即一個人所處的關系結構使其只能依賴另一方,而喪失了其他選擇。有時僅就協議文本來看,效力應當獲得承認,但協議實則源于并激化了本就不平等的關系結構。另一種則是從“依賴”走向“關系性自主”,夫妻雙方都具有了建構、調整和發展關系的能力,形成相互尊重的互動模式。
第二,對自主性的解讀要放置在具體關系中,采取更具動態性、流動性的理解,從而不受束于理性人預設,而考慮情感特質。在婚姻關系中,除卻顯著的欺詐、脅迫等情形,還存在對自主性構成隱性影響的因素,這和協議被提出的時機有很大關系,如在情感初期對婚姻缺乏預見、概念模糊之時,情感破裂期受到離婚威脅之時,等等,都有可能促成協議的簽訂。這類方式也很難被歸類為欺詐、脅迫的情形,而恰恰是婚姻中廣泛存在的情形。如果僅僅因為此時協議的簽訂帶有情緒化的因素而直接認定協議無效,就等同于要求深嵌于婚姻關系當中的雙方能夠不受特定關系影響,以抽身而出的理性狀態簽署協議。在強調婚姻的情感特質的同時,又對人提出高度理性的要求,無疑是割裂的。在婚姻關系中,人們往往出于對伴侶、子女的情感而作出決定,這也是人之自主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沒有顯著的欺詐、脅迫情形,就應直接承認忠誠協議的效力,還需要結合“關系性善”進行價值判斷,后文將予以詳述。
第三,“關系性自主”的觀點不僅用于考察雙方在簽訂之初的關系結構,還用于關注關系的持續發展。在長期契約中,雙方合意的形式外觀僅是協議成立的“觸發器”,鑒于關系具有不可預見的變動性,對效力的認定不能僅僅停留在協議形成階段,還需要考察協議對關系產生的實際影響。“一個人一旦最初作出選擇,就決定了未來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則不是不證自明的真理,而是社會制度的安排。其初衷一方面是維護交易穩定,使契約內的期待利益得以保障,另一方面是尊重個人作為“自利理性人”的選擇偏好。然而在變動不居且難以預見的婚姻關系中,最初的判斷難以觸及未來的情形,“可期待利益”的具體內容應在關系的變化中加以確認,而非由契約內容決定。
概而論之,人的自主性在協議中是否得到尊重,不在于當事人是否具有簽訂忠誠協議的抽象權利、協議中的情感濃度及協議是否在簽訂初期獲得雙方承認,而取決于協議訂立時的具體關系情境及協議對關系結構產生的后續影響。
(三)基于關系性善的效力判斷
關系性善是效力判斷的價值基礎,即忠誠協議是否體現并推動形成了良善的關系模式。麥克尼爾提出了關系性規范,具體包括角色保全規范、關系維持規范、關系沖突協調規范、方法適當性規范,以及超越契約規范。See Ian R. Macneil, Values in Contract: Internal and External, 78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350 (1983-1984);\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4頁。這些規范兼具實然性和應然性,既可用于描述契約關系中發生的行為,也規范了如果期待關系延續下去就應當采取的行為路徑。這為我們如何更好地聚焦關系事實并作出評價提供了指引。
第一,“角色保全規范”要求人能夠一以貫之地扮演在特定關系中的角色,其行為要符合特定的角色倫理。此外,基于人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多元性,角色保全也要求人在多重角色中取得協調。因此需要考察夫妻雙方分別具有哪些社會角色,以及忠誠協議對于這些角色的協調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例如,一些忠誠協議要求伴侶不得和其他異性接觸,或者以放棄對孩子的撫養權及探望權為違約后果。既有研究往往以這些約定違反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或者以協議內容具有外部性,涉及第三人利益為由,否認此類協議效力。參見梅夏英、葉雄彪:《婚姻忠誠協議問題研究》,載《法律適用》2020年第3期,第110頁。然而此種說理無法為其究竟在何種意義上違背公序良俗提供精準闡釋,也無法解釋為什么法律卻允許簽訂離婚情形下的撫養問題協議。“角色保全”規范則可以清晰地說明,此類忠誠協議之所以無效,是因為它使得個人作為社會的工作者及作為父母的多元角色無法得到整合,以夫妻身份的需求不當限制了其他社會角色的需求。問題關鍵在于,上述角色之間本來并不具有互斥性,而可以相互協調。和工作伙伴的正當接觸并不影響夫妻身份行為的履行,父母職能和夫妻關系雖不無關聯,但并不完全具有牽連性。
第二,“關系維持規范”意味著將時間維度納入效力判斷中,即協議的訂立與履行要有利于關系的長期維系。其不僅包括特定關系的維持,也包括更大的關系(即集體)的維持。同時應當避免以后者為名義濫用權力,對關系施以僵化的要求和期待,最終以犧牲前者為代價。例如,認為忠誠協議必將侵蝕公序良俗與社會風氣的觀點即為夸大了忠誠協議的負面影響,未能恰當承認那些本有助于關系維持的協議的效力。參見姚邢:《〈民法典〉體系化視野下的夫妻忠誠協議》,載《法學家》2024年第2期,第90頁。
第三,“關系沖突協調規范”要求考慮到關系的彈性。傳統契約理論強調可度量性和精確性,希望在協議訂立之時就明確規定權利義務并使其得到嚴格遵守。但在不斷變動的關系中,如果訂立充斥著度量與精確性的協議,就難以避免沖突發生。那些規定嚴格的回家時間等方面的忠誠協議,固然沒有違反明確的法律規定與公序良俗,但其無視具體關系的流動性和彈性,無法容納關系實踐的復雜性,對其效力仍不應予以承認。
第四,“方法適當性規范”在麥克尼爾的理論中類同于誠實信用原則。它關乎雙方在契約訂立、履行過程中的具體活動。因此,對協議效力的認定需要考察夫妻雙方是否充分溝通,以及是否有惡意破壞協議履行的行為。例如,如果一方不惜以關系破壞為代價,牟取巨額賠償利益,其必然會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動,惡意促使對方不愿或無法履行義務,這將違背“方法適當性”規范。此時,義務人違約而產生的財產賠償就不屬于權利人的可期待利益,其賠償請求不應得到支持。
第五,“超越契約規范”除了關注契約本身,還關注其所處的廣闊社會中所包含的基于內在人性的普遍規范,這類規范是在人們持續的契約關系中擴展而來的,它為人們的協議設置了基本的限度。當忠誠協議的規定無法與外在社會規范相協調,就無法得到承認。因此,對忠誠協議的效力評價不能僅僅圍繞夫妻關系倫理展開,還要考察這份協議是否符合其他社會規范。這些“超越契約規范”包括分配正義、自由、人的尊嚴、社會平等和不平等、程序正義等。這是一項無法窮盡羅列的清單,而有賴于跨學科的通力合作以共同回應契約關系問題。參見\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頁。
可以發現,“角色保全規范”和“超越契約規范”契合于規范型協議,“關系維持規范”“關系沖突協調規范”和“方法適當性規范”則與累積型協議相契,由此在性質認定和效力判斷之間實現銜接。忠誠協議效力的認定不再是依據二分框架層層歸類的單線程工作,而是要求深入到協議所嵌入的關系結構,目光在協議內容以及更廣闊的關系事實之間反復流轉,對協議是否符合角色倫理和關系倫理進行檢驗,并在分析關系事實的過程中對預設進行調整,對復雜的案件尤需多次重復上述步驟,最終確認適宜的解紛方式并作出裁判(詳見圖1)。這絕非一個更為簡捷的方案,相反,它展現并直面了問題的復雜性。
余論:從關系法理到關系法學
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爭議處于合同法與家庭法的關系、財產與情感的關系、私法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關系等多個法律問題的交叉路口,關系法理為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
當代社會的人際交互更為多元、便捷、廣泛,組織空間又松散、耦合、開放,任何波動所能引發的蝴蝶效應增強。傳統的認知工具(如團體、邊界、財產)等試圖通過靜態規則回應動態演變的策略往往遭遇挫折。而家庭關系所具有的千絲萬縷的變動性和復雜性,恰恰驗證了關系法理在溝通法律體系和經驗世界方面的優勢,并具有突破家庭場域,廣泛運用于各種法律問題的生命力。
通過將關系法理運用于更多領域、更多層面法律問題的探討,有望在未來形成一套系統的、以關系性思維為進路的“關系法學”。在《新社會契約論》的中譯本“代譯序”中,季衛東提出“關系法學”的概念,以概括麥克尼爾所提出的關系契約論及其延長線上的一系列研究并提出對法律體系建構的展望。參見季衛東:《關系契約論的啟示》(代譯序),載\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法社會學》第十一章專章介紹了“關系主義法學的景觀”。參見季衛東主編:《法社會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40-152頁。
關系法學可運用于諸多新興權利的研究。以數據權和冷凍胚胎權為例,數據來源的復雜性、內容的可復制性和強流通性,使得數據界權成為難題。然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可從“維護誰的利益”向“促進何種關系”轉變。相較于確定數據的權利歸屬,構建關系秩序將更具實踐意義。此類研究已有萌芽,參見Salome Viljoe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Data Governance, The Yale Law Journal 573-654 (2021).該文借助安德森的關系平等主義理論,嘗試建構網絡平臺的關系性秩序。又如,傳統理論習慣于將冷凍胚胎視為一種財產加以保障,并以此體現女性對身體的自主掌控。然而,財產權的分析框架可能反而引發對婦女兒童的物化,與實現女性自主性的初衷背道而馳。如果將針對冷凍胚胎的權利視為一種關系性權利,即與胚胎建立緊密關系的權利,上述困境將迎刃而解。
參見\ 詹妮弗·內德爾斯基:《作為財產的“潛在生命”——一個選擇法律范疇的關系性方法》,陳曦宜譯,載劉小楠、王理萬主編:《反歧視評論》(第1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第179-209頁。除卻上述新興議題,關系法學還可運用于特殊群體的社會保障、代際正義等經典議題的再探討,為現代社會秩序尋求新的粘合劑。
中國本土對人際聯絡與情境倫理的關注固然為關系法學的闡發與落地減少了障礙,但也應避免關系法學的異化與庸俗化,應注重發掘關系法學在關系調整和價值規范方面的作用。這要求在未來實踐中從時空兩維對關系法學予以細化:關系性調試應當發生在事前還是事后?例如,有學者指出,無過錯離婚制度增強了人違背承諾的自由(事后自治),但它就會限制人作出有約束力的承諾的自由(事前自治);例如,不能簽訂“不得離婚”的協議。事前自治是一種更為激進的自由。See Elizabeth S. Scott & Robert E. Scott, Marriage as Relational Contract, 84 Virginia Law Review 1246-1247 (1998) . 不同關系類型對關系性解紛方式的需求程度如何?法律規制應側重關系外部環境的建構還是直指關系內部?對上述問題的回應需要以跨學科的視野,結合關系社會學、關系倫理學等對不同關系的類型劃分、經驗研究與規范性分析,以期在未來作出更具區分度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