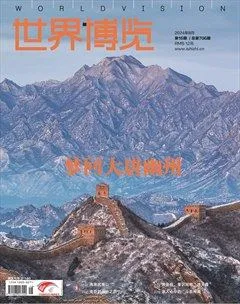價值:人類學家的宇宙觀?

在我讀博士的時候,就知曉語言人類學界有一介奇人——芝加哥大學的特倫斯·特納教授(Terence Turner, 1935—2015)。據說他生前有3—7本的已經寫好的書稿藏在自家抽屜里,永遠覺得沒準備好出版。其中一本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被接受出版,樣本都已印出,芝加哥大學還根據這個樣本給了特倫斯·特納終身教職,所有人都認為這本與結構主義形成最有意義的對話的人類學理論巨著即將面世。結果這位奇人左手拿到終身教職,右手就把書從出版社撤了下來,借口說還要改改。芝加哥大學等這本書出版的時間將近半個世紀,直到我博士畢業一年后,這位奇人過世了,這本書仍然沒有出版。其間,特倫斯·特納沒有出版任何一本書。從他的學生和同行們口中得知他驚人的博學,而且一直被認為是最有可能作出人類學理論突破的學者,但他只出版過一些他認為能夠為他研究的巴西原住民卡亞波部落(Kayapo tribe)爭取到政治權利的文章。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類學家都只知道他是所謂的左翼行動派,甚至完全沒有聽說過他。而他的學生和芝加哥大學的同行們都一直惋惜他最強的理論探索只以手稿的形式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和老師們之間傳播。
結構主義是始于19世紀的一種方法論,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創立,經過維特根斯坦、讓·皮亞杰、拉康、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阿爾都塞等幾代哲學、社會學與語言學和人類學家的演化與批判,已成為當代世界的重要思潮,和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簡單來說,結構主義探索一個文化是透過什么樣的相互關系(也就是結構)被表達和詮釋的。

2017年,那本當年為特倫斯·特納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拿到終身教職的書《豹的火》(The Fire of the Jaguar)終于在他過世2年后面世,這是芝大學者們,尤其是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后已經背棄北美學界、自我放逐到英格蘭的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極力推動的結果。格雷伯親自寫了導讀,而這篇導讀本身就是很好的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梳理與評價的理論力作。格雷伯在導讀的最后一段寫到,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人類學理論經典為后人銘記與學習。然而,與特倫斯·特納同樣以非凡的天才與博學聞名、也同樣飽受爭議的格雷伯沒過幾年就英年早逝了,這本書仍然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但是,格雷伯深受特倫斯·特納影響而寫出的《人類學價值理論:我們夢中的虛假硬幣》一書卻成了在人類學領域作出理論突破的一次珍貴的嘗試。
基于行動的即興宇宙觀
那么《豹的火》和《人類學價值理論》想要探索的究竟是什么呢?
《豹的火》是一部論文集,其中所有文章都與巴西原住民卡亞波部落的神話“豹之火”有關。這是一個簡單的起源神話,講的是一個被豹子收養過的人,最終為了人類從豹子那盜火,作為人類社會用火的起源的故事。特倫斯·特納的整個學術生涯見證了從結構主義如日中天到后結構主義無論如何無法跳出結構主義框架的理論解構過程,他所作的努力是希望把結構詮釋成一種基于行動的即興宇宙觀,而不是一個既定的框架,去限制對人的行為和選擇的詮釋。他在幾十年的田野調查中觀察到這個神話是如何被講述和表演的,人們會在怎樣的情境下,復述哪一段情節,去非常創意地詮釋正在發生的事情(為什么鄰居病了,或者為什么牲口不聽話),人們又會在表演這個神話的時候,哪個情節發生時,變得激動又狂野(哪怕他們已經聽過500多次了)。是人們的行動本身使得這個神話“成真”,被具體感受到,并具有意義和價值,所以我們不該把神話作為一種既定的結構或解釋框架,用觀察到的人類行為去套這個框架。特倫斯·特納認為行動與結構是互相成就的,而行動正是人類最有創意的一面,而且所有的結構都同時既是物質的,也是象征性的。掩蓋在他出了名難懂的寫作風格(這是他不愿意出版自己的書的一大重要原因,因為他認為需要比寫書更多的時間去解釋,才能讓別人搞懂他寫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之下的,是他認為自然而然的結論:即便是結構主義學家們也通常把結構寫作一種隱喻或轉喻,否則,如果結構是既定的,每個人就都只要自然而然地去接受命運就好了。但沒有一個真實的人的人生是這樣的。深受特倫斯·特納影響的格雷伯巧妙地轉換了一下視差,在他的價值理論研究中,問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讓我們覺得結構是最有價值的,而往往忽略了行動或行動者本身?
“價值”作為一個永恒存在的命題深刻影響了過去一個多世紀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每一種理論思辨。格雷伯和法國人類學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 1911—1998)同時認為價值理論是法國哲學與德國哲學界在關于個人主義和整體論的思辨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杜蒙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紀念講座上梳理了從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伊始歐美學界對“文化”的研究中對個人主義和整體論思辨的演化,和對個人價值與對社會作為整體的價值的認識怎樣影響了人們對意義的詮釋和行為選擇。格雷伯的價值理論并沒有嘗試做出閉環式的總結,而是不停地更深入地問各種有意思的問題,啟發我們對價值這個概念進行思考。所以我想,對格雷伯的價值理論進行探討的最佳方式也許不是做一個線性的梳理,而是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問過的一些有意思的問題。

比如說,格雷伯就受特倫斯·特納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解讀的影響,問過這樣一個問題:“假設我們都同意這樣一個前提,即世界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而且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共同更新我們共同創造的世界,但為什么最終我們創造出來的世界很少有人全心喜歡,大部分人覺得并不公平,而所有人都覺得無力掌控?”這個問題里面涉及關于價值的一個本質疑問,就是為什么人本身往往成為了實現自我或集體認可的價值的手段,而不是反過來讓價值成為讓人成就自我或自我滿足的手段。格雷伯同時也問過,為什么我們可以很舒服地去認可和討論根據單位經濟計算、通過工作創造的價值(往往由工資體現),但卻不敢去討論出于宗教信仰的政治選擇造成的價值波動,或者為了愛情或藝術放棄普遍認可的道德準則造成的價值波動?而這些價格往往是無法做等量經濟估算的。還有無處不在而且擔當了人類大部分創意表現的行動——家務,為什么一討論起來就變成了整體論式的價值觀(家庭價值、倫理價值)?格雷伯同時提醒我們,總是要問怎樣創造最大財富的人類社會在歷史中只存在了不到200年,在此之前的漫長歷史中,人類社會關心的不是這個問題。財富和金錢作為價值的象征并不是一個既有的結構,而是我們的經濟行為本身創造的關于金錢的神話。而且大部分時候,人們對于作為象征的結構是不關心的,他們關心的是行動本身,而且他們對價值的詮釋永遠在個體和整體以及不同整體間即興切換。那么在這無限可能的數量的整體和同樣無限可能的價值詮釋之上,存在絕對價值嗎?格雷伯的回答為否。這里我交給讀者們自行思考。

特倫斯·特納和格雷伯都并非會寫出經典教科書式著作或定義任何理論的學者,然而他們的努力的確改善了人類學過去半個世紀內定義自身學科的危機和解構的浪潮,而激勵了無數人類學家們重新鼓起勇氣去講有趣的故事,并進行理論更新和創造。
(責編: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