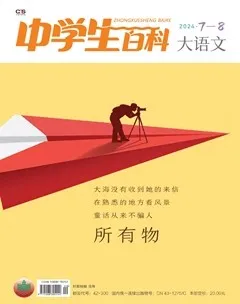歸隱處,有人冷落有人暖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式的隱居田園生活,是無數文人心里的夢。有的人只是做做夢,有的人卻親身實踐了,還有的人在入朝為官與隱居田園之間橫跳、擺蕩,比如唐代的王績,歷經三仕三隱。
1
王績,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叔爺爺,也就是王勃的爺爺的弟弟。王家是書香世家。王勃的爺爺叫王大通,是一個大儒。
王績年少成名,被譽為“神仙童子”。他第一次出來做官,是在隋朝末年。見隋煬帝殘暴無道,百姓民不聊生,他內心痛苦,終日借酒消愁。因為喝酒,他經常被彈劾。于是,在時局大亂之際,他駕一葉扁舟,趁著夜色飄然而去。
他第二次出來做官,是在唐高祖李淵時期。唐高祖為了穩定人心,征召以前在隋朝做過官的官員,王績也在其中。官員陳叔達見他嗜酒,將每日供給他的美酒數量由三升提至一斗。王績日夜痛飲,被人戲稱為“斗酒學士”。他可飲五斗酒而不醉,自稱“五斗先生”,還寫了《五斗先生傳》。后來,“玄武門之變”爆發,李世民獲得天子之位。對此,自幼受儒學浸染的王績無法接受,于是辭官了。
第三次做官,他請求任太樂丞,要在太樂署史焦革身旁為吏。為什么呢?原來焦革擅長釀酒。他就是為了喝酒而做官。那幾年,他過得十分開心,與焦革相處融洽,還學到了不少關于酒的知識。可惜呀,后來焦革去世了。焦革的妻子繼續給他送酒,可一年多以后也去世了。可惜呀,“天乃不令吾飽美酒”,他再一次棄官而去。這一次,是他真的決定離開,徹底離開沒有了美酒的官場。
表面上看,王績出來當官的理由非常不靠譜——酒在官場,人在官場;沒有酒了,就到了辭官的時候了。王績真心愛酒,不僅喝酒,他還為酒寫文章。在第三次隱居之后,他按照焦革家的釀酒方法寫了《酒經》,根據杜康和儀狄的釀酒技藝以及自己的理解編了《酒譜》。令人惋惜的是,這兩部著作都已失傳。
2
在第三次辭官之后,王績就徹底隱居了。有生活,有體驗,就必須寫詩來抒發一下感情了,于是他寫了這首《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這首詩寫的是一個秋天傍晚的山野景象。這里的東皋,據說在山西河津,未必就叫東皋村。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并序)》中寫過“登東皋以舒嘯”,東皋指的是村子東邊臨水的一塊高地。詩中的東皋是王績隱居的地方,他還為自己取了一個號,叫“東皋子”。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這兩句里有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薄暮,指傍晚的時候。傍晚,如果對應著人的一生,就是晚年了。王績一生經歷了兩個朝代,一個是隋朝,一個是唐朝。在亂世,他隱居;在盛世,他也隱居。隱居之后,他還在想,我應該何去何從,就像曹操在《短歌行》當中寫過的南飛的烏鵲——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表面上寫的是夕陽落山時的山野秋景,實際上是說,這些自然景物并不會隨著朝代變遷而改變。自然界就是這般無情呀,不管人間是非。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在黃昏的時候,牧人返歸,僅僅帶著幾頭牛犢而已;獵人打獵歸來,他所謂的獵物不過是幾只小鳥。他們的收獲是如此菲薄。“相顧無相識”,指的是牧人、獵人與“我”,三者之間誰也不認識誰。人與人之間有著隔膜,他們或許并不交談。人們形色匆匆,只是為了活下去。
“長歌懷采薇”是什么意思呢?此句用了《詩經·采薇》當中的典故。伯夷和叔齊,本是商朝人,在商朝被周朝滅了之后,隱居在首陽山。他們以吃周朝的糧食為恥,采野菜吃,最后活活餓死了。世人因此將這二人視為抱節守志的典范。在王績心中,做人是要有操守的。
他沉醉酒鄉,就是為了逃避現實。他從朝堂走向了田園,無人識他,他也不識人,天地茫茫竟然沒有一個知音。他欣賞伯夷和叔齊,只能做他們的隔世知音。
無論是做官還是歸隱,王績都不痛快。他的內心都是寂寥的、冷落的,那里有故鄉田園也無法安撫的憂傷。
3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
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王維的這首《渭川田家》,看起來是不是和王績的《野望》很像?兩首詩寫的都是山野田園生活中日暮歸家的景象。有人推測《渭川田家》是王維隱居于藍田,大約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游覽了渭水兩岸的農村之后,有感而作。
“夕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這個“歸”字寫的就是一個夕陽西下的場景。牛羊歸欄,人也歸家。“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我們要注意“野老”的意思,指的是慈祥的老人,可能是隱居的人,也可能是在野外行走的人,比如詩人自己。在這里,結合“念牧童”和“倚杖候荊扉”,可以確定指的是老人家。守在家里的老人家正看放牧的小孩子有沒有回來,結果小孩子就帶著牛羊回來了。“荊扉”,這個用荊條搭建的柴門,是一個非常有鄉村韻味的事物。“候”就是等候,有人在等待的場景,就是有人在等你回家。有人在等候的家就是一個溫暖的港灣。
“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野雞幾聲叫喚,像在呼喚自己的伴侶。“麥苗秀”,麥子開著花朵。“蠶眠桑葉稀”,指的是蠶在蛻皮的時候,不吃不動,就像睡著了一樣——天地安靜,時間暫停。
“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農夫們三三兩兩地回來了,他們在路上碰見就會溫柔平和地說話。“依依”,這個疊音詞寫出了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交流,有一種關懷,有一種依依不舍的深情。一切都這么溫馨,這么美好。
“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詩人多么羨慕這種閑逸的田園生活!《式微》詩中反復詠嘆:“式微,式微,胡不歸?”你為什么不歸去呢?為什么不隱居起來呢?王維會有這樣一種歸去的想法,是因為他細膩的內心感受到了田園生活的美好與溫暖。在他眼中,田園是身體和心靈棲息的地方,是令人安然歸去的地方。
當然,話說回來,王維不會像陶淵明那樣貼近田園,做一個自食其力的耕作者。他的感觸體驗是隱士的,而不是農民的。王維詩中的安靜之氣,是文人之氣。即便如此,他所向往的人與人之間相依相伴的感覺,依然是真實的。
4
日暮思歸。這兩位詩人皆以隱居生活為題材,描繪了黃昏時分的景象,表達了歸隱之情。然而,仔細品味這兩首詩,你會發現它們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展現了不同的詩歌風格,反映出了各自時代的氛圍。《野望》呈現了凄涼蕭瑟的QKBmZU/+aLSZ5ZtuEZ69XzUg4mwEhl1XM9cl+/+AQRU=秋思,抒發了時代變遷中的跌宕心境。相比之下,《渭川田家》則充滿了和諧悠遠的春意,傳達了盛世中從容歡樂的感悟。
春華秋實,農耕時代的田園并沒有太大的變化,變化的,只是感受田園的人心中的風景。心,是世界的起點。心念一轉,境界不同。
在這兩首詩的結尾,王績迷失在對人生歸途的找尋中;而王維擁抱現實,擁抱人群。王維對人情和人群抱有希望,渴望與現實中的人們交流互動。王維給我們一個錯覺——“詩佛”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大錯特錯了!王維是熱情的,能夠主動敞開心扉,能夠與農夫等社會不同階層的人“語依依”。可以說,王維詩的人情之美就源于此。他將感受到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寫出來,讓讀的人體會到暖和甜,嘆人間值得。

另外,這兩首詩的藝術形式也值得一提。
王維選擇了相對自由的古風寫作《渭川田家》。他自在地走過曠野和村莊,眷念著溫馨寧靜的田園生活,認定這里就是靈魂的歸宿。
而王績,作為一名詩人,在大眾視野里,他的存在感似乎不強。實際上,王績所寫的《野望》在中國詩歌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第一首非常成熟的五言律詩,首尾兩聯抒情,中間兩聯敘事,對仗工整。這首詩橫空出世,一洗當時詩歌創作流行的綺麗文風。人們自南北朝一路讀下來,所見的詩歌大多是濃妝艷抹的,當讀到王績這首詩時,就感覺像忽然看到了一個荊釵布裙、眉目清秀的女子,眼前一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