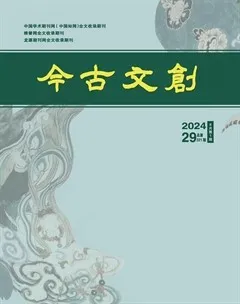困境與突圍
【摘要】加繆在《鼠疫》中深刻洞悉了瘟疫爆發下個體和群體生活以及心理的巨大變化。他用隱喻的形式深化了疾病書寫的內涵,指出疾病在引發恐懼和死亡的同時也能催喚起新生的精神力量,并促成個體及群體的認知轉變,包括對人本身、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多重關系的再思考和重新界定,集體意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也由此萌生。
【關鍵詞】加繆;《鼠疫》;疾病書寫;文學隱喻;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I5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9-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09
基金項目:巢湖學院校級科研一般項目“新冠疫情背景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瘟疫書寫研究——以《鼠疫》為例”(項目編號:XWY-20220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項目:2022年安徽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類重點項目“族裔散居下毛翔青早期作品中的文化身份構建”(項目編號:2022AH051690);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于多模態語料庫的外宣英文網站中‘中國故事’話語研究”(項目編號:23YJA740037)。
與薩特并稱為“戰后法國的良心”的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是法國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其重要代表作《鼠疫》是描繪20世紀40年代阿爾及利亞奧蘭城鼠疫肆虐的文學巨著。在這部小說中,加繆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筆觸,揭示了疾病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如何塑造他們的命運,以及如何促使人們形成命運共同體。
小說自出版以來便廣受關注和褒揚。國內外學者對于《鼠疫》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存在主義、荒誕哲學、人本主義和敘事學等角度,對作品中的疾病現象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聚焦于小說中的疾病書寫,探索瘟疫下個體和群體的創傷和認知轉變,以及集體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萌生。
一、文學隱喻下的疾病書寫
疾病書寫在文學作品中較為普遍,尤其是在大規模瘟疫爆發的背景下,作家會以疾病隱喻其對個體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如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中黑死病橫掃歐洲時的凄慘和絕望,笛福《瘟疫年紀事》中1665年大瘟疫爆發時的恐慌和無助。其中,加繆的《鼠疫》更是從正面描寫了鼠疫這一烈性傳染病給個體和社會帶來的創傷。
在加繆筆下,疾病使特定時期的生活方式、心理機制和認知結構等發生變化,因而又被賦予多重隱喻意義。加繆在小說中描繪了瘟疫爆發時的慘烈狀況,并以瘟疫書寫建構了災難、宗教和道德的三重隱喻。
(一)疾病的災難隱喻
在瘟疫背景下,人們一旦沾染疾病,就會與未感染者區分開來。疾病不僅打破了身體的平衡,更是打破了患者生存空間的平衡。在小說中,當鼠疫疫情發展到近乎難以控制的態勢時,官方下令實施封城舉措。醫生配合警察的工作,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經發現,便會立即帶往隔離點。無論是病人還是病人家屬,從被帶出去的那一刻,基本就意味著就此永別;而尚未感染的人也會在悲傷和恐懼的夾擊中惶惶不可終日。當疫情褪去,城市又恢復了往日的生機,但是人們似乎無法正視這場來勢洶洶的浩劫。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只要他們還未找出科學有效的抗疫方法,鼠疫隨時都有可能卷土重來并再次把人類拉入可怖的人間煉獄。
(二)疾病的宗教隱喻
隨著古代幾次瘟疫的大爆發,醫療知識和醫療手段的滯后性與瘟疫擴散蔓延的爆發性形成了強烈反差,醫學在疫情面前似乎失去了原有效力。因而,身處困境中的人們甚至放棄了對醫學的期待并轉而訴諸宗教,渴望借用宗教的力量尋得生命的救贖和心靈的療愈。
在小說中,由于愈發失控的疫情態勢和民眾難以遏制的恐慌,教會決定舉行為期一周的祈禱儀式。帕納魯神甫在教堂的第一場布道中就為此次疫情的發生進行了歸因:身處水深火熱中的奧蘭城市民都是罪有應得。他認為這場災難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并勸誡人們只有完全信任上帝并真誠禱告,才會幸免于難。即使在后期自己也感染瘟疫,他也堅信自己真誠的禱告就是唯一藥方而拒絕接收醫學治療。然而,這位堅定的信仰者最終也因身染惡疾而撒手人寰。信奉上帝的神甫也未能被救贖,這一事實又再一次加劇了群眾的恐懼。通過神甫這一人物命運安排,加繆表明了自己對瘟疫宗教隱喻的立場——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宗教只存在于人們的情感寄托中,永遠無法幫助人們戰勝客觀存在的瘟疫。
(三)疾病的道德隱喻
作為烈性傳染病,瘟疫會在短時間爆發蔓延,進而引發大范圍社會恐慌和秩序混亂。官方往往會通過多種渠道來宣揚在特殊時期勇于奉獻、不畏犧牲的英雄事跡,給民眾以情感渲染和道德感化。
在小說中,塔魯就是這樣的“時事英雄”。雖是一名外來人口,在鼠疫橫掃奧蘭城時,塔魯毅然將個人安危拋之腦后,主動要求加入感染風險極大的衛生醫療隊伍。然而,加繆卻否認其為一名可歌可頌的“英雄”,他在文中借用里厄醫生的口吻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于夸張,最后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1]403事實上,塔魯是把鼠疫視作可以輕易將個體置于死地的疾病,他給予患者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并企圖用滿腔熱情和必勝的決心與之抗衡。然而這又無外乎在無形中認同、接受并內化了鼠疫的道德隱喻意義,且將其作為道德的對立面加以反抗,尚未真正認識到鼠疫的客觀存在性。此外,作為一個滿身道德污點的罪人,鼠疫并未對科塔爾這種缺乏道德的惡人施以懲罰或宣判死刑。
勇敢無私的塔魯因感染鼠疫而亡,陰暗自私的柯塔爾卻能在鼠疫中茍活,這樣的人物結局安排是加繆對疾病的道德隱喻的一種駁斥。作為客觀存在的瘟疫,鼠疫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個體,既不會因個體高尚的品德而授予“免死金牌”,也不會因個體道德瑕疵而對其宣判死亡。
二、亦滅亦生——疾病的雙重影響
瘟疫的爆發必然引發個體生命的萎靡和死亡以及精神的迷失和異化,但是同時也會催生出強烈的新生力量,激發人類的求生意志和情感需求。
(一)疾病引發的生命死亡和精神異化
疾病會致使人的生理性死亡,即個體生命的終結。在小說“無辜的病孩”這一章節,加繆具體描述了因感染鼠疫而死亡的孩子形象:“他小小的軀體已經完全被瘟神的魔爪控制,被折磨得筋疲力盡,瘦骨嶙峋,離開人世時臉上還殘留著淚痕。”[1]267感染鼠疫的患者在經受了漫長劇烈的痛苦后咽下最后一口氣,而后被蒙上白布送往墳場。隨著死亡人數的不斷攀升,奧蘭城已經沒有空閑土地用以尸體埋葬了,后期甚至出現尸體隨意丟棄的現象。
同時,疾病會致使人的社會性死亡,即個體之間關系的疏離。當被確診以后,患者會處于嚴格的封閉隔離中而無法與他人交流;為了防止傳染,在社會空間中,每個人都與他人保持距離。更糟糕的是,健康人會無意識地將患者的感染癥狀投射于自身,這一心理投射多會引發嚴重的心理危機。為避免引發個體恐慌的自我投射及可能的疾病傳染,人們會避免與他人近距離接觸。小說描繪了人們彼此刻意疏遠的場景:大家都戴起了薄紗口罩,即使交談也保持一定距離。這種在與外界和他人的持續疏離中,個體自我生命力也會不斷減弱并陷于難以調和的身心矛盾中。
社會將疾病人格化,并把患者釘在“恥辱柱”上,患者的自我歸屬感和認同感也會隨之受到損害。疾病給個體帶來的不僅僅是痛苦的創傷體驗,更有創傷后難以釋懷的負面情緒和消極情感。隨著瘟疫的持續擴散,恐懼和懷疑在個體內心瘋狂滋生,人性的自私和無助在瘟疫面前凸顯得更為淋漓盡致。這不僅對社會的相互關系和秩序造成了沖擊,還可能引發經濟困境和地區沖突。
(二)疾病催生的新生力量
疾病在導致以上困境的同時也催發了新生力量,包括生命主體的求救意識和情感補償需求。人類對于疾病的探索過程就是生命主體的自救過程,只有找到正確科學醫治方法,個體才有可能保全自我,社會才有可能穩定發展。在小說中,面對瘟疫的無情襲擊,個體生命顯得尤為脆弱。奧蘭城的人們祈求逃過此劫,求生欲望達到頂峰。父母在面對可能會被感染或者已經感染的孩子更是驚恐萬分。有人抱著孩子不停地祈禱,懇求上帝放過他們;有人哀求醫生給出特效藥方,以緩解巨大傷痛。
同時,在瘟疫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節奏、社交方式乃至心理狀態都可能發生深刻的變化。面對這樣的挑戰,情感補償成了一種重要的心理支持機制,有助于緩解焦慮、孤獨等負面情緒,增強個體的心理韌性。在他者關聯理論中,弗洛姆強調了與有生命的他者建立關聯的必要性,并指出個體的健康有賴于他者關聯情感的滿足。小說中描寫了純粹至深的情感,有深沉的親情,如里厄母親對里厄的關心和愛護;有深厚動人的友情,如里厄與塔魯的心心相惜和相互扶持;還有陌生人之間的鼓勵和善意。這些美好的情感都給人以溫暖和慰藉,以及繼續生活的勇氣和希望。
三、疾病影響下的認知轉變
如同自然災害一般,疾病自始至終貫穿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對于人類來說,瘟疫這種大型烈性傳染病是一項復雜而棘手的挑戰,涉及眾多復雜的因素和層面,每一場瘟疫的爆發都不是個體可以輕率解讀和簡單剖析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會對自我以及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多重認知關系產生轉變,試圖去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模式、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等。
(一)人與自然關系的再思考
在瘟疫這一特殊背景下,個體會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再思考,并對自我身份進行了重新定位。
小說開頭便指出,奧蘭城市民工作的唯一的目標就是賺錢發財。這實際上是病態的“金錢社會”,看似物質財富已經幫助人們擺脫了貧窮并走向文明新階段,但有時對于物質的過度崇拜恰恰是一種極端化的野蠻。鼠疫的突然爆發,打破了城市的寧靜與秩序,使得人們陷入了恐慌與絕望之中。這種無力感,反映了人類在面對自然力量時的脆弱性。
人類在瘟疫面前的束手無策和驚慌失措表明了人類并非是整體自然界的主宰和中心。加繆以一貫的冷靜自持,犀利地指出事態的真相—— “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在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催禍患,重新吸取教訓。”[1]288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永恒話題。在瘟疫肆虐后,人類重新審視自我位置,并重拾對自然界的敬畏之情。
(二)集體意識與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萌發
17世紀英國著名玄學派詩人約翰·鄧恩在《喪鐘為誰而鳴:生死邊緣的沉思錄》中寫道:“沒有人是與世隔絕的孤島;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都讓我受損,因為我與人類息息相關;因此,別去打聽鐘聲為誰鳴響,它為你鳴響。”[3]2這種“喪鐘為你我敲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小說中同樣有所體現。
在鼠疫的肆虐下,個體的生存變得異常艱難,人們不得不放棄部分個人自由,轉而尋求集體的保護與幫助。這種集體意識的萌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斷地恐慌、絕望與掙扎中逐漸形成的。人們逐漸意識到,只有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災難,才能有可能戰勝鼠疫并重獲新生。在集體意識的形成過程中,命運共同體意識也隨之萌生。人們逐漸認識到,在這場災難面前,每個人都是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每個人的命運都與他人緊密相連。這種命運共同體意識不僅體現在人們之間的互相幫助與支持上,更體現在對共同目標的追求與堅守上。人們開始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為了整個社區的安寧而奮斗。
新聞記者朗貝爾原本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但隨著疫情的擴散,他逐漸意識到抗疫是一場需要人人參與的持久戰,利他即利己,他人命運即為自我命運;科塔爾曾因抑郁悲觀而差點自殺,但當他投入抗疫的洪流中,想要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時,他逐漸找到了自我價值感和歸屬感。人們逐漸意識到這樣的事實:個體的命運已融入以鼠疫和全體市民共有的情感和記憶構成的群體命運中。小說中的主人公以及眾多普通市民,都在這場災難中展現出了強烈的集體意識與命運共同體意識。他們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成了一個緊密團結、生死與共的集體。他們共同面對災難,共同承擔責任,共同追求希望。這種集體意識與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萌生,不僅讓他們在災難中找到了力量與勇氣,也讓他們在困境中找到了人性的光輝與希望。
四、結語
不可否認,疾病與人類共生共存。它不僅僅局限于醫學領域,還深入涉及歷史和文化等多個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幾乎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疾病的困擾,而文學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揭示疾病在個體生命中的深刻意義,并引導我們正確看待疾病。通過疾病的書寫,《鼠疫》成功地構建了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觀念。這部小說不僅揭示了人類在面對災難時的種種反應,也展現了人類在面對困境時的團結與互助。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認識到,無論面對何種災難,人類都需要構建命運共同體,共同應對,才能最終戰勝困境,實現自我救贖。
正如王曉路所指出:“實際上,疾病和醫學已經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學表征不僅是在主題上,當然也不僅僅只有關于鼠疫的創傷記憶和書寫。”[4]《鼠疫》以其深刻的疾病書寫和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建構,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人類社會的獨特視角。這部作品不僅是對人類命運的深刻反思,也是對人性、社會以及人類未來的深刻洞察。因此,對這部小說的解讀和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加繆的文學思想,以及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參考文獻:
[1]加繆.鼠疫[M].劉方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2]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3]歐內斯特·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M].李堯,溫小鈺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3.
[4]王曉路.疾病文化與文學表征——以歐洲中世紀鼠疫為例[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27-33.
[5]王予霞.西方文學中的疾病與恐懼[J].外國文學研究,2003,(6):141-146.
[6]麥克尼爾.瘟疫與人[M].余新忠,畢會成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作者簡介:
馬曼華,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