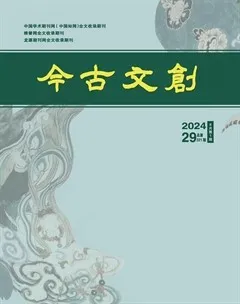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詩經 · 大雅》史詩音樂的社會功能
【摘要】上古社會,音樂已經成為先民祭祀活動、農業生活時歌功頌德、禮樂教化的重要表現形式。《詩經·大雅》中的史詩音樂不僅有利于人們研究西周開國史,并且其強大的社會功能,對培養個人道德情感、維系家族倫理觀念以及穩定政治統治等都發揮著重要功能。
【關鍵詞】《詩經·大雅》;史詩音樂;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9-008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25
一、上古音樂的發展及社會功能
早在我國的原始社會,先民們就已經開始熟練地運用工具去創造和使用音樂了,雖然那時的人們無法解釋音樂本身是什么,但卻可以本能地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通過祭拜上帝和祖先的方式,保佑他們的生產生活,以確保生存環境的穩定和部落血脈的不斷延續。因此,原始社會的音樂多服務于祭祀活動,而這一傳統也在之后音樂的不斷發展中得以保留下來。
隨著夏朝的建立,氏族文化開始向奴隸制文化轉型,音樂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是更加關注對英雄人物功績的謳歌。例如,為表現夏朝開國君主大禹的治水功績,創作了《大夏》舞曲。《呂氏春秋·古樂》記載了此曲誕生之緣由:“禹立……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于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1]《大夏》舞曲以大禹的英雄功績為主要內容,其目的在于“以昭其功”,即通過音樂表演來引起演奏者和表演者的情感共鳴,進而產生民眾對英雄的崇拜,社會責任感也會應運而生。
再到殷商社會,“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2]。殷商王朝注重通過音樂將人與鬼神相通,達到一種“天人交互”的狀態。這種“天人交互”的狀態,不同于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主要是對先王、先妣的祭祀和崇拜,即“祖先崇拜”。
到周代,音樂則發展為一種與“禮”結合的“禮樂”共存狀態,統治階級將傳統的祭祀性禮樂文化轉換為一種政治性禮樂文化,即音樂不僅可以祭祀先祖和贊頌王者,而且可以體現出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德性文化。
二、《詩經·大雅》中的史詩音樂
《大雅》作為一種樂歌名,其音樂本體的功能在周代德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政治倫理功能。《禮記·樂記》有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矣。”[3]儒家學者在研究《詩經》的過程中,認為詩作為音樂,本身就與政治具有一定的關系,且認為“樂者,通倫理也”,即音樂與倫理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從《大雅》的具體內容看,《詩經·大雅》共三十一篇,其中《文王》《大明》《綿》《皇矣》《生民》《公劉》六篇記載了周先祖開疆擴土之歷史功績,程俊英先生在《詩經譯注》中將這六篇稱為“周代史詩”[4]。這六篇史詩敘述了周始祖后稷開創農業,經公劉、古公亶父對建筑和交通等生存條件的開拓,并在兩次遷徙中力克戎狄,創造出較為安穩的生存環境,再由季歷轉功業為德政,最后落腳于文王武王成就偉業德治天下。內容涉及我國古代農業、政治、戰爭以及祭祀等,為西周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支持。因此,相較于前朝音樂,這六首史詩內容的豐富程度使其價值不再拘泥于祭祀和歌頌,轉而表現出一種倫理規范和政治訴求。
《大雅》與《國風》雖同為樂調,但區別于《國風》中富于人民性的民歌,《大雅》史詩則更多地關注于道德教化,以及夾雜著具有部分真實性的歷史記述和一定文學價值的古代神話,其作為樂調本身的傳播性和感染性會對人自身的情感和倫理觀念產生影響。《禮記·樂記》中記載:“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5]聽《雅》聲,會使人產生出一種自發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國風》中“風土之音”,而是類似于在演奏《大夏》時那種人與自然抗爭搏斗,并付出巨大犧牲取得勝利后的一種深刻的社會情感,或者是《禮記·樂記》中記載地對《大武舞》的演奏:“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6]整個舞曲表現了武王對于伐紂的決心與信心,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情感,而且這種情感來自個人卻又不屬于個人,是一種群體性的情緒與感受,這是《大雅》史詩與《國風》的最大區別,也是這種史詩音樂要達到目的的必要效果。
三、《詩經·大雅》史詩音樂的社會功能
對于大雅史詩的作用,《禮記·樂記》中提到:“……群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6]不論男女長幼,貴族百姓,都要經歷禮樂的教化,這種教育中的美育作用遠遠小于道德作用,與其說是美育,不如說是一種德育,且這種德育通過血緣倫理進行規定,進而有益于政權的穩定。
(一)《詩經·大雅》史詩音樂的道德情感功能
《詩經·大雅》中的六首周代史詩都作于西周前期,作為史詩,其音樂本身對人的道德情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周代,音樂與道德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劉向說過:“凡從外入者,莫深于聲音……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7]樂既是實現人的道德教化的最好的方式,也是調和禮所帶來的差異性的合理方法。在禮所帶來等級差異的同時,也會帶來因差異而產生的不滿,而樂就通過對人情感的調和與道德的培養,使人們心情舒緩并且接受這種差異性,這就是禮、樂、德的相互關系。
《禮記·樂記》中認為這種關系的根源在于人心對音樂的感知。《禮記·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8]儒家學者認為,“樂”由音所生,而究其根本在于人心之有感于外界事物。有了人心對外物的感知,才會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才會有不同種類的音樂,而這些音樂也會表現出不同的情感,也就意味著會使人產生出不同的道德自覺。
在《詩經·大雅》的六篇史詩中,不同史詩的音樂韻律不同,所激發的人的道德情感也有所不同。在表現武王克商的戰爭場景時,多采用對戰場環境的描寫,且多用疊字。例如《詩經·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通過“洋洋”“煌煌”“彭彭”等疊字的用法,不僅從側面描繪出了壯闊的戰爭場面,而且也可以通過樂調激發出人內心一種如臨戰爭,奮勇殺敵的情感。《詩經·大雅·皇矣》“臨衛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臨衛茀茀,崇墉仡仡。”運用排比的疊詞,真實地再現了商軍在周武王所帶領軍隊的猛烈攻擊下,土崩瓦解,徹底失敗的情景。彰顯了周“戰必勝矣”的昂揚之氣。在描繪文王之德行時,圍繞天命與德業,再通過樂調舒緩展開,使人產生一種緩和、依附的心情,例如:《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升降,在帝左右。”樂調中時刻不離“上帝”與周的關系,這種感受在人的內心中形成一種對周的崇拜感與依附感,這種崇拜感和依附感是周“魅力型”權力——“克里斯瑪”權威崇拜所必要的。
因此,《詩經·大雅》作為音樂在廣泛傳播的過程中,這種“作為音樂本體的道德作用”對于人內心主體的道德的教化與約束,符合周“德治”的要求。《詩經·大雅》的六首史詩音樂,既體現了周對《大雅》音樂本體功能的合理運用,也體現了在德治過程中對禮所產生的差異性的調和。
(二)《詩經·大雅》史詩音樂的倫理功能
《禮記·樂記》認為:“樂者,通倫理也。”[9]《詩經·大雅》史詩音樂會產生一種由內而外的社會情感,從而使人民產生出一種自覺的倫理規范,通過史詩音樂激發出人自身的倫理自覺。
西周之初,整個社會仍舊保存了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遺制,并逐漸發展為西周宗法等級制。劉大杰指出:“君主政治與父權的家族制度加強以后,于是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尊祖敬天的宗教觀念更為進展……這兩種觀念互相結合推演,祖先也可以配天,于是形成一種上帝祖先的混合宗教,家族組織便成為政治上的主要元素,宗法精神遂成為國家政治上的主要精神了。”[10]而這種一脈相傳的血緣宗法,在《詩經·大雅》六首史詩音樂中得以體現。從《生民》詩起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是為周始祖后稷誕生所送出的祈福,也是強調周始祖的天命不凡。至《公劉》詩“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鍭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和《綿》詩中極富內涵的“綿綿瓜瓞”,強調了周氏族子嗣的連綿不斷,并將周氏族德行一以貫之。再至《皇矣》詩“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和《大明》詩對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結婚的事件的述說,體現著對氏族繼承的重視。最后落腳于《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將周氏族血脈的延續性通過音樂史詩這一形式完美地表現出來。
朱貽庭提道:“所謂西周的道德,實際上就是宗法等級道德。”[11]這種對血緣等級的重視,根本在于生產資料(大部分為土地)歸“王”,即奴隸主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2],因此為了強調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及鞏固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遺制,通過禮與樂相輔相成,“比經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13],將倫理與音樂交融,通過音樂將統治階級自身利益合理化,這不僅體現了周初政權統治的政治智慧,也體現了我國古代倫理道德中以家族為本位或個體必須服從于家族的等級秩序的整體意識。在《禮記·樂記》中也多次提到禮與樂的相互關系與秩序觀念:“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14]
(三)《詩經·大雅》史詩音樂的政治功能
《禮記·樂記》又認為:“聲音之道,與政通矣。”[3]周王朝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綱紀天下,為了達到宗親和睦,君臣一體的政治效果,音樂所表現出的政治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詩經·大雅》中的六首史詩音樂作為先王贊歌,表達了克配上天、以德保民之意。王國維提道:“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15]他認為周公所確立的宗法制、分封制等“禮制”,實則是以“德”為核心的等級制,一切的社會活動都歸于“德”,而“德”又為政治所服務。因此,為了表現出周朝的以德配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之意,《詩經·大雅》的六首史詩音樂通過對周歷代先祖的贊頌,集中體現了君權神授、代天行治、維德之行的政權合法性。在《生民》詩中,通過神話對周始祖后稷進行神化:“牛羊腓字之”“會伐平林”“鳥覆翼之”等“神跡”使人確信后稷就是上天派來,代天行治的天命之主。到《公劉》“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詠嘆”;《綿》“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皇矣》“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比與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中周幾代人通過不斷地耕耘努力與以德服人,從而不斷贏得民心,為周朝基業的不斷發展壯大攢下群眾基礎,在克配于天成為人君之后,修德修行,敬天保民。最后落腳于《大明》“厥德不回,以受六國”與《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夏傳才評價道:“詩的第一章寫一代興亡系于天命,而天德合一,天命無常,唯德是從。這是西周統治者的天命論,說明他們之所以能夠取代殷商奴隸主,是因為他們‘維德之行’而獲天命。”[16]文王之所以能得“天命”,是祖先“維德之行”的結果,這個結果通過《詩經·大雅》六首史詩音樂得以彰顯。
其次,《詩經·大雅》六首史詩音樂作為社會意識的載體,反映了周代政權對于穩定的需求。音樂和道德都來自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是一種社會意識,可以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的一些具體情況。《禮記·樂記》中也記載了這種情況。例如對民生的反映“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17]。不同的音樂所反映出具體地方的民風不同,而音樂也可以反映出整個社會的人民整體情緒的變化:“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因此,每個地方的道德可以通過音樂表現出來,而音樂又可以體現出政治的動蕩與穩定。
周王室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周初,周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以“和”為目的,通過這種“和”來產生周人百姓自身的“歸屬感”以及臣服部落和商之百姓的“臣服感”,也就是“王者功成作樂”,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鞏固統治。周初國家撰寫史詩并通過音樂去傳播,是為了拉近人民與國家的距離,使人民產生出一種由內而外的臣服感以及歸屬感(土地)。而至于商的貴族,周武王沒有過多的去對他們進行追責,只把罪歸于紂一人,稱之為“一夫”,也就是“獨夫”,原因在于武王看到殷貴族人數眾多,勢力龐大,存在發生叛亂的情況,所以通過這種方法防止叛亂的發生。在《詩經·大雅》六首周代史詩音樂中,通過“天命”與“德行”所賦予“歸屬感”與“臣服感”,使周朝政權的穩定性得到保障。
總而言之,《詩經·大雅》史詩音樂所呈現出的不僅僅是文學價值與藝術價值,其所反映的倫理價值也不容忽視。在長期處于禮樂文明孕育的古代社會中,《詩經·大雅》史詩音樂的社會功能既可以對個人道德情感的培養具有教化作用,也為統治階級的倫理道德以及政治教育帶來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增訂版)[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213.
[2]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728.
[3]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72.
[4]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65.
[5]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502.
[6]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88.
[7](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0:508.
[8]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71-472.
[9]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73.
[10]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9.
[11]朱貽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第五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28.
[12]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27.
[13]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85.
[14]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76, 477,478.
[15]傅杰編校.王國維論學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2.
[16]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M].北京:語文出版社,1985: 143.
[17]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47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