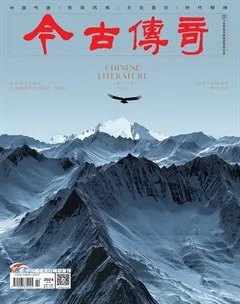古人的吃與行
之一:驚見古人食單
吃是人的必需,也是一種文化。吃的文化是所有文化中最博雜的一類,我們天天為這種文化而活著,卻很難說出個子丑寅卯來。說不清的硬要說,好像有點自討苦吃的意思。不過,既然吃也可以“啟動內需”,且能抉幽發微,從古人的食單上偷學一二絕招,或許是可以大有裨益于天下食客的。
每個地方的飲食習慣不同,每個時代的偏好也不一樣。皇宮與民間的飲食截然兩類,名人有名人的雅好,官人有官人的排場,譬如王羲之、蘇東坡愛吃鵝,毛澤東愛吃紅燒肉,所謂“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對于飲食,古人著述太多,不提也罷,無非講究“水陸羅列”或自家發明。東坡肉、叫花雞,滿漢全席、八大菜系,西湖莼菜舟山鲞,烹龍炮鳳麒麟脯,山珍海味人參燕窩熊掌雀舌……凡此種種,葷食素食紅案白案,盡填肚腹。杜甫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美食及美食者之外,尚有“餓殍遍野”“爭食人肉”的慘狀,觀音土、槐樹花、苦苦菜、谷糠粑,不在飲食文化之內,卻也活人養人,常為人間留點活口,為閻王減點負擔。孔夫子說:“食、色,性也。”想古今四方,口如大海,無物不可以吃(毒物除外),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埋的、樹上結的,人人都在吃,天天都在吃。好在天生萬物,生生不息,吃了幾萬年,似乎是吃不盡的了。
我生于貧寒之家,吃的好東西太少,吃的苦倒挺多。富貴之人天天吃美味,貧寒之人天天吃苦頭,似乎也是天經地義了。我雖貧寒,然于飲食文化,倒也頗有些興趣。吃不到的東西,從古今書本里去讀一讀,用心體會一二,也算是一種心理滿足吧。
讀古人寫的食譜,是很有意思的,讀多了,就對每個朝代的所謂飲食文化有了一個大概的印象。中國人崇尚吃,西方人崇尚性,這是東西方文化的一大差異。中國人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能吃出花樣來,所謂“一招鮮,吃遍天”就是這個意思。中國的飲食文化源遠流長,古人吃的東西,都是“無公害”的“綠色食品”之類,所以,我的感覺是古人比今人要幸運多了。
唐代的中國是足以讓中國人自豪一萬年的偉大帝國,以詩為核心的文化自不必說了,開放跨國婚姻、跨國商貿的程度,也不必說了,博大廣袤的疆土與國富民強也不說了,僅唐代的飲食文化,就可以看出一個偉大帝國的創新與廣博大氣來。
從正史及一些零星的關于唐代的食單上,我注意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在華清宮經常一起吃一種叫“駝蹄羹”的湯。這種東西是以駱駝蹄掌為主要原料再輔以其他山珍烹制的羹湯,聽說“一甌值千金”,但如何烹制法,史料闕如。唐玄宗除了與楊玉環同吃駝蹄羹,還請安祿山這個胡兒吃過“野豬鲊”。野豬鲊是野豬肉剔骨煮熟,晾干切片,用粳米飯相拌,加上茱萸子和食鹽放入壇內,黃泥密封晾曬經月,再蒸熟加各種佐料食之,其味鮮美無比。而奸相李林甫家有一種“甘露羹”,是用何首烏、鹿血、鹿筋制作的美味,在唐代很是著名,據說吃了可以讓人返老還童、白發轉青。唐懿宗與同昌公主所食“紅虬脯”,我無論如何想不出究竟是什么東西,查工具書得知“虬”為傳說中的無角龍,長須卷曲濃密,而“紅虬脯長一丈,以箸抑之,無三數分,撤即復如狀”,大約是一種韌性極強的帶狀食物了。“脯”為肉類,什么肉就不知道了。
除了這些皇族和大官的名食,還有一種在唐代頗為流行的美食,叫作“渾羊歿忽”,名字帶點“胡”味,何人所創不太清楚,大約是宮廷流傳到達官富豪與士大夫家庭的。其制法是:殺鵝去毛除內臟,再填以五味肉末與糯米,再殺一頭大羊去內臟,將鵝置入羊腹,放在火上燒烤,待整頭羊烤得金黃熟透,棄羊不用,取羊腹中鵝分而食之。這種吃法,似乎早已失傳了,肯定好吃,但未免太浪費了些,所以說,大唐就是大唐,講氣派的。
唐代思想開放,社會繁榮,名人自創名菜,老百姓也變著花樣,宮廷吃食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飲食文化發達是十分自然的事。
五代時北方豪族韓熙載到南唐做了大官,但受到后主李煜的猜忌,只好沉湎于聲色。李煜派畫師顧閎中到韓家窺探,顧氏憑記憶繪出反映韓熙載夜開豪宴的長卷呈給后主。這幅《韓熙載夜宴圖》,遂成為中國畫史上最著名的一幅反映古人豪宴情況的不朽之作。畫面分為五個部分:一部分描繪美髯長身的韓熙載與眾賓客宴前聽樂伎彈琵琶;二部分表現韓熙載為跳六幺舞的家妓王屋山助興擊鼓;三部分歇息圖景;四部分坦腹聽樂;五部分散宴送客。整個畫面并未涉筆飲食的場面,但你會感覺出那種豪奢程度。
宋代詞風大盛,但飲食的創新就遜色于唐代,宋人講究精致,唐人講究天下渾融,吸納性強。宋徽宗很愛華貴的餐具與酒器,他在一次大宴時拿出一套玉制酒器,華美到讓他擔心臣子們議論太過奢華的程度。縱觀宋代,宮廷飲食中獨創的名食甚少。鵝肉似乎算得上美味,關于食鵝,朝廷還有規定,官員吃鵝會有不廉的嫌疑。大家都知道蘇東坡一生最喜吃鵝,有關傳說也不少。東坡可謂文學天才,他在飲食上也有不少發明,如“東坡肘子”及煮酒的技巧,他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除了東坡這樣的名人飲食有一定講求,宋人的吃食,并無特別高明與獨到的地方。就是西湖蘇堤上被趙構大加稱賞的“宋五嫂魚羹”,也不過就是將魚湯熬得鮮美一些罷了。其他如宋小巴子的血肚羹,恐怕還不如今天湖南新化縣的“三合湯”(牛血、牛肉、牛肚加山蒼子油)。《楓窗小牘》記載的北宋不少名牌食品,也不過平常東西而已,無非王樓梅花包子、薛家羊肉飯、徐家瓠羹、梅家鵝炙等等。倒是宋人有一個發明,為后來的文人士大夫們所效仿:以“妓鞋飲酒”。拿妓女的繡花鞋盛了酒來喝,宋人以為風流風雅,今人也許會不屑一顧,因為有礙衛生文明。
真正稱得上將飲食文化發揚光大的,要算明清兩代。這兩代著錄吃食的書極多,幾乎凡文人都會在筆下提及飲食,專門研究的著作也不在少數。明代萬歷年間有一個大官叫周舜五,此人對太湖中生長的一種草本植物莼菜極其偏愛,幾乎食必有此物,且有辭官歸隱太湖專為吃那莼菜之舉,一時傳為佳話。所以畫家張君度還專為他繪了一幅《采莼圖》,名士題跋者不少。此事流傳極廣,不過,周舜五這人,我看倒有幾分做作,無非文人故技,以此搏名而已。在明代一些筆記體小說中,常見有關于“盒子會”的描寫。“盒子會”是南京青樓女子炫耀烹調技藝的一種聚會,也是烹調比賽的意思。她們將自制的菜肴、菜點、面食,用提盒裝了,約定時間和地點,齊集一起,然后請風流名士或美食家逐一品嘗評點,分出高下。一者張其艷幟,再者作一集體廣告,當然也是姐妹們嬉戲與交流的機會。余懷的《板橋雜記》曾對此作過詳盡的記述,《金瓶梅》第四十五回也描寫了桂姐在五姨媽家做過盒子會。“盒子會”自明代才有,明代社會風氣糜爛,娼妓業發達,妓女們連帶著也推動了飲食文化的發展。妓女們的食品講究的是“精潔”兩字,名酒好茶、荷花細餅,加上絲竹裊裊,“盒子會”便有一種獨特的飲食韻味了。
和妓女的“盒子會”有相同之處的是文人的“蟹會”與士大夫的“湯餅會”。大文豪張岱與一幫文友在紹興城曾成立過一個“蟹會”。九月秋高,菊黃蟹肥之時,張岱便邀集一幫文友聚于菊圃,設蟹宴、飲美酒、品佳茗、賦好詞,逸興遄飛,望之如神仙中人。據《陶庵夢記》上記錄,蟹會上是每人六只大肥蟹,以小木槌敲開蟹殼,就了花雕、女兒紅這類美酒食之。
其實,這種文人的飲食聚會,自古就很流行。文人愛成堆,成堆便離不開飲食、棋書琴酒。如“曲水流觴”就是一例,王羲之的《蘭亭序》對此寫得十分精絕生動。“觴”為酒器,以漆、木、銅為之,雙耳,質輕薄,以之盛酒,放入曲曲流水之中任其漂流,岸上雅士文人順手取而飲之,可謂別出心裁,見出文人的風雅與生活的情趣,堪稱飲食文化的高境界。唐代詩仙李太白與長安城中其余酒中七仙一起名揚海內,太白的飲酒且不論,寫酒的詩也不談,他作過一篇堪與書圣《蘭亭序》齊名的文人飲宴聚會的名篇,叫《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中有“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以醉月”的句子,且有“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這樣不朽的絕唱。由飲宴而文化,由文化而哲思,只有中國人才會從“吃”中悟出道理來。宋代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也是文人宴樂引發的千古名文,所以真正的飲食文化是離不開文人們的創造的。當然,還有另一篇由文人聚會飲宴引發的曠古絕響,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的,那就是唐代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國人千余年來都會背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名句。王勃參與了一次著名的宴會,寫了一篇著名的散文,這是否算飲食文化的派生物,且不必去深究。
還是把自豪感提回到明代的飲食文化上來。明代在朱元璋時代,是竭力反對和禁止奢靡的,他自己每餐必食豆腐一盤,極少吃什么珍饈美味,而且還規定飲食的器皿不得“僭用”:公侯與一品、二品大員酒盞用金,其余器皿用銀;三至五品酒注用銀、盞用金;六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其余用瓷、漆。但自成化開始,飲食日漸奢華,如宮廷仍用豆腐,但豆腐已非黃豆制成,都是用百鳥腦髓制作的,一盤這樣的“豆腐”,需用千只鳥腦,可見其奢侈程度。又如鵝在明代被視為美食,朝廷曾規定“御史毋食鵝”,也就是不準吃鵝,但明代中晚期,人以吃鵝為時尚,宴客一次,少則殺鵝數只,多則上百只。無錫安氏,家巨富,飲宴豪奢,養有鵝數千只,每日食數只,有時夜半想吃鵝,來不及宰殺,就讓廚子割活鵝一腿,炮而食之,吃完時那鵝還“宛轉未絕”。
明代中晚期既然崇尚奢華,當然不會再有器皿上的禁區,富豪、達官之家,盛行用金、玉所制的器物,我們今天常見的傳世或出土的明代犀角杯、象牙箸、玉杯、金盞之類,就是一個佐證。除了器物上追求華貴之外,飲食的發達與創造也達到了一個頂峰,從宮廷到文人士大夫家庭,再到老百姓,流風所向,吃喝大興,絕不亞于今日的“享受生活”。據說明代的熹宗皇帝很喜歡吃什錦海味雜燴,用炙蛤、鮮蝦、鯊翅等十余品名貴海鮮“共膾一處”。崇禎帝喜食燕窩湯,隆慶帝愛食驢腸,嘉靖帝卻對驢頭肉特感興趣。魏忠賢一生嗜狗肉如命,吃過上千只狗。飲食的怪癖,即追求特殊性,不只與個人喜好有關,在文人,還有標新立異的成分在內。如大文豪張岱,山珍海味吃膩了,就搜求“方物”(地方土特產),張氏自稱“清饞”,吃遍了海內各地特產,并開出一份極長的清單,如北京的馬牙松、山東的羊肚菜、福建的紅腐乳、江西的豐城脯、山西的天花菜、嘉興的黃雀、杭州的花下藕、蕭山的莼菜、嵊縣的蕨粉……所列地方菜食百余品。像張岱這么闊氣的文人,明代比比皆是。當然也有如文徵明這樣清貧的文人畫家,早上吃點餅子,中午喝點酒,晚上吃一碗飯,用菜二三品,如此而已。那種烹龍炮鳳的奢華,離清貧的文士與貧苦的老百姓何止天壤之遙。但不管怎么說,明代飲食文化的發達是不容置疑的,風氣所至,談論有關烹調的專門著述也成為士大夫文人中最流行的著作,如陳眉公著有《萬寶全書》。飲食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菜譜、酒譜、茶譜紛紛擺上“遠庖廚”的雅士們的案幾,成為一種與琴棋書畫同樣緊要的用以炫耀的陳設品。這種時髦顯出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做作與俗氣,口腹之樂,居然成為一種文化的標榜,它所折射出來的社會心態,是頹廢的,而文人們的專著,不過茶余飯后涂鴉之作,看起來頗有講究,頭頭是道,其實許多都是拾人牙慧,不值一談的。
古人食單令人眼花繚亂,有些是“絕吃”,如百鳥腦髓制成的“豆腐”;有些是“雅吃”,如“蟹會”與曲水流觴之類;有些是“豪吃”,如宮廷與巨富家的“水陸羅列”;有些是“名吃”,如滿漢全席之類。只有老百姓沒有這么多講究,以填飽肚子為標準。
清代離我們現在還不算太遙遠,關于飲食方面,從前人各種文體的描述與記錄中,我們能夠略窺一二。號稱清代百科全書的《紅樓夢》,里面涉及飲宴的地方就很多,有盛大場面的描寫、節日排場的寫照及賈寶玉、林黛玉們雅集的記述,堪稱“飲食百科”。雅吃如黛玉,作者著墨甚多,有些詩酒文人做派,又如年輕女尼妙玉對食物與茶水的講究,俗人看了,會覺得太麻煩,而對于妙玉來說,卻是樂在其中,并以此有別于世俗的“濁”。縱觀清代飲食狀況,較之明代,有其獨到之處,即南方和北方來了一次大融合,從風格到技藝都有著前所未有的交流。以北京為中心,各地著名菜系、風味小吃,全都薈萃一處,此外,滿族食品與漢人食品也來了一個大融合,如滿漢全席。“京肴北炒,蘇膾南羹”,名飯店、名酒樓,南北林立,車水馬龍,煞是熱鬧。從皇宮御膳房到秦淮河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這些名妓招客的青樓,再到袁枚、鄭板橋這類文人家庭,以及那些巨族豪門,一飲一啄,全都“食不厭精”,所謂“聚山海珍錯于牌”,除珍異之品外,常備物如雞魚羊,每餐必具。至于皇上用膳,今人多從電視劇里看個大概,總體感覺是浪費太大,每食必百二十個菜,望一眼都覺著膩。餐具必用金、玉、琺瑯器,天下美味羅列于前,非為飽肚,擺的是皇家威嚴。徐啟憲在《清代皇帝的用膳》一文中,記錄了乾隆皇帝一次平常晚膳的情況:乾隆坐在一張洋漆花膳桌旁,太監們魚貫而入,依次傳遞的菜肴有燕窩雞絲香覃絲火熏絲白菜絲餉平安果、續八鮮、燕窩鴨子火熏片月官子白菜雞翅肚子香覃、肥雞白菜、肫吊子、蘇膾、飯房托湯、野雞絲酸菜絲、芽韭炒鹿脯絲、炮狗肉鍋塌雞絲晾羊肉、象眼棋餅小饅頭、折疊奶皮、酥油豆面、南小菜、桂花蘿卜、羊肉臥蛋粉湯、野雞湯,還有蘇造鴨子、水筍絲之類等等,數十余種,極盡奢華。
皇宮飲食,畢竟離老百姓太遠。達官貴人對飲食也格外講究,每食動輒花費數百金,如大貪官和珅的飲食,史書多有記載,其豪奢程度甚至不亞于皇宮。而文人們自古以來無論貧富,總是與明代的陳眉公一樣想著法子花樣翻新,立許多名目。如喝酒就有“薄酌、葫酌、樽酌、杯酌、小酌、草酌、杯茗、菲酌、豆觴”等等名堂,講的還是一個飲食氛圍與心境。秦淮河、夫子廟、八大胡同,南北妓館聚中之地,“花酒”盛行,豪門公子、達官大賈、文人雅士,云集妓館,一筵之費,少則數十金,多則千金,燈火樓臺,酒池肉林,一派糜爛喧嘩之景。
清代最有名的吃食,當然非“滿漢全席”莫屬。在豪族之家,一有盛會,便要做滿漢全席以張排場,上八珍、下八珍、海八珍、大烤全乳豬、燕窩雞絲、駝峰熊掌、鹿脯驢肝、鴿卵雀舌、羊羔江豚,不一而足。滿漢全席最多的有120個菜,少也有幾十個菜品,花費之巨,可想而知。從古到今,“吃”的文化超常發達。驚人的浪費造成驚人的破壞,中國人幾千年來崇尚吃、強調吃的積習流弊,國人對之該深深反省。
之二:古人出行趣考
大詞人溫庭筠對古人的行旅況味有過極為生動感人的描寫:“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而江淹的《別賦》、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之類送行的詩文,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抒情主體之一,很合乎中國人的重情重義傳統。南浦送客、灞橋折柳、長亭餞別,古人對于行旅與離情是十分看重的,遠水迢迢,關山隱隱,鄉井在千里萬里之外,異鄉的月暈與茅檐,讓人感到陌生而擔心。古人的行,無非舟車助步,行走世界,除了兩只腳吃盡辛苦,想不出還有別的什么辦法可以把自己送到目的地。《封神榜》里的土行孫、《西游記》里的孫悟空,天上地下轉瞬即至,騰云駕霧的神仙之流與日行八百的神行太保,幾乎都是古人對于行走方式的一種浪漫稚拙的想象。今天人類的飛機、衛星、火箭或潛艇、火車之類現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已非古人的智慧所能想象,所以,今人對于行旅的感受,已是十分淡漠,送別與離情,幾乎快成為一種被忘卻的古老情懷。
我在湘西沅陵進行文物方面的考察訪問時,曾發現一件由玄武巖打琢的古代船錨。這件石頭的錨,當時被棄置在沅水一個古渡口的沙灘礫石叢中,生滿了苔蘚。石錨的形狀與今天的鐵錨完全一致,其色黝黑如鐵,極沉重,結構堅硬縝密,百十斤。同行的文管部門負責人對我的發現不以為然,但我告訴他:這件東西距今至少三千年以上,是古人行船停泊的遺物,十分罕見,海內其他河流并未有由此種玄武巖打造的石錨發現,它見證著古人行走江河的艱難,這樣難得的歷史文物,棄置河洲,豈不罪過?
沅水上還發現了另一個關于水上行旅的古代實物,即土人所稱的“寡婦鏈”。臨江絕壁之下,腕口粗的生鐵長鏈穿透石壁綿延近百米之長,有些鏈口已銹毀,風生水起之時,鐵鏈發出哐當巨響,使寂靜的古河谷顯出攝人心魄的神秘。有人說此種鐵鏈為古代船客系舟所用,也有說是江上淹死一人便系一鏈以示紀念用的。但根據我的考察以及我查閱的地方志,系舟之說才是準確的。鏈的遺留時間約在四百年左右,為明末清初之物,是古代江河行旅中難得一見的標本。而在我老家的資江河岸,曾發現過不少水祭碑與纖痕,資江八十一險灘,灘灘打爛舟排,有灘處必有水祭碑,時間跨越千年以上。纖痕則是臨河大石上由一道道纖索勒出的深痕。
我曾在福建的泉州市逗留過一段時間,對其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陳列的有關船舶實物,十分在意。從博物館展示的獨木舟及泉州灣古代巨大沉船來看,泉州在東晉時期即以制造大船,且能遠航南海諸國而名揚海外。宋元兩代,泉州已成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南亞、波斯灣、東非等地區的58個國家商旅匯聚的大港口。水上交通工具船,各國造型不同的航海船只云集此地,因此在博物館便能見到一些零星的遺存物。而泉州本土在宋代既能造出全長126米的大船,船身高大如樓,底尖面闊,首尾高昂,有多層船板結構,龍骨粗大無比,主桅桿高達30多米,堅固壯觀。泉州所造大船不僅漂洋過海往返各地,而且也出售給外國商賈,如“耆英號”就是英國人訂購的。海上風波惡,行旅尤其寂寞、驚險,古人視水上路程為畏途,是很有道理的。
泉州陳列的是關于古代海上航行的實物,我們只能根據《鏡花緣》這樣的小說和鄭和下西洋的相關史料記載來猜想古人有關水上行旅的種種狀況。海上歷險,是不同于內地河流行船的,出沒波濤雖也險象環生,常有不幸的事發生,但海難卻更令人觸目驚心。我們經常從新聞媒體看到在海底打撈古代沉船的報道,那些龐然大物不知在什么年代觸礁沉海,遇難者骸骨無存,只留下波濤和魚鱉吞嚼不爛、消化不掉的船的殘骸與歷代瓷器、牙角制品、金銀器具以及無數古代珍寶。所以,水上的路程,于古人而言,是不測的險途。
我的一位朋友,是海內外專藏出水瓷的名家,其中宋代五大名窯瓷器均有收藏,北宋的官窯瓶和鈞窯洗,是他從香港佳士德競拍回的,花掉港幣1600萬元。這兩件東西是從海上沉船中打撈出來的,據介紹為一名英國的沉船打撈專家的遺物,釉色如新、完整無缺,堪稱國寶級文物。另外幾件元、明青花瓷器,也是出水瓷中的珍品,那件元代青花釉里紅大罐,所繪人物山水圖案,海內罕見,曾見諸有關圖錄。出水瓷的面世,證明了海上行船的兇險,所謂“行路難”,應該是古人對于外出行旅而生死難料的痛切感喟。
水上的路固然難走,而陸地上的路也不見得就步步平安。李太白說蜀道難行,有如登天,岑參說塞外行軍是“瀚海闌干百丈冰”“隨風滿地石亂走”。世上的路不好走,坎坷崎嶇,險阻重重,所以馮諼彈鋏而歌,要出門有車;而阮籍駕車,最后慟哭而返。
古人出行,代步的有舟車轎馬。水上行舟之艱已大略說過了,至于古人的另一類代步工具——車,如牛車、馬車、騾車、驢車、獨輪車、人力車……今人已不甚了了。史載秦始皇乘車出行,威儀赫赫,項羽遠遠望見,心向往之,說:“彼可取而代之也。”霸王胸襟與豪氣,由此可見一斑。乘坐高車駟馬,在古人眼里,是威權富貴與身份的象征。漢高祖劉邦在立國之初,崇尚儉樸,出入以牛車代步,頗異于前代與后代的帝王,因此青史流芳。寶馬香車,絕塵而去,呼嘯而來,雖然顛簸,卻能免去步行的辛苦。古代的乘車,似乎也如今人有著級別的差異,等級十分森嚴,皇帝御駕之車,不僅高大寬敞,而且以黃綾為頂,嵌金綴寶,豪華自不用說,后妃乘鳳輦,儀仗威威,宮女太監侍奉兩側,鼓樂隨后,路人須預先回避。
至于官員所乘之車,當然也有不少規定,根據品級高低,拉車的馬或四匹或兩匹不等。但古代官員乘車,也并不完全講究身份等級,就是宰相,如果是一位清廉的,也可能坐那牛車或驢車出門,倒是那種豪富之人,出門就講究得多,比方富可敵國的石崇、沈萬三之流,你讓他坐驢車、牛車,那是不可想象的,除了黃綾車頂不敢用,黃金為飾,珠玉為簾,豪華富麗到你無法設想的程度。除了巨富大賈,艷幟高張的名妓、豪門公子、名士,乘車同樣講究。“香車寶馬”,就是指這類人的。
從漢代磚畫及出土漢棺的漆畫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有關車馬的圖飾,一般的都由兩匹馬拉車,車身不十分華麗,車轱轆卻十分高大。這種大車輪宜于在不平的道路上行走,可見古人是很講究實用與結實的。又如漢代陶制品中出土的車型器物,兩馬在前,車身在后,車為轎式,下裝轱轆與車軸。漢代之后,車的形制有所改進,裝飾也愈見華麗講究,唐代的高車駿馬,較漢代更為舒適氣派,不僅有四輪車,也有了六輪大車。車身四面開窗,以寶珠水晶為簾,坐在車上可看路邊風景與人物,而路人看不清車內的乘車者。六輪大車,車內可坐人若干,有些近似現在的小型面包車,內眷、友人、高級侍者,可同車而行。拉車的馬也很講究,五花馬、汗血馬這類良駒名馬,不僅高大健壯,而且毛色鮮亮,蹄聲得得,跑起來是塵土滾滾。唐代的皇帝后妃乘車,更是排場,所謂“天子鑾輅五等:玉、金、象、革、木,以供服乘用之。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安車、耕根車、四望車、羊車”。而貞觀元年開始,又加豹尾車、黃鋮車,共十二乘,以作儀仗用。
古代的車,都是木制車,不過裝飾不同而已。日常代步之外,還可以運載貨物,如驢車、牛車、騾車。牛車是古代賢人、隱者都喜乘之,漢高祖劉邦與皇后,也乘牛車以示儉樸。還有一種羊車,出入深宮禁苑,是皇帝夜間臨幸后宮嬪妃專用的,元代詩人有“離宮夜半羊車過,別院秋深鶴駕遙”之句。這幾種車外,尚有征戰用的兵車或戰車,西安兵馬俑中就有那種車馬陶質模型,車身四周敞開,上有一頂,車轱轆挺高。這種車適宜山地行走,所謂車轔轔、馬蕭蕭,沖鋒對陣也頗威風。
轎子的運用,古來就很廣泛,上至天子,下至鄉間財佬,甚至老者、郎中之類,三教九流,但凡有點門道的,是無轎不行。轎夫是一個古老的職業,至今有些僻遠的山鄉還有轎和轎夫。坐轎比乘車舒服,不會顛簸難受。
不過,轎子雖廣泛用于朝野城鄉,卻還是等級森嚴。天子所乘,就不稱轎,而叫“步輦”,或“輿”。如唐太宗就讓一大群花朵似的宮女為他抬著步輦去接見吐蕃的那個使臣祿東贊。當然,唐太宗的步輦動用的宮女數量絕對比不上隋煬帝下揚州時拉龍舟的宮女數量,河岸上三百個宮女的纖纖素手負纖而行,香汗十里,美麗而殘忍的風景至今讓人感喟不已。
在皇帝的步輦或輿駕中,元代的“象輦”可以說別具一格。蒙古的大汗出行,選用馴象師馴化得最好的四頭大象,而皇帝所坐大木轎架在四頭大象的背上,轎中襯以金絲所織坐墊,轎外包著獅子皮,轎上插旌旗與黃傘蓋。象輦出行,高高在上,儀仗隨后,極為威嚴也極為新奇,而皇帝也坐得舒適。《元史》上說:“象力最巨,上(皇帝)往還兩都,乘輿象駕。”詩人張昱《輦下曲》曰:“當年大駕幸灤京,象背前馱幄殿行。”
元代皇帝的轎子還有一種叫“腰輿”的,也就是漢人皇帝的步輦。腰輿一般用香木制成,背作山字牙,嵌七寶妝云龍屏風,屏風下置龍床。
皇帝的轎子暫不去管它,有學者考證認為,乘轎成為一種制度,應自明代始,明代以前并無規定。成化年間嚴格規定只有三品以上的文官,才可以乘轎,四品以下只能騎馬。乘轎的大官們,轎前有雙棍引導,武官中要封侯才會賜乘轎,反而太監得便宜,東廠的太監和掌管司禮監的太監,皇帝欽賜乘轎。但到了明代晚期,制度就亂了,官員無論大小,都棄了馬、驢、騾,個個乘轎,四人轎、兩人轎都有。京城之中,凡有一官半職的,都肩輿、腰輿地大大方方坐了,出入于市井和各色衙門。后來連秀才、舉人,進而妓女、郎中、土財主,都坐起了轎子,而且誰有錢誰就坐得氣派漂亮。
轎子在清代,有綠呢大轎、藍呢大轎和八人、六人、四人、兩人抬。督撫大員,用八人抬的綠呢大轎,品級往下則用六人、四人不等,七品縣令,也用四人抬的帷轎子,且可以鳴鑼開道。大官的轎子極華麗,轎前掛一張帷簾,四面密封,每面開一小窗,以象牙或名貴木材為之,不僅價格昂貴,而且不得僭用。當然,清代官轎有嚴格規定之外,民用轎就無一定之規了,那種貴婦人或大闊佬所乘的大轎,一點也不比大官的轎子遜色,有些更為講究。
其實,轎有很多種類,官轎之外,有女轎、涼轎、暖轎、逍遙轎、臥轎、兜轎等。陶淵明患足疾,作一竹籃,兩個弟子用木杠抬著出行,人稱“籃轎”,這是最原始的轎子。鄉間老者所乘,一把竹椅兩邊各橫綁一竹杠,椅下置一踏板,前后壯漢各一人,抬了轎子健步而行,這種轎既無遮風擋雨的頂蓋,也無半點裝飾,鄉人稱為“躺轎”,坐轎人只能半坐半躺也。而逍遙轎是根據古代長檐車改造而來,講的是坐著舒適。女轎裝飾一般都很華麗,城市婦女出行,怕拋頭露面,因此轎的四周密封,左右開小窗,也用絹、綾為簾,上綴珠玉,轎中婦女可窺轎外情景,轎外人則難享眼福。
轎子的材質,以木為多,也有藤、竹材質的。而制作得最精美出名的,是寧波的花轎,鏤雕精絕,飾金嵌銀,大紅漆,華貴不可方物,這種轎專用于婚嫁,講的是排場氣派,觀賞性極強,耗資也最巨。在轎的形制式樣中,以福建、浙江轎式最為世人稱賞,有很強的藝術性和鮮明的地方風格,無論是在南方北方,都為乘轎者所鐘愛。
古人代步最常用的,其實還是馬,當然也有驢子,少數人也用牛。
古人的生活離不開馬,騎馬比坐車乘轎方便,尤其長途出行則非馬莫屬,“路遙知馬力”,此之謂也。士大夫、文人、達官、武將,還有婦女、老百姓,騎馬出行,鞭影飄飄,蹄聲似雨,或奔或行,信馬由韁,一騎絕塵,瘦馬西風,異地懷鄉。古代詩文繪畫中處處見“馬”字,古人的行走,幾乎是與馬分不開的。驛站用馬、征戰用馬、行旅用馬、載物用馬;紙上畫馬、詩里詠馬、伯樂相馬、韓斡畫馬、帝王將相墓前立著石雕的馬(如昭陵八駿),開國之君馬背上得江山,而一個大元帝國怒馬鐵蹄橫掃半個地球。如果說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文明,一半出自馬背,恐怕不為夸大。在馬蹄聲中,走來一代代的英雄豪杰、文豪達官、隱士商賈、帝王將相與平頭百姓;在馬蹄聲中,一切都已經發生過了,一切都已消失了。馬背上的中國,馬背上的故事,說也說不完。
唐代畫家張萱曾作過一幅著名的畫《虢國夫人游春圖》,畫面上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豐肥肉感,騎著高大漂亮的駿馬,黃金為鞍,踏青徐行。唐朝的女人思想解放,既然如武則天一樣敢做皇帝,自然也可以讓馬兒馱著貴夫人外出游春,美人駿馬,是一道風景,正是“麗人行”,游人看騎馬的美人,美人看花鳥,真的富有詩意。古代女子騎馬,是很平常的事,在騎馬的女人中,著名的有花木蘭,替父從軍,千古佳話;和蕃的王昭君,騎馬出塞,功在國家民族;而大破天門陣的穆桂英,在中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但在女人纏足的時代,女人騎馬并不是多數,如清初四大名妓,似乎就沒有騎馬的記錄。不過,既然古人的出行,基本離不開馬,想必不論何代,騎馬的女人也一定不在少數吧?江湖俠女,深閨弱質,或許多多少少都有過騎馬的經驗。
在古代騎馬的男人中,我特別喜歡劉邦和項羽,還有橫槊賦詩的曹操與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的關云長。劉邦在馬背上打下漢室江山,逼得霸王自刎烏江,雖然馬背上得江山的不止他一人,但其智謀之高與氣度之宏,令我拜倒;項羽雖然是一個失敗的英雄,但我很喜歡他的霸氣與剛烈之氣,他的“力拔山兮氣蓋世”,是塵世里的巨響,而項羽自刎烏江,并不是怯弱的表現,自有一股悲壯之氣;曹操是一代梟雄,卻也是古代少見的一位文武全才,他的謀略、權術、文采、征戰的本領絕對是一流的,他的一生,除了廟堂,就是在馬背上;關云長是一位神,一個被神化了的英雄人物,也是義氣的化身,他是中國人的偶像。除了這四位,我還崇拜一位畫馬的名人,那就是唐代的韓斡。歷代都有畫馬的高手,但都超不出韓斡的境界。韓斡畫的馬,不僅高大駿美,線條酣暢雄健,骨肉具有動感與質感,更難得的是他把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畫中,每一匹馬都神完氣足,充滿朝氣與活力,顯現著難以言說的魅力。馬的力量、精神與生氣,在紙上鮮活地凸現出來,讓愛馬的人和不愛馬的人都著迷,這難道僅僅只關乎繪畫的技藝嗎?
中國古人騎馬之外,還喜歡騎驢、騎牛和騎騾。騎牛的名人有老子,傳說他騎著青牛過函谷關,說不定五千言的《道德經》就是在牛背上想出來的;騎驢的名人很多,記得賈島是騎過的,“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騎驢苦尋佳句,真正難能;李商隱也是騎過驢的,他和賈島一樣在驢背上吟詩;杜甫也是騎過驢的,當年旅食京華,十幾年做不上官,潦倒窮愁,騎驢朝叩富兒門,暮逐肥馬塵,心里苦、腹中饑、身上寒。而騎騾子的名人似乎少,但北方與南方的古代,騾子不僅會拉車,也會馱人。騾子性倔,愿走就走,不愿走時連鞭子也打不動,所以世人拿騾子比喻性格倔強剛烈的湖南人,稱“湖南騾子”。
古代代步工具除了舟車轎馬等,還有一個屬于謝靈運的發明——登山屐,值得一提。謝靈運是南朝時寫山水詩的大詩人,喜歡登山,某日靈感來了,就發明了一種專門登山的木屐,上山去掉前齒,下山去掉后齒,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所以李太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就有了“腳著謝公屐”的想象。謝公屐專為登山設計,雖不算代步工具,卻因其奇特附此篇之末,該不算畫蛇添足吧。
(特邀編輯 丁逸楓 2783176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