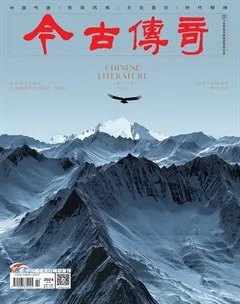梨樹還在

高岸東
土家族,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人。中國散文學會、林業生態作家協會、宜昌市作家協會會員。有百萬余字的散文、小說、詩詞見于報刊和新媒體。
一
四十年后再經板上坡,還真是有些意外。要不是機緣巧合路過,一段記憶恐怕會如深湮在地殼中的碳化物,一直沉睡下去。
論起來,也沒什么可奇怪的。長陽在地圖上本來就像條魚,全縣的公路是站在高空撒下來的漁網,每個綱目都聯結上了,任選一個起點和終點,都不會此路不通,穿過山山嶺嶺溝溝壑壑,總會抵達。
從榔坪到井水,走近道,板上坡便是必經之地。板上坡這地名,像原始的粗布,倘若披著在T臺上一走,卻又有些時尚的新意。其實,它就是個兩里長的山坳,只因山坳兩側都是陡峭如板壁的長長斜坡,故有此名。
二
板上坡有老虎,老虎吃人!小時候,祖母在一個陰雨天給我講這事時,表情極為傳神,眼睛張得像銅鈴,好像趴在她膝上的我,就是那只縱身欲撲的老虎。有個背腳的,從那里過,老虎突然從林中躥出,將他連人帶貨撲倒在地。祖母講到這里,自己的身子都歪了下去。就在我跟著汗毛豎起的時候,祖母總算給了一個喜劇式的結尾——你姑爺爺家的牯牛跑了過來,救下了那個背腳的,算是撿了一條命。腦海里,祖母講述的表情纖毫畢現,但那是差不多五十年前的事了。
姑爺爺向墩是板上坡唯一的住戶,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姑爺爺并非天生就是我姑爺爺,只因他二十七歲那年娶了一個叫高永珍的女人。高永珍的父親叫高順德,都是按輩系取的名兒。這就對上了,我曾祖和祖父正是順字輩和永字輩。高姓雖在當地是土家土著,但卻是小姓,遇到一個姓高的,自然要認族認戚。從戰亂到饑荒,山野里的百姓像動物一樣本能求生,祖上三代以上的事,誰又曉得?
姑爺爺祖上也不知是哪朝哪代到此偏安一隅的。這里地瘠物薄,偏僻險阻,還傳聞有大蟲出沒,那些刮糧抓壯丁的,懶得到此一游。長陽是險峰深谷拼成的,像板上坡這樣的天然避難之所,不在少數。只是現在這樣的地方,已少有人跡。擇地遷居、下山入城、集中安置等等,村落和城鎮像沾了糖的收蜂板,把這些散落的農戶往攏收去。而公路仍如血管脈絡一般,過溝越嶺,串聯著依舊充滿生機的每處肌體。
姑爺爺姑婆婆人還在嗎?房子還在嗎?會不會也搬走了?一個個問號在腦海里盤旋,道路的陡峭險峻倒被忽略,不知不覺中,輕車已過萬重山。
三
按輩分,姑爺爺姑婆婆自是高我兩代,但年齡實與我父母相仿。我六歲那年是個暖冬,雪塊只藏伏在山頭樹叢里,山路雖不干枯,倒也像靜脈曲張一樣清晰。正月初五的早上,陽光像只蠟燭出現在東邊的山坳里。母親找來干凈的衣服,催我起床,說到板上坡姑婆婆那里拜年去。對姑婆婆的記憶,在這個美好的早晨,就這樣邁開了腳步。
姑婆婆有個女兒,初三被舅舅接過去了。我們去的時候,就姑婆婆和姑爺爺以及姑爺爺的母親三個人。火塘的火很旺,時而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姑婆婆稍稍保持著作為長輩的那么一點點矜持,但一張燦爛的笑臉,跟屋外的太陽沒有兩樣。五個大人嗑著比我家飽滿得多的瓜子,山勢越高的地方,瓜子顆粒越大越飽滿,我嗑起來腮幫有些累。
除了瓜子以外,姑婆婆家的飯菜與年貨,與我家并無多大區別。但姑婆婆家有水果,那時我家是沒有的,過年也沒有,連現在爛在樹上沒人摘的橘子柚子都沒有。對植物而言,你看不上它,不理它,反而是一種愛,它們會自由繁衍,更加枝繁葉茂,人丁興旺。人就不同了,當時我不明白單家獨戶的姑婆婆,在沒有計劃生育的年代,為何只有一個女兒。
姑婆婆家的水果,也就一種,梨。姑婆婆點燃油燈,牽著我,從木梯爬到木板鋪成的樓上去。她把油燈小心地放在一口黝黑的木缸蓋板上,雙手扒開厚厚的一層糠,一陣窸窸窣窣之后,一窩梨就出現在眼前,像鱷魚在沙灘里產下的卵。梨我是吃過的,但還是迫不及待地一手抓了一只,我咬了一口,水分沒有下樹時那么足,脆中帶軟,但甜了許多。整個下午,我沉浸在那種不曾有過的甜味中,甚至喝水時,還去舔一下嘴唇。
但真正令我永生難忘的味道是在晚上。大概晚上八點,由于沒有玩伴,五個大人又聊得興味十足,我有些昏昏欲睡。姑婆婆笑著看了我一眼,說,東東,來。她又拿起油燈,朝廚房走去,我揉了揉眼睛,就跟了過去。廚房墻腳處并排擺著大大小小四五個泡菜壇子,姑婆婆去洗了一下手,回來揭開其中一個大的壇蓋,一縷淡淡的酸味迅速跑了過來,我的舌下也跟著酸了起來。姑婆婆先是抓出兩大把腌包白菜塊放在壇蓋里,然后又伸手從里面摸出兩只梨來。
又是梨呀,我的好奇心咚的一聲掉在地上,昏昏欲睡重新襲來。姑婆婆笑著瞟了我一眼。她總是笑著一張慈善的臉。這個是腌梨,不用洗,你啃一口試試,她說。我把濕漉漉的梨拿在手里轉了兩圈,咬了一小口——天哪,那味道酸甜相疊,滿口亂跑,我的口水像暴雨后的水溢出來。
姑婆婆,你為什么有梨呢?因為我有梨樹啊,兩棵,明天我帶你去看好不。姑婆婆邊說邊用手擦了一下我嘴角留下來的水。
四
我松了一腳油門,車很快慢了下來。繞過一座墳包,我看到了,看到了——梨樹還在,兩棵都還在。
主干的上部已經開裂朽空,幾處粗大的枝丫也已斷裂,但也有碗口或杯口粗細的新枝,青青黃黃的葉,在風里搖晃著。老干的黑和新枝的灰,涇渭分明。姑婆婆說過,兩棵梨樹是有故事的,是與姑爺爺的定情之物,也是她的全部嫁妝。
姑婆婆的父親高順德靠背腳(肩挑背扛憑體力替人背貨)養家,在兩河口與資丘碼頭之間十天一個來回,兩百多里的山路。從招徠河過大吉嶺,再從井水下榔坪,板上坡一上一下最為艱險,是大小四十九嶺中最高的一座山。
在姑爺爺二十五歲那年早春的一個黃昏,高順德在路上鬧肚子,體力有些虛脫,當他提著最后一絲力氣,爬上板上坡時,背架還沒靠穩,眼前一黑,就一頭栽倒在地上,兩百斤的貨物將他壓在身下。湊巧姑爺爺的父親出來尋牛,發現了高順德。
那天晚上,兩個相差不到十歲的漢子臉紅耳熱,喝了酒,認了兄弟。第二天早上,高順德起身上路時,似有心事,磨磨蹭蹭。咋的啦,老弟,力氣還沒回來嗎?姑爺爺的父親問道。高順德沒有回答,徑直走向自己的背架,從上面解下兩棵光禿禿的小梨樹苗,雙手托著走到姑爺爺的父親面前:老哥子,這是我前天歇腳的那戶人家送給我的,你一會兒栽上。我知道你家墩子二十五了,還沒說媳婦。我家閨女也吃十九歲的飯了,也沒婆家。三個月后,兩棵苗子要是栽活了,我帶閨女來過個門兒。兩年后,如果樹苗還是長得好好的,閨女就過來給你做兒媳婦。老哥子,你說這事成不成?
成,成,好事成雙,兩棵,兩年!姑爺爺的父親被這意外喜得滾出幾顆眼淚,在屋檐下一把抱住高順德,比昨晚喝醉了還要放蕩。
五
兩株梨樹苗栽在大門對面最好的那塊田里,四周打了六根木樁,圍了兩層竹枝,比雞圈還要豪華。那年春天腳步快,不比山下的來得晚。一個多月后,兩株梨樹苗都長出了葉芽,開始尖尖的,帶點紫紅,舒展開來了,嫩綠如洗,片片心形。
常年在外難落屋,
吃的“筒筒飯”,
走的“閻王路”,
動步唱“路歌”,
歇腳打“杵杵”,
背壓彎,汗流枯,
日頭背進又背出。
姑爺爺的父親正勾著腰伏在竹枝上,看那兩株清秀的梨樹苗,熟悉的背腳佬歌謠從老林中悠悠而來。他連忙伸出手來掐了又掐,喃喃說道,不錯,就是后天,后天剛好三個月。他一下子明白了,高順德的歌聲今天咋就喊得那么遠,扳著指頭算日期的不止他一個。
男婚女嫁,是農家一生中的大片。高順德這次作為總制片人兼總導演,是不允許出什么岔子的。高永珍也就是后來我的姑婆婆,沒出過遠門,當爬了一半板上坡那邊的陡坡時,腳崴了,腿疼了,發散了,不想再往前走,陪同的姑媽也在一旁幫腔。高順德低沉著嗓音說,知道爹是做啥的?替人背貨的,二十年沒出過差錯。今天就是用背架,也要把你背去。
姑婆婆本來不想看墩子也就是后來的姑爺爺一眼,但終究沒能忍住,看了一眼后,又偷偷看了好幾眼。十九歲在那個時候算是大姑娘了,心里有了些心計。姑婆婆找了個機會,悄悄對姑爺爺說,有香皂嗎,爬這么高的坡,汗臭了。姑爺爺遲疑了一下,說,有、有。說完,姑爺爺沒朝內屋去,從大門跑出去了。
雞肉的香味飄到火塘屋的時候,姑爺爺喘著粗氣回來了。他打了一盆熱水,用眼睛示意姑婆婆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洗。洗完,候在外面的姑爺爺去倒水,兩個人目光碰到了一起,彼此都看到了對方臉上的桃紅。姑爺爺從上衣兜里掏出一個紅毛線纏裹的橡皮筋箍箍,遞給姑婆婆,說,把頭發扎上。姑婆婆低著頭問,哪來的?姑爺爺說,在榔坪街上買的。剛才?嗯,剛才。天哪,這面坡一個來回,時間花的比姑婆婆一行人來的時候還要短!
后來的事一切順理成章,如祖母給我講的故事一樣,喜劇收場。總導演高順德繼續背腳,繼續喊他的背腳佬歌謠——
姐兒住在三叉溪,
找個男人背腳的。
早晨聽到打杵響,
姐在屋里嘆長氣,
我的男人使苦力。
六
從一簇竹林腰下鉆過,嘩嘩嘩,車的外殼被竹枝劃出流水的聲音。我看到了,看到了——姑婆婆那棟土筑瓦蓋的房子無聲地出現在眼前。
一個頭發全白的老人,正佝僂著身子在曬場里用薅鋤鏟土,她把隆起來的土鏟起來,挪到坑洼的地方填上,動作遲緩,但穩穩當當。
“您是姑婆婆嗎?”
“哦。”
“您還記得吃過您腌梨的東東嗎?”
“吃梨呀。自己摘去,別把樹弄壞了!”
一晃五十年了,歲月足以讓每個人變成另外一個人,記憶的濾網,總在顛簸的網眼中選擇。我確信,眼前這位老人,就是姑婆婆,那個叫高永珍的女人。
梨樹上的葉子所剩無幾,哪還有梨呢。田里長滿了草,有鳥在樹下草叢里飛起落下,數不清的胡蜂,正在周圍瀠洄,能聽見嗡嗡的聲音,樹下似乎在舉辦一場盛宴。
“姑爺爺呢?您老伴兒呢?”不知道姑婆婆是耳背還是糊涂了,我再一次試圖喚醒她的意識與記憶。
姑婆婆轉過身去,繼續鏟草平地,并開始喃喃自語:“老頭子掉氣的時候說了,這梨樹不能砍。每年都開花,結梨。要吃自己摘,別弄壞了樹……”
我把一提牛奶放在大門邊,大聲說:“我走了啊,您老保重身體!”
“才回來咋又要走,我孫子呢?還有好多梨呢,樓上有,壇子里也有。叫你們自己摘,也不去,甜著呢……”
我重新回到駕駛室,沒有立即開車。姑婆婆仍舊不急不緩地鏟土平地,在她左腳邊不到兩米的地方,有兩道車輪軋出來的槽印,她卻沒動。我緩緩地啟動車子,她還在自顧自地說著:“你們不要說了,我反正是不得去,用背架背,我也不去。背得走人,還背得走樹?”……
梨與離近音,梨不能分了吃,這已是習俗。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呀。盡管那些新枝,還對春天抱有想法,但高大的老梨樹,終有一日會被那瘋長的野草淹沒,就連板上坡這個地名,用不了太久,也會像丟在某個潮濕角落的一塊鐵片,靜靜銹蝕。
七
過去背腳人行走,我們又接著行走的那條路,不知藏到哪里去了,野草萋萋,密林陰森。我沿著下山的之字形公路徐徐而行,陽光時而從車頭,時而從車尾照進來,照得我身上有些刺熱,像一個烙餅被翻來覆去。
母親打來了電話:“你今天得不得回長陽?”
“回,但有點晚。您還記得板上坡的那個姑婆婆嗎?”
“噢,記得,她只大我一兩歲。她還在嗎?”
“在。身體還好,就是有些糊涂了。”
“那兩棵梨樹還在嗎?”
“還在!”
(責任編輯 王仙芳 3495728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