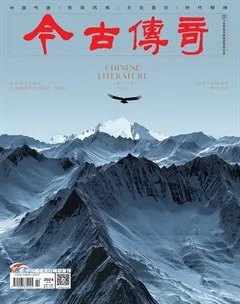陪草木到老

夾竹桃之殤
河西岸是一條不太寬的石子路,路面也不平整,雨后會有一洼一洼的積水。白天也少車輛行人,晚上更是冷清。有一次晚間散步,無意間走到這條路上,走著走著,驀然發(fā)現(xiàn)道路的一邊,竟然開著一大片潔白的花,像枝頭壓了厚厚的一層雪,又像是一堵白色的墻。在朦朧的月光下,這些花愈發(fā)地白,甚至讓我有點目眩。定睛細(xì)看,認(rèn)得出是夾竹桃花。
我有點驚詫,喃喃自語,是誰又是為何要種這么多夾竹桃呢?我一邊走一邊看,足足有兩里多長。從此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連著幾天、幾個星期、幾個月都去。或許是有人來欣賞,這些花兒愈發(fā)開得旺盛,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我心底暗喜,終于有了一個散步的好去處,甚至還為沒有早點來這里而懊惱呢。在好幾年的時光里,我都去看它,它也不負(fù)我,回報我一個又一個長長的花季。
然而,天有不測風(fēng)云。某一天再去時,不禁大吃一驚。眼前景象,已經(jīng)面目全非。路面被挖開,路旁的夾竹桃全部被連根挖起,遺棄一旁,已經(jīng)干枯。挖掘機聲隆隆,正在晚間作業(yè)。看了路邊的戧牌公告,方知這里要建一條四車道的公路。目睹此情此景,我只有心痛惋惜。如今公路早已經(jīng)建成,也有了新的路名。路旁新栽了許多花木,有高枝紅梅、高稈紫荊、高稈紫薇、玉簪花等,只是不見了當(dāng)初的夾竹桃,心中不禁黯然。
不久前,路過附近一小區(qū),又看到了一大排夾竹桃。沿圍墻而栽,有二三百米長。早先沒有察覺,可能那時夾竹桃還矮,被圍墻遮擋。如今高過了圍墻,才被我看到。月光下,滿樹粉紅色的花朵,像極了桃花。開得燦爛熱烈,又勝過桃花。此處夾竹桃,平復(fù)了先前胥浦河邊的傷痛。但也好景不長,一夜醒來,原先好端端的苗木,竟然被攔腰砍斷,很多只剩半截。白森森的傷口觸目驚心,讓人心痛。問過門口保安,為何要毀掉這些夾竹桃?人家回答,長得太茂盛,遮擋了底層住戶的陽光和視線,是應(yīng)業(yè)主要求砍伐的。還有業(yè)主說,這種花有劇毒,不能栽,應(yīng)該鏟除。我更是無語。
我憤憤不平地將這兩處有關(guān)夾竹桃的不幸遭遇講給同事聽,同事見怪不怪,平靜地給我講述他的經(jīng)歷。朋友曾經(jīng)工作過的一所學(xué)校,從辦公室去教室要經(jīng)過一條不太寬的青磚鋪成的小路,路兩旁栽的就是夾竹桃,枝葉茂盛,高過了頭頂。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開花,一邊開紅色的花,一邊開白色的花。不開花的季節(jié)也是綠葉青青,似竹似柳,終年常綠。每天上課下課都從綠葉繁花中穿過,身心仿佛被洗滌,靈魂被凈化,悲喜不亂,寵辱不驚,精神飽滿,情緒穩(wěn)定,心平氣和地走進(jìn)課堂,認(rèn)認(rèn)真真上每一節(jié)課。后來學(xué)校進(jìn)行校園改造,道路拓寬,夾竹桃被挖掉,換栽了低矮的杜鵑花,雖然花色艷麗,但花期極短暫,冬季葉片凋落,呈枯枝狀。問校長為什么不繼續(xù)栽夾竹桃,校長給出了同樣的解釋,夾竹桃有毒,不適宜校園栽種。
夾竹桃是外來物種,早在唐宋時由印度傳入我國。夾竹桃有一些奇怪的古名字,如拘那、拘拿等,都是與印度文字的讀音有關(guān)。夾竹桃其葉似竹,其花似桃,實又非竹非桃,假竹桃也,夾竹桃疑是假竹桃之諧音。夾竹桃兼具竹的挺拔與桃花的柔美,擁有君子佳人的完美形象,深受唐宋時期人們的寵愛,栽種極為普遍。宋沈與求《夾竹桃花》詩:“搖搖兒女花,挺挺君子操。一見適相逢,綢繆結(jié)深好。妾容似桃萼,郎心如竹枝。桃花有時謝,竹枝無時衰。”便是當(dāng)時人喜愛夾竹桃的真實寫照。
夾竹桃受歡迎的另一原因是其花期特別長。夾竹桃為灌木,終年常綠。花朵不大,但許多花聚生在一起,形成聚傘花序,生在枝條的頂端,非常醒目。花朵由下而上次第開放,下面的花凋謝了,中間的花正開,最上面是幼嫩的花蕾,給人源源不竭、無窮無盡的感覺。有人抱怨養(yǎng)花辛苦,弄花一年,看花幾日或幾個星期,覺得付出與回報不對等。我說他養(yǎng)錯了對象,為什么不種夾竹桃呢?紫薇能開百日,稱百日紅,算花中能開的了。但與夾竹桃比,竟是小巫,被甩半條街。夾竹桃能開半年之久,號稱半年紅。有意觀察過夾竹桃的花期,從春天一直開至秋末,說能開半年,還是保守的。另外夾竹桃是木本花卉,同其他樹木一樣,自生自長,無須過多打理,省了無數(shù)辛勞。
清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夾竹桃:“終歲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猶嫣紅鮮好,得水蕩漾,朵朵不分。開與眾花同,而落與眾花異,蓋花之善落者也。故又曰地開桃,似落于地而始開然。”該段文字記述了夾竹桃花一個與眾不同的有趣現(xiàn)象:夾竹桃花落時,不像其他花一瓣一瓣地落,而是整朵花凋落。且落地后的花朵幾日不敗,好像落地后才開的一樣,夾竹桃又叫地開桃,意思是在地上開的桃花。看到這段文字,特意去看了凋落在地上的夾竹桃花。一朵朵花落在草叢里,也能花冠向上,真的像在地上開出的。整朵花凋落也是事實,但落地幾日后仍然新鮮如初,覺得有點夸張。
今人少種夾竹桃,也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歷史的緣故,與桃花有關(guān)。桃花自《詩經(jīng)》“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始,至崔護(hù)的“人面桃花”,口碑一直很好。或是審美疲勞,自明清起,人們對桃花的審美有所改變。可能因其顏色嬌媚,又易凋零,桃花的品性逐漸為人看輕。明王衡《東門觀桃花記》中說:“桃價不堪與牡丹為奴,人且以市娼辱之。”竟以娼妓喻之,實在有點過分。今人語句中“命犯桃花”“交桃花運”,雖不完全是貶義,但對于一個已婚男人,則肯定是不懷好意之詞。桃花從原本的清純美麗,一下子變成輕薄媚俗,形象一落千丈,漸為世人所惡。夾竹桃受其牽連,也漸被冷落。清人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夾竹桃一種,花則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則佳麗之人,道不同不相為謀,合而一之,殊覺矛盾。請易其名為生花竹,去一桃字,便覺相安。”從這一大段敘述來看,李漁還是非常喜歡夾竹桃的,只是極不喜歡它的名中帶桃字,以為將桃與竹放在一起,有損竹的形象。建議將桃字去掉,改夾竹桃為生花竹。福建一帶也流行這樣的諺語:戴花莫戴夾竹桃,做人莫做人細(xì)婆。細(xì)婆,妾也。夾竹桃,賤也。以夾竹桃為賤花。
另一個原因,是世人對夾竹桃的誤解和偏見,以為其有毒,種植有風(fēng)險,便有意疏遠(yuǎn)之。夾竹桃有毒屬實。小時候看動畫片《黑貓警長》,就知道大黃狗是因誤食帶有夾竹桃花粉的韭菜而中毒死亡的。有一部美國電影《白色夾竹桃》,片中女詩人被情人拋棄后,就用自己最喜愛的夾竹桃花毒死了他。國內(nèi)也有一部宮斗劇《甄嬛傳》,有類似情節(jié),齊妃受人挑撥,因妒生恨,將摻了夾竹桃花粉和汁液的栗子糕送給有孕在身的甄嬛,企圖造成其流產(chǎn)。電視劇的傳播,加劇了人們的恐懼心理。其實,害怕夾竹桃有毒而少種或不種的理由太牽強。世間有毒的東西多了,只要不去觸碰它,就會相安無事。香水有毒,好看的蘑菇也有毒。或是夾竹桃花太美了,才產(chǎn)生出毒素,這是一種自我保護(hù),可免遭害蟲攝食,警告人類勿要攀折。夾竹桃在地球上已存在了數(shù)萬年,乃至百萬年,從國外傳來我國也有千年之久。夾竹桃雖然有毒,但它從來不會投毒、放毒,加害于人類和其他生靈。至于產(chǎn)生的毒害,責(zé)任不在夾竹桃,而在于人,是人心有毒,因恨生毒。因夾竹桃有毒而厭惡之,拒栽之,也狹隘了些。
夾竹桃自身有毒,但它也能抗毒消毒。隨著工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城市污染問題越來越嚴(yán)重。夾竹桃能有效地消除重金屬元素鉛對環(huán)境的污染,也能吸收工業(yè)廢氣中的氯氣、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對空氣有較強的凈化能力。夾竹桃也是生態(tài)恢復(fù)的先鋒物種。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廣島被原子彈夷平后,人們本以為廣島幾十年內(nèi)都會因核輻射而寸草不生,但在第二年春天,夾竹桃就在核爆中心一公里內(nèi)的花園里率先發(fā)芽,可見其生命力的強大。在一些重金屬礦的復(fù)墾中,夾竹桃也是首選和必選物種。另外,夾竹桃體內(nèi)還有一種特殊的化學(xué)成分,能夠有效殺死血吸蟲的中間宿主釘螺。因此在我國血吸蟲流行的區(qū)域,采用夾竹桃的水浸液進(jìn)行防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地方干脆就在河堤兩岸,遍植夾竹桃,也能有效降低釘螺的存活率和血吸蟲病的發(fā)病率。我的一個朋友經(jīng)常在微信圈里曬夾竹桃盛開的圖片。他說家住在長江邊,那里的江堤上種滿了夾竹桃,每到夾竹桃盛開季節(jié),一大片紅,一大片白,開得蔚為壯觀,煞是好看。江堤上為什么栽夾竹桃?可防治血吸蟲也。
我常常在想,那些終年生長在大山里或鄉(xiāng)間的草木,還是比較幸運的。它們除了少見一些世面,多承受一些花開無人賞的冷落和寂寞之外,一般不會受刀斧之傷,大都能盡享天年。不像夾竹桃這些生在都市里的花木,看起來風(fēng)光無限,卻命運多舛,整天提心吊膽,看人臉色。不知道哪天就飛來橫禍,枝丫被砍斷,樹干被腰斬,腳下土地被征用,被連根挖起,遭殺身之禍。幸運一點的,遇到好心之人,被移栽別處,雖是撿得一條性命,也是傷筋動骨,元氣大傷。如今城市變化快,讓我們感慨的,不再是從前的“物是人非”,而是眼前的“人是物非”了。也讓那些不能躲、不能藏、不能言、不能語的草木,更覺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了。
愿天下草木都有一個安穩(wěn)的居所,陪我們到老。
風(fēng)中紫云英
童年的記憶里,最美的花兒當(dāng)屬紫云英了。一是名字可人。一個名叫云英的女孩兒,必定是個美人,一朵名叫云英的花兒,自然不會讓人失望。二是花色撩人。童年時見過的,要么是梔子花的白,要么桃花的紅,或者油菜花的黃,很少見過紫云英的紫,即使現(xiàn)在,紫色花也不多見。紫色讓人想起葡萄美酒,想起霓虹閃爍,令人興奮和陶醉。三是花開的場面感人。每年三月,大片大片的紫云英盛開,大紅大紫,大模大樣,燦若云霞,撼人心扉。與今日油菜花海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據(jù)《植物名釋札記》中稱,有一種叫云英的云母礦石,舉起對著太陽觀看,“五色并具而多青”,紫云英的花色與該種云母礦石相似,因此得名紫云英。紫云英屬于豆科,與豌豆、蠶豆同類。花冠蝶形,花小,6-10朵小花聚在一起,呈傘形。掐一支紫云英,捻在手中轉(zhuǎn)動,像極了一只小小的風(fēng)車,迎著風(fēng),呼啦啦地旋轉(zhuǎn)。也像詩人戴望舒的《雨巷》中那把緩緩撐向雨巷盡頭的油紙傘,讓人纏綿悱惻。有時我們還會采摘一把紫云英,擎在手中奔跑,像一面旗幟,更像一支熊熊燃燒的火炬,也像婚禮上新郎手中的手捧花,美麗得讓人心動,心醉。
紫云英有很多名稱,紅花草、紅花郎、荷花郎皆是。紅花草最好理解,紫云英草本,花色紫紅。紅花郎有點兒費解。一朵美艷的花兒,為什么叫郎呢?問過許多人,都說不知道。翻過許多書,也沒有答案。我想了又想,大概最初可能叫紅花浪。春風(fēng)吹過,紅色的紫云英花海,翻卷起層層波浪。陌上踏青尋春的人們,看到如此美景,脫口而出:紅花浪,紅花浪。叫著,叫著,就叫成紅花郎了,就聽成紅花郎了,就寫成紅花郎了。至于荷花郎,許是紅花郎的再一次誤聽誤寫,紅花郎,荷花郎,二者發(fā)音如此相近,錯誤難免。受此啟發(fā),趕忙將紫云英與荷花的圖片放在一起比較,竟發(fā)覺二者還真有些形似和神似,這荷花郎的名字也不純粹無中生有了。因發(fā)音不標(biāo)準(zhǔn)與書寫不規(guī)范,讓紫云英又收獲了兩個別有情趣的名字,也算是一種美麗的錯誤吧。
紫云英極易生長。水稻未收割前,就將其種子撒下去,種子落地成活,自生自長,無須耕耘、施肥。水稻收割后,這些種有紫云英的田塊,就閑置著,任由紫云英生長。而沒有種紫云英的,則耕作后種上小麥。開始時,紫云英苗瘦弱稀疏,一處有,一處無。等春天一到,一下子就豐茂起來,迅速鋪滿整個田野。紫云英同大豆一樣,根上有根瘤,能夠自己固定氮肥。種過紫云英的田地,土壤肥沃,第二年栽種莊稼,能明顯提高產(chǎn)量。農(nóng)諺:花草種三年,瘦田變肥田。種植紫云英可改良土壤,是當(dāng)時人們的共識。寧可少種幾塊田小麥,也要多種幾塊田紫云英。紫云英的莖葉也含有豐富的氮素,可作牲畜的飼料,也可與泥土攪拌在一起,堆在田間地頭的水坑里,漚制后撒入田間,當(dāng)作有機肥料,這項農(nóng)活在我的家鄉(xiāng)叫“搪糞”。搪(音)是攪拌的意思,就是將紫云英和泥土攪和在一起,是件體力活。有時候來不及收割,也沒有人力搪糞,就直接翻耕入土,讓紫云英在土壤里腐爛變成肥料。計劃經(jīng)濟年代,化肥緊張,價格又貴,不易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主要依靠有機肥,紫云英就是一個來源,這也是當(dāng)時紫云英能夠被大面積種植的原因所在,紫云英因此又得名綠肥。一名紫云英,高山流水,陽春白雪。一名綠肥,下里巴人,土得掉渣,與糞水同伍,讓人掩鼻。真是大俗大雅,上天入地,匪夷所思。我私下以為,這個綠肥的名字起得真好,無可替代。一是紫云英的莖葉是綠色的,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綠色肥料。二是它是一種有機肥,環(huán)保無污染,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綠色肥料。
那個年代只有集體才會種植紫云英,充作肥料。各家各戶的自留地要種一些糧食、蔬菜,補貼口糧的不足,一般是舍不得種紫云英的。紫云英的嫩莖可以食用,我卻沒有吃過。因為長在公家田地里,自然不好隨便采摘。至于味道如何,推測應(yīng)當(dāng)一般。那時溫飽尚未解決,紫云英可能只是一種救荒的野草,估計與很多野菜一樣,難以下咽。問了吃過紫云英的人,看了吃過紫云英的人寫的書,都說紫云英遠(yuǎn)不及豌豆尖、薺菜苗鮮嫩美味。此話不會有假,豌豆尖和薺菜從來都是飯桌上的寵兒,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極受追捧。而紫云英卻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不說銷聲匿跡,也是難得一見。試想,倘若紫云英果真美味至極,一向貪戀美食的人類,豈會輕易放手,必定會千方百計挽留,延續(xù)種植的。
紫云英莖干柔弱,呈匍匐狀,在田地里蔓延生長,漸漸鋪成厚厚的一層,像學(xué)校操場上綠色的海綿墊,富有彈性。我們在上面奔跑、跳躍、翻滾、臥倒、摔跤。有時就躺在紫云英的花海里,手腳張開,臉望藍(lán)天,鼻嗅花香,望流動的白云,看翱翔的飛鳥,憧憬著遠(yuǎn)方和未來。那時穿深色的土布衣裳,身上滾滿了草青色,也看不出來臟。不過紫云英被我們踩踏后,會受傷而影響生長,是被禁止的。隊長發(fā)現(xiàn)后,一陣責(zé)罵聲從遠(yuǎn)處傳來,我們立即像野兔一樣,四散而去。
小時候挖豬草,有時貪玩誤事,天黑時,籃筐里的豬草才挖一點點。情急之下,便順手牽羊,偷偷摟幾把紫云英放在籃底,用豬草蓋住,拎回家交差。若被生產(chǎn)隊長發(fā)現(xiàn),除了挨罵,還要扣父母工分。回到家自然又是一頓臭罵,有時還免不了一頓打。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這紫云英雖美不勝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又立下了汗馬功勞,卻名不見經(jīng)傳。《詩經(jīng)》里找不到它的名字,《本草綱目》中也不見它的身影,浩如煙海的古詩詞中,也難覓其蹤跡。有資料顯示,“紫云英”一詞一直到清代才出現(xiàn),別說與身世顯赫的梅蘭菊荷相比,就是與出身卑微的一些野草野花相比,也顯得尷尬,更有些寒酸。更糟糕的是,沒有證據(jù)明確表明,它是何種植物的別稱,它的前生往世肯定是誰。紫云英仿佛橫空出世,從而引發(fā)爭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憤憤不平,這么美艷的花兒,身世來歷怎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便不辭勞苦,窮經(jīng)據(jù)典,竭力考證。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古時有一種植物與紫云英最相像,這種植物在《詩經(jīng)》中叫“苕”、《毛詩草木疏》中叫“翹饒”、《爾雅》中稱“搖車”。這幾個不同的名字都指向同一種植物,可能就是現(xiàn)在的紫云英。但細(xì)致研究后,仍有許多謎團,無法解開,甚至自相矛盾,令人費解。例如《詩經(jīng)》中《陳風(fēng)·防有鵲巢》:“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意思是:喜鵲原本在樹上筑巢,而今卻說鵲巢出現(xiàn)在河堤上;巢菜本應(yīng)生于平坦的原野,卻說它生于山坡。誰在離間我心上人?我心里愁苦又煩惱。這里的“苕”被認(rèn)作紫云英。而另一篇《小雅·苕之華》:“苕之華,蕓其黃矣。”意思是凌霄花開,一片黃色。此處的“苕”又被解讀為凌霄花。同一本《詩經(jīng)》,同一種“苕”,一處說是紫云英,一處又說是凌霄花,讓人摸不著頭腦,將信將疑。
蘇東坡詩:“潤隨甘澤化,暖作春泥融。始終不我負(fù),力與糞壤同。”光看內(nèi)容,以為是寫紫云英的綠肥功效的,再看詩題,卻標(biāo)明《元修菜》。元修菜,即巢菜。詩人的朋友叫巢元修,有一次從四川來嶺南看望蘇東坡,兩人談到家鄉(xiāng)的野蔬巢菜時,詩人竟暗自神傷。想起自己自離開故鄉(xiāng),已有十多年再未嘗過巢菜的味道,頓生感慨,遂寫成此詩。并再三叮囑朋友,若再回四川,一定記得帶些巢菜的種子過來,打算自己栽種。蘇東坡還特意將巢菜改稱元修菜,意在提醒朋友一定不要忘了。從中不難看出,這巢菜肯定是極其美味的,不然,故鄉(xiāng)的美食無數(shù),詩人為何獨記得它的名字?漂泊異鄉(xiāng)多年,詩人為何獨對它念念不忘,記掛在心?“巢”與“苕”音諧,“巢菜”被認(rèn)為就是詩經(jīng)中的“苕”,又被認(rèn)為最可能是紫云英。巢菜到底是不是今天的紫云英?若是,這紫云英真的有那么美味,讓詩人心心念念,難以釋懷?若不是,這紫云英又從何處而來?
有人提出,紫云英可能是一種外來物種,身世自然無從稽考,檔案自然一片空白。若果真如此,就省事多了,所有爭議和疑問,都化成云煙,散入九霄云外。還有一種猜測,說是兩種植物雜交的產(chǎn)物,只是年代久遠(yuǎn),無法查明生身父母是誰。讓我們閉目想象一下,在曠古年代,兩棵年輕的植物,因機緣巧合而走到一起,終日寸步不離。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耳鬢廝磨,日久生情,你情我愿,相親相愛,芳心暗許,珠胎暗結(jié),留下愛情結(jié)晶。紫云英,一個嶄新的物種,仿佛天外來客,突然降凡人間。多么迷人又浪漫的一段愛情。這種猜測雖然合情合理,但缺少證據(jù)支持,也只是一家之言。紫云英的身世終究是個謎。
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更多地依賴清潔速效的工業(yè)化肥。紫云英這種曾經(jīng)的當(dāng)家綠肥,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再也無人種植紫云英了,大面積栽種紫云英的時代,更是一去不復(fù)返了。
菱花向月開
晚間散步,路邊有女子叫賣野生的菱角,記憶一下子回到從前。
童年的故鄉(xiāng),有許多小河和池塘,水里長滿了各種水草,其中就有菱。菱有家菱和野菱之分。家菱是有主的,或公家種的,或私人栽的,有人看守,不敢有非分之想。而野菱則是無主的,也是我們整天惦記的。野菱自生自長,它的種子從何而來,我們并不清楚,也不關(guān)心。只記得開始時,水面只有稀疏的幾處菱盤,后來越長越多,漸漸將整個水面鋪滿。我們每天沿著彎彎曲曲的河堤去學(xué)校,一邊走,一邊望著水中的菱,盼望它快點長,早點結(jié)菱。在食物極度缺乏的年代,菱是上蒼贈予我們這些鄉(xiāng)間孩子為數(shù)不多的幾種零食之一。
野菱成熟的季節(jié),也是我們最心慌意亂、魂不守舍的時候。用母親的話講,我們的魂掉在了河邊。中午碗筷一丟,說是早點去學(xué)校,其實去河邊摘菱。課堂上無心念書,只盼早點放學(xué),趕緊奔到河邊,摘幾只菱,慰藉一下轆轆饑腸。近處的菱摘光了,我們就拿根樹棍,夠遠(yuǎn)處的菱。菱也很配合我們,只要拽住一棵菱盤,慢慢地拖拉,就會拉來一大片。水邊摘菱是有危險的,有時腳下一滑,就會連人帶書包一起掉入水中。好在河不深,趕緊爬上岸,渾身濕透,低著頭回家,免不了父母一頓打,一頓罵。父母聲色俱厲地警告我們,老師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們,不準(zhǔn)再去河邊摘菱了,鄰村就有孩子因摘菱溺水而亡。我們聽了,確實害怕,并保證再也不摘了。記吃不記打的年紀(jì),只要一到水邊,一望見菱,便又兩眼放光,當(dāng)時的保證早就丟到腦后,拋到九霄云外了。
菱葉細(xì)碎,浮于水面,聚集成蓮花狀,我們稱作菱盤。菱很有意思,既可依果得名,也可依葉得名。明代李時珍說,菱又名芰,其葉支散,故從芰,其角棱峭,故謂菱。在古代,芰菱不分,被視同一物,都指現(xiàn)在的菱。另一種說法,菱的葉片呈菱形,故得名為菱。可見菱葉和果的風(fēng)格是一致的,都是有棱有角,棱角分明。
南宋詩人楊萬里有一首專門寫菱葉的詩,別有情趣:“柄似蟾蜍股樣肥,葉如蝴蝶翼相差。蟾蜍翹立蝶飛起,便是菱花著子時。”菱葉的葉柄膨大,中間貯滿空氣,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可使菱葉漂浮于水面。用手使勁擠捏葉柄,會發(fā)出啪啪的響聲,年幼時的我們樂此不疲。詩人說這肥碩的葉柄,看起來好似蟾蜍的大腿,而菱形的葉片又似蝴蝶的翅膀。當(dāng)池塘里擠滿了菱盤,看到菱葉翹起,露出葉柄,就像立起了身子,躍躍欲試的蟾蜍,又像翩翩欲飛的蝴蝶。此時,也正是結(jié)菱的時候,用不了多久,菱就該成熟了。詩人不僅饒有趣味地描寫了菱葉,還順便教會了我們依據(jù)菱葉判斷何時結(jié)菱、何時菱成熟的方法。詩人觀察仔細(xì),也善于總結(jié),不像童年的我們,稀里糊涂,只曉得吃菱。至于什么時候結(jié)菱,什么時候菱成熟,只能笨拙地?fù)破鹆獗P,一看究竟。
菱也開花。《本草綱目》中說:“五六月開小白花,背日而生,晝合宵炕,隨月轉(zhuǎn)移。”菱花一般夜里開放,白天閉合,似乎怕見日光,與牽牛花相像。加上又是開在水中央,目力不及,人跡難至,所以一般難以看到盛開的菱花。平日看到的,不是閉合的菱花,就是開敗后萎蔫的菱花。只有在陰雨天或樹蔭下,才能在白天里看到完整開放的菱花。至于菱花能隨著月光的移動而轉(zhuǎn)動,像向日葵跟隨日光轉(zhuǎn)動一樣,更是無人知曉了。菱花因能隨月轉(zhuǎn)動,又被稱為“向月菱”,一個非常有詩意的名字。
有關(guān)菱花的詩詞很多。南宋詞人張镃在《鵲橋仙》中寫道:“連汀接渚,縈蒲帶藻,萬鏡香浮光滿。”月光皎潔,照在滿湖白色的菱花上,仿佛有萬盞明鏡,閃動銀光,彌漫幽香。清人吳錫麟的《菱花》詞:“漸帶夜深風(fēng)露,淡浸全湖白。尋夢去,誤了幽蝶。”夜晚去湖邊看菱花,整個湖面都是銀色的,菱花如同夢境中迷路的蝴蝶,紛紛停落水面,再也不肯翩飛了。從古人的詩詞中我們才知道,菱花盛開的夜晚是多么地美妙、夢幻、迷人,如此良辰美景,如此浪漫溫馨,卻被我們無端地忽視,一再錯過,甚至完全不知曉,實在太可惜了。
菱花開后,便沉入水中,在水中孕育,漸漸長成菱角,這一點又跟落花生相仿。只是落花生是花開后埋進(jìn)泥土中悄悄結(jié)實,故菱又有“水中落花生”之譽。無論埋進(jìn)土里,還是沒于水,都是為了保護(hù)幼果安全發(fā)育,防止鳥獸過早偷食。凡草木皆有此智慧。花要鮮艷醒目,開在枝頭,高舉過頭頂,讓蜂蝶遠(yuǎn)遠(yuǎn)地望見。甚至未葉先花,赤裸裸地展示。但果要隱藏。花受孕坐果后,落花生藏于泥中,菱藏于水中,其他則藏于綠葉叢中。果實成熟后,則紅通通,黃澄澄,刪減繁葉,完全敞開心扉,大白于天下,無償供鳥獸食用,順便幫其帶走種子,擴大種群。
菱的品種較多,名稱繁復(fù)。從角的數(shù)量上看,四角菱、兩角菱最為常見,三角菱和無角菱也有,極其稀少。從菱的顏色上分,有紅菱、青菱、烏菱、紫菱多種。二角菱,形似牛角,又稱牛角菱。又似彎彎的扁擔(dān),有地方稱為扁擔(dān)菱。離家不遠(yuǎn)的揚州邵伯鎮(zhèn)也盛產(chǎn)菱角,非常有名,世稱邵伯菱,與太湖的紅菱、嘉興的風(fēng)菱并列為江浙三大名菱。邵伯菱青色,四角,上下兩角稍長,尖而翹,左右兩角卷曲抱肋,形同羊角,俗稱“羊角青”。
最奇特的是浙江嘉興南湖產(chǎn)的無角菱,又稱為元寶菱、餛飩菱、和尚菱,長相可愛。傳說南湖菱本是有角的,乾隆下江南時,嘗了南湖菱之后,直呼好吃,吃到興奮時,一不留神被菱角扎了手指,喃喃說了句,要是沒角就好了。第二年,南湖菱果然變成無角了。科學(xué)的解釋是,南湖菱初結(jié)時是有角的,只是角與菱之間的聯(lián)結(jié)不夠緊密,待菱長成后,便自動脫落了,遂成無角菱。
菱可生吃,也可熟食。清人袁枚在《隨園食單》中說:“新出只栗,爛煮之,有松子仁香,新菱依然。”這里的新菱應(yīng)為新摘的老菱,許多人誤以為嫩菱。只有老菱熟食,才有栗子糯糯的口感,才有松子仁濃濃的香氣,所以菱又有“水栗”的稱號。而嫩菱只可作水果生食,若熟食也需快火爆炒。嫩菱若爛煮之,則形同將水果煮爛,口味索然。
嫩菱老菱的判別也很簡單,將采回來的菱倒在大盆里,然后往盆里倒?jié)M水。沉入水底的便是老菱,浮在水面上的是嫩菱。嫩菱殼皮松脆,用手即可剝開。剝開后的白色菱肉,鮮嫩脆甜,有一股草木的清香。老菱外殼堅硬,用手很難剝開,要用牙咬。兩角菱最省事,從中間咔嚓咬斷,再用牙齒將菱米擠出。這種吃法比較粗暴,不夠文雅,也不能得到完整的菱米。溫和又斯文的吃法是,先從菱的背部咬開一個豁口,然后再用手剝開,即可得到完整的菱米。四角菱比較麻煩,先咬斷兩角,再依兩角菱的吃法即可,也可選擇直接從背部咬開的吃法。野菱的角都很尖銳、堅硬,尤其是老的四角野菱,又稱刺菱,一不留神就會扎傷手,扎破嘴。吃野菱,一般要用菜刀先劈成兩半,才能吃到菱肉。
菱適合水煮著吃,不加任何佐料,煮熟的菱角聞起來有一股清香的味道。也可以和豬肉、老鵝、黃鱔等一起燉著吃。菱淀粉多,吸足了肉的油水,味道更佳,肉也變得香而不膩。餐桌上往往菱比肉更受歡迎,常常是菱吃光了,肉剩了下來。
吃菱非常費功夫,尤其老菱、野菱更難,卻充滿樂趣。李漁說:“獨蟹與瓜子、菱角三種,必須自任其勞。旋剝旋食則有味,人剝而我食之,不特味同嚼蠟。”意思是,菱角必須自己剝的才好吃,如果別人剝好了,就沒有滋味了。吃菱的季節(jié),人們喜歡撿家菱、嫩菱、兩角菱吃,野菱、老菱沒人吃,尤其是老的四角野菱,更是少人問津。其實,野菱只是難剝,但更耐咀嚼,更香,更有味。就像現(xiàn)在的野菜、土雞、土豬肉一般。母親會將這些不討人喜歡的野菱曬干,收藏起來,等到臘月寒天,拿出來分給我們姐弟。我們一邊坐在門前曬太陽,一邊津津有味地啃食手中的老菱。有時實在咬不動,就用刀剁,用錘子砸,等不及時,就找塊磚頭砸開,別有一番滋味和情趣。
七月菱角八月落,俗稱“七菱八落”。農(nóng)歷七月菱成熟,開始上市。如果不及時采摘,到了八月,菱熟過了頭,就脫落沉水了,影響收成。所以采菱要適時,要及時。采菱在許多文人筆下是一件極浪漫、極溫馨的美好事情。白居易的《看采菱》:“菱池如鏡凈無波,白點花稀青角多。時唱一聲新水調(diào),謾人道是采菱歌。”李白的《秋浦歌》:“淥水凈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采菱女,一道夜歌歸。”流行歌曲《采紅菱》:“我們倆劃著船兒采紅菱,郎有心,妹有情,就好像兩角菱,從來不分離,我倆一條心。”從中看出,人們是一邊唱著歌,一邊采著菱的。青年男女更是借采菱的機會,相互見面,吐露心聲,互訴衷腸。
采菱看似浪漫,實則極為辛勞,甚至危險。杜甫詩:“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寒冬踏藕是人間極其辛苦的勞作,而詩人將采菱與之并列,可見采菱之艱辛。南宋范成大也知采菱艱難,作《采菱戶》詩:“采菱辛苦似天刑,刺手朱殷鬼質(zhì)青。休問揚荷涉江曲,只堪聊誦楚詞聽。”菱刺尖銳,一不小心就會扎手出血,異常疼痛。
靠近岸邊或淺水處,采菱人就穿著防水衣,站在水中采菱,水齊腰或平胸處。菱塘中央或水深處,則需要乘坐木盆采摘。木盆就是家里的洗澡盆或洗衣盆。洗澡盆長形,摘菱時,人蹲在盆的一頭,尾端會高高翹起。洗衣盆較小,圓形,只能容下一人。乘坐時要掌握好平衡,一不留神,就會連人帶盆翻入水中。摘菱的人都有翻盆的經(jīng)歷。在菱鄉(xiāng),男女老少都敢乘盆摘菱,但不等于人人會游泳。進(jìn)入深水區(qū)摘菱,要格外小心,一旦翻盆落水,就有溺水的危險。為了不耽誤采摘,人們顧不了這些,采菱溺水的悲劇時有發(fā)生。
集體采菱時,大家一字排開,齊頭并進(jìn)。一邊劃著水前行,一邊逐個翻起菱盤,摘下菱角,因此采菱也叫“翻菱”。采過的菱盤就背面朝上,翻在水中,以為標(biāo)記,可防漏采或重復(fù)采,第二天,這些菱盤會自動翻過身來,恢復(fù)原狀。
坐在木盆里采菱,一整天不可站立,彎腰久了,會累得腰酸背痛。一方菱塘,要反反復(fù)復(fù)采許多回,辛苦勞累可想而知。另外,采菱時經(jīng)常遇到老鼠、水蛇、鏈蛇、無名甲蟲出沒,一陣驚惶。螞蟥也不知什么時候叮在了手臂上、小腿上,不斷有尖叫聲傳來。更令人厭惡的是,蚊蟲比岸上更猖獗,叮人也更癢,更痛,有種蠓蟲更叮得人奇癢難忍,簡直要發(fā)瘋。
少數(shù)漏采的老菱會沉入水底,作為種菱,來年在淤泥中萌發(fā),又會長出一塘新菱。故菱塘只需播種一次,便可年年收獲。
采完菱的菱盤,仍有價值。父親將它們拖上岸,用板車?yán)丶遥菇o豬做飼料。有時拉得太多,豬一時吃不完,奶奶就將它們剁碎,放在一口大缸里發(fā)酵。以后每頓舀一點,拌在豬飼料中。在經(jīng)濟困難時期,人們也會以菱的幼莖嫩葉為食,度過饑荒。摘取菱的幼莖嫩葉洗凈,放進(jìn)開水中焯幾分鐘,除去苦澀味,撈起瀝干,擠去水分,切碎,放鹽腌制,可當(dāng)咸菜。也可下鍋炒熟,盡管苦澀難咽,卻可充饑救荒。若是現(xiàn)在來做,則放入香油,加入肉絲、紅椒絲,倒些香醋,澆些生抽,淋些麻油,急火爆炒,肯定美味。
如今的村莊,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早年的小河水塘多被填平,遺存的也整治一新,河水清澈,水中的雜草全部被清除,野菱自然無存身之地。即使家菱,因為采摘辛苦,也很少有人種植了。有一種細(xì)果野菱,又稱作四角刻葉菱,數(shù)量極少,已成瀕危物種,早在1999年就被列為國家二級野生保護(hù)植物了。
(責(zé)任編輯 王仙芳 349572849@qq.com)
- 今古傳奇·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其它文章
- 影響力人物——彭四平
- 少年的祈禱
- 雪落又新年
- 讓每一朵花都守住芬芳
- “在草尖的低矮處開出白花”
- 天路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