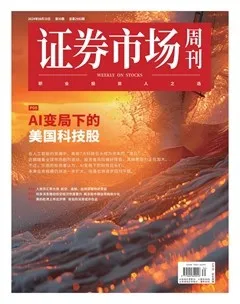從不確定性中獲得勝算
亞當·庫哈爾斯基的《勝算》是一本講述如何利用系統的概率分析、數學模型和科學取勝的故事。正如庫哈爾斯基所說的,這是“勝算背后的科學”。在歷史長河中,“下注”這件事徹底改變了人類對運氣的理解。
有關完美投注系統的想法很誘人。那些通過下注賺大錢的故事挑戰了賭場和莊家不可戰勝的認知,但這些故事暗示概率博弈中存在漏洞。如果我們足夠聰明就能發現并利用這些漏洞,那么隨機性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運氣似乎也可以用公式來控制。
誕生驚人思想的流水線
庫哈爾斯基將“勝算”視為科學。有趣的是,研究“勝算”的人并非都是賭徒,而是那些成名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們。
早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數學家杰羅拉莫·卡爾達諾就研究出一個公式。這個公式被稱為“卡爾達諾公式”,是一個三次方程的求解公式。卡爾達諾本身也喜歡賭博,他以此來測量隨機事件的發生概率。在卡爾達諾的時代,現在所知的概率論尚未被提出,那時沒有關于偶然事件的定律,也沒有關于事件發生可能性的規律。如果誰擲骰子擲出了兩個6,那純屬運氣好。對很多博弈游戲來說,玩家并不知道什么叫“公平”的賭法。
卡爾達諾是發現賭博游戲可以用數學知識進行分析的其中一個人。他發現,要在靠運氣取勝的世界找到正確的方向,就必須找到它的邊界所在。所以他會查看所有可能結果,然后關注那些他感興趣的結果。
接下來幾十年,其他研究者也逐漸揭開了概率的奧秘。伽利略·伽利雷研究了某些點數的組合比其他組合出現更多的原因;約翰內斯·開普勒在研究行星運動之余,寫了一篇關于骰子和投注理論的簡短文章。
1654年,法國作家安托萬·貢博提出了一個博弈難題,概率科學得以蓬勃發展。他的難題是:是一個骰子擲4次出一個6容易,還是兩顆骰子擲24次出兩個6容易?他認為兩者出現的概率是相同的,但沒有辦法證明。于是,他向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求教。
為解決這個問題,帕斯卡找到了大數學家皮埃爾·德·費馬。他們在卡爾達諾關于隨機性的成果基礎上,共同確立了概率論的基本定律。他們定義了博弈的期望值,用以衡量重復賭博的平均收益率。他們的研究證明貢博的想法是錯誤的,一個骰子擲4次出一個6,比兩顆骰子擲24次出兩個6容易。多虧了貢博的問題,數學領域才出現了一套全新的思想。
到了18世紀時,瑞士數學家丹尼爾·伯努利在解決投注問題時,使用的方法是從“期望效用”而非預期收益著手。他認為,人們擁有多少錢,可以決定相同數額的錢的價值的高低。比如,一枚硬幣在窮人眼中就比富人眼中更值錢。這一見解極其高明,從此以后,效用的概念奠定了整個保險業的基礎。
進入現代社會,投注問題持續影響科學的思想,它涉及從博弈論與統計學到混沌理論與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畢竟,投注是進入運氣世界的窗口,它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平衡風險與收益,以及人們為什么對事物的估值因情景而異。它幫助我們弄清楚如何做決策,以及如何控制運氣的影響。投注行為涵蓋了數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物理學,因此吸引了對隨機事件或看似隨機事件感興趣的研究者。很多時候,科學與投注的概念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那些最初由研究者的學術興趣而產生的投注方法,促成了人們在實踐中擊敗莊家的嘗試。
20世紀40年代后期,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來到拉斯維加斯。他嘗試了很多投注方法,以確定自己大概能贏多少或者可能會輸多少。但他很快就輸了。他認識一個叫尼克·丹多洛斯的職業賭徒,這個人總是能贏錢。丹多洛斯告訴費曼說,他只在賠率對他有利時下注。他不是在牌桌上賭,而是在跟牌桌旁的其他人賭,那些迷信幸運數字的、心存偏見的人。那些顯而易見的策略只會讓他輸錢,他找到了一種讓賠率有利于他的方法。
算出數字從來不是最難的,真正的技巧在于把它轉化為有效的策略。一直以來,投注不斷催生新的科學領域,啟發人們對運氣和決策產生新的見解,并進而對科技、金融等多個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從簡單到復雜,從大膽到荒謬,投注是一個誕生驚人思想的流水線。查理·芒格就把投資當做投注。全世界的投注者都在挑戰可預測性的極限,努力跨越秩序與混沌的邊界。通過剖析成功的投注策略,我們發現投注為何會影響人們對運氣的理解,以及運氣如何為我們所用。
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
物理學家亨利·龐加萊對輪盤賭十分興趣。他提出,我們可以根據水平的無知來分類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一個物體的準確初始狀態,比如位置和速度以及它遵循的物理定律,那么要解決的就是教科書介紹的那類物理問題。龐加萊將其稱為“一級無知”:掌握所有需要的信息,只需進行簡單的計算。“二級無知”指的是,我們知道物理定律,但不知道事物的準確初始狀態,或者無法準確的測量其初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要么改進測量方法,要么就只能將對事物狀態的預測限制在很小的范圍內。“三級無知”則是最廣泛的無知:我們既不知道事物的初始狀態,也不知道它們所遵循的物理定律。當定律過于復雜、無法徹底解開時,人們就會陷入三級無知。
輪盤賭也是一樣,小球的軌跡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只通過觀察旋轉的輪盤,是很難把握這些因素的。根據龐加萊的建議,我們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讓小球停在了最終位置,我們只需要觀察很多次旋轉,再來分析最終的結果即可。這正是1947年人工智能科學家阿爾伯特·希布斯和病理學家羅伊·沃爾福德所做的事。賭場的優勢取決于輪盤產生每個數字的機會是均等的,但同其他任何機器一樣,輪盤賭賭桌可能有缺陷或因長時間使用而磨損。他們找的就是這種產生數字不再均勻分布的桌子。
龐加萊認為,小球初始狀態的差異可能會導致最終結果的差異大到我們無法忽視的程度,但正是由于初始狀態差異又小到無法引起我們的注意,于是我們認為結果只是偶然出現。這個問題被稱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意味著我們收集了一個過程的詳細測量結果,無論是輪盤賭的旋轉還是熱帶風暴,我們未注意到微小事件都可能會產生無法忽視的重大結果。氣象學家愛德華·洛倫茲在一次演講中問道:“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動翅膀,是否會在德克薩斯州掀起一場龍卷風?”孰料在此70年前,龐加萊就已經為世人勾勒出了“蝴蝶效應”的概貌。
洛倫茲的研究最終發展成了主要用于預測的“混沌理論”。他的初衷是希望做出更好的天氣預測,并找到一種方法來預測未來更長時間內的天氣情況。而龐加萊對相反的問題感興趣:一個過程要花多長時間才會變得隨機?輪盤賭小球的路徑真的會變得隨機嗎?
輪盤賭給了龐加萊啟發,但他在對更大規模的軌跡進行研究時才真正取得了突破。龐加萊向人們展示了“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也發生在小行星軌道上。他認為,在足夠多次之后,小球的最終位置將是完全隨機的。他還指出,堅持對某些選擇進行投注會比其他選擇更早表現出隨機性。
成功的輪盤賭策略建立在賭場確信輪盤的旋轉結果無法預測的基礎上,其策略演化反映了概率科學在20世紀的發展。早期擊敗輪盤賭的努力在于逃離龐加萊所說的三級無知,即逃離對物理過程一無所知的狀態。卡爾·皮爾遜的研究則是純粹的統計研究學,意在發現數據的模式。后來人們在賭局中牟利的嘗試,則采用了不同的路徑。這些策略嘗試克服龐加萊所說的二級無知:賭局結果對輪盤和小球的初始條件敏感依賴。
對龐加萊而言,輪盤賭只是一個用來展示他的思想的途徑:簡單的物理過程可以逐漸陷入隨機狀態。這一思想成為混沌理論的重要部分,并在20世紀70年代促成了一個全新的學術領域的誕生。
關注如何輸得最少
在這些全新的學術領域里,涌現了馮·諾依曼的“博弈論”、約翰·納什的“納什均衡”、羅納德·費歇爾的“極值理論”、愛德華·索普的“21點致勝策略”、約翰·凱利的“凱利公式”,等等。
但是,投注與其他投資類別似乎差異較大。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很多資產價格驟降。投資者總是試圖建立一個能抵御這種沖擊的資產組合,例如,他們會持有不同行業的多家公司的股票。但當市場出現問題時,這種多樣性還是不足以抵抗風險。根據美國華威大學的復雜系統研究者托比亞斯·普萊斯的說法,當金融市場遇到艱難時期時,股票也會有類似的表現。普萊斯分析了1939年至2010年道瓊斯指數中的股票價格,發現當市場承壓時,股票價格也隨之下降。如此,本該保護一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分散效應,在市場虧損時也不復存在了。
這個問題并不只限于股票。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前夕,越來越多投資者開始交易“債務抵押債券”。這些金融產品把像房貸這樣的未償貸款打包到一起,讓投資者可以通過承擔部分借款者的風險來賺錢。盡管其中某個人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很大,但投資者認為所有人同時違約純屬天方夜譚。但事實證明,這種假設是錯誤的。金融危機出現后,一套房子失去價值后,其他的房子也會如此。
最優策略關注的并不是“如何贏得最多”,而是“如何輸得最少”。因為隨著時間推移,莊家和賭徒會逐漸掌握那些最知名的策略,結果就是很難從中賺到錢了。人們傾向于用“經驗加權吸引”來學會策略,也就是更偏好那些過去成功過的行為。而最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研究被其他人忽略的人。所以,有的人經常選擇“反人類”的策略,而不是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更好的策略。
研究發現,隨著玩家的數量增加,無序的決策會變得越發普遍。當游戲很復雜時,玩家的選擇變得幾乎無法預測。數學家伯努瓦·曼德布羅特于20世紀60年代初觀察金融市場時,注意到股市的動蕩期往往會扎堆出現。他寫道,大變化總是跟著大變化出現,而小變化總是跟著小變化出現。“波動扎堆”的出現引起了經濟學家的興趣。
愛德華·索普正是發現撲克游戲21點中的巨大漏洞,才寫出那本暢銷書《擊敗莊家》的。但勝利取決于運氣還是技巧的爭論還是蔓延到其他游戲,這一爭論甚至決定了曾經利潤豐厚的美國撲克產業的命運。2011年,美國權威機構關閉了幾個大型撲克網站,使得席卷全美的“撲克熱”宣告終結。
經濟學家蘭德爾·希布相信撲克是一種技巧游戲。他指出,排名前列的玩家除了少數幾天表現不佳外,其余時間一直穩定獲勝,而技術較差的玩家一年下來輸得很慘。有人能以打牌為生這一事實無疑就是這個游戲需要技巧的證明。優秀的撲克玩家能贏得部分原因是,他們能夠控制局面。
而另一位經濟學家戴維·德羅薩并不認同,他以計算機模擬了如果1000個人拋硬幣10000次會發生什么。模擬結果與希布呈現的結果非常相似:一小部分人持續獲勝,余下的人則輸得很慘。這并不能說明拋硬幣涉及技巧,只能說明如果我們觀察的樣本足夠大,罕見事件就有可能發生,就像“無限猴子”一樣。因此,核心的問題是,我們要等多久,技巧的影響才會超過運氣的影響。
“無限猴子”的說法來自數學家埃米爾·博雷爾。博雷爾曾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猴子隨意敲擊打字機的鍵盤,碰巧創作出了莎士比亞全集。他寫道:“盡管這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無法得到合理的論證,但由于其發生的概率極小,以至于任何理智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認為它是不可能發生的。”
用學術知識和新技術武裝
盡管輪盤賭一直被視為隨機性的典范,但它先被統計學再被物理學所顛覆。其他游戲也都輸給了科學。撲克玩家利用博弈論,投注團隊則將體育博彩變成了投資。根據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氫彈的斯坦尼斯瓦夫·烏拉姆的說法,在這樣的游戲中技巧的存在并不總是很明顯。他說:“有一種東西叫習慣性運氣,人們認為玩牌手氣特別好的人可能在這些游戲上有某些隱藏的天分,其中就包括技巧。”烏拉姆相信在科學研究中也是如此。有些科學家碰上好運的次數多得讓人很難不懷疑其中包含天分的因素。
完全移除運氣是不可能的,但經驗顯示它經常可以一定程度的被技巧取代。因此,隨機的過程經常并非隨機。在國際象棋中,不存在固有的隨機性。如果兩個玩家每次下相同的棋步,那么結果永遠都是一樣的,但運氣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因為最優策略是未知的,所以一系列隨機棋步仍有可能擊敗最好的玩家。
然而,在進行決策時,我們看待運氣的眼光有時是片面的。如果選擇結果不錯,我們就將其歸功于技巧;而如果失敗了,那就是運氣不好。我們對技巧的看法也會被外部信息來源所歪曲。媒體愛寫那些抓住風口成為富豪的創業者或是突然變得家喻戶曉的名人的故事。我們也總會聽到新人作家寫出暢銷書或品牌一夜成名的故事。
統計學家馬克·魯爾斯頓和戴維·漢德指出,受歡迎程度的隨機性也會影響投資基金的排名。“假設基金經理在沒有使用任何技術的情況下隨便選擇了一組基金,其中有些靠運氣產生了豐厚的回報,那么這些基金就會吸引投資者,而表現糟糕的基金則會關閉,它們的結果也就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了。看看那些幸存基金的結果,你會認為它們大體上是包含一些技巧成分的。”
運氣與技巧以及投注與投資之間的那條分界線,很少像我們想像的那么清晰。如果我們想在某個情景下區分運氣與技巧,首先必須找到一個衡量它們的方法。但有時結果對微小變化非常敏感,看上去不經意的決定完全改變了結果。單個事件也可以產生戲劇性效果,尤其是在足球和冰球這類進球很少的活動中。在這類運動中,這類事件可能是一個決勝的大膽傳球,也可能是一個擊中門柱的冰球擊球。
愛德華·索普在他的《擊敗莊家》的最后一頁做出了預測:接下來10年我們會見到全新的一批試圖馴服運氣的方法。“大多數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它們的出現是令人激動的。”之后,投注的科學確實進化了。它開創了全新的研究領域,范圍已經遠超拉斯維加斯的真實賭桌和塑料籌碼。
我們已經看到輪盤賭如何幫助亨利·龐加萊完善混沌理論的早期思想,并幫助卡爾·皮爾遜測試了他的新型統計技術。我們還看到了斯坦尼斯瓦夫·烏拉姆的紙牌游戲促成了蒙特卡羅法的提出,該方法現在應用在了從3D計算機圖形到疾病爆發分析的各種事情上。我們還看到了博弈論如何從馮·諾依曼對撲克的分析中浮現出來。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幾乎所有游戲都可以被擊敗,但利潤很少來自幸運數字或萬無一失的系統。成功投注需要耐心和才智。它們需要選擇無視教條、遵循自己好奇心的創造者。
特別是概率論,它是人類創造的最有價值的分析工具之一,它給了我們判斷事件可能性和評估信息可靠性的能力,也因此成為從DNA測序到粒子物理的現代科學研究的核心組成部分。一門從對運氣游戲的思考中起步的科學最后成為人類知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實在令人驚嘆。在這個領域中,迷信的思想已經式微,被嚴謹和研究所取代。正如通過21點和賭馬致富的比爾·本特所說的,并不是擁有街頭智慧的拉斯維加斯賭徒想出了一個系統。成功之所以到來,是因為用學術知識和新技術武裝的外來者走了進來,照亮了這片曾經幽暗的領域。
(作者為資深專業投資人士)
讀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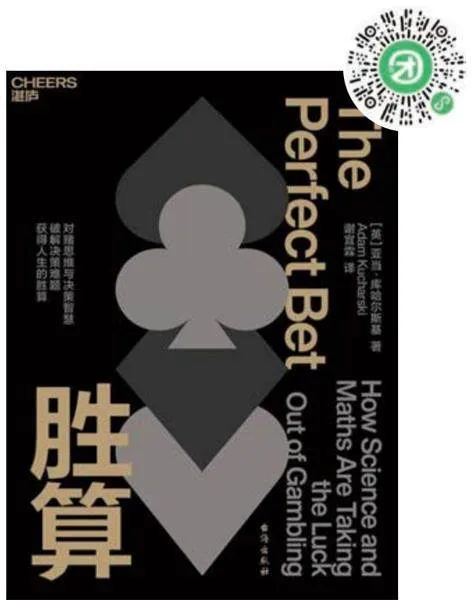
最優策略關注的并不是“如何贏得最多”,而是“如何輸得最少”。因為隨著時間推移,莊家和賭徒會逐漸掌握那些最知名的策略,結果就是很難從中賺到錢了。
人們傾向于用“經驗加權吸引”來學會策略,也就是更偏好那些過去成功過的行為。而最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研究被其他人忽略的人。
所以,有的人經常選擇“反人類”的策略,而不是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更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