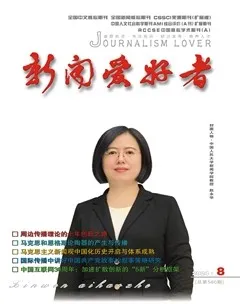集體生活的“第三空間”:大學生宿舍短視頻的創作邏輯與價值
【摘要】宿舍生活短視頻融合了集體生活的真實場所與虛擬圖景,是索亞所言的“第三空間”的典型代表,也成為探析人與媒介技術、空間之間關系的獨特切口。研究發現,狹小空間中的“集體感”成為宿舍空間感知的常態,為了記錄生活、娛樂展演、加強社交,學生們通過拍攝短視頻這一方式,實現了身心空間的賽博舒展、空間記憶的媒介重塑、社交空間的云端延伸。短視頻成為主體再造集體生活的“補償性空間”,與現實空間交織融合,但其中仍然存在著制度、文化、市場三者間的話語沖突,需要在發展改造中堅持“人本邏輯”,進而消除空間中人的異化狀態。
【關鍵詞】集體宿舍;短視頻;第三空間;人本空間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空間形式,大學生宿舍空間及其背后的集體生活對以青年為主體的高校學生而言影響廣泛且深刻。在短視頻等新媒介的介入下,大學生在宿舍中的活動形式更為豐富,對集體生活的意義感知逐漸多元化個性化,但也面臨著如隱私泄露、價值錯位等風險。因此,新媒體環境下對宿舍空間的研究不僅關涉我國高校立德樹人的功能在空間設計層面的效能檢驗,也能夠助益其對空間權力運作、使用者與空間之間互動關系的理解,進而更好地管理集體空間,以媒介技術賦能空間設計管理,促進高校學生的全面發展。
一、作為“第三空間”的短視頻與宿舍媒介實踐
隨著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對空間社會屬性的發掘與拓展,空間的社會意味、社會關系逐漸擺脫被遮蔽、被忽視的境況。愛德華·索亞結合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組合、福柯的“權力空間”理論等,提出了“第三空間”理論。索亞認為:第一層空間是能夠通過環境、位置、標識等具身化把握的物質空間;第二層空間是通過意義圖像、話語建構的被編碼的構想空間;第三層空間則包容了真實與想象、物質與精神,融合了主導話語體系與邊緣話語體系,既是現代生活權力、觀念多元異質的開放性空間,也是一種發現了“他者”的關懷性空間。[1]
進入數字時代,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相互嵌合,數字技術以其中介性改變著人們對空間的感知與體驗。[2]短視頻作為一種開放的、去中心化的異質空間,其生產主體的多元和拍攝視角的微觀,能夠為以往空間的宏觀敘事和單一焦點提供有益的補充,并憑借其低使用門檻使人—媒介—空間三方有機鏈接、深度嵌合,進一步推動了空間權力向草根大眾的轉移。這與“第三空間”理論的“他者化——第三化”切入視角相契合,即對邊緣化立場的堅持和打破二元論的思維方式,將空間在解構中重構,從而讓空間走向無限開放。[3]
以往對集體宿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教育管理[4]、文化氛圍[5]、人際關系[6]等,對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且廣泛存在的空間背后的媒介化進程鮮有關注。僅有的部分研究,大多也集中于對宿舍的信息化改造或數字平臺建設[7]等。一方面仍然是基于技術擴散視角,聚焦學校管理部門這一權力主體對宿舍的技術改造,而忽視了宿舍居住者在協調“自身—空間—技術”三者時的能動性和源需求;另一方面常常將宿舍作為形象宣傳、思想教育的“靜止”的空間形態,對宿舍內部的日常化媒介實踐與宿舍空間之間的復雜關系關注不多。因此,本研究通過對10名宿舍生活短視頻創作者進行訪談,包括男性受訪者5名(M1-M5),女性受訪者5名(F1-F5),并結合短視頻平臺中熱門大學生宿舍生活短視頻的內容主題、評論等,從宿舍這一個體生活與集體管理的典型空間交界處出發,探析短視頻作為“第三空間”為創作者帶來的空間賦權與認知變遷。
二、功能缺位與需求補償:宿舍生活感知與短視頻創作動因
受限于有限的空間資源和大量的學生人數,除卻部分學校宿舍外,宿舍內外空間帶給居住者的第一感受大多是狹小和封閉。同時,集體宿舍配套的管理制度代表著空間背后的權力屬性,在給予學生有限度的自由時也以多種方式監督學生們的日常行為,“集體感”從而成為這一空間場域中不言自明的生活潛意識,規訓學生顧及他人感受、約束自身行為。宿舍空間的物理屬性和制度屬性使學生的空間需求無法充分實現,促使他們通過短視頻實現對實體空間功能的補足。對于學生而言,空間功能的缺失致使他們產生創作宿舍生活短視頻的多種動因,這些動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種。
(一)生活記錄: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媒介鏈接
進入大學階段后,校園制度對學生個人時空的管理逐漸松弛,不再以集約型、全時型方式把控包括住校生在內的學生群體的生活空間。但對于住校生而言,由于課業瑣事、有限精力等的限制,宿舍空間仍是他們展開休憩娛樂活動的主要場所。個人活動和宿舍空間的高度結合使得他們逐漸意識到“宿舍那個床位是屬于自己的一個小窩”(受訪者F3),但圍繞專屬床位的“蝸居”仍然無法完全擺脫集體生活這一背景。在他們求學期間,日常生活中的見聞以及室友間發生的點點滴滴,早已融入他們的生命體驗之中,昭示著個體生命記憶與集體記憶在宿舍空間內的深度鏈接。通過對宿舍生活的視頻化記錄,空間的場所感也得以強化,個體實現了與空間及其代表的集體生活的精神聯系,進而加深了個體對集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二)娛樂展演:短視頻塑造理想化空間狀態
大學生宿舍內部幾乎不包含可供娛樂的空間和設備,由于天氣、距離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作為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交界地的集體宿舍就成為住校生釋放壓力、娛樂自我的主要場地。但受訪者M4同樣表示,“在宿舍的話,因為空間有限,而且有一些規章制度的設定,很多娛樂活動是很難展開的”,因此拍攝短視頻這種媒介化娛樂方式成為一種替代性選擇。在課程之余,演繹網絡熱梗、翻跳流行舞蹈等娛樂活動不僅讓個體得以從日常壓力中獲得短暫的喘息,也有利于形成宿舍內活躍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氛圍。同時,這種娛樂化的生活碎片經過技術加工、美化,形成一個個理想化的“空間—自我圖景”,在朋友圈、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的傳播進一步滿足了青年學生展現自我、貼近理想空間狀態的愿望。
(三)加強社交:空間內部關系的媒介化改良
空間中的社會關系受制于空間本身的設計邏輯,也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們對空間的認知與體驗。宿舍作為集體生活的實踐空間,需要每個人參與維系穩定、和諧的關系,但同居本身并不能直接確保良好社交關系的萌生與維持。正如受訪者F4所言,“(生活感受)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家的運氣……因為如果大家的課表不一致,就需要互相配合、互相遷就。如果大家都比較對這個事情上心的話,不管大家的安排多么復雜,都會相處得很好,如果都是我行我素的話,宿舍的氛圍肯定不會太好”。因此,媒介技術的介入形成了宿舍內一場“空間生產的儀式”,視頻創作者在室友們的參與互動中提供了相互磨合、深入理解的契機,從而提升空間內社交關系的活躍度和堅韌度。
三、短視頻“第三空間”對宿舍空間的功能補足
短視頻中的宿舍生活作為一種第三空間,是在第一空間(集體宿舍的物理實體)和第二空間(宿舍的空間感知與話語想象)的融合交織中生成,并通過將真實的空間狀態加以反映、制造對理想空間狀態的媒介想象[8],實現了住校生身心空間的舒展、空間記憶的存留以及社交關系的再造。
(一)身體空間的賽博舒展
身體是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的個體化空間,也是人的空間體驗的最基礎層次。[9]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和身體是同構的,因此它們追求共同的解放,從而消除空間對人的異化狀態。[10]
作為一種個人化的、邊界寬闊的空間形式,短視頻對他們進行了身心領域的雙重賦能,讓他們得以超越物理空間的限制,在空間的主體性改造與想象中獲得個體空間的舒展。一方面,視頻中的個性化表演讓他們需要改造物理空間,從而為身體行動提供充足場地,身體空間的伸展便順勢而為,這一過程是與他們常態化空間體驗相區別的;另一方面,他們也實現了心理空間的延伸和放松,超脫了單調的宿舍空間,平日積攢的生活壓力感得以釋放,在短視頻中擺脫了物理界限的束縛,制作、展現、反芻自身理想中的空間生存狀態。短視頻作為一種媒介空間,既成為學生“身體的延伸”,改造了他們的身體體驗,也給予了他們“情感的按摩”,實現了有限空間中的身心舒展。
(二)空間記憶的媒介重塑
宿舍不僅僅是可供休憩的居留點,也是承載學生日常生活實踐、孕育校園感情的獨特“地方”,是一個重要的“記憶場所”。通過拍攝短視頻這一集體化的媒介儀式,住校生們實現了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空間記憶的深度融合,凝聚了基于宿舍地緣和業緣的心理認同。對大學生而言,宿舍空間聯結了個人生活與校園經歷,以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嵌入達成了青春記憶與集體空間的捆綁鏈接。因此,空間中的日常起居被賦予了個體生命記憶的獨特價值,成為他們記錄生活故事、保留青春記憶的重要載體。
此外,集體記憶可以作為家園感的支柱[11]。于是與室友合拍成為大學生紀念友情、銘刻當下的重要方式,媒介化的空間記憶助力他們對宿舍這一群體性空間進行個性化的意義調適,也實現了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合流,強化了他們對集體生活的認同感。“我室友一直都挺支持我(拍短視頻)的,而且我們會覺得非常好玩,畢竟大家在學校的時光也就那么幾年。能碰到大家都感興趣的一件事情,不說所有人都參與進來,就是看著室友拍完之后再去看他們的作品,我就會覺得很開心”(受訪者M4)。
(三)社交空間的云端延伸
借助視頻合拍這一媒介化社交方式,住校生將宿舍空間轉化為共享的媒介儀式場。從具身共在到賽博共存,從身體親近到情感鏈接,合拍儀式的共同參與豐富和強化了實體空間內外的社交關系,凝聚了團體向心力和歸屬感。短視頻對宿舍社交空間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強化室友之間的關系,也具備將趣緣關系等納入社交范疇的可能性。例如,受訪者們可以將其他宿舍的好朋友一起合拍表演,他們上傳的宿舍短視頻也會獲得其他同學的稱贊和催更(受訪者F1)。
在短視頻這一碎片化空間中,傳統社會人際交往方式依據媒介邏輯而嬗變,制造出“陌生的親密人”這一新型社交關系[12],打破了院校、專業等交往限制。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中宿舍生活短視頻的走紅,激發了學生群體對自己宿舍居住經歷的回憶和互動,凝結出云端共生的“想象宿舍共同體”,讓跨越實體和抽象界限的“超時空同居”得以實現。
四、結語:第三空間的人性化改造
作為“第三空間”的宿舍生活短視頻補償了大學生對空間功能的需求,重塑了他們與空間的交互關系,并導致空間的主導意識形態既實現了延伸也遭遇了挑戰。一方面,學生通過拍攝短視頻豐富了自身的居住體驗,對物理空間和觀念空間實現了功能和意義的再造;另一方面,短視頻空間的生成與可見,仍然要在物質基礎和價值觀念兩方面受到集體宿舍空間意識形態的制約。即便在較為私人化和個體化的媒介空間內,由于宿舍內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曖昧關系,集體宿舍的數字化空間無法脫離保持集體意識這一空間意識形態的管控。
同時,短視頻這一媒介技術并非完全價值無涉的,若以簡單的反抗空間主導意識形態的角度去一味頌揚短視頻帶來的效用,不僅可能低估了集體宿舍空間本身帶來的正面效應和技術資本主義等對第三空間形態的負面導向,也會忽視空間中的弱勢群體自身的多元體驗和能動實踐。宿舍這一空間單元對學生的身心健康和自我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需要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堅持空間規劃的“人本邏輯”[13],使虛實空間的設計與建構更好地滿足人的本真性和本質利益,打造更有益于人生存發展的“人本空間”。
[基金項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一般項目“新聞傳播學研究生人才培養的國際視野與新媒體路徑創新研究與實踐”(2021SJGLX086Y)]
參考文獻:
[1]張志慶,劉佳麗.愛德華·索亞第三空間理論的淵源與啟示[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12):14-20.
[2]徐迪.空間、感知與關系嵌入:論數字空間媒介化過程中的技術中介效應[J].新聞大學,2021(10):94-107+120-121.
[3]張志慶,劉佳麗.愛德華·索亞第三空間理論的淵源與啟示[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12):14-20.
[4]李明善.高校學生宿舍集體建設的思考[J].學術界,2013(S1):193-195.
[5]馬倩.人學視域下大學生寢室場域文化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18.
[6]許傳新.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質量研究[J].當代青年研究,2005(4):6-9.
[7]劉合富,史永銀,江迎春,等.信息化2.0背景下高校智慧宿舍建設模式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2):218-223.
[8]張華.空間媒介再造城市意象:第三空間視野下的報刊亭[J].現代出版,2023(3):104-113.
[9]陳家熙,翁時秀,彭華.打工文學中的城市空間書寫:基于索亞“第三空間”的分析[J].熱帶地理,2018(5):629-640.
[10]邁克·費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現代主義與認同[M].楊渝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29.
[11]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4.
[12]李晶.第三空間視閾下移動短視頻的空間特征、建構邏輯與正義實現[J].當代電視,2021(12):4-9.
[13]劉偉.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城市化模式的“中國道路”:“資本邏輯”到“人本邏輯”空間重塑[J].新疆社會科學,2023(6):43-53.
作者簡介:方澤華,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鄭州 450001);王依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博士生(北京 100191)。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