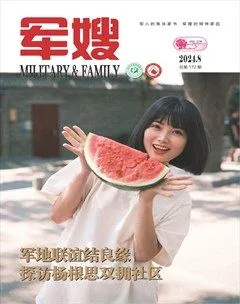接力等待
生在軍人家庭,都少不了等待。
當年,爺爺在空軍某部當飛行員,一年也回不了幾次家。奶奶在老家山東煙臺顧不過來4個孩子,就把4歲的爸爸送到遼寧大連的大爺爺(爺爺的哥哥)家。
爸爸想念自己的家,就故意惹大爺爺一家人生氣,希望他們把自己送回家,但一次次鬧騰,結果都沒能如愿。
一次,爸爸疊了一只小紙船放到海里,他想看看船會不會沉沒,如果不沉,他準備做一只更大的紙船,這樣就可以乘著船回家了。然而,紙船很快就沉沒了,他也放棄了這種天真的想法,轉而常常對著天空發呆,看到飛機飛過,就覺得有可能是爺爺來接他的。
1972年12月,爺爺因身體原因退役回了家,爸爸也結束了他的“外放”生涯。
與爺爺團聚9年后,17歲的爸爸入伍到沿海某陸軍部隊。
他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干,與媽媽相識、相戀、結婚,后來有了我。
1992年,3歲的我跟著媽媽隨軍,與爸爸實現了團聚。
記憶中,爸爸常常忙得不著家。1994年夏,媽媽因突發腰椎間盤突出摔倒了。那時,爸爸在外參加演習,無法趕回家。媽媽強忍著病痛站起來,繼續照顧著我的飲食起居。后來實在撐不住了,才把我暫時托付給對門阿姨,又請來了遠在老家的爺爺、奶奶。
安頓好一切后,媽媽住進了醫院。幾天后,我突然想起好長時間沒看見媽媽了,便開始哭鬧……盡管爺爺、奶奶盡力向我解釋,媽媽只是住院幾天,但我不懂“住院”的意思,只覺得爸爸天天不在家,現在連媽媽也不見了,自己成了沒人要的“野孩子”,越想越委屈,越哭越厲害。
等爸爸演習歸來,媽媽也康復出院了。雖然爸爸、媽媽輪流哄我,說著他們有多愛我,但我還是不買賬,心里怨恨爸爸多一些,怨他不和我聯系,怨他“偷跑”了好長時間,甚至連媽媽生病也不管不顧……
1995年初,爸爸被安排到湖北武漢某軍校學習。那段時間,每天睡醒睜眼就能看到爸爸,成了我的一個盼想,但每次醒來,看到的只有他的照片。聽到家里的電話響起,我就會問媽媽是不是爸爸打來的,錯過了爸爸的電話,我還會跟媽媽鬧情緒。

7月的一個清晨,我還沒從睡夢中完全醒過來,就聽見客廳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我飛奔出去,發現還果真是爸爸!我又驚又喜,恨不得蹦到他身上。爸爸從行李箱里掏出了一套《貓和老鼠》光盤——是那個年代很難買到的動畫片。爸爸還給我買了當年十分流行的自動鉛筆、自動鉛筆盒……他似乎想把一切的好東西都買給我。
暑期結束,爸爸回學校前,教會了我“倒計時”,他說,過去一天你就在日歷上劃掉一天。我按照爸爸說的去做,等待的日子果然變得不再那么難熬。
1999年9月,爸爸轉業了,我們一家回到了煙臺老家。
我長大后,未能如愿參軍,后來,便嫁給了軍人,成了一名軍嫂。2019年6月,我們有了一個女兒。
女兒長大一些,可以和丈夫視頻了。因為總是見不到他,女兒經常認不出來他,女兒總會偷偷問我:“媽媽,這是爸爸嗎?”
有時網絡信號不好,視頻會卡頓,當視頻里的愛人不動時,女兒就說:“媽媽,這是一個假爸爸。”
女兒再大一些,每次和丈夫視頻時總會問一句:“爸爸,你什么時候回來啊?”
女兒雖然還不明白什么是等待,但她也會在丈夫不回家或突然歸隊時鬧脾氣。每次看到這樣的場景,我就莫名地想笑,就像看到了當年的自己。
有人說,聽到風吹過峽谷,才知道那就是風;看過白云浮過山脈,才知道那就是云。而對我來說,只有經歷過等待,才知道什么是來自軍人家庭的最深切的期盼。
(作者單位:山東省煙臺市牟平區文化街道楊子榮社區)
實習編輯/劉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