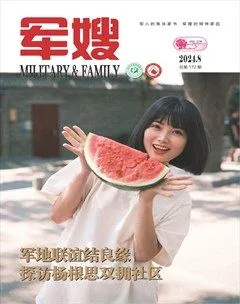一路軍歌嘹亮
“咱當兵的人,有啥不一樣……”周末途經家屬院,營區廣播里傳出了嘹亮的歌聲,幾個孩子一邊跟著哼唱,一邊收集著掉落在地上的槐花。
似曾相識的畫面,讓我仿佛回到以前。
6歲那年,我跟隨母親奔赴新疆葉城零公里。那是我第一次走近這個坐落于葉爾羌河旁、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端的小城。作為219國道的起點,這里既是起點亦是歸宿,而對長年穿行在新藏線上的汽車兵來講,零公里更是無人區與繁華小鎮的銜接點。
但于我而言,對零公里的記憶更多地停留在大院柏油路面上車輛碾過的黑色印痕,炎炎夏日午睡時院外傳來的“嗒嗒”馬蹄聲,以及從小聽到大、耳熟能詳的一首首軍歌……
放學后,我們大院里的孩子喜歡聚在荷花池邊玩耍。因荷花池靠近連隊,官兵的歌聲總會清晰地傳入耳中,聲音很洪亮,歌詞卻很難辨別。我們總是圍攏在一起討論,揣摩著歌里唱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們唱的是‘咱當兵的人,就是不一樣’。”
“不對,不對,他們唱的是‘咱當兵的人,有啥不一樣’。”
“你們說的都不對,他們好像唱的是‘說不一樣,其實也一樣’……”
那到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呢?我們爭論不休,也沒有結果。
通常每次討論,都不了了之,到最后大家便是不自覺地跟著官兵哼唱起來,也不管對錯,誰的嗓門高過對方便算勝利。
直到我考入軍校,才發現那時的我們純粹瞎蒙瞎碰,領會錯了歌詞。
但教官說,軍歌本身就是為提振士氣,那我們當時也算歪打正著,至少在吼這一點上下足了功夫。
2017年軍校畢業后,我再次回到熟悉的邊疆。我們單位是紅歌《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的發源地,小時候我也曾聽過這首軍歌,只是并不了解歌詞背后蘊含的真正深意。
到單位不久,我接手了團史館講解任務。我覺得,人對事物的銘記往往來自對歷史的追溯。起初,團史館幾十頁的講解稿,密密麻麻的數字年份,反復堆疊的背景一度讓我無從下手。那時候,唯有史館里循環播放的《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陪伴我至一個個深夜。
記得每次疲憊時,我會坐在地上不自覺地隨曲反復哼唱,躁動的心會很快沉靜下來,再回頭看看展板上的歌曲背景,枯燥的講解仿佛突然靈動起來——關于這首歌的歷史,成為團史館里我最愛講解的部分。
后來,我有幸前往紅歌誕生地——阿拉馬力邊防連。當我聽見20世紀60年代唱片中回蕩出略帶雜音的歌聲,老一輩革命者戰天斗地、艱苦奮斗的畫面猶在眼前,他們樂觀向上、鐵心戍邊,為一代代邊防官兵建起榜樣。
“祖國要我守邊卡,扛起槍桿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發……”廣播里的歌聲更加嘹亮,我不禁隨著節奏加快了步伐……
(作者單位:69348部隊)
編輯/吳萍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