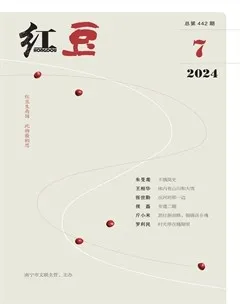由詩(shī)歌開啟的修行之路
在詩(shī)歌界,詩(shī)人簡(jiǎn)明是一個(gè)提燈的人,他的燈照亮過許多人,詩(shī)人王相華便是其中之一。他稱簡(jiǎn)明為恩師,顯然這不僅是出于感恩,更是一個(gè)詩(shī)人對(duì)待自己內(nèi)心標(biāo)桿的一種態(tài)度。簡(jiǎn)明曾言:“媚俗是人性中最難抵御的物質(zhì)動(dòng)力,而詩(shī)意則是人性中最難洞察的精神閃念,它們分別解構(gòu)人性的兩端。”
從知人論世的角度看,王相華的詩(shī)歌文本恰恰印證了他的藝術(shù)人生。評(píng)論家陳超先生強(qiáng)調(diào)“生命詩(shī)學(xué)”的重要性,從王相華的文本以及他辛苦輾轉(zhuǎn)與漂泊的人生中也能感覺到這一點(diǎn)。他之所以有如此詩(shī)意的生命狀態(tài),是因?yàn)椤霸?shī)歌是他真正的動(dòng)力,也是他最重要的行李”。這樣修行式的日常,使得他在世俗空間里保持一份鎮(zhèn)定,在自我加持的道路上,也就逐漸地“活在了時(shí)間之外”。這是一個(gè)艱難的過程,是一個(gè)“沉舟側(cè)畔千帆過”的過程,如今人到中年的他,也可以說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了。
但那種對(duì)生命的熱忱一直激勵(lì)著他、鼓舞著他。他以詩(shī)學(xué)與佛學(xué)的雙重努力,構(gòu)建出了一個(gè)相對(duì)澄明的世界,尤其是他以民間的方式創(chuàng)辦了“新詩(shī)高地”這一平臺(tái)。這是一個(gè)陣地,更是一個(gè)詩(shī)學(xué)交流與切磋的“道場(chǎng)”,正是這一空間的存在,使得日常忙碌于生意的王相華相對(duì)就有了“另外一個(gè)空間”,這讓他的精神世界有了彈性與張力。這也成全了他,使得他找到了一種意義。這個(gè)意義的生成,就王相華的精神成長(zhǎng)來講,倘若沒有忍耐,沒有加持,到頭來頑石仍是頑石,永遠(yuǎn)成不了通靈寶玉。
審視王相華的長(zhǎng)詩(shī)《體內(nèi)有山川和大雪》,可以體會(huì)到一個(gè)詩(shī)人的生命輾轉(zhuǎn)與精神歷險(xiǎn)。王相華這一組詩(shī)的書寫,從形式上來講,讓我想起了詩(shī)佛王維在輞川寫下的二十首詩(shī)。當(dāng)然這只是一種聯(lián)想,從文本的追求來講,王相華顯然對(duì)“古典主義”是警惕的,他是堅(jiān)定的現(xiàn)代詩(shī)的追求者,從“新詩(shī)高地”所呈現(xiàn)的文本風(fēng)貌大抵可窺之。王維在輞川的生活是帶有一種隱居意味的,雖屬于山水田園詩(shī),但他與柳宗元不同,他是一如陶潛隱入桃花源。盡管陶潛也曾“猛志固常在”,王維也有“萬戶傷心生野煙”,但他們終究還是“隱”了。作為新時(shí)代詩(shī)人的王相華,我們看到的是他的“與時(shí)俱進(jìn)”,是在“儒、釋、道”之間的一種平衡,是做到了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人。這對(duì)于一個(gè)詩(shī)人來講是寶貴的,無論多少磨難與挫折,始終以曠達(dá)之心活著,心中裝著人,裝著人間疾苦,這樣生命就不會(huì)枯,語(yǔ)言也就不會(huì)枯。我想王相華是悟到了這一高度,所以他從故鄉(xiāng)日照到天津,又從天津回到了故鄉(xiāng)日照。他的生命在精神的太陽(yáng)照耀下,充滿了進(jìn)取,這也應(yīng)和了簡(jiǎn)明先生對(duì)他的引領(lǐng)與告誡。
“行走在山水之間,離開煙火與喧囂/就只剩下鳥鳴和流水/皺紋深藏時(shí)間擦傷的痕跡,終會(huì)慢慢修復(fù)/太陽(yáng)和月亮——/是我無數(shù)次輪轉(zhuǎn)中唯一的眼睛”。作為詩(shī)人,他不是“躲進(jìn)小樓成一統(tǒng)”,而是以向外行走的方式完成內(nèi)在的覺醒,當(dāng)然這是功課,是要面臨悖論與掙扎的。
“我假裝對(duì)陌生的人和事/提起新生的喜悅,打招呼,寒暄/一切都順理成章/而我的腳步跟著心念游離在荒野”,這寫的是孤獨(dú),是詩(shī)人直面內(nèi)心世界的一次叩問。在世俗世界,太多的名利裹挾著我們每一個(gè)人,如何在這一維度突圍?
就內(nèi)省這一點(diǎn)來講,王相華是做了很深的功課的。他在接受詩(shī)人余兮的訪談時(shí)曾說,他讀書比較雜,更多的是傳統(tǒng)文化之類的經(jīng)典。
“經(jīng)歷知天命之年,我還是愿意/相信。順應(yīng)大自然界的規(guī)律,被堅(jiān)冰/封存的天性,在雷電/爆裂中凸顯它們本有的模樣……”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王相華深受孔夫子的影響。
“連綿起伏的群山,無法看到距離/還有多遠(yuǎn),一些高峰隱匿在天上/云霧是隔開視線的利刃,我的想象力……”這是“進(jìn)山”了,是一種行者般的主動(dòng)面對(duì),讓自己陷入一種空茫。在空茫中,讓自己練習(xí)安靜。這一過程讓自己有了“自由選擇新的落腳點(diǎn)和高度”的可能,于是,“我開始脫離一些依附在萬物上的/念頭。在光與光的重疊中/退出迷失的劇場(chǎng)”。這是一種孤絕之勇。“進(jìn)”與“退”,不僅僅考驗(yàn)勇氣與意志,更考驗(yàn)一個(gè)人的理性,而理性恰恰是一個(gè)人抵達(dá)智慧與圓融的必要條件。正是一種不畏難的意志使得詩(shī)人持續(xù)精進(jìn),詩(shī)人把自己比喻為“蟲蛹”,將化蛹為蝶。
也正是這樣的意識(shí),詩(shī)人的心緒與情感持續(xù)深入到新的境地。
“……習(xí)慣性反芻/那些憂傷且?guī)в行谩T谛募獾奈璧?以及異鄉(xiāng)公園里,一座假山之間的池塘/落在晃動(dòng)的蓮蓬里。我有大睡五百年的想法”。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我愿化身石橋”,是甘心櫛風(fēng)沐雨,愿意去磨煉。每個(gè)人心里都有一只欲望的猛虎,如何馴服它,如何最終抵達(dá)靈山,任重而道遠(yuǎn)。王相華這一組長(zhǎng)詩(shī)《體內(nèi)有山川和大雪》所呈現(xiàn)的生命狀態(tài),何嘗不是一種艱難的心路歷程?從這一角度理解,詩(shī)人寫詩(shī)的過程,就是“見自我,見天地,見眾生”的過程。這種慈悲,使詩(shī)人對(duì)自己的詩(shī)學(xué)與文本建設(shè)有著清晰的目標(biāo)。他說:“一個(gè)真正的詩(shī)人,對(duì)所有藝術(shù)種類都要保持敬畏和起碼的尊重,萬法不離自性,一切鏡像的顯現(xiàn)都是內(nèi)心返照的影子。隨著自己的修為不斷提升,詩(shī)歌的意境也會(huì)隨著心境的提升而抵達(dá)更高的藝術(shù)領(lǐng)地。”
“我像一塊石頭,不能告訴你,內(nèi)心是一片/空曠的田野,在冬天開花,在夏天也會(huì)結(jié)冰/事實(shí)是在你對(duì)我產(chǎn)生疑惑之前,我就變成/你眼中無情又與現(xiàn)實(shí)格格不入的人”。怎么辦?必須“駕長(zhǎng)車,踏破賀蘭山缺”,必須再次出發(fā),必須重啟“歸去來兮”,必須如屈原一樣“涉江”,必須讓自己“從遙遠(yuǎn)年輪中找到刻在靈魂上的名字/而大片的葉子正快速生長(zhǎng)/像多年前的大雪,一片片落在視線之外/落在彎曲的山脊上”。這也就是說,人世間的善惡曾經(jīng)讓詩(shī)人驚魂,讓靈魂不安,而這種不安,磨煉了詩(shī)人,使詩(shī)人的內(nèi)心在矛盾的統(tǒng)一中獲得了短暫的安定。有了這樣的安定,“當(dāng)安靜成了一種狀態(tài),山間每一棵草木/都懷有善意”。這是詩(shī)人與外部世界達(dá)成的一次和諧,有了這種心境,詩(shī)人觀察外物的心情也隨之變化,我們說“境由心造”,也可如是觀。此時(shí)詩(shī)人的狀態(tài)是“日子平淡如水,連大海也收斂了不少脾氣”。我們寫詩(shī)也好,做人也罷,最重要的是要對(duì)自己心靈中那些習(xí)以為常的陋習(xí)進(jìn)行甄別并修正,用一種“暮鼓晨鐘”的力量來撞擊我們的“心門”:“一次次引渡三十年前的大雪,或者以颶風(fēng)/壓制無聲的暗涌。面對(duì)動(dòng)蕩/我沒有退縮半步,安靜等待著/一場(chǎng)風(fēng)暴。在定慧中恢復(fù)如初”。
人生幾度秋涼,遭遇困境,突破困境,就可能柳暗花明。到第九節(jié),詩(shī)人有了一次總結(jié):“從體內(nèi)退到現(xiàn)實(shí)的畫面,一切/就像從未發(fā)生過一樣/就像是我們,剛從大夢(mèng)里蘇醒/夢(mèng)里夢(mèng)外都是真實(shí)的觸感/眼角濕潤(rùn),調(diào)整的思緒由此進(jìn)入……”詩(shī)人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大夢(mèng)”,而“大夢(mèng)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嗎?事實(shí)上,詩(shī)人沒有落入那種窠臼,而是更加小心謹(jǐn)慎、更加客觀地看待自身:“那些矗立的高山更高,海水更深/人性的正反、身份的貴賤都在我之上/坐在人間的低處,我比二十一克更輕”。這種輕,不是司馬遷那種“輕于鴻毛”的感嘆,而是再次把自己置于天地之間、萬物之中,以眾生平等的心態(tài)來面對(duì)世間一切:“我分明聽見,那些生命微弱的回聲/從某個(gè)深夜到黎明,到一個(gè)未知的覺醒/我們有共同的宿命,和對(duì)生命的認(rèn)知力/那些探索的、基于哲學(xué)的命題/似乎有了模糊的答案”。這“玄念”來自感念,來自理念,來自風(fēng)餐露宿,來自行走與慈悲。
但這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我們絕不能止于發(fā)愿,而是要以向上的精神來強(qiáng)健自己。空,絕不意味著虛無與頹廢,恰恰相反,只有“舍”而后“得”才可能抵達(dá)澄明之境。詩(shī)人在第十一節(jié)中這樣表達(dá):“誰又不是在塵世的路途中/千錘百煉成鐵成鋼?/才相信,那些生活中假裝堅(jiān)強(qiáng)的人/那些沖破防線、自行消解的事物/背負(fù)一座又一座高峰”。有所“負(fù)重”,讓詩(shī)人再次走進(jìn)現(xiàn)實(shí)來度量自己,這種從“自然”又返回“樊籠”的狀態(tài),是反向于陶淵明的,因?yàn)樵?shī)人坦陳:“我們終究只是凡人,不能通過/沒有證悟的詩(shī)句,尋求到/一個(gè)或兩個(gè)詞性指向的明月”。這是詩(shī)人真正的證悟與回歸。
正是有了從第一節(jié)到第十四節(jié)的“艱辛”歷程,山高路遠(yuǎn)也好,峰回路轉(zhuǎn)也罷,詩(shī)人始終以一顆虔誠(chéng)而活潑的心,真正直面世間種種,“我也終于明白/這遙遠(yuǎn)路途和路途中經(jīng)歷的事物不過是/早就在未出生前勾勒出/苦樂的劇本,和那些透過磨礪/擦亮我手持的利刃……在山川與大雪中/打開最初種植在人間/千年的菩提”。這一“明白”,讓我們感慨,讓我們熱淚盈眶,我們?yōu)樵?shī)人深深祝福的同時(shí),也提醒自己要直面內(nèi)心的困境,不斷超越自我、超越時(shí)間,讓自己成為一條流動(dòng)的精神之河。這樣,我們才可能讓“體內(nèi)的山川和大雪”成為文明意義上的永恒風(fēng)景。
【作者簡(jiǎn)介】古心,本名沈世坤,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閔行區(qū)作家協(xié)會(huì)文學(xué)評(píng)論組組長(zhǎng),著有詩(shī)集《世界一幅水墨模樣》《如果不曾相見》,散文集《相逢不語(yǔ)》《在文字里與你相逢》,評(píng)論集《沉吟與微享》《閱讀無韁》等。
責(zé)任編輯 梁樂欣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