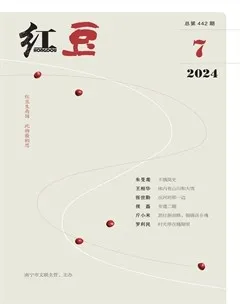兩幅簡筆畫
1
人民路上有好幾家修腳店,室內布置大同小異,靠一邊墻放幾張可以調節升降的修腳椅,對面墻上掛著密密麻麻的錦旗。王一刀修腳店有一點兒與眾不同,室內沒有錦旗,在偌大的一面墻上只掛了兩個小小的畫框,里面裝裱著A4復印紙。畫框玻璃映著光,像兩只睜開的眼睛,常常引起顧客的注意。紙上只簡單地畫了幾筆,有好奇的顧客就問王寶忠:“這是不是你家孩子的簡筆畫?”王寶忠話少,只是習慣性地抬起修腳刀一樣瘦削的下巴咧嘴笑笑。他一咧嘴,臉上便出現兩條大弧線,像撇開的括號。王寶忠從不對顧客說這兩幅簡筆畫是丈母娘的遺書。
2
王寶忠的丈母娘患有糖尿病,退休后視力急速下降,尤其是左眼,看啥都重影。她的大兒子李青松說:“那好,數錢一張變成兩張。”
李青萍帶母親到醫院檢查,發現是白內障,需要做微創手術。李青松是一家國企的副總,講話時習慣左手叉腰,右手高高舉起,幾根手指像鳥喙一樣啄著空氣,他說:“一大把年紀,房子有你住的,退休金每月按時打到你的賬上,又有兒有女。放著福氣不享,炒什么股票?天天盯著電腦,眼睛不壞才怪。”
手術安排在晚上。李青松說晚上有個會,不管幾點鐘做完,打個電話他開車來接。李青萍說:“哥,你去忙,別耽誤了工作,這里有我和寶忠呢。”
做罷手術已經是半夜十一點了,丈母娘讓王寶忠給李青松打電話。王寶忠說:“我們打的士回吧。”丈母娘說:“為什么要打的士?你給青松打電話。”王寶忠就撥打了李青松的電話,按了免提。電話里傳出李青松的聲音:“寶忠啊,你看看這都啥時候了,你就不會打個的士?有我開車跑過去這工夫,你打個的士早就把被窩焐熱了,是不是?媽老糊涂了,是個人都會算賬,打的士多省事。我明天上午有個會,你辛苦了。”
王寶忠攙扶著丈母娘往外走。出了病房大樓,他們忍不住縮了縮脖子。風從耳邊吹過的聲音,就像大人給孩子把尿時嘴里發出的噓噓聲,灰色的塑料袋像鳥一樣在空中盤旋,樹葉在腳下翻滾的聲音,和在鐵鍋里炒菜的刺啦聲一樣。王寶忠趕忙脫下外套給丈母娘披上。丈母娘左眼蒙著紗布,此刻右眼也閉上了,耳朵也閉上了,嘴巴也閉上了。
王寶忠聽見丈母娘呼呼的出氣聲和半夜的風聲一樣急促。
3
那天早晨,丈母娘站在床邊時,感覺室內的物品像全有了生命一樣晃動起來,在倒下去的那一刻她抓起了床頭的手機。
重癥監護室外,李青松的臉擰得像包子褶兒。他一邊舉起右手敲擊空氣,一邊痛心疾首地說:“那些教授博士經濟學家炒股都虧,她一個只讀過高中的普通人炒什么股票!把那點兒積蓄存在銀行吃利息不好嗎?留給兒子孫子不好嗎?請個保姆享清福不好嗎?”李青萍說:“媽還不是想多賺一些錢補貼兒女?她又能花多少?”李青松說:“問題是現在不僅僅虧了錢,人也中風了,開顱手術就得一大筆費用,醫生說她以后離不了人伺候。你們有沒有聽說過,一人中風,全家發瘋!她會拖累一家人的,最終結局是人財兩空。”
丈母娘從重癥監護室轉到普通病房。醫生反復強調:“病人這段時間處在昏迷狀態,至少得兩三個人輪流看護,不超過兩個小時就得喊醒一次,多和她說說話。她雖然不能說話,但是能聽見。”李青萍請了一個有經驗的護工,給母親抽痰、翻身、喂流食、換護墊。護工說:“我一個人是看不過來的,每晚總得打個盹睡個覺。你們再雇個護工吧,兩個人可以輪換。”李青松把大伙兒叫到走廊盡頭,說開個家庭會討論一下。李青萍說:“你是大哥你拿主意。”李青松掃了大伙兒一眼,說:“雇八個護工都抵不上一個親人,我們暫時只雇一個護工,由我們幾個輪流排班給護工換換手。我是老大,我排第一個晚上,青萍排第二個晚上,青海排第三個晚上。”李青萍說:“還有寶忠。多一個人多一份力。”王寶忠咧嘴點點頭。
在第四個晚上,王寶忠讓護工先睡。護工說:“我這些年照看的病人,啥樣的家庭啥樣的人都見過,你這樣的女婿比兒子還孝順。”王寶忠咧咧嘴說:“哪兒有兒子不孝順的?”護工拍了一下大腿說:“你們老大就不如你。你抓著丈母娘的手不停地和她說話。他一直待在走廊連病床都不碰一下。天擦黑他就走了。”王寶忠說話不會拐彎,見到李青松就直接問:“你值班時咋不在醫院睡覺?”李青松背著雙手,說:“有一個專業的護工在這里,抽痰、翻身什么的我都不會做,還有必要守著嗎?再說了,我有高血壓,不能熬夜。媽中風后肯定偏癱,她生命已經倒計時了,如果把一個好端端的人也拖累得偏癱了,是不是不明智?”王寶忠像剛被撈出水的魚一樣張著嘴巴,不知道說什么好。
丈母娘蘇醒后脫離了危險期。李青松走進醫院時眉毛總是揪成疙瘩,埋怨多,他每到醫院站幾分鐘就匆忙離去。老三李青海在另外一座城市上班,隔半個月回來探望一次。
為了緩解呼吸困難,醫生給丈母娘做了氣管切開術,喉嚨外面插著導管。她想講話時,嘴唇像喇叭一樣張開著,含混不清的聲音像拉風箱一樣從導管里呼呼竄出來,而且不斷被痰堵塞。醫生說:“病人迫切想講話,你們可以讓她寫字,她右手能動彈。”王寶忠買了一包A4復印紙和一個板夾。當一串呼呼的聲音掃落葉一樣跑出來時,他趕忙把板夾舉到丈母娘面前,將圓珠筆塞到她手里。
丈母娘每天都寫,她有一肚子的話要急著說出來。她寫的每一個字都四分五裂,醉漢一樣東倒西歪,而且忽大忽小比例失調,往往三五個字就把一張紙寫廢。她寫罷了,便眼巴巴地望著床前的親人,期待他們能夠看懂。有的字大家能看懂,有的字大家看不懂。大家像哄孩子一樣表現出足夠的耐心,同時又像小時候圍著媽媽猜謎語一樣,紛紛去揣摩她要表達的是什么意思。猜對了她就笑,猜錯了她就一臉的失落。
丈母娘在白紙上歪歪扭扭地寫了幾筆,是個散了架的 “月”字。丈母娘又在右下角畫了一條線,明顯力不從心,線像蚯蚓一樣彎彎曲曲。李青松說:“媽想問什么日子。”丈母娘的眼睛一動不動。李青萍說:“媽的意思是不是讓我們吃胖一些?她看我們都瘦了。”李青海勾著的腦袋像吊著個皮球,滿是內疚地說:“媽在責怪我半個月才來看她一次。”王寶忠接過板夾,顛來倒去琢磨了好一陣兒,說:“媽想寫個‘股’字,還操心股票呢。”李青松擰著眉毛盯了王寶忠好一陣,說:“真沒想到,還是寶忠聰明。”他把大伙兒叫到病房外面,強調為了媽的身體,都得裝糊涂,誰也不能和她提股票。
丈母娘在紙上畫了一根豎線,又在豎線上面打個叉,大家都猜不出她的意思。因為丈母娘重復畫了好幾次,大家就抓破腦殼使勁猜。李青松瞇著眼微微點著下巴說:“媽先畫一根豎線,再打個叉,意思是人終有一死,讓我們都看開一點兒。”李青海的后腦勺上像藏著蟲子,幾根指頭一直撓著,說:“媽畫的是射線,意思是兒女大了,不管朝哪個方向都是從母親身邊走出去的,不管走多遠都要回到母親身邊。”李青萍拍拍手說:“你們是不是想復雜了?媽畫的是一個‘米’字,可能就是餓了想吃米飯。等她能咀嚼了我給她蒸香噴噴的大米飯。”說罷又用胳膊肘磕磕王寶忠,王寶忠像睡著了突然被叫醒一樣身子一顫。幾個人都把目光聚攏到王寶忠瘦削的下巴上,他的嘴巴緊繃著一動不動,臉上的“梯田”難得平整。王寶忠搖搖頭,咧開嘴,臉上立即堆出“梯田”的斷層。李青松看著王寶忠的嘴巴像貝殼一樣打開又合上,說:“依我看只有你能懂。你再看看,媽到底想表達什么意思。”
丈母娘轉到康復科做了一個月的康復治療,順利取下了喉部的導管。雖然只能含混不清地說幾個字,但終究能通過嘴巴發音了。醫生說下一步要進行站立訓練,大致再過一個月就可以出院了。王寶忠湊近李青萍說:“醫保之外的醫療費、護工費你們三個兒女平攤了,但出院后的輪椅、拐棍、康復站立架、護理床怎么辦?”李青萍說:“虧你問得出口,這能要多少錢?”王寶忠說:“大大小小加起來得兩萬多元,我修一雙腳才五十元,這得我弓著腰低著頭修四百多雙腳,就算一天修十來個人,我也得修一兩個月。”李青萍說:“寶忠你想想,大頭我們都分擔了,這一點兒我和你就承擔不起嗎?”王寶忠的胳膊肘支在膝蓋上,雙手插入頭發里,甕聲甕氣地說:“老大、老三的條件都比我們好,他們都有單位。我們呢,關一天門就少一天的收入。我們擠一擠也不是承擔不起,關鍵是老大、老三連吭都不吭一聲。”李青萍說:“我們多承擔一點兒,哥哥弟弟也不是傻子,他們心里有數的。”王寶忠的喉結像顆珠子接連滾了幾下,說:“就怕他們一直當我是傻子。”
4
當丈母娘進行站立訓練時,大伙兒就開始商量出院后的事情。李青松抬手往后腦勺壓著頭發,說:“我想把媽接到我那兒,只是我要上班,文山會海的身不由己。”李青海用雙手撐著下巴,說:“如果不是要還房貸我就辭職回來專門照看媽。我在外地上班,鞭長莫及,平時顧及不了,我只能按比例分擔醫療費用,一分不會少。”李青萍左看看右看看,說:“我和寶忠開個修腳店,媽住院這幾個月老是關門,再這樣下去生意怕要黃了。”王寶忠的聲音勉強能讓大伙兒聽見,他說:“要不還是雇個護工?”李青松立馬揮揮手:“不行不行,后面又不需要抽痰呀翻身呀什么的,護工的工資高倒是小事情,問題在于請八個護工都抵不上一個親人。”李青萍嘆口氣,說:“唉,看來只有我的時間可以自己支配。”李青松的目光落在李青萍身上,說:“青萍是照看媽最合適的人選,女兒家心細。寶忠也心細又有力氣,可以幫忙挪動。”李青萍說:“這都沒有問題,只是我們住的是老式板樓沒有電梯,媽上下樓不方便。”李青松說:“這好辦呀,讓媽住你們店里,你們修腳店在馬路門面上,再方便不過了。”
回到店里,王寶忠問李青萍:“咱們店面就這么大,外面一間門臉當了操作間,里面一間當了倉庫兼廚房,你說咋拾掇?”李青萍說:“我們可以找房東說說,看能不能換一套大點兒的。”王寶忠說:“裝修費暫且不提,還得看房東同意不同意。”李青萍說:“我想請住建局的馬科長幫忙打個招呼,房東找她幫過忙,這個情面肯定會給的。”
馬科長是一個愛美的女人,她容忍不了右手大拇指上的那只灰指甲,平常在外面吃飯都不好意思伸筷子;左腳上也有一只灰指甲,夏天不敢穿涼鞋。經過幾個月的修護,手上的灰指甲好了,腳上的灰指甲還看不出痊愈的苗頭,她就有一些焦慮。王寶忠說:“腳指甲在封閉的環境里,活動量也沒有手指甲多,生長速度最多能達到手指甲的三分之一,就像樓房北面背陰的樹總是沒有南面向陽的樹長得高長得快,所以你要有足夠的耐心。”馬科長笑著點點頭:“你說得蠻有道理的。向陽的樹是親兒子,背陰的樹是女婿,從母親那里灑下來的陽光肯定是有區別的。”王寶忠咧咧嘴,說家家都是這樣。馬科長說:“也不一定家家都這樣,比如你這個當女婿的比當兒子的還孝順,將來丈母娘的遺產肯定會多分一些給你。”在馬科長的幫助下,房東答應給他們調了房子,新房子前面有一個門臉,后面有兩間倉庫。
在丈母娘出院之前,王寶忠幾乎花光了手頭的積蓄。他抓緊時間裝修好房子,在里間專門給丈母娘準備了臥室,并且配備了帶馬桶的衛生間,馬桶周邊還安裝了防滑扶手。在醫院待了幾個月的丈母娘坐上輪椅,被推進裝飾一新的修腳店時,抓了王寶忠的手,嘴唇像篩糠的篩子一樣抖動著。
5
轉眼之間,丈母娘出院快兩年了。鄰居們都熟悉這個規律,白天,只要有太陽王寶忠就會把丈母娘推出來曬曬。陽光特別強的時候,王寶忠會將輪椅掉個頭,讓丈母娘的后背曬得熱乎乎的。沒有顧客的時候,王寶忠會攙扶著丈母娘偏癱的左胳膊,讓丈母娘用右胳膊拄著拐棍一瘸一拐地練習走路。晚上,王寶忠和李青萍輪流住在店里照看她,給她麻木的肢體一遍遍按摩。
那天晚上打發走最后一個顧客,王寶忠拉下卷簾門,轉身給丈母娘端了盆熱水泡腳,給她按摩腳板。丈母娘說:“我有一個事情要你幫忙,不能告訴青萍他們幾個。現在我最信得過的也就你一個人了。我的銀行卡和筆記本電腦都鎖在抽屜里,得有人去拿過來。唉,就怪我,炒股票不僅虧了血本,還熬壞了身體,拖累了一大家子。如果我不炒股,這么多年省吃儉用攢下的存款也有七位數了。七位數的存款如果能回來,我會把這些錢都留給你和青萍,我那兩個兒子是白眼狼。可惜呀,這個世界上唯獨沒有后悔藥。”王寶忠說:“大哥、小弟都好著呢。”丈母娘苦笑著說:“好,好,好個屁!我住院時,青松他從來沒有像你一樣抓著我的手跟我說過一句話,我知道他嫌棄我。他每次到醫院都是做樣子給外人看的。”王寶忠不吱聲,挺了挺身子,背過兩只手捶自己的腰。丈母娘偏著腦袋說:“我知道你長年累月修腳落下了腰椎病、頸椎病,你不嫌這兒疼那兒疼,還要堅持每天給我泡腳按摩。青松他連個護工都不如,從來沒有站在床邊給我擦過一次口水、喂過一口飯、洗過一次腳,更沒有一個晚上照看我。我把他拉扯大了,他的良心卻讓狗給吃了。”王寶忠說:“大哥工作忙,他說只要有時間會開車帶你到廣場、江灘、公園玩呢。”丈母娘望著天花板,苦澀地笑著,說:“聽他的話明天就過年,他是八十歲的老頭兒叨九十斤的煙鍋——嘴勁。如果沒有青萍和你,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她說著說著眼角就混濁一片。
王寶忠從丈母娘那套房子里取了筆記本電腦,趁著李青萍下午到學校開家長會給證券公司的客戶經理打了電話。客戶經理很快就趕了過來。登錄交易賬戶后,客戶經理的嘴巴張得像個鵝蛋那么大,他問:“阿姨您到底有多長時間沒有登錄賬戶了?”丈母娘說:“有兩年多了,孩子們不讓我碰電腦。這不是突然想起來了嗎?我今晚脫了鞋子可能明早就穿不上了,得趕緊把這賬戶打理好了。”客戶經理說:“阿姨可別這樣說,您兒子這么孝心,您精神氣色也好著呢。我現在還要祝賀您,您是股神啊!瞧瞧您滿倉的這只新能源電池股票,雖然價格回調了百分之二十,但凈利潤還是足足翻了十倍。這真是一個典型的投資案例,對我啟發太大了!”客戶經理沉浸在一種莫名的興奮中,卻沒有看見她已經靠在輪椅上僵住不動了。王寶忠捧著丈母娘的臉頰,用右手大拇指掐她的人中,看她眼睛動了動、喘不過氣的樣子,趕忙扳過肩膀讓她靠在自己左胳膊上,右手攏成空心拳輕輕給她捶背。
客戶經理走后,丈母娘仍舊半張著嘴巴喘氣,她無法看清資產表里的數字,那行紅色的數字像針尖扎出的一排血點。她用顫顫巍巍的手指著屏幕,對王寶忠說:“你把表格中那些紅色的都讀給我聽。”王寶忠就把紅色的數字逐一讀給她聽。她垂下眼皮半張著嘴巴像睡著了似的,口水不斷溢出,王寶忠不停地抽出餐巾紙給她抹去吊在嘴角的黏液。丈母娘思索了很久才抬起眼皮,說:“我這些年投了一百多萬元,總是小賺大虧。那次遇到上千只股票連續跌停的大股災,我的賬戶一口氣虧得只剩七萬多元了。我就想黑夜的盡頭是曙光,挺過去了就是一片光明。我豁出去了,把最后的十萬元又加了進去。蒼天有眼,現在賬戶上有一百六十七萬元,算來算去我賺了幾十萬元。明天上午開市后,你按我說的全部清倉。”王寶忠問:“不瞞著了?”丈母娘說:“還有啥好瞞的?都瞞不了。”
第二天上午還沒有開市,丈母娘就指揮王寶忠打開交易軟件,以大幅低于昨天收盤的價格委托賣清倉。王寶忠看見丈母娘像打擺子一樣身子一顫一顫地抖著,怕她冷。丈母娘說:“冷啥?我是緊張。”股票在集合競價時間全部成交,減去當天股價下跌的金額以及手續費,凈資產還有一百六十多萬元。丈母娘猶如卸下了千斤重擔,繃緊的臉龐漸漸松弛,她說:“這筆錢明天就能轉到銀行卡上了,你們給我記住,以后誰都不能再碰股票。”
丈母娘午睡時,李青萍對王寶忠說:“媽悄悄給我說了她炒股賺錢了。她說先給我們十萬元補貼門面裝修,剩下的錢都存在卡上,以后看病不要兒女再出錢了。”王寶忠說:“她的錢她想咋花由她說了算。”李青萍笑著說:“媽像個孩子呢,她不好意思對你說。她說她前幾天剛給你說過一些話。”王寶忠說:“我只當她和我嘮閑嗑,不管她給錢不給錢,我該做啥還是做啥。”
一個星期天,兒女都到齊了。李青松說:“媽把我們都叫齊了,有啥要緊的事快點兒說,我下午還有個會,不能耽誤久了。”丈母娘坐在輪椅上緩慢地轉動腦袋環顧一圈,說:“我現在是過一天少一天,趁還能說話的時候得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了。我這幾十年摳摳搜搜省吃儉用,炒股票又踩了狗屎運,不僅回了本,還賺回了利息。現在我的銀行卡上有一百五十萬元,這個錢讓青萍暫時保管著,留著后面我看病買藥,以后不再讓你們出錢。哪一天我走了后,卡上剩下的錢由你們三家平分。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一個都不會偏袒。”李青松聽了母親的話立刻板了臉,他清了清嗓子上前一步抓了母親的胳膊說:“不是我這個當兒子的非要當著你的面批評你,你怎么能夠說出這種糊涂話?你這樣說不僅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也是對兒女不負責任。嗯,看看你現在身體多好,思路多清晰。如果不是坐在輪椅上,只看氣色,誰能相信你是一個中過風的病人?有很多醫學無法解釋的例子,一些病人心放寬了病不知不覺就好了,說不定就有啥奇跡在你身上發生。”丈母娘像是困了,頭靠著輪椅上的枕頭,瞇著眼睛,輕聲說:“那都是哄小孩兒的話。”李青海聽了母親的話像只受到驚嚇的兔子,身子猛抖一下,也上前一步抓住她的另一只胳膊,說:“大哥講得有道理,媽你真是想多了,話可不能像你那么說,你太悲觀了。那筆錢你該咋花就咋花,吃好喝好開心就好,你生病住院我們幾個還能不給你出錢呀?”李青萍抽出一張餐巾紙,擦去懸在母親嘴角的口水,說:“媽只是當面給哥哥、弟弟說清楚,讓我們都知道她是一碗水端平。”李青松說:“嗯嗯,理解理解,媽一向是公正無私的。”李青海看了哥哥一眼,又看了姐姐一眼,說:“媽生病住院啥時候我們幾個沒搶著拿錢?還用存一筆錢操心看病買藥嗎?如果說出去別人準會笑話我們這些當兒女的,好像我們不管老人家似的。依我看還不如早點兒把錢分了,我也能提前把房貸還清,沒了還貸壓力我就能辭職回來多陪陪媽。”李青松當即接過話茬兒說:“錢怎么著,這得尊重媽的意見。我們現在抓得嚴,我那個兒子成天吵著要買輛車我死活都沒有答應,一是手頭緊,二是怕惹眼。像我們當領導的總得防備著被別人說三道四,后面要買車了就說是奶奶送的。”
丈母娘“咔”了一聲,想咳嗽卻被噎住了,張大嘴巴憋出了眼淚。李青萍慌了手腳連聲喊王寶忠。王寶忠聽丈母娘和兒女們談錢的時候就悄悄地走出里間,走到店門口。他蹲下去把浸透了的磨刀石從水盆里撈起來,開始磨一把圓口片刀。刀刃在細膩的磨刀石上發出沙沙的聲音,像一群蠶在啃桑葉,刀柄映著室外斑駁的寒光。李青萍的臉像突然遭到擠壓一樣變了形,用哭腔說:“媽還沒有走呢,你們就想著怎么分錢。寶忠,寶忠,快來看看。”王寶忠把修腳刀扔在地上,站起來一邊撩起衣角擦手一邊快步跑進里間。他裹著一陣風走到輪椅前,熟練地扳過丈母娘的肩膀,舉起空心拳給她捶背。
丈母娘因為突然昏迷被緊急送進醫院。急診室的醫生說:“短暫性腦缺血,如果再嚴重一點兒可能引發二次腦卒中,會在原有基礎上增加新的癥狀,這兩天陪護人員很關鍵,病人身邊不能離人,萬萬不要麻痹大意。”
李青松對李青萍說:“別猶豫了,你趕緊雇個護工吧。”李青海撓著后腦勺說:“如果要排班的話,我可以退了火車票值一個夜班。最近單位考勤嚴得很,如果長期要排班的話,建議雇兩個護工。”李青萍說:“還是先雇一個護工,總得有親人守護在旁邊的。我們先排班,走一步看一步吧。”李青松舉起的手像啄木鳥,說:“嗯嗯,我看行,就按上次一二三四的順序。”
李青松和李青海走出病房后,王寶忠對李青萍嘀咕了一句:“分錢時按照三個,值班時咋就四個了?”李青萍瞅了他一眼:“都啥時候了你還說這些?”王寶忠嘟囔道:“我也就給你說說,該做啥我一點兒不會少做。”
丈母娘的病情在第三天就穩定了,只是身體變得虛弱許多,再也無法站立。住院第五天,醫生說沒有啥問題了,可以辦理出院回家休養。李青松緊跟在主治醫生后面,反復咨詢母親的病況。主治醫生被問急了,搖搖頭說:“此前能恢復到這個樣子是你們精心伺候得好,已經出人意料了,在后面的日子繼續努力盡一份孝心吧。”
李青松又召集大伙兒到走廊開家庭會,說:“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場告別,做兒女的終將對母親說再見,我必須在媽最后的日子里盡做子女的孝道。媽現在不能站立,哪怕出再多的錢,也得雇一個最好的最專業的護工,媽和護工以后輪流在我和青萍那里住,出院了先到我家住一個月。”
李青海蹲下去,雙手握拳捶著腦袋,說:“就我不能把媽接過去照看,我對不住媽,對不住哥哥、姐姐。”
6
王寶忠按照慣例給馬科長泡了護理液。馬科長說:“我右腳大拇趾內側隱隱疼痛,你給看看咋回事。”王寶忠抬手把落地燈的燈臂壓下來,讓燈頭貼近她的右腳。馬科長的右腳明顯感受到了燈管的熱度。她看見自己的右腳一下子變得白花花的。王寶忠捏捏她的右腳大拇趾,說:“嵌甲,也就是指甲變形頂著肉了,我給你修一下你就不疼了。”馬科長說:“有一段時間不見你丈母娘,她咋瘦了那么多?”王寶忠說:“她住到我大舅子家去了,你怎么會看到?”馬科長說:“我們服務大廳人來人往的,看見有人推輪椅,我才認出坐在輪椅上的那個老太太是你丈母娘。真的,瘦得我都不敢認了。”王寶忠說:“她去干什么?”馬科長說:“你不知道哇?她攜帶證件和委托書把房子過戶給孫子,本人要到現場拍照。我那陣兒正忙著,還說忙完了去和她打個招呼的。她拍罷照就被推走了。”馬科長尖叫了一聲,“哎喲。”王寶忠用棉簽探進瓶里蘸了紫紅色的藥水按壓在傷口上面。馬科長齜牙咧嘴地說:“都說你王一刀的刀工好,怎么會修破腳?”王寶忠的臉像涂了層紅漆,說:“不好意思,失手了,現在已經止住血了。”馬科長嘆口氣說:“唉,你看你這個女婿當的,丈母娘把房子過戶給孫子了你都不知道。喂,你老婆總該知道吧?”王寶忠說:“青萍一嘴都沒有給我提過,她應該也不知道。”馬科長撇了一下嘴,又一聲長嘆,說:“唉,虧你這么孝順,看來手心手背終究是有區別的。你想想那套房子為啥不過戶給你兒子,只因為你兒子姓王,不姓李,別說你丈母娘,擱誰誰都會這樣做,換了我也會這樣。”
王寶忠早早鎖了店門回到家里,倒頭就睡。李青萍納悶兒了,坐在床邊說:“我下午去看媽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媽出院個把月咋就瘦了那么多?她看見我直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李青萍說著說著肩膀抽了起來,從床頭柜上抽出餐巾紙蘸著眼角說,“媽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想早點兒把她接到店里住一段時間。”王寶忠裹著被子甕聲甕氣地說:“我啥也不爭啥也不圖,現在把她接過來,青松會不會有想法?”李青萍越哭越傷心,拿餐巾紙擤了把鼻涕,說:“他能有啥想法?本來就約好一家照顧一個月的。”王寶忠就把馬科長講的話告訴了李青萍。李青萍像被塞了撐嘴器,愣了好大一陣兒才說話:“寶忠,我們就當啥也不知道,媽這時候受不得刺激。你明天把店里拾掇好了,我讓大哥和護工把媽送過來。”
第二天,李青萍還沒有來得及給李青松打電話,李青松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說媽昏迷過去了,這次不像是短暫性腦缺血,已經打了120急救電話拉到醫院。
李青萍急匆匆從醫院趕到修腳店,連口水也不喝,嘶啞著嗓子對王寶忠說:“媽二次腦卒中,暫時在重癥監護室,種種跡象表明這次估計真不行了。后面一段時間我們又要排班,你參加嗎?”王寶忠望著李青萍像陌生人一樣:“不一直都由你做主嗎,咋突然問起我來了?”李青萍定定地看著他,說:“這次不一樣,我得征求你的意見。”王寶忠咧咧嘴,說:“還是你做主吧。”李青萍搖搖頭說:“那就不排你了。”王寶忠沉默了一會兒,抬起頭說:“這次不排以后怕是再也沒有機會了。”李青萍抬起胳膊用袖頭蘸了兩只眼角,哽咽著說:“寶忠,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做。人在做,天在看呢。”
丈母娘身上插滿了管子,床頭的各種儀器不斷地閃爍著數字。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虛弱的目光陡然亮了起來,近乎貪婪地看著身邊的親人,憑借回光返照的力量顫顫巍巍地拿起筆在復印紙上留下了最后的遺言。她又畫了那幅圖案,一條豎線蚯蚓一樣爬在紙上,另外兩條蚯蚓組成了一個“叉”。因為力不從心,叉與豎線的交會處往左邊偏離了一厘米,這是大家早已熟悉了的一幅圖案。她顫抖的手仍舊頑強地捏著圓珠筆。李青萍趕忙換了一張紙,再次把板夾舉到母親面前。大家看見她在紙上畫了一個癟癟的圓圈,雖然癟得像蠶豆,但是大家確信她是在畫一個圓圈。略微停頓,她在圓圈中心打了一個鉤,像拐棍一樣的鉤,然后將目光落在王寶忠身上,圓珠筆從她手里滑落下去。平時只是咧嘴啞笑不見出聲的王寶忠喇叭一樣哇地哭出聲來,他跪在床頭雙手緊緊攥住丈母娘寫字的右手,喊了一聲:“媽……”
站在一旁的李青松蹙眉問:“喂,寶忠,只有你知道媽到底想說啥,她到底想說啥?”王寶忠一言不發,只是閉著眼睛搖頭,淚水被甩得飛起來。
7
王寶忠像揣著存折一樣把兩張復印紙拿到隔壁的裝裱店,全程盯著師傅裝了畫框。他回到修腳店,把墻上的錦旗取了下來,然后把兩個畫框掛在墻中央。他對李青萍說:“媽一直看著我們呢。”
次年清明節,李青海回來了。王寶忠把兩張茶幾拼起來,在小吃店點了四菜一湯,打開一瓶老白干。李青海喝了酒話多起來,他說:“我對不住媽,陪她的時間太少了。我這個當兒子的還沒有你這個當女婿的做得多,我要再敬姐夫你一杯。”王寶忠只喝酒不吱聲。李青萍看著一瓶酒喝空了,說:“敢情你們哥兒倆談得來,我再開一瓶。寶忠你就放開了陪青海喝好,咱們今天歇業好好休息一天。”李青海抹抹下巴上的油水,說:“姐姐和姐夫都是好人,大哥不是人。”李青萍忙說:“莫要亂說,別人會看笑話的。”李青海說:“我就要說,難道他能做得出來我就不能說出來?”李青萍站起來把店里的燈全部打開,然后走到門口拉下了卷簾門。李青海說:“媽向來是一碗水端平的,大哥他肯定是打印了委托書,通過哄騙或者軟磨硬泡,也許是強迫著讓媽按了手印把房子辦了過戶。你們想想,他怎么可能良心發現主動把媽接過去照看?太陽能從西邊出來嗎?”李青萍說:“菜都涼了,我端到后面熱一熱,你們多說說話,喝好,別喝多了。”李青海踉踉蹌蹌地站起來指著墻上的兩幅畫,說:“姐夫你最了解媽,你告訴我,媽最后說的是啥意思。”王寶忠舌頭已經硬了,說:“我不喝了,我睡覺去。”李青海一把扯住他袖子,說:“姐夫你莫走,你今兒個必須告訴我,要不然我覺都睡不著。”王寶忠被李青海突然一扯,一屁股坐在地上。李青海彎腰端起兩個酒杯,碰出清脆的聲響,然后遞給王寶忠一個,說:“姐夫,我再敬你一杯,喝了這杯你就告訴我。”
王寶忠撐著胳膊從地上坐起來,接過酒杯一仰脖喝下,然后趴在一張修腳椅上打起呼嚕。李青萍跑出來,把修腳椅緩緩放平,又用力把王寶忠扶正,而后再把李青海扶到另一張修腳椅上,分別給他們蓋上毛毯。
王寶忠說夢話似的說:“媽,我知道你寫的‘1’,是在說老大呢……”
【作者簡介】北極,本名熊萬里。作品散見于《長江文藝》《芳草》《青年作家》《天津文學》《草原》《文學自由談》等刊物。
責任編輯 梁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