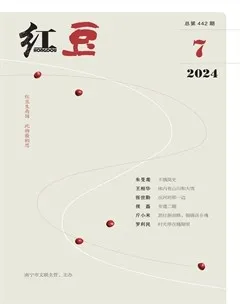影影綽綽
租住在這棟老舊的樓房快七年了。從最初的諸多不適到現在安之若素,我漸漸習慣了在這舊屋子里的生活。
老屋有一個朝北的小陽臺。推開紗門出去,站在陽臺上能看見對面那戶人家廚房窄小的窗口。廚房是人間煙火所在,廚房的溫度就是一個家庭的溫度。如果哪一家的廚房早、中、晚三個時段都能準時飄散出嗆人的油煙或是誘人的香氣,那一定是稱得上幸福的人家。在隔開我們這兩棟樓的空地上有四棵高大的樹,從東往西依次是一棵玉蘭樹和三棵蒲桃樹。樹冠遠遠高出了兩棟樓的樓頂,枝葉濃密婆娑,亭亭如蓋,遮住了陽光。我讓單位做后勤的老謝對枝丫進行一些修剪,好讓陽光透下來。老謝望樹興嘆:“樹太高,架上梯子也砍不到,而且還危險。大院里的路窄,工程車又進不來。你們只能將就啦!”住在一樓的小鄭說:“有時抬頭看樹,感到遮天蔽日,不知晨昏。”幸好,去年的臺風刮斷了中間那兩棵蒲桃樹的幾根枝丫,讓陽光終于能夠占領一塊地面。樓距近,樹又太密,我住在三樓,即便把衣服晾在陽臺伸出的晾衣架上,衣服也很少能曬到陽光。沒有光,屋子里白天也有些陰暗。
陽臺上擺放著四盆花和幾個空花盆。兩盆是喜陰的綠蘿,一盆是茉莉。還有一盆綠植類似藤蔓,葉片小而肥厚,種了快三年的時間,也沒見長大。空花盆之前也是種有花的。其中一盆種的是藍雪花,另一盆種的是蘭花草。藍雪花葉色深綠,花色淡雅,呈藍白兩色,花形類似紫云英,在七八月間開花,炎炎夏日里讓人一見就有清涼的感覺。它得名藍雪花或許因此。從花店剛買回這些花時,藍雪花很是熱鬧地開了一陣,可一開一落很快就死掉了。后來知道藍雪花喜陽,也就明白它曾努力地活過。蘭花草則是從大院的花圃里移植過來的,看著它會想到那首流行一時的臺灣校園民謠《蘭花草》,花朵朝開夕敗,也確實驚艷了一回。茉莉花開過一季,現在偃旗息鼓也變得要死不活了。
家鄉傳說,世上的人都是花山上的花。花婆神把花送到人間,女子是白花,男子為紅花。人死后又化為花魂回到花山重新生長。花化為人,人變成花。如此輪回,花山上的花長盛,世間的人繁衍生息。那世間的花又是什么?是陪伴,是治愈,抑或是開悟。
風起,葉沙沙落,落葉亦有聲。陽臺上除了花的葉子,還有樹的葉子。大風、大雨、樹上搗蛋的松鼠都會給陽臺送來落葉。樹葉的顏色隨季節變化而略有不同,春時綠得淺,夏時綠得深,秋冬時葉片暗灰,即使泛黃也是暗暗的。落葉是季節的信使,告訴我四季的變遷。我從不輕待它們,總是讓落葉在陽臺上匯集,積攢上一段時間才掃走。在時光的調教下,葉子的水分流失后會慢慢地變干,干燥得自己的腳踩上去時,能聽到清脆的聲響。古人云“開瓶酒色嫩,踏地葉聲干”,又說“掩關苔色老,盤徑葉聲枯”,可見聽枯葉聲響亦是一種追求自然真境的詩意行為。
萬籟有聲,發出聲響的又豈止是落葉?
壁虎是窗臺上的常客,它們總是在夜晚出現,匍匐在窗口的外沿灰白老舊的墻上,它們白灰灰的身體是天然的偽裝。那些被室內燈光吸引,朝著窗口飛來,或是停留在紗窗上伺機鉆進窗子的飛蛾一類的蟲子都是它們的獵物。壁虎悄無聲息地逼近,舌頭迅疾地一伸一縮,那些蟲子就成了它們的腹中之物。壁虎似乎總是不能飽腹,夜深人靜之際仍然不肯離去。我在桌前讀書困乏時,抬頭之際有時能看到它們趴在窗網上。詩人說壁虎“庶魚庶草劇難名,每訝寒宵壁虎鳴”,又說“土蛇不蟄日紛騰,壁虎高吟夜守燈”,可見深夜里壁虎是會叫喚,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的。是它們的聲音太微弱,還是我沒有細心地去聆聽,我竟然從沒有聽到過。它的叫喚是為了呼朋引伴,還是僅僅因為孤寂而長吟?我對它們知之甚少,實在猜不出來。
今夜不知道老鼠會不會來。往夜它們都會急吼吼地跑過我的窗沿,像是去趕一個將要遲到的約會。窗沿那么窄,管線那么細,它們都如履平地,健步如飛。那次公休回老家,陽臺上晾著一些紅薯,忘了收進屋內,廚房里也有十多個放在地上。十余天后我回來,看到陽臺和廚房地板上只剩下紅薯的些許殘渣,還有十幾顆老鼠屎。是老鼠光臨了我的陋室。它們應該是吃完了陽臺上的紅薯,然后循著氣味進到廚房,把廚房里的紅薯也掃蕩一空。有一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時,我聽到了窸窸窣窣的聲響,睜開眼,側身看窗簾。室外的光照在窗簾上,一只老鼠正沿著窗簾爬上窗框,從兩扇玻璃推窗之間的縫隙鉆了出去。鼠輩氣定神閑輕車熟路,定是夜夜趁我沉睡之后如此。此后幾天,我陸續在電視機柜、衣柜、書柜等處發現它們的活動痕跡,食物殘渣、咬碎的紙屑、咬爛的行李包……只是沒有見到作案的鼠輩。看來它們只是把我這陋室當作行宮,沒打算長住。可人鼠豈能共存?我買來粘鼠板,每晚睡前一一放置在窗臺、電視機柜、門廳、廚房門口。據我觀察這些地方是老鼠的必經之處。它們一旦從這些地方走過,踩上粘鼠板,一定難逃。我要做的就是等著早上醒來,將大膽鼠輩“鼠贓俱獲”。一連四天,粘鼠板上沒有留下鼠輩的一點兒痕跡,只粘住了一只蟑螂和一只長期出沒在廚房的壁虎。后來幾天,我幾次調整粘鼠板的位置,可仍舊未能擒獲老鼠。就在我心灰意懶,打算撤掉所有粘鼠板時,某天早晨天未亮,我起床如廁,廚房里傳出唰唰的響動聲和老鼠吱吱吱的叫聲。我打開燈,看到米桶旁邊的粘鼠板粘住了一只尖嘴尖腮的老鼠。很顯然,這只老鼠偷米時不小心從桶邊掉到了粘鼠板上。我蹲下來,看到它的四只鼠足和細長尾及鼠身的后部被粘住了,只剩尖尖的頭在亂晃。粘鼠板已被它咬破一個小洞,它的努力顯然白費了。它鼓脹的小眼盯著我,似乎知道自己的末日降臨。我想將老鼠正法,起床看熱鬧的兒子卻說:“讓它自生自滅吧。”不忍拂了孩子的意,我將粘鼠板卷起,把老鼠卷在其中,拿到樓下丟進了垃圾桶。對于老鼠,我只能做到這步了。無論何時何地,老鼠都是不會受到人類歡迎的,何況這還是繞床饑鼠。
除了老鼠,還有松鼠。松鼠不會像老鼠一樣登堂入室,房屋之外的空間都是松鼠的。靠近陽臺的那棵樹上就有松鼠搭建的窩。平時也能見到一身皮毛灰黃或灰黑的松鼠在樹叢中躥來躥去、在枝丫間跳躍,在小區各棟住宿樓的陽臺、窗戶的防盜網上活動。凌空飛架的各種線纜成為松鼠們往來各樓棟的便捷通道。它們在人類的居所外逗留,當然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果腹之物。有好幾次我晾曬在陽臺上的花生、板栗、紅薯都被松鼠拿去吃了。不過,我并不覺得氣惱。有這樣的萌物做鄰居,偶爾窺視一會兒它們的生活,足以忘掉一些煩心事。
我住在老城區的中心,蟲子見得少,蟲子的鳴聲也很少聽聞。晚上偶爾聽到樓下蛐蛐兒、螻蛄的叫聲,單調而乏味。它們叫上一兩個晚上又不叫了,我就聽不到了。想來是鳴唱的蟲兒沒有聽到其他蟲子的回應,自己跑開了。“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蟲子和人類有著同樣的心思。
我有一個老師曾擔任桂西南某貧困村扶貧第一書記,夜里他最大的樂趣是用手機拍攝鄉村的飛蛾,然后展示在微信朋友圈。手機鏡頭下的蛾子奇形怪狀、色彩斑斕,飛翅上的圖形絢爛奪目。許多人從他的朋友圈認識了眾多種類的蛾子,見識了繽紛的蛾類世界。他告訴我,拍攝近一年的時間,到最后那些飛蛾像是把他當作了朋友,見到他時不會四散飛逃。一些蛾子飛舞時不好拍攝,他會說:“你這樣亂飛,我怎么好拍?”聽到他的話,那些飛舞的蛾子竟然會停下來,歇息在墻上、窗戶上,展開羽翼讓他拍照。蛾子和他似乎已有了心靈感應。是啊,也許那些蛾子就是來拜訪他的客人。我知道,很多時候是這些蛾子和耐泡的茶以及杜甫的詩集慰藉了他孤身獨處鄉村的寂寞。
在城里很難見到那些美麗的飛蛾,偶爾在陽臺上會發現蝴蝶或是蜻蜓的軀殼。說軀殼是因為它們已經死去。或許在前一個夜晚它們朝向熒熒之光,試圖進入我的屋子,卻沒有成功,只能在陽臺上徘徊。最后累了,或是受到壁虎的襲擊,它們墜落下來,成為一具沒有生命的軀殼。
那只馬蜂進屋時,我沒注意到它。夜里聽到嗡嗡的振翅聲,憑經驗我知道有蟲子飛進了屋里。我在書桌前、窗子周沿找了一陣,沒有找到。奈何睡意襲擾,我躺在床上睡著了。夢里一直聽到有什么東西在飛,似困獸猶斗的掙扎,又像是有斷斷續續的激情。早上醒來,在干衣機里給兒子找衣服,才發現一只馬蜂正從干衣機底部努力地往上爬著。我趕緊找一個塑料盒把馬蜂扣住,然后把塑料盒倒過來將馬蜂裝到了盒子里。一夜掙扎過后,馬蜂精疲力竭。人類的氣味顯然刺激了它,它在塑料盒里不安地爬動著。兒子知道捉住了馬蜂,刷著牙就跑過來瞧熱鬧。我說:“把馬蜂拿到陽臺上放了。”兒子說:“馬蜂一定餓了,要喂些東西給它吃,補充能量。”我把盒子拿到陽臺,放到茉莉花盆里。小小的塑料盒關不住馬蜂,它努力爬出了盒子,又爬到茉莉花葉上,但很快又掉落到花盆里。被困了一夜,它太虛弱了。我再次把它捉回盒子里。看著馬蜂,我希望它能明白我的善意。兒子又拿來螺絲刀讓我給塑料盒戳幾個孔,讓馬蜂透氣。這小子平時愛讀《你好,我的植物鄰居》《荒野求生》等書籍,看來沒有白讀。做完這一切,我去上班,兒子上學。傍晚回來,我再去看茉莉花盆中的塑料盒,馬蜂已經不見了。在花盆、陽臺、樓下的瓦房頂上也沒有見到它的蹤影。或許馬蜂真的飛走了吧。
我租住在這舊屋,早晨出門,傍晚歸來。進屋后,先在廚房里忙碌,接著和兒子在老舊的餐桌上吃飯,然后父子倆看書、學習、打游戲、出門散步……日子簡單地重復著。只有夜晚會有一些不同。我知道,在不知曉的黑夜深處,存在著一個精彩紛呈的世界。那是動物的,也是人類的。
有時深夜返家,看著那四棵樹,像是舊樓前四個沉默站立的人。它們陪伴著我,也陪伴著那些深夜來訪的不速之客。當然還有夜色中所有的影影綽綽。
【作者簡介】陽崇波,廣西羅城人,仫佬族,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廣西作家協會會員。有散文、詩歌散見于報刊。
責任編輯 藍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