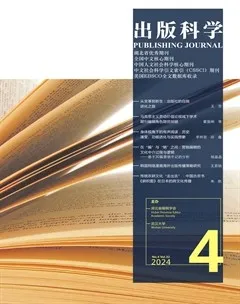加強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史料學建設
史料學是歷史學科的一個基礎學科,是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專門考察史料,研究史料的源流、價值和利用方法的一門學科。我國是史學十分發達的國家,史料學源遠流長。相比而言,出版史研究起步較晚,而嚴格意義的出版史料學動議則很晚才被提出來,劉光裕先生前些年曾有《關于建立出版史料學》的專文刊出,從學科建設角度加以倡導,所論重點在中國古代出版史料研究。筆者以為,出版史料學的建設確實需要提上議事日程,而更具學術價值、更有現實意義的當屬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史料學。
出版史學界認為,中國出版史研究濫觴于19世紀末期,以1897年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為肇始。中國傳統的出版史料大量潛藏于眾多的書史研究和古典文獻學成果之中。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才有了《中國出版界簡史》之類的出版史著刊行,1950年代有了張靜廬編選的《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料》問世。出版學和出版史研究的恢復與快速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1990年代以來,大量出版史料得到系統整理與刊布,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機構,宋原放、宋應離、徐蜀、吳永貴、劉洪權等專家為此做出了積極貢獻。《中國出版史研究》《出版史料》《新聞出版博物館》等專業刊物(含集刊)的出版,相關的國內國際出版史學術會議的召開,以及一些國家級課題,尤其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的上馬,研究生相關學位論文特別是博士論文的撰寫,都有力地推進了出版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當出版史料的整理和利用發展到一定階段,加強對它自身的學理化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也是出版史史料學的職責和任務。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史料研究有一個合法化、學科化的問題。
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史料學如何編纂,涉及技術層面的問題。既有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學》《中國近代史史料學》等高校教材,大體都是采取先總后分的編寫策略。一般是用一兩章就史料與史料學,近現代史史料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現狀,相關工具書的使用等進行探討,并就近現代史料的鑒別等問題展開論述,進而分別從歷史檔案史料、書信和日記類史料、傳記類史料、報刊類史料、方志和典制類史料、口碑和實物類史料等,分門別類論析其價值,介紹其代表性史料,并舉例予以示范性說明。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史料學也應當做這種基礎性工作,形成簡明而規范的本子。
中國近現代出版史若細分還可以有文學出版史、教育出版史、科技出版史等。其實相近領域、關聯學科的成果和經驗也值得汲取和借鑒。如近現代教科書既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出版史的一個側面。至于20世紀30年代由編輯出版家趙家璧策劃、眾多現代文學名家參與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這一規模宏大的史料整理活動,就具有現代文學和文學出版的雙重價值。其中的第十集《史料·索引》(阿英編選)的文學出版史料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
現代文學史家金宏宇教授認為“史料派”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一脈,其中的“史料學建構派”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提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等論著均對現代出版史史料學建構有一定參考作用。他本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更是厚重扎實、富有創新的現代文學史史料學研究專著。他借用西方史學的“史料批判”概念(相當于中國傳統文史研究中的史料考證),分別從10個方面探討史料批判、史料分類批判、輯佚批判、辨偽批判、版本研究批判、校勘批判、目錄實踐批判、考證方法批判、注釋批判、匯編批判。這中間相當多的內容對現代出版史史料學具有啟發之功。中國近現代出版史史料學既需要中規中矩的教材編寫,也需要深入系統的專門研究,進而有力推進出版史學和出版學的三大體系的建設與發展。
(作者單位:武漢商學院;華中師范大學文化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