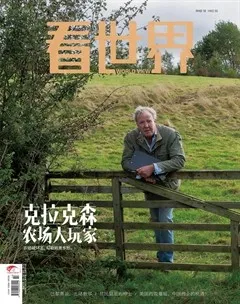從尼克松時代看美國的當代挑戰

《論領導力》
[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胡利平 / 林華 譯
中信出版社
2024年3月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總統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被迫辭職的總統。同時,作為一位在冷戰高峰時期重塑了已呈敗象的世界秩序的總統,尼克松還深深影響了他任職期間的外交政策及其后果。
尼克松總統在5 年半的任期內結束了美國對越南的入侵,奠定了美國作為一個域外國家在中東的霸主地位,借打開與中國的外交關系將兩極化冷戰置入一種三角動態格局,最終使蘇聯陷入戰略被動。
從1968 年12 月尼克松邀請我出任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到1974 年8 月他離開總統職位,我始終是他的親密助手,在他領導下參與了他的決策。在尼克松余生的20 余年里,我倆始終來往不斷。
尼克松的挑戰
我年逾99 歲,重提尼克松不是要炒半個世紀前是是非非的冷飯(我在3 卷本回憶錄中已經寫過了),而是為了分析一位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和性格。尼克松就職總統時,美國社會正處于前所未有的文化政治動蕩中。他毅然采納了關于國家利益的地緣政治概念,從而變革了美國的對外政策。
1969 年1 月20 日尼克松宣誓就職總統時正值冷戰高峰。在戰后年代里,美國似乎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國力,在海外四處承擔義務。如今美國無論在物質能力上還是情感上都開始對以往做出的承諾感到力不從心。
美國國內在越南問題上爆發的沖突已呈白熱化。美國國內一些人士于是呼吁軍事上從越南撤軍,政治上收縮。當時美國和蘇聯正在部署有效載荷更重、更精確、具有洲際射程的導彈。蘇聯在遠程戰略核武器數量上與美國不分伯仲。一些分析家認為,蘇聯甚至有可能正在獲得對美國的戰略優勢。美國人不禁憂心忡忡,擔心會突然遭到末日襲擊和長期政治訛詐。
1968 年11 月尼克松贏得大選前幾個月,他出任總統后即將面臨的挑戰開始在三個重大戰略地區顯現:歐洲、中東和東亞。
1968 年8 月,蘇聯聯合幾個東歐國家出兵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前捷克斯洛伐克試圖在不脫離蘇聯軌道的前提下推行經濟改革,結果成了它的一大罪狀。在聯邦德國,蘇聯對西柏林的威脅依然存在。莫斯科時不時發出威脅,要封鎖處境艱難的西柏林。
對西柏林的威脅始于赫魯曉夫。1958 年,赫魯曉夫對幾個西方占領國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它們6 個月內從西柏林撤軍。飽受戰火創傷的歐洲和日本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實現了復蘇,開始與美國展開經濟競爭。同時,歐日還對演變中的世界秩序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觀點,有時還是與美國相左的觀點。
1964 年10 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后第5 個擁有世界上最具毀滅力武器的國家。北京在參與還是遠離國際體系之間搖擺不定。
在中東,尼克松面對的是一個在沖突中掙扎的地區。1916 年,英國和法國締結了《賽克斯-皮科協議》,搖搖欲墜的奧斯曼帝國的部分領土被劃分為英法勢力范圍。這一協議出臺后,產生了一批阿拉伯穆斯林政權。這些政權看上去類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創造的那種國家體系的成員,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20 世紀中葉的中東國家與依然處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下的歐洲領土不同,既沒有共同的民族身份認同,又沒有共同的歷史。
歷史上法國和英國曾稱霸中東。兩次世界大戰后英法元氣大傷,勢力日衰,無力向中東投射自己的力量。當地起于反殖民運動的動蕩不斷蔓延,演變成為阿拉伯世界內部以及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國之間的沖突。1948 年以色列獨立后,兩年內就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國家的承認,現在正爭取周邊鄰國的承認。而鄰國認為以色列侵占了本應屬于它們的領土,因此根本就是非法的。
孤立主義的流行
尼克松就任總統之前的10 年間,蘇聯開始趁中東走向大動蕩之際與當地的專制軍人政權搭上了線,中東更是亂上加亂。這些軍人政權取代了奧斯曼帝國覆滅后留下的封建色彩濃厚的統治體制。由蘇聯武器裝備的阿拉伯軍隊把冷戰引入此前西方稱霸的中東,導致該地區矛盾日益尖銳,有可能引發一場全球大災難的風險隨之上升。
尼克松就任總統之時,血腥的越南戰爭泥潭已是頭等大事,以上關切均退居其后。前一屆約翰遜政府向這一地區派遣了多達50 余萬美軍,這是一個無論地理上還是文化和心理上都與美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區。尼克松宣誓就職時,超過5 萬美軍正在奔赴越南途中。
讓美國從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中脫身的擔子落到了尼克松肩上,而且是自美國內戰以來國內局勢最動蕩之時接過的這副擔子。
尼克松當選總統前5 年,美國國內政治分歧之劇烈,為美國內戰以來所未見。約翰·肯尼迪總統、他弟弟(當時是呼聲最高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和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先后遇刺身亡。美國各地城市街頭爆發了激烈的反戰示威,抗議馬丁·路德·金遇害的示威游行遍及全國,華盛頓常常一連數日陷入癱瘓狀態。
在美國歷史上,國內因尖銳分歧吵成一團屢見不鮮,然而尼克松面對的局面前所未有。一個新興的美國精英階層堅信,戰敗不僅在戰略上不可避免,在道義上也不失為一件好事。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信念意味著存在了數百年之久的一項共識—國家利益代表了合法目標,甚至可以說代表了合乎道義的目標—破裂了。
在一定程度上,這類觀點標志著昔日孤立主義的沖動再次冒頭。孤立主義者認為,美國“卷入”海外麻煩不僅絲毫無益于國家福祉,還腐蝕了它的性質。然而今天與昔日孤立主義的區別是,這股新孤立主義思潮提出的理由不是美國的崇高價值觀不允許它卷入遙遠地區的沖突,而是美國自身已腐敗至極,沒資格在海外充當道德榜樣。
宣揚這一觀點的人在高等學府先站穩了腳跟,之后影響越來越大,幾乎左右了大學師生的思想。他們既沒有從地緣政治角度審視越南悲劇,也沒有把它視為一場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把越南悲劇看作全民情緒宣泄的先兆,激發美國做早就該做的事—自掃門前雪。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董可馨 dkx@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