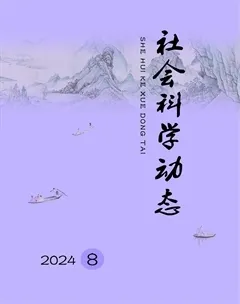加繆作品中的身份意義與思想特質
摘要:思想是文學的靈魂。加繆作為20世紀深受年輕一代歡迎的作家和思想家,其小說創作呈現出鮮明的思想特色。梳理加繆的人生軌跡、文學創作與思想主張的基本關系,可以發現,加繆小說書寫了在罪惡世界里如何奮起反抗、在荒誕世界中如何帶著病痛活下去的堅韌力量,其所刻畫的與時代鑿枘不投的異鄉人、追求愛與平等的正義者、奮起抵抗的局外人,融入他的政治踐行及其社會擔當的責任與愛之中,深刻揭示了加繆小說的跨文化身份意義。由此,可以洞見文學史與思想史的內在關聯,從而理解“文學是人學”的永恒命題。
關鍵詞:加繆;小說;責任與愛;跨文化身份
中圖分類號:I565.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08-0025-06
一、問題的緣起
文學研究向思想史的推進,呈現了文學與思想的本質關系,即思想是文學的靈魂。文學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史”的真實、“詩”的藝術外,關鍵還有“思”的力量。著名學者黃曼君認為:“經典既是一種實在本體又是一種關系本體的特殊本體,亦即是那些能夠產生持久影響的偉大作品,它具有原創性、典范性和歷史穿透性,并且包含著巨大的闡釋空間。”(1) 黃曼君關注到經典的起源品格、價值定位與歷史功能,突顯其被闡釋的可能性。后來他又發展了自己的經典學說,從較模糊的品格定性向清晰的邏輯維度轉型,從精神意蘊、藝術審美、民族特色三個邏輯維度來深刻辨析文學經典內涵,指出文學經典是以詩性為中心的“思、詩、史相交融”的文學形態。(2) 這一關于“經典”的概念,展現了宏闊、長久、深刻的偉大作品屬性,成為后學者認識與把握經典文學的基礎性概念。以此為問題出發點,筆者觀照阿爾貝·加繆小說的經典文學生成史,尋找加繆文學思想得以形成的內在詩性、史質與哲思的重要因素。
加繆的作品滲透著作家個體社會責任的觀念,代表著一種責任倫理。加繆認為,作家不應為制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他長年從事政治寫作,也積極介入政治活動,從二戰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態度、反殖民主義報道、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立場等問題,都可以看到他始終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不管是作為與時代鑿枘不投的夾縫人,追求愛與平等的正義者,抑或從荒誕出發,奮起抵抗的局外人,加繆的小說創作與其介入政治的態度和行為,均可見其文學思想特性:他不僅擔當了作家的社會責任,還表現出對人民的愛。全面考察加繆的人生境遇與特殊的跨文化身份,理解其文學思想形成脈絡,可見其小說創作的文學史價值與精神品格。
二、異鄉人的“雙重流亡”
加繆的人生充滿了矛盾張力與兩難選擇。無論是其阿爾及爾的童年經歷、青少年求學生涯、巴黎文化圈時期,還是后來遠離政治文化的生活,失落感、流亡感、錯位感,始終是加繆生活和作品的中心命題。
加繆自幼生活在割裂的世界里。1913年,他出生在北非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一個歐洲移民工人階級家庭。從小家境貧寒,父親死于一戰,半聾母親以幫傭為生,勉強維持生活。作為戰爭孤兒,加繆白天可以去城里上學,享受象牙塔的學習生活,晚上回到貝爾庫貧困區,那里是現實,是文盲母親。在其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第一個人》中,加繆表達了童年生活中自己與周圍環境的割裂感。印刷的書目令加繆和母親都著了迷。他們一個是廢寢忘食的閱讀者,另一個是無法進入閱讀世界的著迷旁觀者。(3) 母親不明白,這神秘符號如何讓她的兒子一連幾個小時地埋頭于她未知的生活,而當兒子回到現實之中時,他眼里的母親似乎是個陌生人。中學時代,由于家境貧寒,加繆是走讀生,每天乘電車從貝爾庫到行政廣場的汽車站,然后和同學們一起步行到學校,在那里與老師和同學們度過美好的學習時光。這也就意味著他每天晚上回家陪母親的時間不過三小時。但事實上,除了在窮人的睡夢中,他幾乎沒有真正與母親在一起過。(4)加繆的早期生活在貝爾庫與校園之間分割:一方面,對于來自工人階級的加繆來說,貝爾庫是其早期生活的核心,但漫長的中學歲月又使得這個社區對于這名中學生來說,不過是夜晚、睡覺和夢。讀書和對書的世界的密切接觸,讓加繆幼年早慧,也將他與家庭生活分割開來。作家的職業道路對于來自貧困工人階層的加繆來說,是某種形式的背叛,是與家庭出身的背道而馳。
家鄉生活的文化狹隘讓加繆遠離阿爾及利亞,而歷史的機遇卻把他“空投”到了喧囂、嘈雜、人人利己的巴黎知識界。他從一開始就深深覺察到自己與巴黎知識界的格格不入。他不是巴黎精英教育的成果,而只是畢業于阿爾及爾大學;他沒有其他新認識的大部分同伴都有的教育文憑——因為肺結核,報考國家教師資格被拒。與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雷蒙·阿隆及其他同輩人相比,加繆自覺社會背景、外省出生、教育程度都不如人家,這讓他在心理上處于一種絕對的劣勢。
加繆發現巴黎與阿爾及利亞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場域。文化場域本質上關注的是場域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對人和社會的影響。巴黎知識界和阿爾及利亞的生活學習圈文化場域的差異,給加繆以強烈的沖擊。在巴黎,沒人在乎他是誰,甚至不在乎他是否在那里,巴黎不需要他。不可避免地,加繆對自己的存在產生了難以逃避的自我懷疑情緒,這是一種近于空虛的文化心理。
然而這種劣勢卻被巴黎知識分子無情地用來攻擊加繆。巴黎評論圈約定俗成將加繆貶低為“面向中學生的哲學家”,認為其作品“只適合入選中學教材”。其中薩特最為惡意用心、口無遮攔。他對加繆的作品和人格均進行了殘酷的攻擊,認為加繆的推論虛弱、含糊不清、雜亂無章;認為他的性格自鳴得意和容易受傷令人沮喪,使人們無法告訴他全部真相。(5) "然而,令加繆受傷的不僅僅是這些話本身,而是薩特作為法國當時頂級的哲學家所具有的絕對權威讓他絕望。青年時代,加繆的人生格言是:要緊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出去看世界的理想讓他付出了雙重流亡的代價:離開家鄉阿爾及爾是身體的流亡,來到巴黎后繼續內心的流亡。這種境況讓他感覺到,巴黎是座森林,野獸遍地,形容丑惡。他在《墮落》中將巴黎描述為一個裝滿鋸齒鯉的池子——它們只需五分鐘就能把一件藝術品撕了,僅僅出于毀滅的快感。(6) "社會出身和教育經歷讓加繆在巴黎產生了深刻的疏離感、失落感、流亡感、錯位感,使其成為一個身處巴黎的異鄉人。
加繆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二戰期間,他加入反法西斯陣營,警告軍事主義的危險性。1945年廣島原子彈爆炸后,法國、美國和英國新聞界歡呼其為科學的偉大成就,而加繆則怒斥這是一場不體面的“可怕的音樂會”,機械文明達到了最后的野蠻程度。現代機械時代使屠殺變得容易了,使人們看不到殺戮的后果。加繆發出了人文主義的呼喊:“不要通過殺戮和死亡來生產我們并非是的存在,我們必須活著,也讓別人活著,以創造我們之所是。”(7)
二戰后,法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憎恨和醉心暴力體現在以薩特、波伏娃和埃馬努埃爾·穆尼埃為主的知識分子身上。他們力挺工人運動主義和親蘇維埃主義。對待戰后肅清問題,加繆與巴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法國共產黨均產生了分歧。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看重的是經典作家所謂的“權衡”,“是一種超越恣縱的邏輯推理的審慎的智慧”(8)。反對暴力革命讓加繆在巴黎文化圈更加進退維谷。阿爾及利亞在二戰后掀起了民族獨立的高潮,加繆在該問題上拒絕加入這場權力的游戲,拒絕選擇立場,保持緘默。因此,他受到沖突雙方的責難。1959年,阿爾及利亞為爭取獨立,與法國開戰。加繆在政治上采取的中立態度,或者說模棱兩可的態度,讓他在兩地都陷入困境,這也是當時很多法裔阿爾及利亞人的兩難處境。地中海把加繆的內心割裂成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阿爾及利亞)泉源即將枯竭,而另一個世界(法國)風沙遠遠卷走人跡。
這種人在異己世界中的孤獨感,加繆小說《蒂巴薩的婚禮》中的美狄亞就是很好的體現。美狄亞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悲劇人物,為愛情背井離鄉,傾盡所有,最后卻遭到丈夫的驅逐。加繆在這部作品中發出呼喊:“一個沒有城邦的人是何其不幸。”(9)為了丈夫,美狄亞不惜背叛母族,偷了金羊毛,丈夫卻因為權利和新歡將她拋棄、驅逐,如此造成了其身體的流亡和內心的折磨。受到傷害的美狄亞對丈夫實施了死亡的報復,在絕望中殺子,造成了可怕的人倫悲劇,不僅自己成為殺子的魔鬼,在精神上也遭到世人的棄絕。加繆從人生到創作到思想均體現出“異鄉人意識”,進而成為如他一樣處于夾縫中的千千萬萬個身份迷茫者、無根者的“心靈”代言人。
三、正義者的悲劇
二戰前后巴黎文化圈的政治撕扯,讓加繆從一個精力充沛的激進分子轉變為一個溫和的改良分子。他拋棄了誘人的政治神話,拒絕選擇立場。特別是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他譴責法國殖民制度和法國軍隊的殘酷鎮壓,同時拒絕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主義襲擊戰術。(10) 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和一位詰問者有過一段著名的交鋒,他為自己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拒絕站隊作出辯護:“我一直譴責恐怖。因此我必須譴責一種,比如說,在阿爾及利亞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義,有朝一日它會襲擊我的母親或我的家人。”(11)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在于采取立場,而是在不存在立場的地方拒絕采取立場。人活著,不但要靠正義,也要追求良心的清白。這也是加繆的戲劇《正義者》(1949年)中所傳達的主題。
《正義者》是一部悲劇作品,其悲劇性體現在主人公卡利亞耶夫在正義與愛之間做出的艱難選擇。類似于狄更斯《雙城記》中揭示的革命困境:一方面,革命是出于不正義而做出的反抗行為;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在反抗中會產生邪惡。換句話說,一面是革命的正義,一面是革命的不義。《正義者》取材于1905年俄國社會革命黨的一個恐怖小組用炸彈炸死皇叔塞爾日大公的真實歷史事件。劇中,年輕的蘇聯詩人和革命者卡利亞耶夫參加了暗殺任務,奉命炸死塞爾日大公。可是當他手持炸彈瞄準大公疾馳而過的馬車時,卻發現車上還坐著兩個孩子——大公的侄兒侄女,他的手顫抖了,他的心遲疑了,于是冒著極大風險,臨時取消暗殺行動。后來,他再次尋找機會成功殺死了塞爾日大公。但他還是因為未能擺脫良心的不安和自責,不僅拒絕了敵人的赦免,還主動走向絞刑架,試圖通過死亡為自己的行為凈罪,贖回暗殺的恥辱和非正義。(12)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傾向于表現比今天的人好的人。”(13)卡利亞耶夫是渴望愛和健全的正義的人。第一次刺殺任務中,他在危急時刻毅然取消任務,放下了對準孩子們的炸彈。行動敗北,讓他意識到暗殺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為了推翻舊制度,解放俄羅斯,他必須殺死大使,但是這所謂的“為了正義”的刺殺行動必定要導致暴力流血,又與其健全的正義背道而馳——卡利亞耶夫承受著愛與正義的撕裂。他的戀人多拉也提醒:“流血太多。暴力行為太多。真正熱愛正義的人,是沒有權利愛的。他們都訓練成我這樣,昂首挺胸,目不斜視。在這些自豪的心中,哪有愛的容身之處?愛,雅奈克,就是微微低下頭。”(14)而在卡利亞耶夫的世界里,正義與愛之間有著絕對的沖突和無法逾越的界限。卡利亞耶夫只能犧牲愛,去追求正義。(15)
在20世紀極權政治的語言泡沫中思考的加繆,與法國大革命后的德國作家荷爾德林視通意合。在為革命帶來的解放而歡呼后,他們都逐漸意識到了革命的局限,從而轉向對革命的失望和懷疑。加繆試圖在時代轉折與人心劇變的年代,利用悲劇電光石火的藝術力量,探索人類進步中的痛苦。加繆認為,悲劇沖突的原因是人的無度——人唯我獨尊,試圖以自義來徹底否定他義。在諾貝爾文學獎致謝詞中,加繆說,藝術家的使命是要防止這個世界分崩離析,而要防止世界的分崩離析,則要效法古希臘悲劇時期的反思和節制的美德,這是現代人自我救贖的良藥。
真正的正義是愛。卡利亞耶夫最后的犧牲有一種圣徒氣質,犧牲自我,更加接近愛。因為身處所謂的“正義”和愛的撕扯中,他需要為自己犯下的暴力屠殺行為贖罪,從而救贖自己的靈魂。在非正義的社會環境中,正義者也無法實現踐行正義的理想,他們會被現實無情地拖入罪惡的深淵。所以在非人的環境中,正義者是注定要品嘗悲劇的。加繆作品中正義與反抗暴力的合法化努力,在風起云涌的歷史激蕩中抗擊非正義,最后匯集成筆下一個個追求愛與自由的戰士。
四、局外人的荒誕與反抗
荒誕以及如何對待荒誕,是加繆文學作品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在《局外人》《西西弗神話》《鼠疫》等作品中,加繆先是發現了荒誕,指出荒誕是人存在的一種必然狀態。荒誕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兩者的共存。認識到兩者的對立,就是認識到了荒誕。(16) 發現了荒誕,然后呢?加繆早在1938年《評讓—保爾·薩特的〈惡心〉》一文中指出:“看到生活的荒誕,這還不能成為目的,而僅僅是個起點。這是一個真理,幾乎所有的偉大思想都由此起步。令人感興趣不是發現(荒誕),而是人從其中引出的結論和行動準則。”(17) 面對荒誕,加繆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種態度。第一種是生理上的自殺。既然荒誕存在于人與世界的共存,那么自殺就是一種自行消滅,是一種逃避荒誕的終極手段,當然也是一種消極逃避、俯首投降的姿態。第二種是哲學上的自殺,也就是信仰某種宗教,企圖寄希望于某種神、來世或者天堂來回避現實生活的荒誕,這是精神的逃避。加繆自己則主張第三種態度,那就是直視生活的荒誕,堅持奮斗,勇敢抗爭。
《局外人》是加繆1942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說,是關于“發現荒誕”的作品。故事主要圍繞一樁命案及其法律程序進行。主人公默爾索是一個“反英雄”。他不同于文學史中那些積極入世、執著勇敢的主人公,他對待親人、同事、朋友、周圍發生的事情、自己的命運、前途的態度都是漠然的、超脫的、無所謂的。他看起來不近人情、冷漠孤僻、渾渾噩噩。因為在母親死亡下葬的過程中,他表現得異常冷靜,甚至無動于衷,人們給他貼上了冷血的標簽。在社會世俗觀念面前,他是局外人。然而默爾索其實是個活得很清醒真實的人。他拒絕說謊、不耍花招、拒絕矯飾自己的感情。最后他被卷入一場謀殺案,但因為社會世俗早已斷定他是一個毫無人性、違背社會道義的人,在案件的預審、庭審、起訴、審訊、辯護直至判決的整個過程中,他始終被排除在決策之外,處于一個局外人的位置。(18) 加繆曾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19) 這種近乎荒謬的說法背后隱藏著一個嚴酷的邏輯:任何違背社會基本原則的個體,都將遭受社會的制裁。然而,這種制裁本身卻暴露了現代司法程序的矛盾和司法體系的荒謬性。默爾索在被處死前拒絕向神父懺悔,拒絕信仰上帝。他看透了一切,不僅看透了司法的荒謬、宗教的虛妄,而且也看透了人類生存狀況的尷尬與荒誕。所以,《局外人》是一本“荒誕的證明”,是關于“發現荒誕”的書。
局外人是認識到荒誕的人,但是面對荒誕最重要的不是認識,而是如何應對。前文提到加繆面對荒誕的態度是抵抗。這種態度不是人人利己的巴黎文化圈滋養出來的,也不是見證戰爭的歷史淬煉出來的,而是要回溯到加繆在阿爾及爾貝爾庫的早期生活。加繆父親死于一戰,母親卡特琳·桑特深受刺激,幾乎失聰。但是生活要繼續,她帶著加繆兄弟倆投奔娘家,做傭人艱難度日。因為母親失聰,口頭交流也很有限,所以加繆的早期生活是在沉默的貧窮中度過的。在《第一個人》中,他對母親的生活狀態進行了描述。于她而言,生活幾乎是無望的:沒有丈夫,沒有依靠,家徒四壁,她跪著擦地板,生活在別人油膩的縫隙和骯臟的抹布之中。一天又一天的漫長的勞動,累積成這樣一種沒有希望的生活,沒有憤怒、沒有意識、堅持操守的一種生活,平靜地接受各種痛苦。晚上加繆從學校回到家,看到夜幕降臨在母親身邊,她的無聲傳達了一種無可救藥的荒蕪。對于年輕的加繆來說,母親“動物般的沉默”不僅讓她拒人于千里之外,也讓她情感孤獨,即便加繆對母親無比憐愛,卻也無能為力。這種看似無望的生活是如此荒誕,母親卻日復一日,因為生活即使再無望,她的信念也沒有被打垮,她仍被自己作為母親的責任支撐著,在絕望中尋找希望,默默反抗生活給她的磋磨。整個一生,加繆都看到她躲在那種看不見的障礙背后——溫順、謙虛、殷勤,甚至恭順,但從未被任何人或任何事所征服。她由于半聾而孤獨,表達困難,但無疑美麗,道德上高不可攀。她是加繆生命中的第一個西西弗,推石上山,無休止地做著“無用且無望的工作”,而推石任務本身就足以使人內心充實。母親的生活是不幸的,但幸運的是她默默承擔起自己作為母親的職責,在履行職責的艱難過程中實現對荒誕的反抗和制勝。
這種積極的反抗精神也很好地體現在《鼠疫》這部小說中。醞釀這部小說期間,加繆因二戰流離失所,沿著荒誕哲學,戰爭災難,法西斯勢力猖獗肆虐,自然而然與自然災害聯系到了一起。《鼠疫》出版于1947年。戰后的法國讀者將這部小說與納粹侵略的經歷聯系起來,因為法國人將納粹占領稱為“褐色鼠疫”(占領法國的德國士兵軍裝為褐色),所以《鼠疫》是一部象征小說。
疫病狂襲,奧蘭城里人們大批大批地死亡,這也是納粹陰霾下歐洲的真實寫照。奧蘭城的居民在面臨災難性疫情的威脅時,展現出了團結和協作的精神,共同抵抗瘟疫。這象征著20世紀40年代,國際民主力量和法國抵抗運動在抗擊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斗爭中所表現出的堅定和勇氣。奧蘭城人民最終戰勝了鼠疫,這象征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傳遞了希望和勝利的信息。小說中,貝爾納·里約醫生頑強抗擊疫病的精神最為人所動容,他深知醫學的力量有限,難以消滅鼠疫,但他仍忠于職守,醫治病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日夜奔波,廢寢忘食,不顧個人安危與危險周旋。面對困難和挑戰,他從不屈服,持續與鼠疫抗爭。他的辛勤、堅韌和勇氣,就像西西弗斯不斷推石上山的不屈不撓。這種精神感染了周圍的人,激勵他們不放棄、不屈服、不投降,團結起來,共同對抗瘟疫的侵襲。與貝爾納·里約相對照或相補充的人物有巴勒魯、約瑟夫·格朗、雷蒙·朗貝爾等。巴勒魯是個正直高尚的神父,但他深信鼠疫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只能聽憑上帝的安排。他面對荒誕的世界,放棄與現實抗爭,消極避世,選擇依賴虛妄的上帝,正是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所批判的“哲學自殺”。但最后,在事實的沖擊下,巴勒魯也投入了抗擊鼠疫的斗爭。約瑟夫·格朗是另一個西西弗斯,他在抗疫斗爭中堅守崗位,埋頭苦干,是一位默默無聞無關緊要的英雄。雷蒙·朗貝爾是一個充滿浪漫情懷的人,他渴望幸福的生活和激情四射的愛情。然而當鼠疫橫行時,他堅定地將個人的情感和幸福放在第二位,選擇承擔起高尚的責任,與眾人并肩作戰,共同面對挑戰。
加繆通過這群青年人在艱苦而可怕的戰疫中,完美展現了人類反抗荒誕、反抗惡的精神風貌,也將荒誕哲學推向了頂峰。雖說加繆從來就否認自己哲學家的身份,“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也從來沒有這樣自稱過”(20)。筆者也很愿意尊重加繆對自己不是哲學家的定位,但他在文學作品里卻實在地抒發了一種哲學表達。因為小說從來都是形象的哲學,形象與哲學水乳交融。加繆的荒誕哲學也是從文學寫作中展現出來的。試想,作家為何要寫數十萬字的小說?洋洋萬言后的字斟句酌、案牘勞形,其實就是在闡釋一種生活的哲思。加繆的哲學表達正是在于,他立足于荒誕,勇于反抗荒誕,并由此形成了他的荒誕理論:面對荒誕現實反抗到底,反抗本身就充滿意義,反抗本身體現出作家肩負起的對自己和社會的責任。
五、結語:加繆小說的思想史價值
通過梳理加繆的生平軌跡、文學創作和思想理念之間的基本聯系,我們可以發現,加繆的小說描繪了在充滿罪惡的世界中人們如何勇敢抗爭,以及在荒謬的現實中人們如何帶著痛苦堅持生活的勇氣。他在不同小說中所塑造的角色,無論是那些與時代格格不入的邊緣人,還是那些追求愛與公正的道德者,亦或是那些反抗命運的局外人,都深深融入其政治行動和社會責任感之中。這些角色不僅體現了加繆對愛與責任的追求,也深刻地展示了其小說的跨文化價值。作者就像讀者的朋友,以講故事的方式邀請讀者一起參與精神的探索之旅,其中既有感情的投入又有理性的認知。加繆筆下那些頑強的靈魂,是其所生活時代的局外人。一定意義上,所有的自傳都在講故事,所有創作都是一種自傳。加繆也是那個風云變化的時代的局外人,是“百無一用的先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加繆的文字仍然帶著人性的溫度,最大限度地保護那些失去發言權的人不被作為代價而遭到無情碾壓。
《西西弗神話》是加繆根據希臘神話改編的哲理文集。西西弗斯觸怒了眾神,成為了天界的流放者,也是天界的“局外人”。他被判終身做苦役,將一塊巨大的石頭推上山頂。然而,每當巨石到達山頂,它就會立刻滾落,迫使西西弗斯再次下山,重新開始他的勞作。他被迫不斷地重復這種看似“無用且無望”的工作,循環往復,永無休止。眾神認為,沒有什么比這種無效且無盡頭的勞役更令人恐懼的懲罰了。加繆表示自己感興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西弗斯。“我注意到此公再次下山時,邁著沉重而均勻的步伐,走向他不知盡頭的苦海。”(21) 西西弗斯意識到了自己悲慘的命運。但他勇敢地面對那塊巨石,再次將其推向山頂。在他下山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對命運的蔑視、挑戰和反抗的精神。因此“攀登山頂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實一顆人心。應當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22)。加繆的行動準則是挑戰,是反抗,既要認識到現實的局限性,又要義無反顧地生活。加繆把荒誕等同于笛卡爾的懷疑,“我反抗故我在”,以此為出發點,尋求和創造人類的幸福。(23) 世界工人們的勞動無異于西西弗斯的苦役,西西弗斯是天上的無產者,他的苦役象征著人類的命運,但面對苦役,西西弗斯那種正視荒誕、戰勝荒誕的精神卻是積極的,也是人生的正確打開方式。
加繆的這種可貴精神和價值立場,啟迪著后代作家的文學創作,其文學思想所揭橥的責任與愛,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活著,就是帶著世界賦予我們的傷痕前行,用我們不完美的雙手去撫慰彼此的傷痛,堅定地追求幸福。因為沒有任何命運是作為對人的懲罰而存在的,只要我們全力以赴,就應當感到幸福。擁抱現實中的光明,不將希望寄托于遙不可及的烏托邦,保持振奮和昂揚的態度,生存本身便是對荒謬最有力的回擊。正是這樣的價值影響,加繆完成了跨文化身份意義的深度發掘,其源自人生的文學審美追求,最終朝向人類的思想史追求,在“文學是人學”的永恒主題下,開創了屬于自己的關于自由與孤獨、虛無與抵抗的文學創作。
注釋:
(1) 黃曼君:《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與延傳》,《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2) 黃曼君:《新文學傳統與經典闡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頁。
(3)(4) 阿爾貝·加繆:《第一個人》,劉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
(5)(6)(8)(11)(20) 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布羅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章樂天譯,新星出版社2007版,第115、115、143、152、102頁。
(7) 愛德華·休斯:《加繆》,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頁。
(9) 阿爾貝·加繆:《蒂巴薩的婚禮》,郭宏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頁。
(10) 菲利普·羅杰:《加繆的永恒回歸》,郭真珍 、卓悅譯,《文藝理論研究》 2022年第1期。
(12)(15) 劉文瑾:《正義者的悲劇——試論加繆〈正義者〉中的悲劇性》,《跨文化對話》第39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450、453頁。
(13) 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8頁。
(14) 阿爾貝·加繆:《正義者》,李玉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頁。
(16)(19)(23) 郭宏安:《法國文學講演錄》,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73、167—168頁。
(17) 阿爾貝·加繆:《評讓—保爾·薩特的〈惡心〉》,楊林譯,《文藝理論譯叢》第3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5頁。
(18) 柳鳴九主編:《加繆全集:小說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15頁。
(21)(22) 阿爾貝·加繆:《西西弗神話》,沈志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131頁。
作者簡介:張甜,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