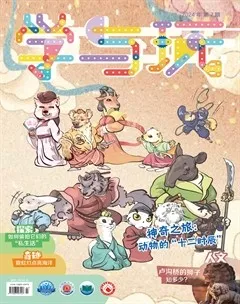中國國家海洋博物館:讀懂大海這部“無字書”
中國國家海洋博物館坐落在天津東部,緊鄰渤海。
這座巨大建筑物容納的一個個展廳,講述著人類與海洋漫長的因緣。
海水覆蓋地球表面的比例,決定了這顆星球在太空中的模樣。
人們通過海洋聯絡彼此,建立起今天的文明。
而在大海深處,還有很多奧秘等待人們去發現。
無懼“海怪”勇敢出航
國家海洋博物館的“今日海洋”展區,是從一件巨大的大王烏賊塑化標本開始的。這只比人還要大的軟體動物,曾經在實驗室里接受了特殊的處理——它的肉身被一點點替換成高分子材料,保留下栩栩如生的模樣,仿佛仍然在海中游泳。
幾個世紀以來,大王烏賊和體型略大于它的“親戚”——世界上體型最大的軟體動物大王酸漿魷,還有更為聰慧的章魚,都曾是各種“海怪”傳說的主角。人們曾經以為這些巨大的軟體動物能擁有超過大帆船的體型,可以用觸手將船只和冒險者卷入海中。然而,真正的大王烏賊幾乎只能達到與塑化標本相當的尺寸,雖然在海上突然遇見會覺得可怕,卻不會對船只構成威脅。不過,在人類難以抵達的大洋深處,生活著哪些未知的生命,我們現在還很難知曉。
“生命自會找到出路”
海洋覆蓋了地球表面71% 的面積,從太空中看去,地球擁有著迷人的藍色,是個名副其實的“水球”。而在不同溫度與不同深度的水中,都可以找到適應這些環境的生命。海水對陽光的阻擋,使大約1000 米之下的深海一片漆黑,但仍然有一些動物克服了黑暗帶來的不便,棲息于此,并且演化出獨特的生存之道。
在深海中遇到配偶非常不易,因此鮟鱇(ānkāng)魚演化出了獨特的繁殖策略,雄魚和雌魚的體型相差極為懸殊,雄魚只要遇到雌魚便會“寄生”在它的身上,頭部漸漸融入雌魚的身體。最終,雄魚會成為雌魚身上的一個器官。
深海雖然黑漆漆一片,但也并非只有荒涼。在富含硫化物的海底熱泉,也就是深海“黑煙囪”周圍,生活著依靠化學物質來養育自己的微生物。從它們開始,大洋深處形成了一個無需植物光合作用作為基礎的獨特的食物鏈,讓我們得以了解地球剛剛擁有生命時的模樣;鯨類死亡后沉入海底形成的“鯨落”,如同深海中臨時性的市集,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各種生命會逐漸分解鯨類的遺體,讓原本荒涼的深海“熱鬧”起來,直到再沒有資源可分,鯨類的骨架便會成為礁石的一部分。而在地球上不同緯度的海洋,溫度和洋流也在塑造著居住在那里的生命。實際上,地球上分布最靠北的企鵝,竟然可以在赤道附近生活。在南美洲的西部,秘魯寒流將南極洲的寒氣向北輸送,為加拉帕戈斯企鵝在赤道營造出更寒冷的環境。
航海,了解世界樣貌
由于世界各地的海洋連為一體,因此人們可以乘坐船只環球航行,探索世界各地不同區域的樣貌,了解當地動物的生存之道。在“航海發現之旅”展區,展現了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乘坐“貝格爾”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島進行航海探險,發現了生命演化的奧秘的故事。一代代探險家通過航海,前往遠離“文明中心”的非洲叢林、草原、極地冰原,以及長期以來與世隔絕的“南方大陸”——澳大利亞,逐漸補上了世界地圖上的空白,對當地動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研究,也讓人們認識到世界各地的動物們差異巨大的生存之道。
隨著世界越發緊密地連為一體,人類曾經因為考慮欠周,將一些動物引入原本不屬于它們的生存空間,最終造成難以控制的危害。在反映歐洲人探訪澳大利亞的展柜里,一只幾乎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小兔子,提醒著我們生物入侵的嚴重后果——為了在澳大利亞狩獵,一位移民將24 只兔子釋放到野外。兔子不受控制的繁殖,成為嚴重沖擊澳大利亞畜牧業的災難,直到兔子的瘋狂繁殖被兔黏液瘤病毒所遏制,才勉強達成微妙的平衡。
在中國國家海洋博物館里看過一個個關于生存的故事后,我們不禁會為大自然的偉力所折服。正如科幻小說《侏羅紀公園》所說的那樣: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而人類需要對大自然的創造懷有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