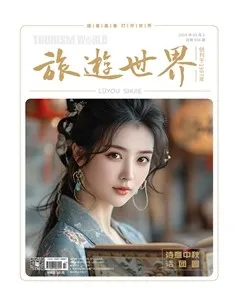《封禪儀記》:泰山游記的開山之作

《封禪儀記》,東漢馬第伯創作的散文,記錄了漢光武帝封禪泰山的經過。雖早佚,但幸有東漢泰山太守應劭將其載錄于《漢官儀》中而流傳。宋代之后,應劭的《漢官儀》亦大部亡失,后人可睹者有南梁劉昭為《后漢書· 祭祀志》作注所存的《封禪儀記》。《封禪儀記》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一篇游記,是早期描繪泰山山水、風物的佳作,對后世文學影響較大,史料價值日益凸顯。
敘事:足為史鑒
東漢建武元年(25),光武帝劉秀即位。建武三十二年(56)光武“奉圖書之瑞”,于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馬第伯作為劉秀身邊隨行的侍從官,將他親聞、親見、親歷之事詳實記錄于《封禪儀記》,其文獻性更為真實、豐富,可彌補一般史書之不足。其中,很多資料具有唯一性。
治泰山道: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
……
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
泰山很早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就登山的道路而言就有周御道、秦御道、漢御道之說,但對道路修治的記述尚屬首次。光武帝的這次封禪先后驅使“道徒”“五百人”“千人”修治其道,可見工程量巨大,不過從時間上看,應主要是道路阻礙的清理及平整。在這段文字中,從光武帝啟程、至魯,再到泰山,相應的具體事項安排,在時間上具體、明確。
封禪助祭:
……(二月)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洛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
關于這一方面的信息,《后漢書·祭祀志》僅提示“漢賓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東后,藩王十二,咸來助祭”。而以《封禪儀記》所記較之,更為詳實。這為進一步研究東漢封禪從封成員的構成,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封禪立石:
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
秦始皇、漢武帝封禪,都有立石頌其功德的刻石,故在相關記載中有“上石”“立石”的說法,但往往為人所誤。如現立于岱頂的無字碑,因“無字”而多疑惑。有云:漢武帝以為功高蓋世無以文對,故無字。或云:由“無字”委推于秦始皇,“本意欲焚書, 立碑故無字”。
《封禪儀記》的記載清晰明了,封禪刻石有二:一為“立石”,一為“功德石”。“立石”是封的標志石,也號封石(即“壇上方石”),自然無字;“功德石”也就是紀功刻石,一定會有文字。“無字碑”是封石,本就不應該有刻字。有了其所記封禪“石二枚”,一枚“立石”,一枚“紀功”石,無字碑無字的疑問迎刃而解。
風物習俗:
早食上,晡后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壇,見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詔問其故,主者曰: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上曰:封禪大禮,千載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
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黃河去泰山二百余里,于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址。……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始皇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為五大夫。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
“置錢物壇上”“散錢”“置梨棗錢于道”,這些泰山封禪祭祀遺俗,不見于其他書冊中。泰山日出,是歷代文人騷客所歌詠、贊美的奇觀,馬第伯的“雞一鳴時,見日……”“欲出”“長三丈所”是對泰山日出的首次記載。所謂“四觀”的說法,也是首次出現在泰山的史料中。山下的岱廟,以柏樹為特點,且其樹為漢武帝所植,是對廟貌特點最早的記述。還有“玉盤”“玉龜”“神泉”之說,也首見于其記。
寫景:另辟蹊徑
《封禪儀記》圍繞封禪這一主題事件,以時間為軸記錄其所歷、所見、所感。似乎有所“跑題”,馬第伯關注最多的還是登泰山的整個歷程。一路走來,山水相擁,峰回路轉,別有洞天。“極望”“仰視”,其人、其道、其石、其峰、其水,視覺的、心理的,虛實相生,物我交融。
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端如桿升,或以為小白石,或以為冰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赍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己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郁郁蒼蒼,若在云中。……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窗矣。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后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后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蹀蹀據居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
……
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這一部分在《封禪儀記》中最為搶眼。從“是朝”上,到“日入”下,是一整天的歷程。
記錄行程,寫景狀物。從馬第伯提到的地名及當時人文地理環境來看,光武帝是從“東御道”上山,入山口位于今天燭峰景區(大津口鄉上梨園)。這是一條山脈較為開闊的溪谷,地勢相對平緩。沿溪西上可達中天門。從山下到“中觀”(大致相當于今之中天門)的行程中,雖然道路“峻峭”,但尚可步、騎相替,到了“中觀”只好“留馬”步登。登途之中,可見“處處有泉水”“巖石松樹,郁郁蒼蒼”。而艱難的“天關”(今之南天門)之登,步足難開,一路險阻。最困苦的是“直上七里”,依靠“絙索”方可登也,乃至疲憊不堪,兩腳不聽使喚。落日下山,傍晚又有雨霧遮道,尚需有人在前探知路徑。到達天門下,已經是夜深人靜。寫景記行,山路難、人勞困。上山、下山,時間、地點,具體完整。路途經歷,曲折多變、驚心動魄。
以視覺感受, 言山之高。馬第伯用“ 極望”“仰望”,寫泰山之高。他們到達“中觀”,這時的高度“去平地二十里”,放眼南去已是“極望無不睹”。北向而視,則只能抬頭“仰望”,望天門“如視浮云”。近觀,石壁遮目,道徑難尋。“遙望”遠處之人,端立如光禿之朽木,“或以為白石或以為冰雪”,因有所移動“乃知是人也”。到達天門之下,視天門如視“天窗”,是在由下而上的“直望”。登山者“后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后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極強畫面感如同現實影像。馬第伯又記:“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嵩山。”同樣,也在說泰山之高,于此可觀日、觀秦、觀會稽,觀嵩山。
以肢體感受,寫登山之難。天門似“殊不可上”,登山者心神疲憊,不得已只能“四布僵臥石上”獲取喘息,在食以“酒脯”后,并在“泉水”止渴明目的加持下,始有精神再登。文中的“磨胸”“石”“捫天” ,是用舉止動作來修飾上山之“難”。上山途中,初有“十余步一休”,后到“五六步一休”,先有“咽唇焦”的“稍疲”,再到 “目視而兩腳不隨”的疲勞過度,以致出現坐臥不擇干濕的窘迫境地。然正是經歷如此之“難”,才能于山頂 “四觀”,才有了“南向極望無不睹”、北瞻天門“如從谷底仰觀抗峰”的愜意。

謀篇:堪為范式
關于《封禪儀記》的文學屬性,歷代學者多有評判。其中,清·袁枚《古人摹仿》中說,“古人作文摹仿,痕跡未化,雖韓柳不免……柳子厚作記與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句調相似”。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字子厚),其山水游記一貫被視為典范之作,故人們每每說到游記,必以其論優劣。從以上評論看,作為山水記游的《封禪儀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柳氏之文對其還就有所效法。
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談及歷史上的游記之文,有如此批評: “按前此模山范水之文,惟馬第伯《封禪儀記》、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二篇跳出,其他辭、賦、書、志,佳處偶遭,可惋在碎,復苦板滯。吳之三書與酈道元《水經注》中寫景各節,輕倩之筆為刻劃之詞,實柳宗元以下游記之具體而微。”在教育部“面向21 世紀課程教材”《中國文學史》中,將馬第伯《封禪儀記》定義為“現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游記” 。
縱觀歷代評說,可見《封禪儀記》在中國山水游記中的崇高地位,它所具有的文學價值,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在體式上,以“雄渾雅壯”為特點。在描寫手法上,則以視覺為主導,大小、高低、遠近、色彩、動靜等,都會成為觸動文思的重要元素。以身體驗、用心感受,去察示人與景物的聯動契合。在語言上風格上,則“碎語如畫”,寫人狀物文字“極工”。《封禪儀記》是泰山歷史上現存最早的游記;同時,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山水游記體式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