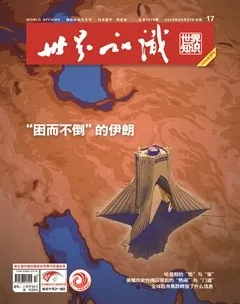中東“和解潮”以來,伊朗國內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近些年,尤其是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后,中東國家間普遍出現“和解潮”,伊朗作為地區大國和“抵抗軸心”領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23年4月,伊朗與其“地區夙敵”沙特的正式和解及其外溢效應,更是將“和解潮”推上高峰。
事實上,自2018年以來,伊朗便開始積極尋求與地區競爭國家緩和關系、加大合作,其主要動力是尋求在美國的“極限施壓”下維護國家政權和社會穩定。魯哈尼政府(2013~2021年)認為,通過緩和與沙特、阿聯酋等地區國家的關系,不僅可減少美國自中東戰略收縮的顧慮,還可減少美國重返伊朗核協議的阻力。而一旦美國撤出中東并重返伊朗核協議,伊朗長期面臨的外部安全威脅、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等困境都將大幅減弱。2021年8月,伊朗總統萊希上臺后,不僅延續了魯哈尼政府的務實主義外交路線,更將發展與周邊國家關系作為外交工作的優先方向,尤其是將緩和與海灣國家間關系作為重中之重,對魯哈尼政府以美西方為中心的外交政策做出調整。伊朗希望通過推動中東“和解潮”來為其擺脫當前困局創造契機,然而自“和解潮”以來,該國在國內政治與經濟層面都分別面臨哪些新挑戰,又將如何脫困?
“和解潮”以來伊朗的政治發展
2018年5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出爾反爾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并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后,伊朗民生狀況急劇惡化,社會不滿情緒增加,國家內政穩定性由此受到挑戰。此后,伊朗國內爆發了兩起全國性社會運動,分別是2019年因汽油價格上調引發的“八月運動”和2022年因女性佩戴頭巾問題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這兩場社會運動呈現出顯著的暴力性和跨界層性。
此外,伊朗參與選舉政治人口的大幅減少,是其內政穩定性遭遇挑戰的又一表現。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以來,伊朗選舉政治長期維持著較高投票率,通常在溫和改革派獲勝的選舉中,投票率更高。以總統選舉為例,伊朗第1~12屆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均在50%以上,其中改革派總統哈塔米勝選的第七屆(1997年)和第八屆(2001年)投票率分別為79.9%和66.8%,溫和派總統魯哈尼勝選的第11屆(2013年)和第12屆(2017年)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分別為72.9%和73.7%。但是,2021年保守派總統萊希勝選時投票率僅有48.7%,今年6月,改革派總統佩澤希齊揚參與的選舉第一輪投票率甚至不到40%。這表明,現階段多數伊朗民眾對改革失去信心。
與此同時,溫和務實勢力在伊朗政治中正逐漸占據優勢地位。自2013年魯哈尼政府執政以來,溫和務實勢力便一直占據優勢。相對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進勢力,溫和務實勢力傾向于通過對話和協商來解決分歧,愿同競爭派系合作,傾向于從國家經濟利益出發制定國內外政策,不僅僅以意識形態為行動綱領。盡管司法部出身的教士萊希經常被貼上“激進保守派”的標簽,但在其任期內,他一直保持著與美西方的溝通,并積極推動重振伊朗核協議。此外,雖然在其任期內出現了因頭巾問題引發的社會運動,但筆者在伊朗實地觀察發現,萊希政府實際上已大幅放松對女性佩戴頭巾的管控。新當選的佩澤希齊揚也是改革派中的溫和派,盡管他也支持限制教權、依法治國和保障公民權,但與保守派一樣,他堅定捍衛最高領袖的權威,公開表達對“伊斯蘭抵抗陣線”的堅定支持。正因如此,在此次總統選舉中,前議長阿里·拉里賈尼、前副議長阿里·莫塔哈里、最高領袖辦公室行政事務負責人瓦希德·哈加尼揚等重要的溫和保守派政客都支持佩澤希齊揚,議長加里巴夫也在第二輪選舉前轉而支持他。
在立法機構方面,在今年舉行的第12屆議會選舉中,盡管保守派仍占據多數席位,但是具有溫和務實傾向的保守派議員數量較上一屆議會增加了兩倍,務實保守派政客加里巴夫也以約68%的得票率連任議長。此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傾向于由一個“實干家”執掌政府,有報道稱他在第一輪投票中投了加里巴夫,在第二輪中投了佩澤希齊揚。就目前來看,溫和務實勢力逐漸占據政治優勢減少了伊朗國內各派系競爭帶來的內耗,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伊朗政治、經濟、安全和社會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國內輿論有關最高領袖繼承問題的討論正不斷增加。盡管前任總統萊希從未被正式任命為伊朗最高領袖繼承人,但是由于其最符合領袖繼承人的條件,尤其是擁有總統的行政經驗、合格的宗教資歷和圣裔身份,所以有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萊希有極高概率成為下任伊朗最高領袖。但在今年5月19日萊希意外墜機遇難后,最高領袖繼承人問題再度成為懸念,伊朗各政治勢力間正在激烈暗斗。不過,考慮到伊朗憲法中詳細規定了最高領袖的選拔和繼承程序,萊希遇難后伊朗行政權按照憲法規定也實現了平穩過渡,可以看出伊朗已達到較高政治制度化水平,由此可以預期,伊朗有較高概率將實現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
美國長期制裁下,深受經濟危機困擾
面對美西方的長期制裁,2014年2月,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與最高利益委員會、議會及政府高層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發布建設抵抗型經濟的24條綱領。哈梅內伊認為,伊朗有較好的基礎設施,民眾也有高漲的發展熱情,伊朗完全可以建設抵抗型經濟,抵御外部制裁及經濟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擺脫經濟困境,最終建立一個具有伊斯蘭特色的經濟體系,提高伊朗經濟的獨立性和韌性。此后,伊朗一直致力于通過增加國內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減少對外依賴,增加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來應對外部發起的“經濟戰”,以確保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隨著國家加大制造業補貼力度、增加投資、拓展反制裁渠道及改善與周邊國家關系,伊朗經濟在中東“和解潮”出現以來逐步復蘇。

據世界銀行數據,2020年伊朗國內生產總值(GDP)實現正增長,GDP增長率從2019年的-3.1%增加到2020年的3.3%,2021~2023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4.7%、3.8%和5%。伊朗的失業率也從2019年的10.74%下降到2023年的9.1%,青年群體失業率則從2019年的25.97%下降到2023年的22.79%,不過,雖然下降明顯,但伊朗整體失業率仍保持在高水平。
然而,盡管伊朗制造業取得一定發展,但其生產的多數產品僅能滿足國內需求,無法實現大量出口。此外,由于伊朗制造業發展嚴重依賴國家的外匯補貼和政策支持,因而以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業為主。在此情況下,2018年伊朗石油出口受美國制裁影響大幅減少后,伊朗對外貿易額在2020年、2022年和2023年都出現嚴重逆差,其中2023年第四季度的貿易逆差高達56.3億美元。
自2018年8月美國全面恢復對伊朗的單邊經濟和軍事制裁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減少,國家收入銳減。2018年伊朗石油收入為580億美元,2019年減少至260億美元,2020年進一步降低至210億美元。石油收入減少導致伊朗國家外匯儲備大幅縮水,進而引發嚴重經濟危機。
為保障基本民生,伊朗自2018年以來維持著對民生商品的高額補貼。以能源補貼為例,2020年伊朗對能源的補貼(包括汽油、電和天然氣)共計297億美元,占當年世界能源總補貼的16%。然而,這種高額補貼在財政收入減少的背景下進一步加劇政府的財政壓力。
隨著國家收入的減少和財政支出的增多,伊朗的貨幣供應量和政府預算赤字大幅增加。2019年春季,伊朗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5.3%,2020年春季則同比增長7.3%,遠高于同時期GDP增長率。2018年后,伊朗的預算赤字保持在高水平,2018年預算赤字為GDP的1.6%,2019年大幅增加至4.5%。截至2023年,伊朗預算赤字仍保持高位,約為GDP的5.5%。為彌補財政赤字,伊朗政府持續增加貨幣供應量,導致貨幣超發,進而造成通貨膨脹問題愈發嚴重,貨幣不斷貶值。2019~2022年,伊朗通貨膨脹率連續四年上升,分別為41.2%、47.1%、46.2%和46.5%。伊朗自由外匯市場美元兌換里亞爾的匯率從2019年的1∶11200跌到2024年7月的1∶58650,跌幅高達420%。通貨膨脹高企導致伊朗物價頻繁上漲,民眾生活水平不斷下降,貧困率從2018年的25%增至2019年的31%,此后便一直維持在30%左右。
從整體上看,盡管自中東“和解潮”出現以來伊朗的周邊環境和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在美西方的長期制裁下,伊朗仍處于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石油出口受限、財政赤字增加、通貨膨脹高企、貨幣貶值等問題仍困擾著伊朗。
新政府的脫困之策
今年7月30日,伊朗新任總統佩澤希齊揚宣誓就職。佩澤希齊揚于1997年加入改革派總統哈塔米的內閣,從而開始其政治生涯。2016~2020年,他曾任伊朗議會第一副議長。盡管佩澤希齊揚在競選時與宣誓就職后并未給出細化的政治經濟領域執政方案,但他在不同場合給出了其政府針對前述困境可能采取的破局之策。佩澤希齊揚在選舉中以“為了伊朗”為競選口號參與角逐,主張努力實現社會的“正義”“團結和凝聚力”。他在競選時承諾,將組建一個政府監督委員會,促進人民與政府、國家之間的聯系。為盡快緩解伊朗面臨的內政穩定性挑戰,佩澤希齊揚表示將尊重公民權,放松國家對社會的管制。同時,他認為女性有權自主決定是否佩戴頭巾,反對道德警察對頭巾佩戴不規范的女性采取強制措施。
佩澤希齊揚奉行以國家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他將努力推動西方國家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作為破解伊朗經濟困局的前提。佩澤希齊揚認為,阻礙伊朗經濟發展的直接原因是西方經濟制裁,深層原因是伊朗經濟的封閉及與世界缺乏互動,而根本原因則是伊朗沒有堅持以國家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平衡外交政策。因此,佩澤希齊揚在其政府任期內,或將把重振伊朗核協議、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改善與西方國家關系作為主要政策方向。此外,在經濟發展政策上,佩澤希齊揚表示不會在最高領袖提出的建設“抵抗型經濟”政策和既有的第七個“五年發展規劃”外提出新的系統方案,而是將通過提升政策完成率來實現經濟發展。佩澤希齊揚指出,當前,伊朗既有經濟計劃的完成率只有25%~30%,這主要是因為負責實施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規劃,也沒有遵循政策目標,同時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來落實相關工作。因此,佩澤希齊揚政府內閣主要由相關領域內的技術專家組成,專業務實將是其政府的主要特征。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