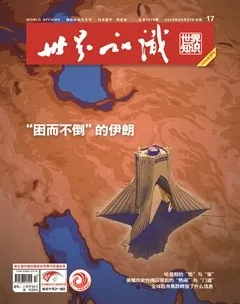西非多國與烏克蘭斷交,薩赫勒成美俄“斗法”前沿
8月上旬,西非地區掀起了一場頗受矚目的外交風波。馬里、尼日爾相繼宣布與烏克蘭斷絕外交關系,塞內加爾召見烏大使,布基納法索呼吁國際社會調查烏“支持恐怖主義”行徑,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譴責烏“干涉馬里和平與安全事務”。此次外交風波看似是烏克蘭干涉非洲國家內政,實則反映出美西方與俄羅斯在非洲圍繞多個議題展開的博弈愈演愈烈。
西非國家緣何動怒
6月以來,馬里政府軍在俄私營安保公司瓦格納人員的配合下,對盤踞馬里北部基達爾地區的圖阿雷格武裝分子開展清剿行動。7月25日,馬里政府軍與瓦格納組成的聯合巡邏隊向馬里北部邊境城市廷扎瓦滕挺進,打算奪取該地空置的軍事基地作為前沿陣地。然而,聯合巡邏隊遭遇了圖阿雷格武裝分子攔截,被迫撤往基達爾方向,撤退途中不慎落入陷阱,慘遭伏擊。“基地”組織分支“支持伊斯蘭與穆斯林組織”(JNIM)宣稱參與了此次伏擊。馬里政府軍與瓦格納此番損失慘重,但各方說法不一。圖阿雷格武裝分子表示,約有47名馬里士兵和84名瓦格納雇傭兵死亡。馬里官方和瓦格納均未給出具體數字,但表示確實遭受“重大損失”。這也是瓦格納進駐非洲以來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打擊。
7月29日,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發言人安德里·尤索夫表示,圖阿雷格武裝分子“收到了必要信息以及信息以外的東西”,對俄方人員“發動了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這一言論迅速點燃馬里政府的憤怒情緒。在馬里看來,烏克蘭無異于承認參與了武裝襲擊。8月4日,馬里宣布與烏克蘭斷交。恐怖組織的介入讓烏克蘭的情報活動“變了味”,使其被扣上了“支持恐怖主義”的帽子。盡管烏克蘭隨后極力否認參與此次行動,但該事件的負面影響卻在持續發酵。8月6日,尼日爾宣布與烏克蘭斷交,政府發言人阿馬杜·阿卜杜拉馬內表示,“譴責烏克蘭對恐怖組織的支持,尼日爾完全支持馬里政府和人民”。這一事件再次凸顯了非洲馬里地區復雜多變的安全局勢,以及背后可能涉及的國際博弈。
俄加速“重返非洲”,烏推進對非外交
烏克蘭干涉馬里內政反映出美西方對俄在非洲發起的新一輪攻勢,將非洲進一步卷入大國博弈的漩渦之中。俄在非洲的軍事安全存在再度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
冷戰時期,蘇聯曾向非洲多國提供援助,支持非洲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并藉此與美國爭奪“勢力范圍”。蘇聯解體后,伴隨俄實力的衰落,俄非關系一度陷入低谷,非洲在俄外交戰略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后,面對西方圍追堵截,俄迫切需要強化與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為此,俄積極尋求俄非利益契合點,多措并舉加強對非戰略投入力度。
俄將非洲視為打破西方外交孤立、爭取“全球南方”支持的重要地緣伙伴。2023年俄新版《外交政策構想》將非洲的外交優先次序由上一版的第十位提升至第六位。2022年以來,俄外長拉夫羅夫先后六次訪問非洲,涉及18個國家,主要集中在薩赫勒、非洲之角以及南部非洲地區。俄還借助多邊會議,拉近與非洲國家距離。2023年7月,俄舉辦第二屆俄非峰會,非洲49國參加。
俄還善用自身優勢,深化與非洲利益捆綁。一是強化在非軍事部署。近年來,俄依托瓦格納進入中非共和國、莫桑比克、馬里、布基納法索、尼日爾等國,通過提供軍事培訓、高層安保和一線反恐作戰等服務,全面強化對非洲軍事安全事務影響力。2023年11月,俄將瓦格納等七家私營安保公司整合為“非洲軍團”,重新派入馬里、布基納法索等七國。俄還是非洲最主要的軍事裝備供應國,與40余個非洲國家簽署了軍事技術合作協議,向其提供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二是以糧食援助拉緊非洲。2020年以來,受內外多重因素影響,非洲多國深陷糧食危機。俄加大對在非重點合作國的糧援力度,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共向非洲出口糧食2150萬噸。在第二屆俄非峰會上,普京表示向布基納法索、津巴布韋、馬里等六國無償提供2.5萬噸至5萬噸糧食。

三是擴大對非能源合作。2022~2023年間,俄原油、石油產品、液化天然氣對非出口增加1.6倍。俄還加大對非能源基礎設施投資,俄非洲能源商會表示將參與非洲多國液化天然氣基建項目。近期,俄企許諾將向馬里投資2.17億美元,支持其太陽能發電廠建設。
俄對非經略成效明顯,非洲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對俄“最友好”的地緣力量。例如,在2022年3月聯合國大會涉烏克蘭危機第一次投票中,非洲有17國棄權,一國反對,28國贊成。而在2023年12月最近一次投票中,非洲有34國棄權,六國反對,僅三國贊成。蓋洛普公司最新民調顯示,2023年俄在非洲的支持率為42%,比2022年提升八個百分點。俄在薩赫勒地區國家中的支持率尤為高漲,如馬里為89%、布基納法索為81%、乍得為76%。
事實上,烏克蘭也在推進對非外交,以爭取“全球南方”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持,同時對抗俄在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2022年7月,烏克蘭任命了非洲和中東問題特別代表,還在非洲增設大使館,增進與非洲國家高層互動,外長庫列巴2022年和2023年曾三度出訪非洲。今年8月4日至8日,庫列巴接連訪問馬拉維、贊比亞和毛里求斯三國,這也是烏外長歷史上首次到訪上述國家。在烏高層非洲之行中,烏邀請非洲國家參與烏克蘭危機解決,另外,貿易、向基輔提供武器是烏與非洲國家進行商討的主要議題。
美俄在地區博弈進入新階段
俄在非影響力提升的同時,美、法等西方國家在非霸權體系相應衰落。2020年以來,薩赫勒三國馬里、布基納法索、尼日爾相繼發生政變,軍政府上臺后外交急劇轉向。政變前,三國均為歐美在該地區反恐的重要盟友,接受了大量西方援助。政變后,三國先后廢除與法簽署的防務協定,驅逐法國駐軍。法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一落千丈,“非洲憲兵”的歷史趨于終結。
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也未能“幸免于難”。尼日爾發生政變后,美曾試圖通過外交渠道維持與尼軍政府的溝通,確保其在當地的兩個軍事基地免遭波及。特別是位于尼北部的阿加德茲空軍基地,建設投資超一億美元,是支持美在北非和薩赫勒地區搜集情報、開展地面行動的唯一基地。不料今年4月,尼軍政府譴責美干涉其內政,正式要求美軍撤離。乍得過渡政府緊隨其后,以美未提交駐軍協議文件為由,也要求美軍限期撤離。截至8月5日,美軍駐尼日爾1000名士兵完成撤離。據《華盛頓郵報》援引一名美國官員的話稱,美俄在薩赫勒地區博弈已進入新階段。
法、美相繼撤出導致薩赫勒地區出現巨大“安全真空”,為俄羅斯進一步拓展其影響力提供重要契機。2023年11月,第一批俄軍事人員進駐布基納法索,后又有100名軍事顧問抵達。俄還同意在尼日爾部署防空系統,幫助其組建和訓練軍隊。乍得也表示希望與俄開展軍事合作,獲得俄軍事技術裝備。目前,俄“非洲軍團”在薩赫勒三國共有約1400人,且未來還有增加的趨勢;法國則在中西非地區仍有2300余名駐軍,但其已計劃在未來數月將兵力降至600人。美國在該地區已無常駐軍事人員,僅與部分國家以聯演聯訓、定期輪換等方式實現常態化存在。
西方國家在反思其非洲政策時,聚焦對反恐策略的成效評估,指出因未能協同推進安全、發展、外交政策,導致其反恐效果不彰、非洲國家經濟衰退,最終誘發政變以及西方在非的“全面潰敗”。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視俄羅斯為助推非洲政變和“反西方”的始作俑者,指責俄利用“虛假信息戰”散布西方“不實言論”誤導非洲民眾。
不過,針對俄羅斯在薩赫勒地區的強勢介入,美國等西方國家也不甘心“坐以待斃”,而是將目光投向緊鄰薩赫勒的西非沿海國家,試圖打造新的“安全支點”。據多家媒體報道,科特迪瓦已與美達成初步協議,同意美在該國西北部籌建軍事基地。科特迪瓦此前與美合作態勢良好,兩國軍隊定期開展反恐聯訓,美軍非洲司令部多次在該國舉辦“燧發槍”軍事演習。今年1月以來,美國務卿布林肯、非洲司令部司令邁克爾·蘭利等高級官員陸續訪問科特迪瓦。蘭利在訪問期間宣布,非洲司令部本年度將向科特迪瓦投入6500萬美元,用于打擊恐怖主義和確保其北部邊境安全。
總體來看,薩赫勒地區已成美西方與俄羅斯在非洲博弈的“前沿陣地”,俄暫時保持戰略領先優勢。可以預見,今后一段時間雙方在非角力會更趨激烈,俄烏在非洲的“斗法”或將持續上演。不過,大國在非博弈白熱化也將誘發更多不穩定因素,恐怖主義、部族分離武裝、有組織犯罪等本土安全威脅或將上升。
(作者分別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長、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