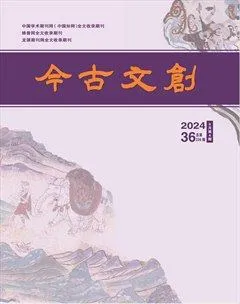創(chuàng)傷理論視角下《大地之上》中的多重創(chuàng)傷研究
【摘要】《大地之上》是印度裔加拿大作家羅欣頓·米斯特里的長篇代表作之一,作家以1975年前后女總理英迪拉·甘地的鐵腕統(tǒng)治下混亂的印度社會為背景進(jìn)行創(chuàng)作,那時的印度陷入政治、經(jīng)濟(jì)的雙重危機(jī)之中,在緊急狀態(tài)期間,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被剝奪,產(chǎn)生了強(qiáng)制絕育以及暴力拆毀貧民窟運動,社會動蕩不安。小說以一女三男的命運糾葛為主線,描繪了在特殊的年代中小人物的苦難和堅韌。本文運用創(chuàng)傷理論的相關(guān)觀點,結(jié)合社會歷史背景,對小說中主要人物遭受的創(chuàng)傷進(jìn)行剖析,旨在通過對主人公造成創(chuàng)傷的原因進(jìn)行分析,研究父權(quán)制、種姓制度以及社會政治環(huán)境對個體的摧殘,并尋求擺脫創(chuàng)傷的方法。
【關(guān)鍵詞】《大地之上》;創(chuàng)傷理論;父權(quán)制;種姓制度;現(xiàn)代化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36-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4
《大地之上》是羅欣頓·米斯特里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之一,該小說出版僅兩年便榮獲了加拿大最高文學(xué)獎吉勒獎以及英聯(lián)邦作家獎。印度裔作家米斯特里雖在二十多歲時移民到加拿大,但對印度的底層社會仍有著切身體會。小說中的四個主要角色,有拒絕再嫁、謀求自立的美貌寡婦迪娜,一對出身“賤民”階層、在種姓沖突的滅門慘案中幸存下來的裁縫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還有一個出自山區(qū)商人家庭、無法適應(yīng)城市生活的靦腆大學(xué)生馬內(nèi)克。小說中的四個主人公見證了1975年前后印度進(jìn)入緊急狀態(tài)時期社會歷史的變遷,也是不同家庭背景、性別與種姓的人所承受時代烙印和創(chuàng)傷的縮影。在迪娜身上,集中了印度社會對于單身女性的看法,反映出無法消弭的女性群體之傷,從迪娜少女時期的生活到她亡夫后獨自在外工作,都可見一斑。作為印度種姓制度里面“賤民”族群之一的裁縫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他們一生掙扎在種姓制度的陰影下,為此流離失所,身心飽受摧殘。而大學(xué)生馬內(nèi)克則因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城市化變遷等因素家庭受到影響,命運急轉(zhuǎn)直下。他們的人生經(jīng)歷都與外界的環(huán)境緊密相連,經(jīng)歷了暴動、宗教斗爭以及社會的種種不公,每個人都在社會中受到創(chuàng)傷。
創(chuàng)傷理論興起于戰(zhàn)爭頻發(fā)的20世紀(jì),由于兩次世界范圍內(nèi)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難以抹去的心理陰影,導(dǎo)致了創(chuàng)傷理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創(chuàng)傷”也是精神分析學(xué)的核心概念之一,對于弗洛伊德而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都經(jīng)歷過某種身體和心理的創(chuàng)傷。如今,創(chuàng)傷理論的發(fā)展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戰(zhàn)OHA7c96KAbjMcXWu8luZtGTmQhILid7wt4U9gPUi8Gc=爭等大規(guī)模創(chuàng)傷事件對個體心理產(chǎn)生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的小規(guī)模創(chuàng)傷事件,這些事件既有突發(fā)性的,例如交通事故,也有持續(xù)性的,如家庭暴力等。創(chuàng)傷理論作為一個跨學(xué)科的人文研究領(lǐng)域,近年來,逐漸受到文學(xué)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文學(xué)評論家運用創(chuàng)傷理論分析文學(xué)作品的覆蓋面頗廣,包括殖民創(chuàng)傷、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也包括女性、少數(shù)族裔因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經(jīng)歷的創(chuàng)傷。
《大地之上》作為一本兩年前才出版的新書,學(xué)術(shù)界對此書的關(guān)注度還不高。目前國內(nèi)學(xué)術(shù)期刊發(fā)表的相關(guān)論文也不多,學(xué)者們主要還是集中于對小說中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進(jìn)行解讀。其中朱希的《平衡與希望之歌——解讀羅欣頓·米斯特里〈大地之上〉》以“平衡”一詞為切入點,討論了四個主人公在人生和社會的雙重失衡中如何努力找到自己生命的平衡。綜觀有關(guān)《大地之上》的學(xué)術(shù)成果,可以發(fā)現(xiàn)落腳點幾乎都在探討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與他們面對苦難時的韌性,但是缺少對于造成苦難原因的分析。因此本文運用創(chuàng)傷理論,深入研究《大地之上》中造成底層人民受到的多重創(chuàng)傷及其原因。從創(chuàng)傷理論這一角度剖析文學(xué)著作,一方面可以研討文學(xué)著作中是如何體現(xiàn)和反映創(chuàng)傷的,另一方面可以分析作品中展現(xiàn)出來的有關(guān)個人、群體或社會的困境,并尋求解決方法。
一、無法消弭的女性群體之傷
“創(chuàng)傷”即指個體經(jīng)歷、目睹或遭遇一個或多個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者受到死亡的威脅,或軀體完整性受到威脅的情境。而個體在面對事件時產(chǎn)生的無助、恐懼等情感,或因創(chuàng)傷事件導(dǎo)致的長期對自己或他人的負(fù)面信念和預(yù)期,則被認(rèn)為創(chuàng)傷的主觀體驗。個體在創(chuàng)傷事件之后的反應(yīng)在情緒層面則表現(xiàn)為失去信心、失去自尊等。由于迪娜的家族屬于富裕的帕西族家庭,所以她并沒有像其他低種姓的印度女人受到來自宗教和種姓制度的雙重壓迫,但是迪娜的生活經(jīng)歷仍然反映了印度社會中婦女的低下地位給女性帶來的創(chuàng)傷。
(一)創(chuàng)傷表現(xiàn)——迪娜的成長之痛
迪娜出生于印度小康之家,是一個醫(yī)生的女兒,她的父親比同行都更加熱忱地踐行著希波拉底誓言,迪娜夢想像爸爸一樣做個醫(yī)生,但是父親的離世斷送了迪娜的夢想。迪娜的母親沉浸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無法自拔,并且她將導(dǎo)致丈夫死亡的責(zé)任推到了女兒身上,她認(rèn)為是由于女兒沒有成功勸說自己的父親不去參與醫(yī)療活動,進(jìn)而間接導(dǎo)致了丈夫的喪生。面對父親的離世和母親的責(zé)怪,迪娜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創(chuàng)傷。來自家人的指責(zé)讓迪娜不斷陷入“是因為我做錯事,他們才會責(zé)怪我”這一心理困境,導(dǎo)致即使她已經(jīng)長大成人,脫離了父母的世界,也難以擺脫愧疚的陰影。
父親死后,迪娜便淪為了哥哥努斯萬的奴隸,她遭受了哥哥的凌虐,這種凌虐帶給迪娜的創(chuàng)傷,不僅是在身體上,更多的是精神上。因為迪娜的哥哥,需要的是迪娜絕對的服從。由于努斯萬向來把父親看作厲行紀(jì)律的人,所以他認(rèn)為既然他要接過父親的角色,就必須讓其他人感到同樣的恐懼。當(dāng)?shù)夏鹊男惺律杂胁豁樧约旱男囊猓惚┨缋住2⑶耶?dāng)努斯萬從父親手上接過監(jiān)護(hù)迪娜的職責(zé)后,迪娜便失去了受教育的權(quán)利,她的夢想就此夭折了。在追求紀(jì)律的道路上,尺子成了努斯萬最常用的工具。除此之外,哥哥努斯萬還禁止迪娜剪短發(fā),禁止她拜訪朋友。年幼的迪娜在哥哥父權(quán)制的壓迫下,只能遵從哥哥的要求,沒有自由也沒有獨立的思想。
長大后的迪娜在一次次的壓迫中奮起反抗,拒絕了哥哥介紹的相親對象,與興趣相投的藥劑師魯斯圖姆自由戀愛結(jié)婚。年輕時她本以為遇到了可以遇到托付終身的伴侶,但是結(jié)婚三年后,丈夫遭遇車禍意外身亡。此后的幾十年,她獨自一人寡居在丈夫留下的一套小公寓中,靠縫縫補(bǔ)補(bǔ)的手藝勉強(qiáng)維持生計。但最終迪娜還是由于印度社會對于女性不平等的眼光,被沒收了房子,回到了哥哥家,又一次成了哥哥的用人。
迪娜的成長過程中充斥著來自哥哥努斯萬的暴力、傷害、虐待,這些都對迪娜的身體和心靈造成了無法消除的傷害。一旦有人試圖與迪娜建立親密關(guān)系,迪娜就會擔(dān)心自己再次受到傷害,變得多疑、易怒、神經(jīng)質(zhì),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毫無緣由地發(fā)脾氣,并且習(xí)慣性地逃避。迪娜從自己的童年開始就被宗教與傳統(tǒng)束縛得透不過氣,她一直試圖擺脫這種傳統(tǒng),不管是與丈夫結(jié)婚,還是丈夫離世后回到公寓靠自己生存。但最終在生活的壓迫下,她不得不屈服,回到哥哥家寄人籬下,回到那桎梏的枷鎖牢籠中。
(二)創(chuàng)傷原因——父權(quán)制的牢籠
印度是一個宗教盛行的國度,宗教和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摩奴法典》作為古印度有關(guān)宗教、道德、哲學(xué)和法律的匯編之一,在印度次大陸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它是古代婆羅門祭司為了維護(hù)種姓制度,強(qiáng)調(diào)婆羅門至高無上地位而編纂的法論,對各種姓的地位、權(quán)利義務(wù)等做了種種規(guī)定。涉及女性方面,權(quán)利方面的敘述幾乎沒有,但義務(wù)方面卻有大段的贅述。此外,婆羅門教認(rèn)為女性是罪惡的,是邪淫的源頭,會造成男性的墮落,因此印度的女性,常因為印度特有的歷史與文化,被迫陷入性別、戰(zhàn)爭、種姓沖突以及宗教沖突的壓迫中,進(jìn)而喪失了弱小的話語權(quán)。宗教和種姓是加在印度女性身上的兩道枷鎖,但女性遭受苦痛的根本原因,是男權(quán)思想下的極端父權(quán)制。同時印度對女性的道德要求極高,經(jīng)常把女性視為父親和丈夫的附庸,并且不能與外界有任何接觸,這導(dǎo)致印度女性的成長環(huán)境往往非常封建閉塞。小說中的迪娜一直以來只能被哥哥編造的謊言所恐嚇,承受著哥哥的暴力虐待,而喪父后母親的不作為更加劇了哥哥對迪娜的壓迫,進(jìn)一步加深了迪娜的生存困境。迪娜的哥哥就是印度男權(quán)壓迫的典型人物,他從來沒有把迪娜視為一個平等的、有獨立人格的人。在迪娜的丈夫意外去世后,迪娜為了謀生主動去學(xué)習(xí)了裁縫的技術(shù),她竭盡全力在男權(quán)社會里尋求生存空間,但又頻繁地被房東騷擾,被商人欺騙,她去法院起訴,卻被房東搶先申請強(qiáng)制令,被趕出公寓,不得不回到哥哥家寄人籬下。
家庭本應(yīng)該是最溫暖的避風(fēng)港,一旦家庭里的其他成員變得面目猙獰,家人這一身份就會變成加害者的保護(hù)符,讓他們有恃無恐,只要被傷害者不想失去自己的家人,那他們就永遠(yuǎn)不會逃離這一牢籠。迪娜對愛的渴望,讓她難以反抗哥哥的虐待,血緣和親情就像拴在迪娜身上的鎖鏈,讓她只能忍受糟糕的家庭帶給她的傷痛。迪娜是印度社會中的小部分女性,但她有擺脫當(dāng)下的傳統(tǒng)眼光的勇氣,她想要在社會的夾縫中努力生存,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她做出的反抗代表著印度女性也在逐漸努力進(jìn)入到男權(quán)社會,是印度女性覺醒的標(biāo)志。
二、難以磨滅的種姓制度之傷
可能導(dǎo)致心理創(chuàng)傷的事件有自然災(zāi)難、意外災(zāi)難、人為災(zāi)難等。除此之外,來自他人的情緒忽視與情緒虐待也會給個體帶來一定的創(chuàng)傷。這種創(chuàng)傷主要表現(xiàn)為文化氛圍中的某些觀念在個體身上的投射,導(dǎo)致小說中裁縫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產(chǎn)生創(chuàng)傷的原因主要是極端的種姓制度對他們生活各方面的控制。
(一)創(chuàng)傷表現(xiàn)——裁縫伯侄的生存之痛
裁縫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作為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祖祖輩輩只能從事最低賤的職業(yè),他們與死去的牛打交道,剝皮、鞣制皮革、加工成各種成品,他們祖上幾代人的毛孔里都浸染了皮毛的臭味。小翁的祖父以非凡的勇氣,打破種姓的隔閡,送小翁的大伯和父親去學(xué)裁縫。然后也正是這富有遠(yuǎn)見的安排,給家族招來了滅門慘禍。在小翁年少時,同鎮(zhèn)的高種姓一把火燒掉了小翁全家。伊什瓦和小翁去警察局報案,但由于涉及高低種姓糾紛,警察置之不理。滅門慘案,無處申冤,喪失親人的痛苦給伊什瓦和小翁伯侄帶來了第一次由于種姓制度引起的創(chuàng)傷。
小翁和大伯僥幸逃脫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從北部一個小鎮(zhèn)來到迪娜這個海濱之城,作為迪娜的雇員得以謀生。并且經(jīng)人介紹兩人在棚戶區(qū)租到了一間小房落腳,可突然政府以維護(hù)市容為由,將棚戶區(qū)強(qiáng)拆。兩人被迫在藥房門口露宿,卻被警察當(dāng)作乞丐抓走,送去一處灌溉工程的工地干活,兩人向官員解釋是誤抓,可根本無人理睬,只有重體力活和無法下咽的餐食。兩人回來后,迪娜因兩人失蹤兩個月,縫紉活中斷,不得不向哥哥伸手借錢。她擔(dān)心兩人再次露宿街頭再有什么意外,善良的她讓叔伯兩人住在門廊。
裁縫伯侄與迪娜、馬內(nèi)克四人度過了幸福的幾個月,有了一點積蓄的伊什瓦突然要給小翁找媳婦。伊什瓦帶著小翁回到城鎮(zhèn),在集市上買東西,卻遭到警察把集市上的人全部帶去做節(jié)育手術(shù)。高種姓貴族達(dá)拉姆西庫塔庫爾認(rèn)出了小翁,不僅命令醫(yī)生給還未結(jié)婚生育的小翁做了結(jié)扎手術(shù),還切割了他的睪丸,讓小翁失去了生育能力。由于消毒工具出現(xiàn)了故障,官員們命令醫(yī)生用還未消毒的工具手術(shù),致使伊什瓦術(shù)后感染,雙腿被截肢。而此時迪娜的縫紉機(jī)也由于欠款被拉走,迪娜自己也被趕出公寓,不得不回到哥哥家寄人籬下,伊什瓦叔侄則淪為乞丐。
(二)創(chuàng)傷原因——種姓制度的禁錮
種姓制度是印度的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人們按照自己的出身分別屬于不同等級的社會集團(tuán),并且終身固定不變,在職業(yè)、婚姻、社會交往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受其嚴(yán)格制約。印度社會有四大種姓,分別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是被排除在印度四大種姓之外的,他們沒有種姓身份,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備受印度種姓的壓迫和凌辱。他們在經(jīng)濟(jì)上受剝削,在政治上受壓迫。小說中伊什瓦一家都在為了能生活得更好一點而努力,但是這努力帶來的卻是幾乎整個家族的滅頂之災(zāi)。心理學(xué)家赫爾曼認(rèn)為:當(dāng)創(chuàng)傷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者死亡時,負(fù)罪感會特別嚴(yán)重。因為他會感到自己從災(zāi)難性的事件中逃生,而無力拯救他所熱愛的人。裁縫伯侄眼看著全家人被燒死,卻無能為力,這樣的負(fù)罪感使得他們更加堅定了擺脫低種姓制約的決心。
裁縫伯侄認(rèn)為到了城市能夠進(jìn)入到一個新的世界,卻發(fā)現(xiàn)無論走到哪里,都有他們承受不完的苦難。他們在大城市睡了幾個星期的大街,終于遇到了雇主迪娜。有了工作的伊什瓦和小翁終于可以住進(jìn)貧民窟,卻又遇到了英迪拉·甘地政府的一系列“城市美化運動”“計劃生育”政策。明明有工作但貧窮的叔侄倆失去了暫居之地,被趕到大街上,但是又因為“影響市容”而被帶走“建設(shè)城市”。
當(dāng)然,面對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印度各地的“賤民”也會為自己的生存展開了斗爭,他們采用的比較普遍、歷史較久的斗爭方式便是脫離原來信奉的印度教而改信其他宗教。歷史上在1981年2月19日泰米爾納杜邦米納克西普拉姆村的1000多名“賤民”便皈依了其他宗教,并以此為起點,在以后幾個月中,很多其他許多地區(qū)也掀起了“賤民”改信宗教的浪潮。種姓制度維護(hù)者在國民志愿團(tuán)的組織下,對很多“賤民”進(jìn)行了劫掠和殘殺。小說中阿什拉夫叔叔的裁縫店便險遭厄運,是納拉揚和伊什瓦站出來冒充店鋪的主人而保護(hù)了阿什拉夫一家。種姓制度下的“賤民”們認(rèn)為只要擺脫不平等的印度教,皈依其他主張平等的宗教,他們就能擺脫壓迫。然而宗教皈依并沒有給“賤民”帶來自身的解放。政治上,不僅印度教徒仍把他們當(dāng)作賤民,即使他們所皈依的宗教的其他教徒也仍把他們當(dāng)作不可接觸者。種姓制度的毒素已滲透到印度的各種宗教之中。
裁縫伯侄倆安安定定地在迪娜女士家工作了一段時間,攢了些錢,眼看著日子越過越好,他們開始盤算給小翁娶媳婦。回到家鄉(xiāng)的伯侄二人卻遇到了鎮(zhèn)上負(fù)責(zé)計劃生育運動的,也正是當(dāng)年燒死家人的高種姓,于是小翁被閹割,而伊什卡也因為結(jié)扎手術(shù)感染,不得不截肢。二人再次無家可歸,做起了可憐的乞丐。
小說中伊什瓦與小翁這個恰馬爾家庭的越階行動雖然最終也以失敗告終,但他們所代表的是一個家族兩代人與種姓制度的斗爭,也是很多“賤民”的縮影。伊什瓦的父輩們斗爭的對象是高種姓的地主,而伊什瓦和小翁斗爭的是由于處于低種姓而帶來的無形的規(guī)章制度,他們的反抗更多是出于對自我的保全,雖然于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而言,這樣的反抗是無力的,但也反映出“賤民”們對于種姓制度這一社會濫觴的不滿。
三、難以逃脫的現(xiàn)代化之傷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當(dāng)今社會造成創(chuàng)傷的事件并不僅僅局限于戰(zhàn)爭、大屠殺等,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以及由此帶來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上的雙刃劍與政治上的腐敗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固有的生存和發(fā)展方式被重構(gòu),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zhàn)。面對社會變化,有些人無所適從,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錯位中被扭曲,馬內(nèi)克受到的創(chuàng)傷便是由于自身無法融入現(xiàn)代社會帶來的。
(一)創(chuàng)傷表現(xiàn)——馬內(nèi)克的成熟之痛
馬內(nèi)克的父輩皆是家境富裕,地產(chǎn)頗豐的階層。然而因為印巴分治的一道國境線,一夜之間,馬內(nèi)克家族所有祖?zhèn)鞯耐恋厝急粍澚顺鋈ァS谑牵R內(nèi)克的父親只能靠一間雜貨鋪和自己制汽水的獨門技術(shù)養(yǎng)活妻兒。然而隨著經(jīng)濟(jì)的不斷發(fā)展,父親法魯赫·科拉喜歡的群山被過度開發(fā),獨家的科拉汽水也遭到國外品牌競爭,銷量每況愈下。父親為了兒子的遠(yuǎn)大前程,將十一歲的兒子送到遠(yuǎn)離家鄉(xiāng)的大城市求學(xué)。
突然來到城市的馬內(nèi)克與城市的喧囂格格不入,唯一的朋友阿維納什是他學(xué)習(xí)生活唯一的慰藉。可是阿維納什在為學(xué)生呼吁奔走中突然失蹤。馬內(nèi)克也遭到同學(xué)霸凌。他無法忍受宿舍,本想借機(jī)回家,正好母親的同學(xué)迪娜尋找房客,于是他搬到了迪娜家,與同齡的小翁成了朋友。
馬內(nèi)克畢業(yè)返家后,前往迪拜工作八年,由于父親去世,他奔喪返家。從迪拜回到家后的他發(fā)現(xiàn)家里的商店經(jīng)營慘淡,父親引以為傲的汽水被新的品牌取代,母親每天都郁郁寡歡。回到孟買后,他以為會看到小翁結(jié)婚,子女成群,但在親眼見到迪娜阿姨頂著哥哥的壓力還在接濟(jì)已淪為乞丐的伯侄二人時,馬內(nèi)克的內(nèi)心崩潰了。最后他不堪忍受生活的磨難,抱著同學(xué)阿維納什的棋盒,選擇和他同樣的方式,臥軌而亡。
(二)創(chuàng)傷原因——現(xiàn)代社會的壓迫
作品創(chuàng)作的背景即英迪拉·甘地領(lǐng)導(dǎo)的國大黨政府突然宣布國家進(jìn)入緊急狀態(tài),在緊急狀態(tài)期間,國家實行新聞審查,逮捕了成千上萬的持不同政見者,此外無數(shù)弱勢群體的權(quán)益受到了侵犯而無人顧及,剝奪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的不合法行為到處彌漫。此外,由于印巴分治導(dǎo)致次大陸億萬人群固有的生活邊界一夜間被改變,大量的難民匆匆離開世代生存的家園,去往陌生的地方。馬內(nèi)克的父親便是由于印巴分治的一道國境線而導(dǎo)致家產(chǎn)盡失,并且由于二戰(zhàn)后大量的軍事和軍需刺激了印度的經(jīng)濟(jì),在印度建立了金屬冶煉加工、機(jī)械制造等工業(yè),馬內(nèi)克一家安逸的鄉(xiāng)村生活也被現(xiàn)代化的快速發(fā)展打破了。隨之而來帶給馬內(nèi)克的是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雙重創(chuàng)傷。
在慌亂的工業(yè)化發(fā)展中,印度社會的各個階層都躁動不安,村莊里沒有地的人來到城市,導(dǎo)致城市人口激增,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馬內(nèi)克的朋友阿維納什便是由于在學(xué)校參與抗議活動而喪失了生命,馬內(nèi)克便是在目睹迪娜與伊什瓦等人的不幸結(jié)局后走上了與阿維納什同樣的道路。
心理學(xué)上認(rèn)為大部分患者的創(chuàng)傷問題,往往都涵蓋人際關(guān)系、童年經(jīng)歷及親人朋友離世等其他創(chuàng)傷性事件多種創(chuàng)傷源。創(chuàng)傷的概念也不局限于特定的生命階段或特定的事件,即一個人可能在任何時間,被任何事件所壓倒而感到創(chuàng)傷。伊什瓦伯侄雖然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但其樂觀精神卻使他們在每個苦難階段都能渡過難關(guān),而馬內(nèi)克在遭遇了屠殺錫克教徒事件、父親去世以及故人巨變后選擇了自殺。伊什瓦伯侄之所以與馬內(nèi)克的結(jié)果不同,是因為伊什瓦伯侄尤其是伊什瓦自小就生存在低種姓身份的陰影下,見慣了社會的不公,而馬內(nèi)克童年的幸福生活給了其極高的生活與社會期待,一切破滅的落差使其精神崩潰,最終臥軌自殺。
四、結(jié)語
《大地之上》通過講述寡婦迪娜、大學(xué)生馬內(nèi)克以及裁縫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四位主人公的命運,刻畫了特殊歷史時期下印度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tài)。這部作品中的四個主人公,幾乎每個人都帶著創(chuàng)傷生活,沒有一個能夠逃過劫難。故事的發(fā)展正如最后一章的題目“完整的輪回”最終形成了閉環(huán)。迪娜在努力工作之后還是失去了一切回到了哥哥家;滿懷希望地離開遭受極度迫害的裁縫伯侄最終還是淪為了乞丐;而出國務(wù)工的馬內(nèi)克八年后返鄉(xiāng)了解到朋友的悲慘遭遇后還是選擇了不歸路。20世紀(jì)50年代到80年代的印度讓人窒息的不是貧窮,而是人權(quán)的踐踏。底層的群眾像螻蟻一般,都在被無情踐踏,成為歷史的犧牲品。本文從創(chuàng)傷理論這一視角切入,關(guān)注主人公身心創(chuàng)傷的同時,從父權(quán)制、種姓制度以及現(xiàn)代化等角度分析導(dǎo)致創(chuàng)傷的原因。通過研究可以得出,迪娜等人的創(chuàng)傷不僅僅是特殊家庭環(huán)境造就的個體創(chuàng)傷,背后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社會制度的腐朽與社會快速發(fā)展的弊端。小說中主人公受到的創(chuàng)傷與他們的人生悲劇,讓讀者看到了歷史與現(xiàn)實之于個人的偶然性。在此意義上,迪娜等人的悲劇連同的可能是許多印度家庭的悲劇,也都是對于印度腐朽的制度與社會的一種反諷和質(zhì)疑。
此外,故事的主人公都曾或多或少的受到過創(chuàng)傷,陷入過精神困境,對于他們而言,往往很難憑借自己的力量走出來,此時人生過程中的一點點溫暖都顯得至關(guān)重要,這些溫情就像一顆種子,一旦受害者有走出來的決心,就會變成支撐他們的參天大樹。萬幸的是,他們彼此成了對方黑暗道路中支撐勇敢前行的力量,給予了彼此對抗混亂而又充滿壓迫的生活的非凡勇氣。因而小說主人公們的互相療愈也啟示我們,不要忽略治愈創(chuàng)傷的重要性。作者羅欣頓·米斯特里用真實自然的筆觸,將畸形又略顯荒誕的印度社會環(huán)境呈現(xiàn)出來,將創(chuàng)傷治愈中那些痛苦掙扎赤裸裸地擺在讀者眼前。小說既不勵志,也不熱血,充滿了壓抑、困窘和自我懷疑,卻能給予讀者無限的力量。
參考文獻(xiàn):
[1](加拿大)羅欣頓·米斯特里.大地之上[M].張亦綺譯.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
[2]張呈敏.論《微妙的平衡》的底層敘事[D].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2017.
[3]張磊.《燦爛千陽》的創(chuàng)傷解讀[D].黑龍江大學(xué),2015.
[4]姚斌潔.創(chuàng)傷理論視角下的海明威戰(zhàn)爭小說研究[D].吉林師范大學(xué),2017.
[5]朱希.平衡與希望之歌——解讀羅欣頓·米斯特里《大地之上》 [J].文學(xué)評論,2023,(46):15-18.
[6]趙鳳英,李鳳.《縱橫交錯的世界》中的多重創(chuàng)傷研究[J].金陵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3,37(3):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