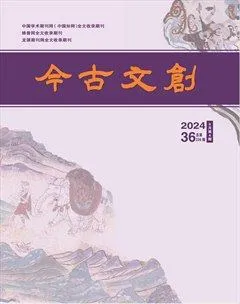目的論視角下《紅樓夢》英譯本中歲時節日翻譯的對比分析
【摘要】本文從目的論視角出發,以楊憲益和霍克斯兩版《紅樓夢》英譯本作為語料,選取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臘八節的英譯作為案例進行對比分析,探究不同的翻譯目的如何影響翻譯策略的選擇,并根據目的論三原則對譯文進行評價。
【關鍵詞】《紅樓夢》;英譯本;節日;翻譯目的論
【中圖分類號】H3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36-009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9
一、引言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章回體長篇小說,位居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該書詳細描寫中國古代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禮儀習俗、詩詞歌賦、宗教信仰等多個文化領域,因此享有“中國封建時代的百科全書”的美譽。自19世紀30年代以來,陸續有中外譯者對《紅樓夢》進行英譯并對外傳播,至今已有190多年的歷史,擁有數量眾多的摘譯本、節譯本和全譯本,在中國典籍英譯領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紅樓夢》的英語全譯本中,有兩版譯本傳播最為廣泛、學術影響最為深遠:其一是楊憲益和戴乃迭共同翻譯,由外文出版社在1978年至1980年間出版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共三卷;其二是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和閔福德(John Minford)共同翻譯,由企鵝出版社在1974年至1986年間發行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共五卷。
本文將結合節日背后的風俗文化、禁忌寓意,從目的論角度對比分析楊、霍譯本如何就其翻譯目的選擇歲時節日的翻譯策略、方法、技巧,并就其優缺點展開討論和評價。
二、翻譯目的論
20世紀70年代,德國功能學派的翻譯理論家漢斯·弗米爾(Hans Josef Vermeer)提出翻譯目的論(Skopos Theory)。該理論認為,翻譯過程要遵循三大原則:第一,目的性原則(skopos rule)。翻譯行為遵循的首要原則是目的性原則,即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2]第二,連貫性原則(coherence rule)。該原則強調語內連貫,要求譯文必須能讓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語文化以及使用譯文的交際環境中有意義。[2]由于預期譯文的接受者是譯者決定翻譯目的的首要因素,可以說“翻譯是在目的語情境中為某種目的及目的受眾而產生的語篇”[3]。第三,忠實性原則(fidelity rule)。該原則要求原文與譯文間應存在語際連貫一致,即譯文需要忠實于原文[2],忠實程度取決于譯文目的和譯者對原文的理解。然而,當語內連貫和語際連貫相沖突時,前者應被優先考慮,以保證目的語讀者能夠接受理解譯文。在目的論三原則的指導下,譯者先確定翻譯目的,再選擇合適的策略以滿足翻譯要求。
三、《紅樓夢》中的歲時節日
歲時節日主要是指與天時、物候的周期性轉換相適應,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具有某種風俗活動內容的特定時日。[8]作為“清代風俗的百科全書”,《紅樓夢》生動展現了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臘八、除夕等多個中國傳統節日及其豐富多彩的習俗,其中又以除夕、元宵、中秋三個節日為描寫重點。
《紅樓夢》對賈府歲時節日的描寫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和學術價值。首先,書中常以歲時節日為舞臺展開劇情,如元妃省親的元宵、黛玉葬花的芒種、賈府的中秋夜宴、大觀園的重陽詩會等,這有助于推動劇情發展和展現人物魅力。其次,書中某些人物以節日為生日,他們的命運暗藏在節日寓意背后,如賈元春生于正月初一,這個特殊的日子象征著新的開始和希望,她的出生預示著賈府的繁榮鼎盛。反之,她的死亡則是賈府走向衰亡的征兆。最后,該書對清代幾乎所有重大節日的慶祝活動進行細致描寫,為后世對18世紀中國歲時風俗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四、目的論視角下楊、霍譯本歲時節日翻譯的
對比分析
在長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和語言接觸中,中國傳統節日目前已經形成一套較為固定的譯名。例如,除夕譯為“Chinese New Year’s Eve”,中秋節譯為“Mid-autumn Festival”,冬至譯為“Winter Solstice”。然而,楊、霍譯本中部分節日沒有使用通用譯名,甚至出現同一節日使用多個英譯名稱的情況。卞建華認為,不同的目的自然會導致同一源文不同的譯文和不同類型的翻譯。[5]本節將從目的論視角出發,通過六個譯例對比分析翻譯目的如何影響楊、霍譯本選擇歲時節日的英譯策略方法及其優缺點。
(一)目的性原則下的歲時節日翻譯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楊、霍譯本的翻譯目的有所不同。一方面,楊憲益和戴乃迭是在外文出版社的委托下翻譯《紅樓夢》。他們為目的語讀者帶去精彩故事外,還承擔起對外介紹中華傳統文化的任務,因此傾向采取保守的翻譯策略,較少改動譯文。另一方面,霍克斯翻譯《紅樓夢》的初心是向目的語讀者分享讀這本小說的樂趣,因此他更多站在讀者角度開展翻譯工作,不惜對譯文進行增刪改譯。
例1:
原文:清明涕送江邊望。
楊譯:Through tears she watches the stream On the Clear and Bright Day.
霍譯:In spring through tears at river’s bank you gaze...
例2:
原文: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
楊譯:Now the Clear and Bright Festival came around again.
霍譯:It was the day of the Spring Cleaning festival...
分析:清明節是“二十四節氣”之一,也是中國人祭祖掃墓、慎終追遠的傳統節日,時間在每年公歷4月5日前后。節日期間,民間有上墳掃墓、踏青春游等風俗活動。
在例1和例2中,楊譯本采取直譯法,將清明節譯為“Clear and Bright Day/Festival”,恰如其分地傳達出初春期間氣清景明的季候特點,符合語義上的準確性。此外,楊譯本在正文外添加腳注“The festival,usually on the 5th of April,when the Chinese visited their family graves”,闡釋清明節的日期以及主要習俗,幫助讀者跨越文化壁壘,促進理解。
霍譯本為了提升讀者的閱讀體驗,在歸化策略的指導下為例1和例2中的“清明節”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例1出自第五回賈探春的七言絕句判詞,預示她將于清明時節出海遠嫁,淚別親人。此處譯者選擇將“清明節”改譯為“spring”,這種處理方式有兩種作用:第一,詩中“清明”的主要作用是點明季節,節日本身并非重點內容,此處改譯能降低目的語讀者對異國文化的理解成本。第二,霍譯本考慮到目的語讀者對于“清明”的文化象征不太熟悉,因此選擇更為普遍接受的表述“spring”,以便傳達出初春的意象和氛圍。
例2出自第五十八回,提及賈府眾子弟于清明節前往鐵檻寺祭靈燒紙。此處,霍譯本使用歸化策略,將“清明”改譯為“Spring Cleaning festival”,即“春季掃除節”。春季大掃除是西方一項由來已久的傳統,人們仔細清掃家中的灰塵和雜物,迎接春天的到來。該傳統有多種由來,其中一個便來自基督教:在耶穌受難日之前,會將教堂的祭壇打掃一番,以迎接節日。而清明掃墓時中國人為祖墳清除雜草、培添新土,形式類似于打掃祭壇,這與春季大掃除的習俗源頭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使用“Spring Cleaning Festival”有一定合理性。該譯文向目的語文化靠攏,更能達到令目的語讀者喜聞樂見的目的,但仍有不足之處。首先,“Spring Cleaning”既沒有傳達“清明”本義,又丟失祭祖追思的內涵,令節日失去核心意義;其次,在中國文化中,“春季大掃除”更多指春節前打掃家庭衛生的活動,因此該譯文可能會誤導目的語讀者。
(二)連貫性原則下的歲時節日翻譯
連貫性原則強調譯文的可讀性和交際意義,在讀者充分領悟原文內涵的基礎上,令譯文通順達意,實現語內連貫。為此,譯者在處理歲時節日翻譯時,要考慮其背后歷史文化典故和寓意,幫助讀者跨越理解障礙。
例3:
原文: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
楊譯:The magpies are gone,the needle of the Double Seventh Festival rests idle.
霍譯:It is in vain for the maidens to hang up their needles on Seventh Night and pray for nimble fingers.
分析:七夕節,又稱“乞巧節”“七姐誕”“女兒節”等。農歷七月初七是織女的生日,古代女子會在庭院中拜祭織女,向她乞求巧藝。此外,根據神話傳說,每年七月初七夜,牛郎織女在天河相會,因此七夕在后世逐漸成為象征愛情的節日。例3節選自第七十八回的《芙蓉女兒誄》,是賈寶玉為悼念晴雯寫的一篇祭文。此處作者使用七夕節及其穿針乞巧的習俗典故,如果不加以解釋,目的語讀者難以理解其中的內涵。為了實現語內連貫,楊、霍譯本對“七夕節”的翻譯進行了額外處理。
楊譯本根據七夕的日期農歷七月初七,將其譯為“Double Seventh Festival”。并且譯者還使用釋義法,在正文以外添加注釋,補充說明牛郎織女被迫分開,只能在每年的七月初七于鵲橋相會的神話傳說,體現了譯者的跨文化意識。然而,由于譯者的疏忽,注釋中并未提及七夕穿針的典故,缺失的信息令目的語讀者無法領會原文“七夕之針”的內涵,導致理解障礙。
霍譯本使用直譯法,將七夕譯為“Seventh Night”,并且也采取釋義法,試圖讓目的語讀者了解七夕穿針乞巧的典故。但與楊譯本的文外注釋不同,霍譯本在完全理解原作者意圖的基礎上,拋棄原句式結構,用更自然、更接近目的語表達習慣的方式重構句子,并通過增譯“pray for nimble fingers”向讀者說明七夕女子穿針的習俗及其目的。
例4:
原文:“不知他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
楊譯: “When was she born?”“That’s the trouble: the seventh of the seventh month.”
霍譯: “When was she born?”“Ah, that’s just the trouble,”said Xi-feng.“She was born on Qiao-jie—the Seventh of the Seventh—a very unlucky date.”
分析:例4出自第四十二回,王熙鳳請劉姥姥給女兒起名。王熙鳳的女兒生于農歷七月初七,即七夕節。有些民間傳說認為,數字“七”是不祥的數字。其一,在古代,人死后,葬禮從“頭七”日開始,到“七七”日結束,因此古人避諱“七”。其二,農歷七月也被稱為“鬼月”,是傳說中“鬼門關”大開的時間,民間認為孤魂野鬼會投胎到七月生的人身上,令此人命途多舛。因此,王熙鳳認為這個日子不好,需要用名字來“沖一沖”。
楊譯本將“七月初七”直譯為“the seventh of the seventh month”,沒有解釋在該節日出生的民間忌諱。對于目的語讀者來說,其文化中的七月七日并不存在相同的避諱,此處的文化缺省導致原文意義的流失,難以令讀者心領神會。有鑒于此,霍譯本使用增譯的方法,指出“七月初七”指代的節日及其不祥的象征,令讀者能夠輕松理解原文要旨,不需要查詢額外資料打斷閱讀節奏。
由例3、例4的對比分析可知,霍譯本比楊譯本更加注重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觀感,在明確節日文化的內涵后,使用增譯、釋譯等手段對原文進行一定程度的改譯,在連貫性原則上比楊譯本更勝一籌。
(三)忠實性原則下的歲時節日翻譯
在目的論中,忠實并不意味著字對字的直譯,而是在實現翻譯目的和理解原文的基礎上,不拘泥于原文形式,靈活再現原文的內涵。
例5:
原文: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
楊譯:Tomorrow is the Feast of Winter Gruel when all men on earth will be cooking their sweet gruel.
霍譯:“Tomorrow is Nibbansday,”he said,“an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of men they will be cooking frumenty.”
分析:臘八節源于佛教,傳說釋迦牟尼在農歷十二月初八成佛,因此寺院在每年的這一天煮粥供佛,隨后民間沿用成為風俗。對于“臘八節”的英譯,楊、霍譯本沒有拘泥于直譯或音譯,而是在打破原文結構的基礎上,使用不同譯法令譯文再現節日內涵。
楊譯本的翻譯目的是向目的語讀者介紹臘八節的風俗,因此采用異化的策略,將“臘八”意譯為“the Feast of Winter Gruel”,即“冬日粥節”,令讀者迅速準確了解該節日的時令和喝臘八粥的風俗,在遵守目的性和連貫性原則下達成忠實。然而,將臘八粥譯成“gruel”略有瑕疵。“gruel”在牛津詞典里的解釋是“a simple dish made by boiling oats in milk or water,eaten especially in the past by poor people”,即“窮人吃的燕麥粥”。但中國人吃的臘八粥是由谷物和干果煮成的,并不是燕麥粥。如果選用“gruel”,目的語讀者可能誤以為臘八節有吃燕麥粥的傳統。該詞可用“congee”代替,特指中國料理里的粥。
霍譯本根據古印度巴利語“Nibbana(涅槃)”,通過音譯兼意譯的方法創造性地構造新詞“Nibbansday”,即“涅槃日”。該詞在發音上與“臘八”相似,保留原詞的音韻;在詞素上融合了佛教元素,傳達原詞的文化內涵;在構詞上與西方的節日名稱相似,增加目的語讀者對該節日的親切感。然而,該譯文犯了一個文化性錯誤,將佛祖的涅槃日與成佛日混為一談。臘八節是紀念釋迦牟尼成佛的日子,時間為農歷十二月初八,而佛祖涅槃的日子則為農歷二月十五日。因此,霍譯本把釋迦牟尼成佛的節日錯譯為釋迦牟尼涅槃的節日,違反了忠實性原則。
例6:
原文: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
楊譯:...as moreover it was just before the Double Fifth Festival...
霍譯:...this was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and the first day of the Summer Festival...
分析:端午節,又稱端陽節、重午節。中國人在每年的農歷五月初五慶祝該節日。作為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傳統節日,端午節的由來有多種說法,包括天象崇拜說、紀念愛國詩人屈原說、紀念伍子胥說等等。這一天,民間有賽龍舟、吃粽子、喝雄黃酒、門上掛菖蒲的習俗。
如例6所示,楊譯本根據端午節的別稱“重五節”,直譯為“Double Fifth Festival”,忠實地向讀者介紹節日的慶祝時間。霍譯本同樣從時間角度選擇譯名,將其譯為“Summer Festival”,即“夏節”。“夏節”是端午節較為罕見的別稱,出現時間較晚,其歷史追溯到北洋政府時期。1914年1月24日,北洋政府內務部總長朱啟鈐提交的《四時節假呈》建議,“擬請定陰歷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7]。但當時民間對“夏節”的接受度非常低,并繼續沿用舊稱端午節。因此,“Summer Festival”是一個不合適的翻譯:一方面,中國人難以將夏節與端午節畫等號,對該名稱的認同感十分低;另一方面,“Summer Festival”的時間定義過于寬泛,不如“Double Fifth Festival”精準,目的語讀者可能會誤認其為“夏至”,違背忠實性原則。由此看來,“Double Fifth Festival”是個更好的選擇。
五、結語
本文選取楊、霍兩版《紅樓夢》英譯本,從翻譯目的論視角出發,對其中的歲時節日翻譯進行對比分析。研究發現,受到個人想法、母語文化、讀者受眾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楊、霍雙方產生不同的翻譯目的,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也隨之變化,形成兩部各具特色的《紅樓夢》經典英譯本。楊譯本積極使用異化策略,通過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翻譯歲時節日,并適當增加文外注釋進行補充,準確傳達節日時間、習俗、由來等信息,盡力達成對外傳播中華節日文化的目的。霍譯本為優化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體驗,針對性地使用意譯、音譯、省譯、改譯等多種翻譯方法,力圖提高譯本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然而,受到譯者的文化背景限制,霍譯本出現較多文化的錯誤,存在誤導讀者的風險。
參考文獻:
[1]Hawkes,David.(Translate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Group,1980.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7-32.
[3]Vermeer H J.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0.
[4]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9.
[5]卞建華.傳承與超越: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80.
[6]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政府公報[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661.
[8]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138.
作者簡介:
羅慧妍,湖南農業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