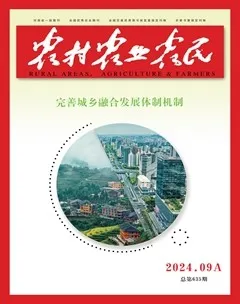新鄉賢文化的培育與構建
摘 要:新鄉賢文化的培育和構建既需要傳統鄉賢文化的滋養,也需要在“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下作出制度安排。厘清紳士—鄉紳—鄉賢—新鄉賢發展脈絡,梳理自發性鄉賢文化和制度性鄉賢文化,落腳點都在構建當代“新鄉賢文化”。新鄉賢文化的構建既要對新鄉賢“從哪來”“怎么用”作出制度性安排,也要培育自發性“新鄉賢文化”,激活新鄉賢的內生動力,著力培育新鄉賢文化主體、搭建新鄉賢治村平臺、增進新鄉賢文化認同。
關鍵詞:新鄉賢;鄉賢文化;歷史源流;鄉村振興
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會議傳達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包括“七個著力”的具體要求。其中“第五個著力”是指“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在紛繁浩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鄉賢文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鄉賢對于維護傳統鄉村社會秩序發揮過重要作用。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推動鄉賢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培育和弘揚新鄉賢文化,吸引和激勵新鄉賢深度融入鄉村建設,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舉措。進一步梳理鄉賢文化的歷史源流,挖掘自發性鄉賢文化傳統與制度性鄉賢文化傳統的形成機制,或能為新鄉賢文化的培育提供方法借鑒。
一、鄉賢文化的歷史源流
王先明先生的《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一書,明確將“紳士”界定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階層。這種“紳士”作為階層身份的獲得必須是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等,并具有一定的特權。有的紳士居住在城市,有的則居住在鄉村,故而稱之為“鄉紳”。因鄉紳或推恩于里黨,或樹德于桑梓。所謂“紳而富,以財濟于鄉;紳而耆,以德式于鄉”;故稱“賢”,謂之“鄉賢”。這就是“鄉賢”一詞的由來。
古代鄉賢文化,從官方和民間不同的視角,可以分為“自發性鄉賢文化”和“制度性鄉賢文化”。所謂自發性鄉賢文化,是站在民間的立場而言的,是鄉賢自發、積極地主導、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造福桑梓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傳統。所謂制度性鄉賢文化,是站在官方視角而言的,是一種推選、祭祀、書寫鄉賢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傳統。
(一)自發性鄉賢文化傳統
鄉賢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自發性鄉賢文化傳統的興起,建立在農業經濟相對穩定和發展的基礎之上。農業生產的提高和剩余產品的增加,為地方社會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物質基礎,使得地方社會能夠支持一定數量的非農業人口。宗族內部的經濟互助和財產共有,為鄉賢提供了經濟支持,使他們能夠更好地履行社會職責。古代“皇權不下縣”,地方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鄉賢能夠在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如管理地方公共工程、慈善事業和教育等。
梳理而言,鄉賢文化的雛形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社會結構以宗族和村落為單位,村落中的長者或是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往往能在村務管理、解決糾紛、教化村民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到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德治”理念得到推廣,地方上的鄉紳、儒生等逐漸成為鄉村社會的領導者,他們通過自己的德行和學識影響和治理鄉村,形成了較為明確的鄉賢文化。唐宋時期,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許多“未能進入”或“已退出”中央或地方官府的士人回到鄉村,成為鄉賢的主體。明清時期,鄉賢文化達到鼎盛。這一時期,鄉賢不僅是鄉村社會的管理者,也是鄉村文化和道德的維護者。他們采取建立宗族祠堂、編纂族譜、修建學校等方式,維護和傳承地方文化。傳統知識分子于“得君行道”之外,另辟一條“覺民行道”,成為儒家知識分子實現修齊治平理想的新路徑。一般來說,“鄉賢們”或積極興辦鄉村教育,民間的義學和義塾成為鄉村教育的重要力量。明代的泰州學派,更是高舉“覺民行道”的大旗,要重塑傳統社會中的農民。或積極參與鄉村慈善事業,好善樂施、救災賑災,通過義莊、義倉救助百姓,在民間獲得很高的聲望。或通過德行、禮儀教化鄉里,具有影響力的鄉賢往往通過制定族規、鄉約來化民成俗,一種自發性鄉賢文化傳統蔚然成風。
(二)制度性鄉賢文化傳統
從官方視角而言,對鄉賢與鄉賢文化作出制度性安排,代表了鄉賢文化的逐漸成熟,時間不晚于漢代。漢高祖時期,就下詔推舉“能帥眾為善者”為“三老”。《漢書·高帝紀》記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傳統中國的政治是“雙軌制”——有著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兩層。政府的政令一旦與下層民眾接觸,就會落入“鄉約”的特殊軌道,鄉賢具有很大的效力。《漢書·高帝紀》的詔令為“三老”設置了推選標準,規定了參與鄉村治理的渠道以及可獲得的相應特權和禮遇,這可以說是“鄉賢”參與治理最早的制度性安排,是制度性鄉賢文化傳統的開端。唐宋時期由于科舉制度的發展,加之民間書院的興起,鄉賢逐漸成為一個數量龐大的階層。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唐以后中國社會是“科舉社會”,宋以下甚至可以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絕大多數科舉錄取者是民間出生的白衣舉子。白衣舉子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受到皇權的重視。為優化與鄉賢的權力合作,皇權為鄉賢參與鄉村事務作出更多的制度安排。并且,出現了“祭祀鄉賢”的制度,宋代開始有專門祭祀鄉賢的“鄉賢祠”,剛開始還是由民間發起,到明代實現了制度化,開始由官方大力推動地方建設鄉賢祠。為與“名宦祠”區分,官方甚至明確:“仕于其地,而在政績,惠澤及于民者,謂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業學行傳于世者,謂之鄉賢。”鄉賢的推選流程較為復雜,從推舉、商議、審定、復核、批復,有一整套規范,官方和民間都非常重視,希望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達公論”。另外,“書寫鄉賢”的制度也值得注意,即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名錄、傳記、碑銘等表彰鄉賢,以遺風化俗,敦厚鄉里。因記錄鄉賢、書寫鄉賢,逐漸構建出對后人有極具勸勉作用的鄉賢文化。被推舉為鄉賢、進入鄉賢祠,成為許多士人終生的夢想,所謂“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顯然,制度性的鄉賢文化的構建,是這種人生理想的幕后推手。
二、鄉賢文化的現代傳承與發展
2014年,《光明日報》推出《新鄉賢·新鄉村》系列報道,從此“新鄉賢”這一概念被廣泛討論并接受。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提出:要積極發揮新鄉賢的作用。傳承鄉賢文化傳統,培育新鄉賢文化。從方法論而言,自發性新鄉賢文化和制度性新鄉賢文化的構建缺一不可。
鄉賢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儒家文化傳統以及科舉制度等緊密相關。它強調的是地方精英在地方治理和文化傳承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尊重知識和道德的價值觀。在新時代背景下,鄉賢文化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其價值和意義在鄉村振興和社會治理中仍然被重視。
(一)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中,激活自發性新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17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挖掘和保護鄉土文化資源。建設新鄉賢文化,培育和扶持鄉村文化骨干,提升鄉土文化內涵,形成良性鄉村文化生態,讓子孫后代記得住鄉愁。近年來,國家倡導新鄉賢文化,將新鄉賢視為當代鄉土的守護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一種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新鄉賢之“新”,首先就表現在與古代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的“鄉賢”不同,他們既傳承傳統鄉賢文化,造福桑梓,為民眾所廣泛認同,又跳出了傳統鄉賢由階級和階層意識所伴生的狹隘、閉塞、本位的思維局限,以民主和平等取代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放下“架子”參與到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共同體格局中。當代鄉村社會的新鄉賢,并非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更為恰當的定位應該是鄉村社會的一個新群體,新鄉賢自身則將其看成一種“榮譽稱號”。自發性新鄉賢文化的培育,需要以鄉緣、血緣、業緣為紐帶,激發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助力鄉村發展的意愿,以激活新鄉賢振興鄉村的內生動力為重點。
(二)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背景下,構建制度性新鄉賢文化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將“鄉賢文化”列入農村思想道德建設。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新鄉賢文化”進行了闡述。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提出要“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在之后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新鄉賢”的作用滲透在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與組織振興中。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進程中,通過整合鄉村社會資源,借助鄉情紐帶,將有情懷、有能力、有資源、有文化的“在村的”或“在外的”賢達人士整合起來,參與鄉村治理、助力鄉村振興,需要構建制度性新鄉賢文化。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重要政策背景是現代基層的自治制度,可以說“三治融合”的治理體系,已經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打開相應的制度空間。然而,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角色定位尚需準確把握。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不能“窄化”為“慈善公益”,不能“泛化”為單向付出的“好人好事”,而應建立起較為科學的治理機制。這種科學的治理機制,不是否定現有的鄉村治理的組織架構并取而代之,而是為新鄉賢在民主協商、經濟合作、文明教化等方面發揮自身優勢搭建平臺、提供制度保障,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助力鄉村振興,打通“最后一公里”。同時,不可忽視的是,要繼承和弘揚鄉賢傳統,倡導“知鄉賢”“頌鄉賢”“學鄉賢”的文化氛圍,寫好新時代新鄉賢的動人故事。
三、培育構建新鄉賢文化的策略建議
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下,新鄉賢作為自治和德治的重要力量,加之自帶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技術資本等資源屬性,又有城鄉融合的“文化中間人”角色定位,是應對鄉村的治理困境、資源匱乏、人才缺乏、文化凋敝等問題的解決思路之一。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背景下,新鄉賢的價值越發被重視,需著力培育新鄉賢文化,充分發揮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作用。
(一)培育新鄉賢文化主體
在培育新鄉賢文化主體時,既要注重傳統鄉賢與新鄉賢的內在傳承,傳承和發展鄉賢文化自發性傳統和制度性傳統中合理、積極的部分,又要符合時代發展需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新鄉賢文化主體的界定,應符合最大限度發掘、整合鄉村社會資源的需要。當代新鄉賢的群體來源,不應過多設限,一般來說,大抵有三種方式:或經普查——篩選,或經推舉——聘選,或經申請——評選。根據鄉村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分類標準,規范程序流程。在新鄉賢的各種分類的嘗試中,按照“空間”和“價值”分類,與新鄉賢的培育、使用關系最為緊密。
按照“空間”不同,新鄉賢可以分為“離土”和“在土”兩類。其中“在土”的新鄉賢又可以細分為“本土”與“外來”兩種。“在土鄉賢”,因人熟、地熟、事熟的“在地化優勢”,具有深度參與鄉村實踐的現實可能性。“離土鄉賢”因長期不在鄉村生活,深度參與鄉村事務并不現實,更多的是在“資源下鄉”“建言獻策”“提供資源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對于“離土”新鄉賢,一般通過家鄉發展促進會等組織進行資源整合。值得注意的是,家鄉發展促進會這類資源型組織,并不一定局限在資金資源,還包括政策、信息等其他形式的資源。
按照“價值”不同,新鄉賢可以分為“富鄉賢”“文鄉賢”“德鄉賢”“技鄉賢”等,不同類型的新鄉賢群體的推選、培育、使用應有不同的側重。要著重引導“富鄉賢”側重經濟資源導入,“文鄉賢”側重鄉土文化傳承,“德鄉賢”側重鄉風文明涵養,“技鄉賢”側重鄉村產業帶動,為其助力鄉村振興搭建平臺與舞臺。
總而言之,新鄉賢的涌現需要我們用好“鄉緣、血緣、業緣”紐帶,面對“離土”新鄉賢回流難、“本土”新鄉賢遴選難、“外來”新鄉賢引進難的現實困難,要采取明確標準、盤點摸底、引流遴選、搭建平臺、廣泛宣傳、機制保障等方式不斷培育、挖掘新鄉賢主體,培育新鄉賢文化。
(二)搭建新鄉賢治村平臺
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也需要制度化的途徑和平臺,完善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運作機制。古代的“三老制度”,正是鄉賢治鄉的一條制度化途徑。當代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途徑很多,比如浙江省常山縣的“歸雁計劃”,直接推出“賢人治鄉”,推選新鄉賢進入村“兩委”。但畢竟“兩委”人員有限,為用好鄉賢資源,新鄉賢各類組織的培育不可或缺。散兵游勇終究獨木難成舟,搭建好組織和平臺,才能更好發揮效能,促進新鄉賢文化的良性發展。
鑒于“離土鄉賢”和“在土鄉賢”的不同情況,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也分為“強參與”“弱參與”,應有不同的組織承載。一般來說,當代新鄉賢組織有家鄉發展促進會、鄉賢工作室、鄉賢理事會等。家鄉發展促進會屬于資源型組織,側重于在外新鄉賢的資源整合,為“離土鄉賢”建立回歸故鄉的通道。鄉賢工作室則屬于日常型工作平臺,以半官方的形式參與各種具體鄉村事務。更具復雜性或綜合性的鄉賢理事會等組織,既是作為鄉村治理的參事、議事機構,同時又是作為新鄉賢團體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組織載體。這類新鄉賢組織發起和運行需由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牽頭,對其規范運行給予支持與監督,使新鄉賢組織在制度框架內發揮作用,扮演好村“兩委”的“協同者”這一角色,既不至于越俎代庖,又能促進新鄉賢文化的健康發展。
(三)增進新鄉賢文化認同
培育新鄉賢文化的關鍵是如何激發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助力鄉村發展的意愿,重點在增強新鄉賢的鄉緣認同、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
增強鄉緣認同是基礎。不管是現在的“村BA”“村晚”還是“家鄉聯誼會”各類形式活潑、情感真摯的文藝活動,鄉緣都在被不斷創造的“共同敘事”中更加鮮活起來,以增強更深的鄉緣認同。增強身份認同是路徑。賦予“新鄉賢”身份標簽,通過美麗屋場、文化長廊、鄉賢名錄等平臺,不斷書寫新鄉賢故事,不斷加強新鄉賢的身份認同,并通過知事、理事、議事來增強參與感和認同感。增強價值認同是歸宿。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多數并沒有具體的經濟目的,更多的是來源于內心的成就感和滿足感。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自我實現是最高層次的需求。從高層次需求出發構建起的價值認同,是深層次、牢固、穩定的認同。要從高層次需求入手,進行培育和引導,加強鄉村振興與新鄉賢自我價值實現之間的正向關系,激發其蓬勃動力。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2:59-68.
[2]錢穆.國史大綱[M].上海:商務印書館,2010:69.
[3]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9.
[4]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23-32.
[5]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2-24.
[6]游子安.明末清初功過格的盛行及善書所反映的江南社會[J].中國史研究,1997(4):127-133.
[7]孫敏.鄉賢理事會的組織特征及其治理機制:基于清遠市農村鄉賢理事會的考察[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6):49-55.
[責任編輯:樊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