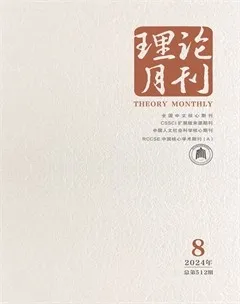《純粹理性批判》的前夜
[摘 要] 康德在1770至1781年“十年沉寂”期間,除了發表3篇小文章之外沒有任何重要作品問世,原因是此時的他正在籌劃、寫作《純粹理性批判》。關于這一歷史事實,人們沒有大的爭議。不過,對于他何以要在這一時段寫作第一批判,以及如何寫作第一批判的問題,后世學者鮮有論及。雖然亦有康德傳記作家翔實記錄過他人際交往等方面的生活瑣事,但對其哲學義理與理論演化的分辨梳理并不多見。然而,這一時段的積淀對康德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借助對康德在這一時期的往來書信、思想札記等材料的考證,人們不難發現:他在形而上學、道德哲學以及宗教學說等方面的思考,不僅直接塑造了第一批判的理論架構和基本內容,還間接影響到了批判哲學時期的諸多作品。
[關鍵詞] 前批判哲學時期;《純粹理性批判》;認識論;道德形而上學;道德宗教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8.015
[中圖分類號] B516.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8-0139-11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康德批判哲學的宗教之維研究”(20FZXB028);南京農業大學資助項目“馬克思之德國古典哲學淵源考:惡之檢討”。
作者簡介:馬彪(1980—),男,哲學博士,南京農業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一般而言,康德哲學被分為前批判哲學時期與批判哲學時期兩個階段,兩者以1781年的《純粹理性批判》初版面世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康德側重研究的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比如星云假說、地震成因、自然地理等;在此之后,他的關注重心轉向了認識論、道德哲學、宗教神學等關涉“人是什么”的三大子命題之上。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康德兩個時期的論題并非互不相涉,比如他在前期對物理影響(influxus physicus)、樂觀主義(Optimismus)等因果關系與神義論問題的處理,明顯與其后期的研究存在交叉。然而,在學界對兩個時期的研究中,我們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康德哲學的系統研究而言,大多數學者忽略了對康德1770到1781之間思想演變的探討,有的研究雖略有涉及,但總給人以語焉不詳之憾1。與此同時,諸多康德傳記作家雖對其生平活動給予了頗為詳細的記載,但對其哲學義理的闡釋則相對不足1。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結果,是因為這一時期康德除了《論可感世界與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則》(1770)這一重要著作之外,只發表了學術意義不大的3篇小文章即《莫斯卡蒂〈論動物與人之間身體上的本質區別〉一文述評》(1771)、《論人的不同種族》(1775)、《有關博愛學院的文章》(1776—1777)。就此而言,后世學者把康德這一時期稱為“沉寂的十年”而不進行深入探究,似乎也有其道理。
誠然,康德沉寂多年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要構思與寫作《純粹理性批判》這一巨著,借用他自己的話說:“十二年來,我雖然年復一年地精心思索材料,但還沒有把這些材料按照普遍的可理解性加工成文稿,要達到這個目的,似乎還需要幾年時間。然而相反,我實現這個目的只用了約四五個月的時間。”2需要指出的是,康德這一自述只解決了他在沉寂期間要做什么的問題,并沒解決他如何做以及為什么這樣做的問題,而后兩者正是我們這里所要追問的論題。在此,我們所要借助的是康德與其交際圈在1770—1781年之間的往來書信3,以及科學院版《康德全集》中第14—20卷中的“遺留手稿”等資料。它們或隱或顯地提示著康德在這一階段的哲學運思,揭示出前批判時期與第一批判之間內在的思想關聯問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前批判時期的哪些觀點是他在批判哲學時期所堅守的,而哪些又是他后來所斷然摒棄的。出于這一考量,根據康德自身對哲學領域的劃分4,筆者嘗試從“我能夠認識什么”(形而上學)、“我應當做什么”(道德)、“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三個維度闡釋其“十年沉寂”期的哲學研究。
一、形而上學:我能夠認識什么?
一般認為,1770年,康德在完成《論可感世界與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則》并作就職論文答辯之后,即開啟了他沉寂多年的關于《純粹理性批判》的籌劃與寫作。這一習慣性看法雖不無道理,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由此推斷康德在1770年之后立刻發生了思想轉向,因為真實情況遠比看上去要復雜一些5。事實上,在寫完就職論文后,康德就復印了幾本讓赫茨(Marcus Herz)分別寄送給了當時較有名望的學者如蘇爾策(Johann Georg Sulzer)、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以及蘭貝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等人,期望得到他們的批評與回應,以反思自己思想的不足與缺陷。其中,蘭貝特在1770年10月13日的回信對康德的觸動較大,它在某種程度上對康德其后的哲學運思方向亦有一定的影響。
康德在寄給蘭貝特的就職論文中指出,人的認知對象分為可感事物與理知事物,它們對應于人的感性與理性的認知能力。其中,感性涉及主體的接受能力,對應的是現象世界,借助感性我們能夠感知在場的事物;理性涉及主體的自發能力,對應的是本體世界,通過理性我們可以表象所有無法進入感官的東西。而形而上學關涉的就是后一領域,在此領域中沒有經驗對象及其原則的存在空間1 。對于康德的這個劃分,蘭貝特在回信中指出了若干問題:其一,在什么層面上可以說這“兩種認知方式是能夠完全分離的,而不是在一起的”2?如果它們的區分是先天的,那就需要對其何以如此的原因作出闡釋;反之,如果是后天的,則要對它們如何從經驗對象中析取作出澄清;其二,蘭貝特認為,本體論中“處理的那些由現象來確保的概念是有用的,因為本體論思想確實必須再次應用于這些現象之上”3,這一點應與天文學所做的一樣——它從現象中總結出一套假說,然后再將其用于現象以檢驗其真偽,繼而為未來的研究給出參考和預測。換句話說,蘭貝特不同意康德隔絕感性世界與理知世界的做法,因為假若感性世界真如康德所說指的是“如其顯現”的世界,而理知世界指的是“如其所是”的世界,那么形而上學所要探討的就只能是作為本體的世界,而如何連通現象世界的問題將不屬于其研究的領域。
蘭貝特認為康德與他的不同之處在于:康德強調的是“特殊形而上學”(special metaphysics),而他側重的是“一般形而上學”(general metaphysics)4。特殊形而上學與一般形而上學這兩個概念來自沃爾夫,前者關涉理性心理學與理性神學的論題,后者指關于一般存在的科學,它處理的不僅是上帝與靈魂的問題,還涉及一切存在及其屬性如原因、目的、必然性、偶然性、可能性等關系的論題。相較而言,一般形而上學關涉的領域更為寬泛,不僅涉及“如其所是”的世界,還涉及“如其顯現”的世界。而康德把感性與理性斷然分割,那么他將如何統合感性世界與理知世界呢?是從前者來統攝后者,還是由后者統攝前者呢?其中的理據又是什么?蘭貝特認為,康德的就職論文雖對一般形而上學中的相關概念有所論述,但他側重的始終是“不要讓感性認識私有的原則越過自己的界限,影響到理性認識”5,因為康德始終認定,一旦混淆了這兩種機能,必將導致“形而上學的欺詐錯誤”(vitium subreptionis metaphysicum),繼而從感性所偽造的公理中產生出虛假的理性原則,由此形成紛爭不休的形而上學戰場。
問題在于,康德是否真的像蘭貝特所說的那樣,傾心于特殊形而上學而忽視了一般形而上學呢?答案并非如此。康德此時對形而上學的理解已經與1755年前后的看法大不相同,如果說18世紀50年代康德對形而上學的認識還停留在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的脈絡之中的話,那么18世紀60年代的他已逐漸擺脫了這一束縛。康德為形而上學劃界的意識并不始于批判哲學時期,早在1766年《一位視靈者的夢》中他就已明確地提出這一問題,即“形而上學是一門關于人類理性的界限的科學”6,他在就職論文中不過是重申了這一看法而已。另外,關于一般形而上學的探討,康德早在1763年《證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證據》中就已經在自然神學的框架內討論了一般形而上學的范疇,例如可能性、必然性等,并在“可能性”概念的基礎上從先天維度對上帝的存在給予了證明。
既然如此,康德為何在7年后的就職論文中故意忽略一般形而上學,而側重以非物質性為客體的特殊形而上學呢?原因在于,康德18世紀60年代曾基于牛頓的力學原理在“物理影響”的理論框架下對身心問題,以及物質與非物質性的單子之間如何產生相互作用的問題給予闡述7,并以此批判萊布尼茨的前定和諧論與馬勒伯朗士的偶因論,但就其直接意義來看,康德的這一詮釋存在以物質的方式來把握非物質性客體的風險。康德在其18世紀70年代的《形而上學反思》中對于這一問題展開了思考:“以物體的(korperlich)方式來思考心靈問題是荒謬的,因為我們的實體概念來自心靈,而在此后我們才有了物體的概念。”1基于這一前提,可以發現蘭貝特對康德的批評雖然有其道理但亦不完全切實,因為康德并沒有忽視一般形而上學問題。與其說康德在1770年忽視了特殊形而上學,不如說他是在一般形而上學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特殊形而上學何以可能的問題。當然,我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蘭貝特對康德的批評沒有意義,事實恰好相反,蘭貝特的提示相當重要,其影響甚至可以媲美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對康德的震撼。正是由于他們的思想提示,康德才開始聚焦理性概念如何與客體必然相契的議題。
關于這一問題,康德在1772年致赫茨的信中闡釋得最為清晰:“為了引導作者重新檢驗自己的學說,門德爾松或者蘭貝特的一封信,要比十個這種文筆輕浮的評價更9DJauOP1Ss4NlzFBmus7+g==加有用。”2康德指出,他在就職論文中只是表明純粹知性概念必然不能從感官的感覺中抽象出來,它的根源在于人的心靈,但他從不談論一個沒有以某種方式受到對象的刺激,卻又與對象發生關系的表象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在數學中,時空直觀與量具有一致的同構關系,自然能夠制定出關于數量的先天基本原理。但在形而上學的質的關系中,“我的知性是怎樣完全先天地自己構造物的概念,而事物又與這些概念必然一致呢?我的知性是怎樣構思出關于事物可能性的現實基本原理,而經驗必定忠實地與這些基本原理保持一致,但這些基本原理又不依賴于經驗呢?對于我們的知性能力來說,它與物本身的這種一致的根源何在,這一問題一直還處在晦暗之中”3。換句話說,康德在這一期間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對知性范疇進行先驗演繹的問題,而這無疑也是他在“十年沉寂”期間的最大課題4。康德后來十分滿意這一工作成就,他在1787年《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表明:他曾“向形而上學許諾了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因為根據思維方式的這種變革,人們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釋一種先天知識的可能性,并且更進一步,給為作為經驗對象之總和的自然先天地提供基礎的那些規律配備它們令人滿意的證明,這二者按照迄今為止的行事方式是不可能的”5。也就是說,形而上學的知識只涉及顯象,與此相對,自在之物本身雖就其自身來說是實在的,但卻并不能為我們所認識。
其實,按照康德的規劃,他在1772年就已經對知性概念給予了系統考察,并且能夠把先驗哲學的所有概念歸結為一定數量的范疇。不過與亞里士多德偶然給出的10個范疇不同,他從知性自身出發,根據其基本法則重新梳理了范疇,并對它們作出了系統排序。康德相信,大約在3個月內他就能夠寫出一部名為《純粹理性批判》的著作6。顯然,康德太過樂觀了。他沒有如期兌現承諾的原因是,他對于知性概念和純粹直觀如何把雜多整合于統一的意識這個問題還沒有考慮清楚。康德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我們可以從其1775年的手稿中探得一點端倪,在他看來:“具備完全規定的所有顯象(Erscheinung)必須在心靈中統一起來,只有在此條件下并通過它,表象的統一性才是可能的,因為只有表象所需的這一條件,才是客觀的條件。統覺的這一綜合必然關涉時空直觀的統一,沒有統覺的綜合,后者的實在表象不可能出現。”7顯然,康德這里還沒有明確提及第一批判“經驗的類比”等原理分析論中的表述,但無疑已為其后思想發展作了充分的鋪墊。另外,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康德對于二律背反的發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時間亦相對較晚。據沃什伯恩(Michael Washburn)的研究,康德第一個二律背反的發現時間應在1775—1778年1,這一點可以在其關于《鮑姆嘉登〈形而上學〉注釋》中得以證實。康德在其中指出:“綜合須在理知(intellectuellen)中完成,但對這一完成條件的確認卻在感性之中,因此理性要求對感性的獨立,可其概念的確認卻只能是感性的(二律背反)。”2似乎為防止后人誤解,康德特意在這句話的括號中添加了“Antinomie”一詞,提請人們注意這里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二律背反問題:認知理性的理念需要直觀,但感性又無法提供與絕對理念相應的直觀。
整體來看,就形而上學(認識論)而言,1770至1781年期間對康德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盧梭、牛頓、休謨、萊布尼茨等人之外,蘭貝特無疑也是不容忽視的一位,其1770年的批評建議讓康德意識到了就職論文中的缺陷,使其關注概念與客體間的連通對形而上學的核心意義。而這無疑促成康德1772年以后對第一批判中“先驗分析論”的思考,并開啟了“純粹知性概念先驗演繹”的端緒。與此相對,1775—1778年間,康德關于時空、概念與心靈統覺之關系的反思,以及理性與感性直觀悖論的闡述,對其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中先驗原理分析與二律背反的考察影響巨大。不了解康德“十年沉寂”期的思想演化歷程,我們就不能真正把握其第一批判的核心內容及其哲學上的革命價值。
二、道德哲學:我應當做什么?
除了形而上學之外,康德“十年沉寂”期間的思考亦對其批判哲學時期的道德學說影響深遠。康德在致赫茨的信中明確指出,他在1772年時已經著手寫作一部名為《感性和理性的界限》的著作,該書包括兩個部分即理論的部分與實踐的部分。其中,前者可分為兩章,即一般現象學和形而上學;后者也分為兩章,即感受性、鑒賞和感性欲望的普遍原則,以及德性的最初動機3。不過,就在這同一封信中,康德不忘指出,他嘗試先寫出理論的部分,再寫實踐的純粹德性原則部分。我們從康德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此時的他還沒有完全把審美與道德的問題區分開來,以至于他將鑒賞的論題與德性的原則一并作為道德哲學的內容加以考察。
事實上,康德前批判哲學在道德探究方面的確存在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根據李明輝的考察4,康德早年接受的是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的理性主義倫理學,但18世紀50年代以后他日益發現這一學派的不足和缺陷。原因在于,這一倫理學派以“完滿性”(Vollkommenheit)為道德最高原則,但這一原則不包含任何內容,無法規定具體的義務與行動。對此,沃爾夫將這一原則與目的概念加以勾連,并在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中來理解它。但這么一來,道德行為至多只具有工具價值,沒有絕對性的價值,而這無異于摧毀了道德。到了18世紀60年代,康德接觸到了英國的道德情感學說,深為所動,因為這一學說既能夠作為具體原則應用于特殊的語境之中,同時又保留了道德無條件性的基本規定,可以免于理性主義倫理學的道德困境。不過,康德并未由此而拋棄完滿性的理性原則,而是試圖把兩者融入一個系統的道德哲學,繼而形成自己的倫理學立場。他的這一努力在《關于自然神學與道德的原則之明晰性的研究》中表現得較為明顯:“如果一個行動直接被表象為善的,它并不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包含通過解析可以在其中認識到的某種別的善,以及為什么它叫作完滿之原因,那么,這個行動的必然性就是責任的一個無法證明的質料原則。例如,愛那愛你的人,這是一個實踐命題。它雖然處在責任的最高形式的肯定規則之下,但卻是直接的。”1可以看到,康德在這里把“理性原則”和“道德情感”一并視為了道德義務的判斷原則。區別在于:前者是形式原則,后者是質料原則。換句話說,康德在1770年之前并沒有把道德法則和道德情感看作截然不同的東西,而是在其倫理學中賦予道德主體以情感與理性二分的架構。
1770年之后,康德把道德放在了理智世界而非可感世界領域,并指出道德判斷隸屬于純粹理性,而這無疑構成了康德與之前倫理思想的決裂2。正如康德在1770年9月2日致蘭貝特的信中所指的那樣:“今年冬天,我打算再把關于純粹道德的世界智慧(Weltweissheit)的研究列入日程,并且加以完成,在這里找不到任何經驗的原則,似乎可以說它是道德形而上學(die Metaphysic der Sitten)。”3康德這里所謂的“道德形而上學”是否就是其批判哲學時期的“道德形而上學”或可商榷,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一時期康德關于道德的思考,已經包含其日后成熟倫理思想的萌芽。另外,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康德此時的道德轉向亦與他對斯威登堡的態度密切相關。康德在《一位視靈者的夢》中曾嚴厲批判了斯威登堡的“靈神世界”(目的王國),認為在感官世界之外的這一領域不過是斯威登堡的臆想而已,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隨著他在1770年對于感性世界與理知世界的劃分,康德逐漸改變了昔日看法,繼而將理知世界等同于目的王國即斯威登堡的靈神世界。關于這一問題,約翰遜(Gregory Johnson)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約翰遜指出,康德的“目的王國”(Reich der Zweck)概念便來自斯威登堡所用的拉丁語regnum finium,而這一概念在斯威登堡《天上的奧秘》中出現了5次之多4。除去神秘的宗教外衣,斯威登堡所用的regnum finium與康德的Reich der Zweck幾乎沒有區別:它們涉及的都是超自然世界的人與上帝的目的關系;這一王國的客體都不是人的感知的對象;作為靈神或理性的存在者不能被還原為一個事物。關于“目的王國”與就職論文中的“理知世界”的關系,康德明確指出,兩者其實就是一個東西:“現在,一個理性存在者的世界(理知世界),作為一個目的王國就以這種方式成為可能,而且是通過作為成員的所有人格的自己立法。據此,每一個理性存在者都必須如此行動,就好像它通過自己的準則在任何時候都是普遍的目的王國中的一個立法的成員似的。”5不難發現,康德在18世紀70年代區分兩個世界的基礎上,重新整合了他以前的倫理思想,嘗試在理知世界的范圍內建構其道德哲學的大廈。
到了1773年底,康德在給赫茨的信中指出:“道德的最高理由必須自身就在最高程度上感到滿足,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思辨的表象,而是具有自身的推動力,因此盡管它是理智的,卻必須與意志的最初動機有一個直接的關系。”6康德的這一句話,給了我們兩點提示。其一,道德的滿足取決于自身,不需要在理性之外尋求其規定的理由。借用他自己的話說,道德判斷的原則與神的意志無關,亦與普遍的完滿性概念和幸福概念無關,更與同經驗關聯的個人的幸福、道德情感以及鑒賞無關,它完全是理性內部的事務7。也就是說,康德此時不僅擺脫了完滿性的理性主義倫理學和強調道德情感的經驗主義倫理學的束縛,而且還將道德同鑒賞、審美等作了明確區隔,主張道德只與理性相關。其二,深層挖掘自由意志與道德之間的義理關系。康德明確表示,作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我們既是現象世界的成員,同時也是理知世界的成員。如果說我們在前一世界中與其他萬物一樣必然受到自然規律的約束,那么在后一世界我們則是自由的。人的這種二元身份無疑涉及一個自我把握的疑難:作為主體的人一方面是獨立的,另一方面離不開自我之外的他者,即不完全獨立的事實1 。針對這一問題,康德承認,從知識的角度看我們無論是從后天還是先天的方面都無法證明自由意志的存在,這是因為,自由作為開啟因果鏈條的第一因,不可能由在它之前的其他原因來規定。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理論上完全不能證明自由的存在,它只是一個必然的實踐假設(Hypothesis)”2。誠然,康德這里的“假設”雖與第一批判中的“公設”(Postulat)存在一定距離,但他明顯意識到,自由不是一個知性概念而是一個實踐理性的公設,對它的追問只能在實踐領域展開,將其訴諸理論領域的做法是所要目的與所用手段間的錯位,必無所得。
另外,在由阿迪克斯(Erich Adickes)整理編輯、阿利森(Henry Allison)認定的康德1772—1776年的思想札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十年沉寂”期間他就已對批判哲學時期的“先驗自由”與“實踐自由”作了明確區分。對康德而言,自由在消極意義上是一種擺脫外在刺激及其必然性規定的機能,而在積極意義上它是出于理性而獨立開啟一種因果關系的能力。它分為兩種:“要么是源始的(originarii),要么是衍生的(derivativi);前者是先驗自由,后者則為實踐自由。”3與完全獨立于外在一切刺激的先驗自由不同,實踐自由是相對獨立的,因而是有條件的自發性。就此而言,前者可以歸入理性心理學,而后者可以納入經驗心理學。康德在“十年沉寂”期間對實踐自由的這一刻畫,就其本質而言,與《純粹理性批判》中的觀點較為接近。他傾向于從心理學的維度來揭示這一自由概念,并且嘗試通過自由任性與動物任性之間的對比把它引入進來,而且一如“第一批判”中所做的那樣,獨立于出自感性刺激的這種自由之否定性特征,總是與其在理性基礎上采取行動的肯定性特征緊密相連4。
在對自由做了考察之后,康德隨即聚焦于探究道德形而上學,關于這一點他在札記中已有涉及,而這無疑關涉他后期倫理學的諸多內容,比如義務、三類(或然、實用、道德)強制等概念。在康德看來,實踐哲學處理的是自由之規則的運用問題,它涉及自由意志應該(ought)如何行動的議題,就此而言它與人類學關注的人的實際(actual)行為完全不同。它們的差別之一在于,前者的道德原則具有先天絕對的普遍性,正是這一普遍性保證了義務對有限理性者的必然性約束,而來自經驗的規范顯然不具備這一品格。為了澄清道德原則的獨有特征,康德區分了三種實踐上的必然性概念,即或然的(problematica)、實用的(pragmatica),以及道德(moralis)的判斷5。其中,前兩類涉及為某一目的而采取某種手段(規則),第三類則把一個行為表現為客觀必然的,從而無須與另一個目的相關。非常明顯,康德這里的三類概念分別對應的是《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中的或然、實然與必然命令:“假言的命令式只是說,行為對于某一個可能的或者現實的意圖來說是善的。在第一種情況下,它是一個或然的實踐原則,在第二種情況下,它是一個實然的實踐原則。定言命令式不與任何一個意圖相關,亦即無須任何別的目的,自身就宣稱行為是客觀必然的,所以被視為一個必然的實踐原則。”1與批判哲學時期的看法相同,在前批判哲學時期他認為這一必然的道德命令只對人具有強制性,而不適用于上帝,畢竟在無限者上帝那里根本就沒有義務之說,自然也就不存在強制的問題。
由此可以發現,康德自18世紀70年代前后已逐漸擺脫了萊布尼茨—沃爾夫理性主義倫理學與沙夫茨伯里、哈奇遜等經驗主義道德情感理論的束縛,穩固地走上了一條他自己的獨特道路。對康德而言,道德哲學如何可能的問題只能在理性的范圍內才能加以解決,任何由上帝意志、完善概念、經驗情感等維度展開的研究都不可能成功,因為它們無法解決道德何以必然普遍和有效這一核心問題。只有從理性及其先天的道德原則出發打通其與自由意志的關系,才能為道德哲學的可行性奠定基礎。關于這一點,康德在1770—1777年間的道德反思不僅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其第一批判中有關倫理問題的原初資源,也為我們檢視《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的形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思契機。不過要完全理解這一點,我們還要對道德與宗教的關系進行翔實的梳理。
三、宗教學說:我可以希望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對宗教的關注亦不始于“十年沉寂”期間,出身于虔誠教派(pietism)的他很早就已開始關心宗教話題,而這一話題也是貫穿其哲學生涯的核心命題之一。事實上,早在1753—1754年,為參與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的有獎征文,年僅30歲的康德在《論樂觀主義》2這一題目下寫了3小節反思神義論的殘篇。雖然他后來并未提交這篇征文,但他反對萊布尼茨而支持蒲柏(Alexander Pope)的態度在此已表露無遺。當然,康德在這一時期的宗教立場還不穩固,充滿變數3。比如,到了1759年時他在《試對樂觀主義作若干考察》中又開始反駁克魯修斯(Christian August Crusius)的主張,反而對萊布尼茨的“最好的世界”這一神學思想給予辯護。
康德1770年之后接續了上述話題,對他而言,有德之人必然不會否認上帝的存在。他堅信,上帝不僅是存在的,而且還是知性能夠認知的客體:“上帝的實存能夠借助知性來加以認知,因為這一概念是知性的至上概念,它不受經驗對象的限制。”4上帝是一切經驗對象的基礎,包含萬有,而它是自因的,不能被外在于它的事物所說明。康德這里關于上帝的闡述與其1763年《證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證據》中對于上帝的證明存在異曲同工之處,在這后一作品中康德不僅涉及了對上帝的本體論、宇宙論、自然神學的證明,而且也明確論證了作為邏輯與實在謂詞的“存在”之間的區別5,所有這些思想都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有所呈現。不過由康德的講義等材料看,他于18世紀70年代之后又延續了他在18世紀50年代未竟的神義論事業。他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既然全善、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與維系者,那么惡從哪來的?惡也是上帝的創造嗎?是不是像人會犯錯一樣,惡也是上帝偶爾的疏忽所致呢?
在1772—1773年的哲學反思片段中,康德明確指出:將上帝與人加以類比是錯誤的,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比性,兩者不是量或程度上的不同,而是存在著質的差別。“人們樂于拿人與上帝做類比,但關于它們的表象其實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而且人神同形同性論比無神論更為有害。”6康德指出,上帝與人是根本不同的對象,善是出于上帝之自然秩序的和諧,而惡則是出于人的自由使用的結果。換句話說,惡出自人的自由,它不是上帝的神圣規定所致。全善的上帝是創造一個充滿自由的存在者的世界好呢,還是創造一個沒有自由的存在者好呢?顯然前者更好一些,因為這更符合上帝的善的本質規定:為了創造一個好的世界,上帝理應把一切可能的東西都賦予自由的存在者,包括為惡的自由,但這僅是就上帝對人之為惡的前件規定而言的;至于人是否將這一可能的惡付諸現實,那是人及其自由的運用問題,對于這一后件規定,上帝不置可否,那是人的自由。可以看到,康德對于神義論問題的處理,雖然與萊布尼茨不完全一樣,但他在處理上帝與惡的問題時,無疑受到了后者關于上帝之“前件意志”(une volonte antecedente)與“后件意志”(la volonte consequente)區分的影響1。康德關于這一問題的處理,要到1791年《論神義論中一切哲學嘗試的失敗》中圍繞約伯問題的闡釋才算最終解決,而這一解決的思想萌芽在康德18世紀70年代中期的書信中已有跡可循。對他而言,使人獲得救贖的不是諂媚上帝,或者因恐懼而信仰上帝,任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經受住考驗的方法只能是“純潔的正直”,在這一點上康德認為他與約伯的立場并無二致2。康德將“諂媚”與“純潔的正直”并舉,對應的顯然是其批判哲學時期“教義的”(doktrinal)與“本真的”(authentisch)神義論這一對概念,事實上這也的確為康德后來由實踐理性之本真的維度化解神義論的困境作了必要的思想鋪墊。
處理完神義論問題,康德又轉入了對道德與宗教之關系的研究,與此相關的重要資料是他在1775年4月28日致拉法特(Johann Kaspar Lavater)的信箋。在該信中,康德明確將《圣經》中的道德學說與訓誡區分開來,對他而言,基督教中的“道德學說無疑是福音的基本理論,而其他東西則不過是福音的輔助理論”3,前者顯然更為重要。事實上,康德的宗教觀很不正統,雖然從小受洗,但成年后的他幾乎沒有出入過教堂。而康德之所以在此時吐露關于宗教問題的心聲,與他的學生赫爾德的《人類最古老的文獻》一書的出版有關。康德在1774年4月6日寫信給哈曼(Johann Georg Hamman),請他介紹一下這部關于創世紀及其前身的作品,而且要求他盡可能地使用清楚明白的語言加以說明,因為康德承認自己沒有理解神圣語言的理智構造,若有誰可以用普通的概念和邏輯加以解說,那將是十分難得的事情4。哈曼的回信涉及了赫爾德的四個主張:創世的古老文獻并不是摩西傳下來的,而是源于人類的祖先;創世說等材料涉及的內容,比科學的東西更可靠而真實;創世理論是解開人類文明之謎的鑰匙,也是文明與野蠻分野的根據;人們若想真正了解它,只有舍棄現代哲學5。從赫爾德著作中包含的這幾點思想可以看到,康德對他的嘲諷自是有的放矢,兩人之間的關系已非昔日可比。尤其是對于宗教的看法,他們的隔閡與日俱增。正是基于這一背景,當赫爾德的朋友拉法特征詢康德對于宗教有何看法時,康德立刻回信談了他對道德宗教的基本主張。
康德指出,道德是宗教的基礎,真正的宗教教義也與純粹的道德信仰本質相契、并行不悖,上帝支持一切為善的事業,雖然為善的結果并非全然能由人類所洞察或掌控,但人們依然可以做應做之事,并期望同善行相配的幸福。對他而言,宗教中呈現出的輔助理論與道德學說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能說明鑒于我們在上帝面前悔罪以后,上帝能夠為我們提供哪些幫助;而后者關涉為了使我們“自己有資格享有這一切,我們必須做什么”6。事實上,上帝能夠為我們提供哪些幫助我們根本無從知曉,畢竟即使上帝可以對我們有所言說,我們也未必知道。就此而言,接近上帝的方式有且只有一種,那就是道德的方式,因為神恩支持人們的方式,正是神恩自己希望的方式。在他看來,人們對上帝的信賴是無條件的,不應存在一種認知上帝的好奇心,更不能依據一些信息來把握上帝。此外,康德也承認基督教在初創時為了擺脫猶太教而開創了揚棄一切訓誡的純潔宗教,并且將其傳播到廣大民眾中去的確需要奇跡和神秘的啟示等宣傳手段,但是一旦民眾在心中確立了端正的生活方式、純潔的道德意念之后,那么作為宣傳手段的啟示就應該摒除,既然“大廈已經建成,腳手架就必須拆除掉”1。顯然,康德在這一重要的信件中不僅談到了他對道德與宗教關系的看法,還涉及了他對啟示的理解。對康德而言,基于啟示的歷史信仰與出于道德的理性信仰不同,在宗教建立之初歷史信仰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由于人性自身的弱點,人們對事物的認知總是從眼前直接的經驗對象開始,繼而層層推進到超感性的領域。因此,從邏輯上看,宗教自當以道德為前提;但從時間上看,人擺脫不掉自身的感性規定,理應從具有啟示的事件中開啟靈性的心智,進而走向道德宗教這一目標。用康德自己的話說:“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有一天向道德上的信仰敞開自身,就會不需要歷史上的輔助手段,自動地相信道德上的信仰的正確性和必然性。”2可以看出,康德并非像后世學者說的那樣全然否定奇跡等自然現象,而是賦予了它們一定的價值和存在空間,而這一點其晚年在《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第二章附錄關于“奇跡”的闡述中多有發揮3。
始于“十年沉寂”期間的道德宗教學說,一直被康德所遵守,即使那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神學教義亦被他以道德的方式加以解讀,其中較為著名的是他對“三位一體”的實踐詮釋。康德指出:按照字面意思,我們從三位一體學說中得不出任何實踐的東西,因為我們在“上帝”中到底是崇拜3個還是10個位格沒有任何概念;與此相反,如果我們把一種道德意義置入這一信條中,它所包含的就不會是一種沒有結果的信仰,而是一種與我們的道德規定相關的信仰4。相關原因并不復雜,因為作為無限存在的上帝和作為有限存在的人都是理性的,前者的意志與理性的道德法則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或者說它的意志就是道德法則本身;而后者由于是兩個世界的公民,其行為舉止未必完全符合道德的定言命令,故而需要法則的約束才能端正自己的生活態度,進而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而人一旦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且成為了有德之人以后,他就可以希望應得的幸福,雖然這時候他在認知上依然不知道上帝是3個還是10個位格,但絲毫不影響他對上帝的信仰。因為在實踐理性上人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上帝對于我們的要求也是上帝自己希望發生的東西,畢竟“宗教并不是按照內容即客體而在某一部分上與道德有別,因為道德關涉一般的義務,相反,它與后者的區別是純然形式的,也就是說,它是理性的一種立法,為的是通過由道德產生的上帝理念而給予道德以對人的意志的影響,去履行其所有的義務”5。
基于上述考察,不難發現康德早在“十年沉寂”期間就已提出較為成熟的道德宗教學說。在奔赴批判哲學的途中,康德對此進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正。比如,關于惡的理解,他就曾提出把惡視為“善的不完滿狀態”6“非社會的社會性”“原則次序的顛倒”三種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如何,整體來看,康德這一時期的宗教思想大多還是被繼承下來了。
四、結語
長久以來,眾多學者普遍認為:康德在1770—1781年間之所以能夠克服各種名利誘惑,沒有發表任何能夠為其贏得暫時聲名的作品,原因在于此時的他正在潛心寫作《純粹理性批判》這一巨著。平心而論,這一判斷有其合理處,但又不完全準確。合理處在于,我們由前文第一部分的闡述即可發現,除第一批判中的先驗感性論部分來自其就職論文外,先驗分析論、先驗辯證法等核心內容都來自康德“十年沉寂”時期關于形而上學的思考。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沒有這一時期的思想沉潛,自然也就沒有《純粹理性批判》的出版。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另外一個事實,即康德“十年沉寂”中涉及無數的思想萌芽,而這些思想萌芽又絕非第一批判所能囊括。比如,關于實踐公設、神義論、啟示等論題的考察,都與第一批判關聯不大或者不是它所研討的重心。相反,它們是《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論神義論中一切哲學嘗試的失敗》《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以及《學科之爭》等著作的思想主旨。換句話說,就“我能夠認識什么”這一議題而言,除了時空等純粹直觀思想外,康德絕大多數的認識理論都來自1770—1781年這一階段的沉思;就“我應當做什么”這一議題來看,康德被后世所熟知的那些倫理思想如義務、道德法則等亦與這一階段的思想沉淀密切相關;就“我可以希望什么”這一議題來說,理性神學、歷史信仰等諸多話題,也與他在這十多年間的深層思考脫不開關系。就此而言,如果我們的這個刻畫有其道理,那么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康德批判哲學時期的整個思想架構,在“十年沉寂”這一時期已經初具雛形和規模了,以至于我們對其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因為沒有這一漫長的準備期,將沒有《純粹理性批判》的誕生,亦將沒有批判哲學時期其他諸多作品的面世。在這一意義上,康德的這個獨特的沉寂期無疑值得深入挖掘。
責任編輯 羅雨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