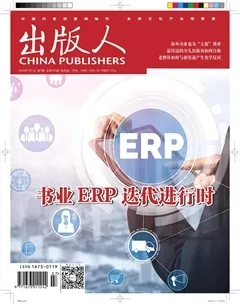儒家王朝士大夫之理想國
吾國歷史之書寫,有眾多方式與體裁。或紀傳,或編年,或紀事本末。而其史觀,大體分兩種。一曰王朝中國,一曰文化中國。王朝之中國,即梁任公所謂之“二十四姓之家譜”,朝代更替之“正史”。文化之中國,則有劉剛、李冬君之《文化的江山》。我們倡導“文化中國”的書寫。
傳統書寫“王朝中國”之北宋王朝,只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度,諸如“杯酒釋兵權”“澶淵之盟”“慶歷新政”“熙寧變法”“靖康之恥”等。而“新史學”之“文化中國”的北宋王朝,威爾·杜蘭稱之為“宋朝的文藝復興”,劉剛、李冬君稱之為“走向文藝復興的歲月”。在孔見的筆下,就是“蘇東坡時代”。北宋一朝之文學與哲理、陶瓷與書畫、詩詞與音樂、雕刻與建筑、哲學與學術、宗教與政治、經學與史學,乃至醫學、水利、生活與藝術諸多方面,在《蘇東坡時代》里,縱橫穿插,索隱鉤沉,描繪了一個“儒家王朝士大夫之理想國”。
無疑,孔見的《蘇東坡時代》就是北宋文化江山最好的書寫文本。孔見的筆下,這個王朝顯得溫情脈脈,生命的價值與人性的尊嚴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權力的眷顧。精神向上生長的可能性空間,也有了足夠開闊的天空。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朵開放得最久最久的曇花”。
大宋兩朝一共319年。孔見不吝筆墨,不惜華美文章,對這個“造極”與“空前絕后”的儒家王朝給予了最高的禮贊。自始至終,孔見亦想誘導出宋朝溫暖繁華之文明盛景,使我們能抵達“理想國”之深處。
這是一個以士大夫為中堅的時代。“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曾鞏、“三蘇”、周敦頤、邵雍、“二程”、黃庭堅等,在政治、文化、學術、思想諸多方面釋放出巨大能量,大放異彩。他們一掃自暴秦以來皇權對士人的精神禁錮和約束,營造了一個開明的政治生態,也為文學藝術的復興、哲學思想的解放創造了條件。文學領域的“唐宋八大家”,除去韓愈、柳宗元,宋占其六,他們完成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學革命。在哲學思想領域,“北宋五子”繼往圣之絕學,將斷流了一千多年的儒家法統承續下來,包容吸收道佛思想,并演繹與重構,從而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以來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
北宋一朝,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應時而發明,陶瓷、茶道與絲綢工藝,居世界之冠。一抔黃土,一片樹葉,一種昆蟲吐出的唾液,經過點石成金般加工完善,注入文化與技術的內涵,名揚世界。在宋朝,天下之大,道理最大。皇帝和臣民一同服從于天理。“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在宋朝,在官僚體系里供職的人,享有足以養廉的俸祿,不需要利用職權搜刮民脂,就可以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在宋朝,一幅《清明上河圖》,一冊《東京夢華錄》,我們就能感受到北宋經濟之繁榮。汴梁城人間煙火之旺盛,幾乎夜夜都升騰到九霄云外了。作為平民,生活在宋朝,比生活在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度都要幸福。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自堯舜至周公、從孔子至孟子所承續的人文精神。縱觀兩千年之歷史,在兩周衰亡后,稱得上儒家王朝的也只有大宋一代了。這應該就是士大夫的理想國吧。
宋之后百年,后千年,士大夫之境遇或顯或幽,王朝政治,或盛或衰,而士大夫心中之“獨立”“自由”之精神,無一時一刻泯滅。家國情懷,憂寄蒼生,繼絕弘遠,追真求理,雖道路崎嶇,九死其猶未悔,一直是歷代士大夫心底永恒之追尋。
今日之知識界,不正在追尋這種精神之路上?“獨立”與“自由”,是文明之源、文明之本。士大夫精神不死,則文明不滅。
孔見說蘇東坡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人,是一個中國文化人格的標本。北宋儒家王朝之士大夫,群星璀璨,而蘇東坡卻是燦爛天空最耀眼的那顆星星。孔見說蘇東坡是一個死透了的大活人,傳蘇東坡者,可謂夥矣。《宋史》有蘇軾傳,林語堂、李一冰、王水照、朱剛、劉傳銘諸君均是傳蘇東坡之高手方家。吾社在20世紀90年代曾有《名人名傳》系列,“林傳”就是其中之一種。近年來,由于“林傳”納入中小學讀書目錄,故“林傳”之銷售竟以幾百萬計。“林傳”之撰寫,林先生寄居海外,史料之殘缺,史實之訛漏,在所難免。而其史觀,也有失偏頗,更何況用英文寫就,為西方人而寫,故其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人人爭讀蘇東坡,人人爭傳蘇東坡,史家、作家、或編輯家爭相加入傳釋蘇東坡之行列,熱則熱也,鬧之則不宜,且圖書良莠不齊,甚至低價而博其流量,過度消耗了東坡。此情形,或亦可休矣。
無疑,孔見是蘇東坡之千年知己,《蘇東坡時代》也是對以往之蘇東坡研究批判與總結之作,亦將開啟新時代對蘇東坡更深入的研究。今日我們亦可以重新審視大宋文化江山,重讀蘇東坡。孔見完成了對蘇東坡以及蘇東坡時代最完整、最理性、最具閱讀快意的書寫。
孔見認為,在東坡之前,中國文化人格是儒道二元互輔結構,而到了北宋,儒釋道三家會通,三位一體,一個以中國人自任的人,三家修養兼備,融會貫通,且與時俱進,其精神人格才得以健全與完整。四十五歲之前,是作為儒者的蘇軾。四十五歲之后,則是以禪立身的東坡居士。無論是儒是禪,他都兼具儒道佛三家修養與智慧,并將三者融會貫通,匯入自己的人格當中,把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交集到一起來踐行與品味。東坡與帝王論對辯難,與傳道高人靜坐參禪,與歌伎泛舟飲酒吃肉,消受人間煙火的肥膩。不論是悲歡離合還是進退浮沉,不論是位極人臣還是深陷死牢,不論是志得意滿還是落魄江湖,不論是寵榮倍加還是罪辱交集,不論是利害得失還是生殺予奪,他都親臨其境,充分經歷體驗,深得個中滋味。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一個完整的社會截面,他都用生命一寸寸地度量。
在眾多蘇東坡傳記中,把蘇東坡視為千古以來第一等的人物,是一個圣人完人。其實不然,在孔見眼中,蘇東坡只是一個通家。東坡在儒道佛各個領域都有建樹,但他都沒有做到極致,沒有抵達“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之境地。于儒學,還不能與周敦頤、邵雍、張載比肩;于道家,與陳摶、張伯瑞、王重陽相去亦遠;于釋家,尚未能參破生死牢關,與同時代臨濟宗、曹洞宗等諸位大德,難以并論。
能出入儒釋道之間,圓融貫通,結成自己開合自如的精神人格,并推廣到現實生活的細節里,形成搖曳多姿的生活方式,千年以來只有東坡一人而已。也正因為東坡的有趣、有味、可溫、可親,有人間煙火,有俠義柔腸,又才氣縱橫,文章錦繡,故歷千年而為人所迷戀而追隨。
人人都學蘇東坡,而蘇東坡不可學。萬卷書已經讀遍,萬里路也已走盡。東坡在回歸中原的那一剎那,他的精神生命已經完成。他的人生止歸,既不在南,也不在北,也不在南北之間。東坡在臨終之前,留下了詩偈《觀潮》,就此一偈,又會憑生出多少感懷。
東坡歿后,“吳越之民,相與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蘇東坡這位時代之子的離去,如同高山崩塌,但他留在世間的珠玉奇石,其分量之重、光輝之璀璨,卻是誰都無法估量的。在他身后拾余者的隊伍更是浩浩蕩蕩,至今看不到盡頭。
東坡歿后16年,北宋終于結束于嗜血的戎狄。書之結尾是“大宋之殤”,充滿了悲憫和無可奈何。野蠻戰勝了文明。“世世代代苦心孤詣積累起來的文明,不僅被橫加掃蕩,而且受盡玷污與恥笑。”
宋朝滅亡,皇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體制隨之崩潰,皇權、相權、臺諫三權分立之精英民主協商政治終告結束。之后的王朝,又回到了“家天下”的屋檐下,君臣關系變為主奴關系。儒家王朝士大夫的理想國也灰飛煙滅了。
《蘇東坡時代》是傳記嗎?是傳記,又不是傳記;是北宋歷史嗎?是歷史,又不僅是歷史。這是北宋一朝的士大夫精神史,是北宋一朝的文明史,是北宋朝中國的“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