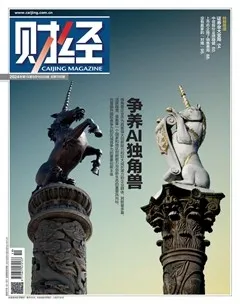別用老方式投資AI新創公司

科技創新與風險投資密不可分。我們正處于以AI大模型為核心的新一代技術浪潮中,這是一個長周期、重投入的新技術,資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的一級市場投資正在發生劇烈變化。從過去的以美元基金為主導,到今天以國有資本和人民幣基金為主,過去以消費互聯網為主題,今天更多以硬科技為主題,市場整體融資規模持續下滑,第三方數據機構企名片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一級市場共完成8617億元融資,同比下降38%,2023年繼續下滑13%。
對于科技投資來說,資本是否有耐心至關重要,過去人民幣基金的周期短于美元基金,但今天隨著國資和政府引導基金入場,人民幣基金也逐漸往長期發展。
9月6日,在第六屆外灘金融峰會上,君聯資本總裁李家慶接受《財經》專訪,他提到,中國一級市場投資過去幾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一次的技術革命又相當于是一次地殼運動,會形成新的高山和地貌,今天同樣在快速變化中。作為投資人,必須調整募資、投資和退出的邏輯,考慮更多復雜影響因素。
他還提到,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要做科技創新成本提升了,不僅對創業者的綜合素質要求極高,還需要整個市場和資本的大力支持,才能跟得上今天的技術變革節奏。
君聯資本成立于2001年,是中國最早一批市場化投資機構,其前身是聯想集團旗下的聯想投資。李家慶2001年加入君聯,從事科技投資已23年。君聯資本累計投資超過600家企業,包括寧德時代、科大訊飛、藥明康德、智譜AI等,目前最新一期基金管理規模約500億元,包含人民幣基金和美元基金。
以下為對話整理:
中國風險投資的變化
問:過去幾年,中國的一級市場投資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李家慶: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和國際經濟、國內經濟、地緣政治、二級市場的變化相關。從美元基金為主體到以人民幣基金為主體,從消費互聯網到硬科技,從民營資本到國有資本,整個行業已經出現了范式變化。
問:聚焦到科技投資來看,科技領域需要長周期,從美元變成人民幣為主體會有影響嗎?
李家慶:有影響,但沒有想象中那么大。今天的人民幣基金的周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我們能看到全國社保基金、國家級戰略基金,包括地方政府的產業投資基金加入,基本有8年-10年的周期,甚至有一些可以長到12年以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影響不大。
更大的影響是資金供應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重大變化,過去是“美元基金+消費互聯網+海外上市”,現在是“人民幣基金+硬科技+國內上市”。對于投資人來說,募資、投資、退出都完全不一樣了。
問:這個不一樣具體體現在什么方面?
李家慶:財務回報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了。除了財務回報,也要考慮國家政策、上市規則、地方招商引資的訴求,更復雜了。
問:有些投資人提到,過去投100個項目里有幾個成功,就有可觀回報,但現在就需要每個項目都能保證回報,市場對于風險的接受度下降了很多。
李家慶:這個說法有點絕對。一方面要看資方的態度,我們合作的一些國家資金還是愿意讓市場化的投資機構來做投資。另一方面,這個差異主要是和行業本身相關。移動互聯網是商業模式創新,是存量資產和存量技術的整合,通過資金注入和推動,短時間形成聚集效應,實現贏家通吃。這樣就會誕生一批平臺型公司,可能實現“超級回報”。
今天我們投的更多是硬科技領域,硬科技有三個特點,一是周期長;二是多路徑發展,有很多路徑都能實現技術突破;三是不具備網絡效應。我們必須接受事情本身的規律,市場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投資人,你要去順應這個變化,當你無法做到“超級回報”的時候,你只能通過技術、產業和市場的發展規律,去實現一個相對高的回報率,通過一批項目的成果來實現基金的整體回報。
科技創業投資的變化
問:前幾年以商湯和曠視為代表的AI創業公司,找到了安防這樣一個巨大的應用場景后,快速拿到大額融資;今天的AI大模型創業公司,還沒有大規模應用就已經拿到很多錢了,這是為什么?
李家慶:這就是我說的行業發展規律。過去,我們習慣于新技術來了,先找到一個具體的應用場景,以應用來帶動技術發展。找到了,就快速起來;找不到,就很困難。
今天我們面對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如果我們把科大訊飛視為第一代AI公司,商湯曠視屬于第二代,現在我們見到的是第三代。今天AI大模型最大的區別是,它是一個底層創新,通常來說底層創新和應用距離就會比較遠。
比如說當年蒸汽機發明的時候,你不知道它最早會應用在哪個領域。技術從發明到滲透行業,甚至在個別領域出現爆發式增長,建立新的生產關系,可能需要20年-30年的時間。如果你還用原有的應用創新模式的投資思路,是有點操之過急,甚至是低估了這件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家、專家,包括媒體的觀點,會對整個產業帶來波動影響,我認為是不值得的。
問:部分人的觀點為什么會對產業造成影響?
李家慶:會給一些非長期的資金、用戶,甚至部分政府主管部門帶來情緒上的波動。一旦有波動,投資力度就會快速下降。
中國風險投資和美國的區別
問:硅谷以市場化基金為主,我們看到的結果是科技公司很早就能拿到高估值,并且引領了技術創新,中國現在的模式特點是什么?
李家慶:現在才剛開始,我很難說結果。但確實兩種模式的底層邏輯是不一樣的,因為資金來源不一樣。中國更適合集中力量辦大事,或者說新型舉國體制。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硅谷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是谷歌、亞馬遜、微軟、蘋果和特斯拉,它們提供資金、應用場景和客戶來源。
在中國,這個責任是政府和央國企在承擔。
其實很難說有所謂的優劣,更多還是不同經濟體制和不同發展模式決定的,但階段性來看,我們得承認美國是跑在前面的。
問:這會對創業生態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李家慶:全世界只有美國有這樣的軟件服務生態,可以快速實現規模化。中國本身的IT基礎設施、企業的能力、應用的水平、服務的意愿都有一定差距。這種情況下,我們的AI走得會比美國艱難一些。因為確實沒有足夠多的企業客戶有信心和你一起往前走。大家愿不愿意在早期就投入進來,愿意為還不夠成熟的過程付錢?其實是有不同聲音的。
問:為什么會有不同聲音?AI是國家戰略了,必須投入;硅谷目前有不少人在質疑商業化和AI安全問題,這會影響AI的戰略重要性嗎?
李家慶:無論是中國還是硅谷,對于AI發展的終極目標是非常堅定的,國內的情況是,目標是明確的,但有些人可能耐心不夠,會更關注怎么還沒賺到錢?這件事到底行不行?是不是已經到頂了?其實過段時間OpenAI又砸出來一個新的東西,大家又覺得,哦,原來還有這么大的空間。
所以現在國內的資本堅定投入,央國企和民營科技創新企業全力合作,變得更重要了。
問:對創新公司來說,現在這個階段創業成本變高了。
李家慶:對,在現在的環境下,民營企業想要創新真的非常不容易,必須要和政府、央國企合作,甚至是獲得更大力度的支持。
第一,民營科技企業要保持住對于新技術的跟蹤,能跟得住就已經很不容易了。第二,你還要強調自主可控,這不光是中國,韓國、日本也一樣強調這一點,所以你不能簡單的“拿來主義”,你要真的投入進去。第三,你還要處理好和政府、央國企的關系,他們對外的投資并購其實并不多。
所以這種情況下,創新很難,而今天的科技公司恰恰碰上的是這種程度的技術革命,是一個重投入、長周期的事。
問:上一代的部分AI公司會遇到一個問題,維護客戶關系占用了太多的精力,甚至影響到了技術研發,這里面有矛盾嗎?
李家慶:不矛盾。上一代的AI公司主要是做人臉識別,它太貼近應用了,且這個應用和各地政企關系太密切了,所以你自然會去這么做,要不然你別創業了。不能把這兩件事對立起來,對于中國的科技公司來說,這是其能力的一部分。就像如果你在美國,除了科研能力,你同樣要具備客戶獲取能力。
問:這種情況下市場規模會是個問題嗎?一些外國創業公司很早就開始做全球化,中國公司大多只能做本地市場,甚至只能和地方政府合作。
李家慶:這其實還好,因為中國市場足夠大。先做本土再去出海,還是全球市場一起做,我覺得無所謂對錯。以色列、韓國的那些公司只能做全球化,因為他們本土市場很小。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直用市場化的、長期的、專業的方式來做事,是否符合規律。
大模型改變中國軟件生態
問:很多投資人說,AI再火,但如果是一家軟件公司,他也不會投。
李家慶:中國市場對于軟件價值的認同度確實不高。這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企業的消費習慣相關。但這件事是會發生變化的。
問:變化的基礎是公有云普及嗎?
李家慶:這一次變化的基礎是大模型,不是公有云。
有很多人會把大模型理解為一種軟件,其實不是,大模型是資產,是數據資產,中國的市場是會為數據資產服務付費的。
過去大家不認為軟件是資產,軟件看不見摸不著,你不把它裝到一個盒子里就賣不出去,還一定要搭配硬件來賣才行。凡是隱性的、長期的東西,市場都不愿意付費。但是當大模型起來之后,它同時是一個軟件和一個養成類資產。它會在使用過程中,價值越來越大,當它展現出資產價值的時候,企業就愿意付費了。就像你要采購桌椅、電腦,你也需要采購智力。
我相信未來大家會越來越接受這件事。
問:如果這件事變成資產,大公司難道不會更愿意自己來做這件事嗎?他們對本地化部署是有要求的。
李家慶:我舉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例子,你家里要請保姆,你一定是去找一個有基本技能的保姆,比如會做飯,到了你家之后,再根據你的需求學習一些新的東西,來適應你家的飲食習慣。這個前提是他已經具備了通用技能水平,而不是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從頭學。
無論你是要私有化部署還是上公有云,都需要一個通用大模型,所以做通用大模型的公司,要不斷去提升模型智能,讓它可以適應任何一個場景。
新一代科技創業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
問:今天大部分科技公司都從基礎大模型到中間層,再到應用,全部都自己做了,從投資人角度看,這樣的公司會更值錢嗎?
李家慶:肯定不會,因為你做不到,一家公司肯定還是有側重的,你到底是做基礎訓練,還是做芯片,還是做集群優化,或者是應用,大家需要各司其職。
今天有很多大模型公司很焦慮,它發現做不了應用,因為它對于具體業務的了解不夠,客戶的需求在數據私有化的情況下做不到。真正底層的技術也做不到,也沒有很強的客戶資源,只想進來快速賺錢。比如早期有很多文生圖的公司,一開始看起來好像很厲害,過了兩天就發現不靠譜,這個東西大家都能做。
大模型的發展會讓整個水面都漲上去,你露出來的冰山一角很快就被淹沒了。核心就是你沒有抓手,或者你的抓手并不牢靠。
問:今天投資人對優秀科技創業者的評價標準發生了哪些變化?
李家慶:以前我們會希望找到銷售出身的創業者,他對市場和客戶很了解,善于運用營銷和流量工具。今天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首先要看的是學術背景。我們自己內部的企業交流活動,幾乎全都是博士和教授,投資人對于創業者對新技術的敏感度和前瞻性還是有要求的。
其次,他也需要經歷從科技工作者到企業家的轉變,這個轉變非常困難。他要善于整合資源。我們不是要把教授變成企業家,教授就做好自己的工作,他要知道讓誰來做CEO(首席執行官),要有組建團隊的能力。
第三,投資人對創業者的價值觀要求提升了。今天這條路很長,資源投入的力度很大,你不能只做短線的事。
問:對比硅谷的創業者來看呢?
李家慶:硅谷對創業者本身素養要求相比中國是更低的。硅谷有相對完備的創業生態,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合適的CEO、CFO(首席財務官),所以對創業者個體要求沒那么高,你做好自己的事,然后把公司賣掉就行了。硅谷要求的是某個方面的長板特別長,不需要是全才。
中國就需要創業者能力更全面。今天在中國創業的真的不是一般人。我們沒有形成并購的氛圍,部分原因其實是沒有什么底層創新,自然也就沒有并購價值。大公司也會想,你都是“拿來主義”,我憑什么要收購你?
所以我還是蠻樂觀的,因為從今天往后,你不能再用過去的方式來做了,我們要自主可控,要底層創新,這樣才能帶來二級市場和并購市場的繁榮,才能形成新的價值和消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