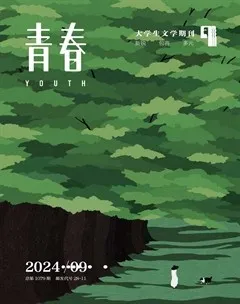遵從小說的“法律”
編者按
本文為畢飛宇工作室第44期小說沙龍討論紀實。本期沙龍由龐余亮主持,汪政、王夔、易康、單枚、劉春龍、李檣等作家、評論家,圍繞短篇小說《近在咫尺》,從小說的文體選擇、內容結構、語言風格、敘述邏輯等多角度進行解讀與點評。
小說是填空的藝術
王夔:這篇小說我剛開始讀的時候很期待。它的開頭部分是一團迷霧,我作為讀者恨不得一口氣讀完,但小說結束的時候我就對它失去了興趣。
讀完再翻到開頭,我覺得作者的初衷可能不是想寫一篇小說,而是一篇散文。這篇小說有過于抒情的語調,然而這種語調不適合小說。
因意外失去愛侶這個主題,我覺得很難寫,因為容易落入俗套。如果一定要寫,要想辦法使它更有沖突性。她雖然死了,但她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我要“殺死”虛無中的她,這樣我才能夠重新生活。在“殺死”她的過程中可能會衍生出一些其他的情節,我相信在寫作時它們會自己跑出來。這種思路是,我確實愛她,但也恨她,因為有時候愛到盡頭就是恨,有時愛是恨的一種,有時恨也是愛的一種。
龐余亮:這個作者最大的問題是,敘述時空出現的時候不懂得如何填滿。我建議作者可以去讀一下克萊爾 · 吉根的《走在藍色的田野上》,寫的是一個教父回憶他的初戀情人。初戀情人要結婚了,他自己不是新郎,但他作為教父要去證婚。小說里就寫了這一天的經歷,從早晨開始一直到晚上,是一篇相當扎實的小說,它前后的經歷全部靠物的東西填滿。
這篇作品其實也可以填滿,比如說冰箱:這是個什么冰箱,什么牌子,單門的還是對開的。冰箱里的酒也可以填進來很多東西:酒的名字,酒的年份(過期的、沒有過期的、接近過期的)。作者都沒寫,但完全可以寫,把它寫多、寫足。我們年輕作家寫東西的時候,物質的東西一定要多一點。
我常說,寫作必須回到名詞當中去,小說沒有名詞是填不滿的。《紅樓夢》里寫愛情故事,里面全是各種各樣的名詞,有名詞,情感才有寄托。作者的情感盡管是好的,但沒有名詞,就永遠是飄著的。小說實際上就是填空的藝術,作者空的地方太多。
初學者的寫作不要太為難自己
易康:作者的語言相對來說比較成熟,也有自己的風格,和其他的年輕作者相比要老練一點,敘述也比較完整。
作者可以改進的地方主要在篇幅,這篇小說太短,連同標點符號都不足五千字。這是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對年輕作者來說,在這么有限的體量里要施展自己的拳腳是比較困難的。當然好的作品未必字數就多,比如《孔乙己》也就兩三千字。但作為初學者,我建議不要給自己出難題。我是個語文老師,我發現有的同學寫作文時,選擇了沒有多大空間的題材,一開始就把自己逼到墻角了。所以我覺得初學者在寫作時,不要為難自己。
首先,小說是形象思維。即便是抒情意味很濃的小說,其實也是形象堆積起來的,比如《了不起的蓋茨比》。認為要寫出情感與詩意就必須忽視形象,是一個誤解。
其次,小說的人物、情節要貼近生活。不是寫愛情小說就一定要有詩意與遠方,我覺得小說要有一點煙火氣。有些小說寫得通俗一點、土氣一點,操作起來相對比較容易。作者如果有志于寫作,功夫要用在平時,把觀察生活、研究人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這樣才能寫出好的小說。
最后,要懂得反向思維。如果作者有志于情感類小說的寫作,我建議閱讀《洛麗塔》和《了不起的蓋茨比》。《洛麗塔》展現了無限的期待和絕望,就是一種反向思維。把兩個東西結合起來,寫作的空間感就出來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蓋茨比認識到真相后依然非常執著。這樣人物顯得與眾不同,想象的空間也就打開了。
龐余亮:其實這篇作品有物質的部分,比如主人公去找禮品店。這是特別好的點,但作者放過去了。我建議作者可以從身邊熟悉的街道入手,寫出有哪些店鋪,店鋪里有哪些人。在這些店鋪中找禮品店,一下就具體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去拍下來,在寫作時進行描述。作者描寫實物的能力還是太弱了。
我們寫小說還是要回到現實當中。比如克萊爾 · 吉根的《走在藍色的田野上》中,主人公初戀情人的臉上有雀斑,他分手后做夢,夢見一陣風吹來,把她臉上的雀斑都吹走了。這個細節里就有很多微妙的東西。愛情最后一定要寫到“微妙”二字,莫名其妙的微妙,像林黛玉跟賈寶玉之間那種微妙,他不知道她為什么就生氣了。這篇作品里提到情侶之間送鬧鐘,其實情侶之間送鬧鐘情況不多,個中理由要說清楚。同時,年輕人的狀態也可以進一步表現出來,例如刷視頻、打游戲、點外賣。小說家一定要落到最實處,現在的作品仍然不夠扎實,有太多東西還飄在半空中,還沒打開。
單玫:閱讀時我想到自己剛開始寫小說時的一種情況,我努力想講一個故事,但該用力的地方用不上力氣,不知道如何把故事向前推進。這個作者該用力的地方沒能用得上,不該用力的地方又描寫得過多,和我當時犯的錯誤是一樣的。他/她的寫作試圖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但沒寫好,沒能把期望或者失望寫出來。像龐老師說的,有點空、有點虛,沒有填實。
另外,好的小說應該體現人物之間復雜的關系,這就像打拳擊一樣。作品里的主人公仿佛一直在對著沙袋打,沒有一個人物跟他對打。如果讓我來設計一個人和他對打,我會選擇他的母親,讓他的母親分量更重。小說叫《近在咫尺》,就該寫身邊的人。飛機失事了,男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當中,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怎么過呢?可以把媽媽這個角色潤色一下,讓她飽滿起來。
留心最熟悉的日常生活
劉春龍:我一開始讀這個小說的時候充滿了期待,很懸疑,我覺得有希區柯克的影子,讓我忍不住往下讀。
但這個小說中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文中很多細節缺乏生活的邏輯和常識。小說再好,它離不開生活的真實。比如文中說“雖是大早,店內的人可真不少”,但“大早”是天剛亮的意思。還有,主人公在極度的悲傷時,他的哥們雨杰竟然給了他“肩頭一拳”。寫作者要有一定的生活積累,即便生活的積累不夠,要有意識地多看雜書,不能提筆就寫。只有準備充分了以后,寫小說才顯得從容。
二是布局的問題。不管是應激障礙還是失憶,主人公是拒絕真相的。到底是愛得太深還是愧對伴侶?我覺得可能是前面一種。但有沒有另外一種情況出現,就是這幾年當中他的愧疚太多?小說中我沒看出來,但我覺得這其中應該有比較多可以寫的地方。
李檣:老師們對這篇作品提出了很多意見,在我看來指出的這些問題都是很對的,但從作者角度來說,要學會批判性地接受。對于一個文學新人來講,既有不足,但也要允許不足的合理存在。每個新手都要走過這樣一個階段才能不斷成熟。
我一看到這篇小說的時候,還挺喜歡的。作者語言當中的傷感氣氛是很均衡的。說傷感可能都輕了。對任何藝術品來講,不管是繪畫還是音樂,傷感幾乎是一個好的藝術品不可剝離的基因。
文學更多的是去揭露與批判,不管是社會現實還是人性。那么這當中就勢必會有悲劇色彩,會有傷感氣氛。甚至我們古今中外的很多經典作品,都有這樣一種氛圍。我覺得作者的調調起得很不錯。
主人公選擇忘記那段自己與深愛的女孩的記憶,但記憶就像一根刺,始終扎在他的身體中,又使他無法自拔。這種感覺在作品的前半段很明顯,但后面有點虎頭蛇尾,前面的力度一下子被沖淡了。讀者從一開始就看到了主人公心里所承受的痛苦、煎熬,到結尾也沒經歷什么高潮,好像在揭謎底一樣,這個就有點牽強,缺乏一個短篇小說應有的沖擊力。
很多寫作者都有這樣一個毛病,我們都很熱愛寫作,把它當成藝術品來對待,會覺得藝術品應該在很遠、很高的地方,而身邊的這些日常,這些最熟悉的人與事,反倒會被我們有意無意地隔離開來,拒絕它們進入我們的文字,拒絕它們進入我們的視野,好像這些都太俗不可耐了,不值得一寫。這顯然是不對的。
小說中母親的形象比較豐滿,令人信服,為什么?因為母親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太熟悉了。我們選擇這個寫作對象的時候,最能觸動愿意下筆的那個地方。因為它太真實了,就在我們身邊。但很多寫作者往往會拒絕這種身邊特別真實的日常,而它們其實是最容易把控的。
另外,這篇小說中間設置了一個小提琴大師,從結構和主題的表現上來講,它是格格不入的。其實如果讓我寫,它倒是可以對這個小說起到一個潤色的作用。比如我在某個場景遇到了這首小提琴樂曲,受它吸引,重點在這個音樂,而沒必要交代小提琴家的身份。
對于一個新人來講,應該說他/她的敘述語言是過關的,剩下的工作就是多寫,越寫越熟練,越熟練越有感覺。如果能堅持下去,我相信作者能寫出好的作品。
夏杰瑋:首先由衷地感謝各位前輩老師,給我提出這么多寶貴的建議。這是我寫的第一篇小說,我也能感覺到里面的情感過于泛濫,內容也不夠充實。這篇小說字數少,并不是因為我不想寫,確實是有心無力、使不上勁。今天聽了老師們的建議,我發現里面有很多地方可以充實,沒有必要寫那么多復雜的情感,可以多寫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我在這里想回應兩個地方。一是信的問題,其實我本來是想寫一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故事,所以才設置了信的情節,里面的語言比較俗套,因為我想情侶之間寫信應該沒有那么多深奧的東西。二是主題的問題,我本來想借小提琴家來表達“我們的生活不能被各種痛苦和困難囚禁,我們要走出這種牢籠,才能走向更好的未來”這個主題,但沒處理好。
寫到自己滿意為止
汪政:夏同學是理工專業的,既然對小說有興趣,要慢慢學。
“詩與遠方”這個話真是害人,害了好多寫作的人。總以為詩和遠方是在一起的,然后誤認為文學也在天邊,其實好多文學都是在身邊的。小說從起源來講是非常世俗的,它就是一個好玩的東西。小說一開始就來自街談巷議,之后慢慢才有書面的知識分子小說。
對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來講,要對自己的小說有個評估,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考察。第一,這個小說是否成立。在構思階段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覺得不成立就不要往下寫。第二,成立以后,就要把它先寫出來,看小說的完成度。一篇小說,起碼有頭有尾、起承轉合,這些都要像模像樣地完成。第三,完成以后,再來看是否完美。初稿可能都有瑕疵,所以要進一步打磨、修改。這個標準就很多了,情節、人物、語言、修辭、敘述等,每個方面都要讓它盡可能地提高,把它寫到極致,寫到自己滿意為止。
我經常提一個概念叫自覺的寫作者:我知道自己在寫什么,我知道自己哪兒做得不夠,我知道好作品的標準,我能夠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我知道自己的強項在哪兒,我知道自己的寫作道路該怎么走,等等。
每次寫作都是一次文體和風格的選擇,前面也有老師提過,覺得這一篇不像小說,更像散文。我覺得,既然夏同學還處在初學寫作的階段,就一定要守規矩,選擇好文體和風格后就要努力按標準來,不能看到什么都想放進來,要懂得取舍。在文學的歷史、演變中,文體是最活躍的,也是最根本的。我曾經說,在諸多的文學要素當中,最具有法律意義的就是文體;在諸多的表達當中,最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文體。醫生可以搞文學創作,但如果他把病歷寫成小說一樣的,肯定不行。這就是規矩,這就是文學的“法律”。夏同學這篇小說在文體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回去可以再好好思考一下。
最后來講小說的語言。好的寫作者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一定要把自己的表達方式跟語言接通起來,可惜很多寫作者一到了寫的時候就開始拿腔拿調。所以,初學寫作者一定要努力建立這樣一個機制:我寫作的語言風格,就是我平常說話的風格。然后再在這個基礎上,按照我剛才所說的進行美化處理,不要端著寫。
注:實錄中涉及的內容為修改前的作品,為保持現場研討原貌,相關敘述予以保留。
本文由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萬子恒整理。
責任編輯 張范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