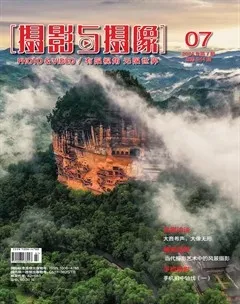大音希聲,大像無形












編者按
他愛好音樂,尤其鐘情小提琴,他亦愛攝影,他說:“藝術是相通的”;
他既擅長發掘小題材,拍攝“小人物”,更善于抓“大題材”,成就時代精品;
中國攝影金像獎,“國展”金牌獎,作品入展國家博物館……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堅定踏實,他的每一項成就都令人矚目;
二十五年軍旅生涯,十年直轄市攝影家協會主席,又帶領新生的重慶市文化旅游攝影協會“從零起步”,構成了他攝影經歷的一座座里程碑。如今,他喜歡和年輕人打成一片,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對攝影新人的“傳道、授業、解惑”。
本期名家訪談,讓我們一起走近第十屆中國攝影金像獎獲得者、全國旅游攝影協會聯盟副主席、重慶市攝影家協會原主席、重慶市文化旅游攝影協會主席馮建新。
馮建新
高級記者,出生于重慶,1970年入伍參軍。1973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北京軍區某軍、師宣傳科(處)專職新聞干事(隨軍記者),1990年任某集團軍軍政治部秘書處上校秘書處處長。1985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榮立二等功兩次,三等功三次,各類嘉獎12次,曾被北京軍區授予先進新聞工作者稱號。1995年轉業,歷任副廳局級副巡視員兼新聞出版處處長,重慶廣播電視集團(總臺)副總裁、副總臺長,《重慶新聞界》雜志總編輯,《中華新聞報》重慶記者站站長。曾任多屆中國新聞獎評委,中國新聞個人成就最高獎“長江韜奮獎”評委,國家藝術基金初評和總評評委。西南大學、重慶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四川外語學院等八所大學客座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現任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旅游攝影協會聯盟副主席,重慶市文化旅游攝影協會主席。中國攝影個人成就最高獎“金像獎”獲得者,中國攝影作品最高獎“國展”金牌獎獲得者。曾任重慶市文聯副主席、重慶市攝影家協會主席。被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全國抗震救災優秀攝影家”稱號,“為中國攝影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攝影工作者”稱號。
主要攝影代表作:
《我的中國故事》(其中包括《和平年代的兵》《老紅軍的心愿》《在丈夫肩上“行走”的鄉村醫生》3個系列50幅作品外加論文《讓攝影飛——紀實攝影的堅守》):榮獲第十屆中國攝影個人成就最高獎“金像獎”;
《無名小站》:榮獲全國第15屆攝影藝術展覽(國展)金牌獎;
《老紅軍李仙義》:榮獲全國聚焦長征路攝影大賽中國攝影家協會收藏大獎;
《重慶老紅軍》(組照):入選全國聚焦長征路影展,其中《老紅軍李仙義》獲中國攝影家協會收藏大獎;
《25000里·COM》(組照):榮獲2010全國攝影藝術展覽(國展)藝術類“評委推薦作品獎”。《圓夢》獲2012全國攝影藝術展覽(國展)多媒體類“評委推薦作品獎”;
《告別》:2018年入展國家博物館改革開放40年《影像見證——全國攝影大展》。
攝影與攝像:馮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專訪。按照采訪慣例,請先簡要介紹一下您的攝影經歷。
馮建新:我的攝影經歷比較簡單,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軍隊的攝影。我在文藝宣傳隊當了幾年文藝兵,后來宣傳隊解散,我調到了師部文化科、宣傳科當新聞報道干事。由于我上稿率比較高,所以又被調到軍宣傳處,成為一名專職的新聞干事(也稱為隨軍記者)。我1980年開始學習攝影,1985年就獲得了中國攝影家協會主辦的首屆全國花卉攝影藝術展覽金牌獎,三年以后,1988年獲得了全國第十五屆攝影藝術展覽(簡稱“國展”)金牌獎。
第二階段:就是1995年以后我轉業回到了重慶,成為重慶市委宣傳部的一名新聞官員,負責全市的新聞管理和新聞發布。攝影就變成了我工作之余的愛好,但是在此期間也獲得了不少的新聞攝影獎項。1997年香港回歸,我結合新聞工作拍攝的《三峽放舟迎回歸》獲得全國攝影抓拍大賽金牌獎,而且利用節假日和休息時間深入基層,拍攝了不少專題照片,也獲了不少獎項。比如《老紅軍的心愿》就獲得了全國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攝影大賽的中國攝影家協會收藏大獎和中國攝影個人成就最高獎金像獎。
第三階段:就是我擔任重慶市攝影家協會主席的十年。這十年里,我把重慶市攝影家協會從一個不知名的協會,做到了全國較為知名的協會,兩次獲得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全國表彰。協會的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從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實現了中國攝影金像獎重慶市零的突破。《中國攝影報》兩次頭版頭條宣傳協會彎道超車,卓有成效地成立體制內第一個當代攝影藝術專業委員會,被《中國攝影報》評為“特大膽人物”,《中國藝術報》刊發了對我的采訪《“鏡頭朝下”的時代攝影家》,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我“為中國攝影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攝影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第四個階段:退休以后。我從重慶廣播電視集團副總裁、重慶市文聯副主席、重慶市攝影家協會主席等職務退出以后,又到重慶市文化旅游攝影協會當主席至今,就一直沒有離開攝影組織工作和攝影創作。新的文化旅游攝影協會的路怎么走?這是又一個新的考題。我認為,新的攝影組織就應該有新的工作方法和方向。所以,我一是強調隊伍的年輕化;二是強調要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突出手機攝影、航拍攝影和短視頻的操作;三是訓練培養出更多的大V,以適應重慶市的文化旅游的發展和需要。過去,我在重慶市攝影家協會帶頭在國展拿獎牌,第一個拿到中國攝影金像獎。現在我要帶頭在新的媒體和新的領域進行實驗和突破,目前,我在《長江頭條》設立了專號,閱讀率25萬多;我在快手講課,單條都是40萬閱讀量;我在《今日頭條》最多的一條有130多萬閱讀量;我發的《美篇》一般都是上萬閱讀量。
攝影與攝像:從你的攝影經歷中,可以看出軍隊是一個大熔爐,你在軍旅題材的拍攝過程中,有哪些特別的記憶?
馮建新:軍隊有著太多的記憶了,因為我的青春都奉獻給了國防事業。但記憶最深的就是我拍攝的那張《無名小站》(1988年獲得全國第15屆攝影藝術展覽“國展”金牌獎)。那是一年冬天。我坐長途公共汽車去連隊采訪,車開出不久,就聽見有個孩子在啼哭。隨哭聲望過去,只見一個抱著嬰兒的婦女坐在一扇破車窗前,冷風夾著細小的雪花直往里灌。當時的承德壩上地區非常窮,這種殘破的公共汽車比比皆是。我看不過去,就和他換位置,順便問了一句:這么冷的天,還帶著孩子出門?婦女是江浙口音,說孩子生下來這么大了,還沒見過他爸爸。他爸爸也在部隊上,總是來信說連對工作太忙,我只好帶孩子來看他爸爸。當時我穿著“四皮”(注:皮大衣、皮帽、皮手套、皮大頭鞋)都覺得冷,這對來自南方的母子更是冷的渾身發抖。這種“一家不圓、為了萬家園”的軍人和家屬們的奉獻精神,真的讓我很感動。聯想到我自己家里也是這樣,女兒到四歲時才隨軍和我在一起,兩地分居的日子就是一種奉獻精神,我想,我一定要拍一張這樣的片子。
在拍攝《無名小站》之前,我的心里已經有了很多無名戰士的情感和生活積累。那是1987年2月,春節剛過,我去駐扎在河北壩上圍場的連隊采訪。這個連隊在一個窮山溝里,因為部隊在此,所以路邊才增加了一個無名的招呼站。一場大雪,封了路,我也留了下來,兩天以后雪停了,來了一輛公共汽車。探親的軍屬門排隊上車,一個小女孩和她媽媽排在最前面。一上車就找窗戶看外面送別的爸爸,但所有的窗戶都已冰封霜凍打不開,她只好跑到后窗的一扇破玻璃縫隙前,伸出她的小手晃著喊著:“爸爸再見,爸爸再見。”只見軍人呆立雪地,仰望著車窗里的妻女。我看到這個情景,耳邊又響起那位軍嫂懷中嬰兒的啼哭聲,心頭一熱,眼前一亮:“這不就是我等了好久的片子嗎?”我馬上掏出攝影包里的相機,把這一感人瞬間抓拍了下來。因為當時的相機都是膠片相機,拍了也看不到。等沖出來以后,我一看,這個瞬間真棒,于是就投稿給“國展”,沒想到居然獲得了金牌獎。當然,這個記憶也隨著作品《無名小站》的傳播成為了更多人的記憶。
攝影與攝像:在四十余年來的攝影經歷中,您的主要創作板塊可以分為幾部分?這些板塊之間有什么關聯關系?這種關聯關系,能否理解為您的攝影感悟或者說是攝影理念?
馮建新:我的創作板塊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在軍隊作為隨軍記者專職攝影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以新聞攝影報道為主;第二部分,主要是轉業回地方以后,作為新聞官員,沒有更多時間去拍攝,而只有將攝影作為業余愛好;第三部分,是作為當選重慶市攝影家協會主席以后,要帶領大家去創作,而更多地介入到一些攝影組織活動中;第四部分,就是退休以后,依然堅持攝影創作,更多的是傳幫帶,到全國各地去做攝影講座,傳播攝影藝術。當然,堅守“光影當隨時代”的理念,爭取在互聯網上有所作為,當一個大V。
至于你說的有何關聯關系?我認為是有的。一是攝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是在部隊搞專職攝影,還是轉業到地方后的攝影愛好,都沒有離開攝影,就像交響樂一樣,有主旋律也要有復調,這樣才能更協和。二是愛好就是動力。其目標,就是要實現人生的價值。我在微信里寫了一條我的座右銘:懷揣初心一路向前,抵達自己仰望的高度!三是一定要處理好工作與愛好的關系,在這方面我是有很深的體會。
下面談一點我的體會:最重要的,必須認真干好本職工作,這樣才能為自己的愛好(攝影)鋪好路。我是1970年入伍參軍,后調任某師宣傳隊擔任小提琴演奏員、樂隊排長、政治指導員,入伍三年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入伍九年后調師文化科、宣傳科任新聞干事(隨軍記者),后又調軍宣傳處任新聞干事(隨軍記者)。(期間:1985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1990年入伍20年后,任北京軍區某集團軍政治部秘書處上校處長,曾被北京軍區授予先進新聞工作者稱號。榮立二等功兩次,三等功三次,各類嘉獎12次。
1995年轉業到重慶市,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廳局級副巡視員兼新聞處處長;重慶廣播電視集團副總裁。曾任重慶市渝中區政協常委,《重慶新聞界》雜志總編輯,《中華新聞報》重慶記者站站長。通過多年來持續不斷地鉆研和學習,在學術研究和專業領域,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與此同時,我在工作之余堅持自已的攝影愛好也收獲不小。可以確定地說,我的工作經歷、學習研究,和我的攝影理念及創作之間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且彼此成就的。
攝影與攝像:結合創作實際經歷和成就,您如何看待“時代性”在攝影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對于廣大攝影人而言,怎樣才能創作出符合時代特征的作品?這也是我們的廣大讀者所關心的問題,希望聽到您的真知灼見。
馮建新:我認為,你說的“時代性”在攝影創作中非常重要。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攝影,離不開攝影人。“攝影就是新時代的新質生產力”,這個論斷我不止一次提出。攝影是與科學技術緊密相連的產物,當然,光影當隨時代是毫無疑問的方向,也應是攝影人的制勝法寶。當前,就攝影界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攝影人普遍偏離現實生活的真實存在,作品缺乏錐心刺骨的“疼痛感”,缺乏應有的精神立場;另一方面,對創作方向目光游移,反映在對現實生活的表面復制,忽視攝影藝術的本體功能。
我認為,對于廣大攝影人而言,怎樣才能創作出符合這個時代特征的作品?怎樣才能緊隨時代而不落伍?辦法有三個:首先,就是要善于學習時事政治。學習是有方法的,只要掌握到方法和訣竅,一切就會迎刃而解;其次,一定要找一位好的老師。在創作中,引領和指導自己的前進方向,以免走歪路,走偏路;再次,就是要努力并刻苦地掌握攝影基本技能,盡可能地涉獵更多的藝術。
我以我金像獎的三組作品為例,來講一下如何拍出這個時代的系列作品。我認為,在新的形勢下,反映生活、再現生活的主流攝影形態應該還是紀實攝影,不管各種流派造成中國攝影界如何的“繁榮”,如何的眾說紛紜,紀實攝影始終是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反映著時代,引領著時代,這個時代離不開紀實攝影。下面以我的三組紀實攝影專題作品作為實驗和探索,提供給大家研究和討論。
第一,《老紅軍的愿望》專題作品,是我從2006年拍攝至今的一組專題,意在揭示當今信息碎片化時代對“中國精神”及人們思想的影響,和對弘揚“中國精神”的思考。在主題敘事上,運用紀實攝影手法講了9位老紅軍最后簽名的故事。
我認為,雖然中國工農紅軍25000里長征的故事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但它在人類戰爭史上創造的史詩般奇跡至今仍在神話般的廣為傳頌。從25000里長征中走過來的紅軍戰士們,他們驚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冊的英雄故事,已隨著他們歲數的增長,一個個悄悄的離開我們而去,給后人留下的只是一部神秘的“紅軍長征史詩”。
我為了續寫這部史詩,從2006年開始,關注和拍攝著重慶這座新興直轄市里的老紅軍戰士,因為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曾經在長征期間分別經過重慶。在采訪中我了解到,老紅軍們有一個共同的愿望:讓共和國的后代們記住他(她)們的名字——紅軍。 在攝影形式的真實性上,用紀實攝影留下老紅軍影像和他們最后的親筆簽名達而到高潮,以期使人頓首憫思(此作品入選“中國人、中國夢”等數個全國影展,分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等地展出;榮獲中國攝影家協會收藏大獎;部分作品通過再制作榮獲2010全國攝影藝術展覽評委推薦獎)。
第二,《和平年代的兵》專題作品,力圖從另一個不被大眾所了解的軍旅內部去揭示出中國軍人的人本。我當過兵,一干就是25年,橫跨70年代到90年代。這組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橫跨二十多年之久的軍事攝影作品,以抓拍紀實為基本手法,以軍營人文精神為主線,一改過去軍隊攝影題材的“高大全”、“威武雄壯”的形象,以平實質樸、小中見大、不事雕琢的畫面來講述軍隊在那個年代的故事。力圖為軍事紀實攝影的創作正本清源,重塑中國軍人的人本形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擺拍風盛行,尤其是在軍隊,上至軍隊全國發行的報紙、畫報編輯記者的傳幫帶,下至軍、師、團攝影骨干的身體力行,無不體現出擺拍就能見報的既得效果。于是拍革命軍人必是“高大全”。一個拍人物必講“三角光”和“輪廓光”,拍環境必講“整潔、明亮”光影加線條的擺拍時代,扭曲和埋沒了一個時代中國軍人在和平年代生存的人本影像。在這種大環境下,怎么才能有自己的個性和獨特的攝影語言?我從布列松“決定性瞬間”中受到啟發。我認為,攝影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別人都不可能拍到的、你拍到了,那你就是Number 1;另一種是別人和你都能拍到,但你拍的比他們更好、更獨特,那你也是Number 1。
軍隊是一種特殊人群構成的團體,這種特殊性就構成了軍隊攝影題材的封閉性。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拍的到的,誰抓住了這種機遇,誰就取得了攝影創作的主動權。抓住機遇,你就成功了一半。但是,軍隊中也有很多攝影記者和攝影骨干,他們文化程度較低,藝術功底較薄,在這種想進來的進不來,軍隊內的又不知怎么去拍的狀態下,我的藝術功底起了作用。我用腦去把普通士兵的生活與攝影紀實的典型性結合起來,所拍的一些照片,看似平平常常,卻又回味無窮;我用心去把普通軍人的平凡小事與人民大眾對子弟兵的感情結合起來,以抓拍的紀實攝影手法,把這些“決定性瞬間”用影像留存下來并奉獻給大家。評委評價為,作品“填補了八、九十年代軍隊這個特殊群體生活的空缺”。
第三,《在丈夫肩上“行走”的鄉村醫生》專題作品,這是一組深入基層,跟隨“小人物”拍攝六天的結果。我與這位已經被評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全國“最美鄉村醫生”等稱號的“小人物”一起同吃、同住、同行動了六天。當然,從中也受到他們的感動,獲益不少。力求通過作品,揭示出當今采用紀實攝影手法,在“鏡頭朝下”的基礎上,記錄偉大的時代中偉大的“小人物”,并通過攝影的真實影像傳播推動社會的進步。這組作品就是以突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一深刻主題,用紀實攝影跟拍的手法,從一個普通的殘疾鄉村醫生這么一個“小人物”的角度出發,用紀實攝影的手法“有思想”地表現平凡人中不平凡的小事,以呼吁各方面高度關注以就業、家庭、倫理為代表的三大傳統觀念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大意義。
總之,紀實攝影的堅守,只有扎根人民中,拍攝人民、歌頌人民、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攝影作品才是攝影人工作的方向;在創作手法上只有在“鏡頭朝下”的基礎上實現個性追求,才能達到紀實攝影真正的堅守,紀實攝影才可具有最純樸的持久力和感染力,才可方興未艾,這才是這個時代所有偉大藝術作品的要旨。
攝影與攝像:作為業內備受關注的中國攝影金像獎獲得者,您如何看待積極參加各種攝影大展/賽、獲取各種獎項在攝影師個人成長中的意義和價值?
馮建新:積極參加各種攝影大賽獲得獎項,這件事情眾所紛紜。但我的觀點是,對于廣大的攝影愛好者來說,參賽獲獎是走向攝影道路上的一條必經之路。當前,在攝影的評判上,是沒有標準的:你說你的好,他說他的好;這個專家說好,那個專家說不好;這個評委說好,那個評委說不好。那么,你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壞呢?唯一的試金石就是到大賽中去比拼。我的成長也就是這么過來的。但是我有我的經驗,我的經驗就是:首先,要瞄準高等級的全國攝影大賽。因為高等級的大賽評委都比較專業,另外也不會有什么貓膩,比的就是水平,能者上庸者下。其次,級別不夠的大賽盡量不要參加,以免誤判。參加多了,還會形成思維定勢,得一些小獎就往往沾沾自喜,止步不前,誤人誤才。再次,積極參賽能從中學到很多很多,即便失敗了,也能從中取得經驗,以利再戰,一個優秀的攝影師就會這樣漸漸地脫穎而出。